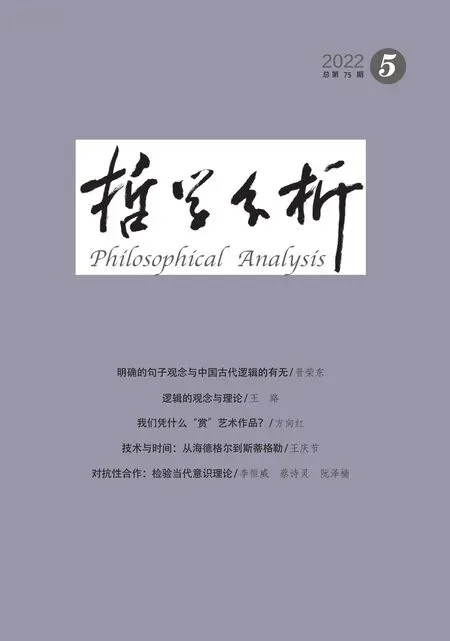優績主義的吸引力與黑暗面
——評桑德爾的《精英的傲慢》
朱慧玲
近年來,優績主義(Meritocracy)成為當代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最前沿的研究領域之一。圍繞優績主義的內涵、功能與局限的諸多討論,構成了相關領域的一道重要的學術景觀。所謂“優績主義”,在一般意義上是指,根據人們的成就和功績來分配收入、財富與機會。在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主張或立場,以及圍繞它而形成的分配觀念或思想并不鮮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諸如“論功行賞”的理念及其制度設計,都可以被追溯至文明社會及思想進程的開端。然而,優績主義之所以在近年來得到更多關注,引發大量爭議并迅速成為研究熱點,卻跟當代分配正義理論和社會現實發展的狀況密切相關。
一方面,當代分配正義理論圍繞具體分配模式而展開的爭論已陷入僵局。由于缺乏對“優績”(merit)等基本前提或其他“元問題”的思考,缺乏更新近思路和視角的引入,分配正義理論的發展如今幾乎遲滯于有關何為平等、哪種平等,以及何為正義等問題的討論,這種困境亟待破解。另一方面,對于現代社會而言,作為一種社會觀念和社會意識的優績主義早已彌漫其間。對“優績”的孜孜以求,對“優績”與分配之間關系不加反思的接受,不僅形成了強大的社會思潮,也帶來了普遍的社會焦慮。盡管不是所有民眾都明確意識或贊同“優績主義”,然而,競相追逐名校和高薪、狹隘理解成就和成功、為獲取成功而不斷“內卷”,以及由于無法成功而選擇“躺平”,都是優績主義在不同維度的現實表現。
近幾年來,眾多學者從這些現實表現入手,從不同角度對優績主義及其引發的社會現實問題進行反思、提出批評并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哈耶斯·克里斯多夫(Hayes Christopher)結合美國的政治與社會實際指出,優績主義的盛行不僅導致政治撕裂,造成經濟不平等,而且阻礙社會流動性。而斯蒂芬·麥克納米(Stephen J. Mcnamee)則指出,優績主義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神話,因為它所依賴的基礎是虛妄的。一方面,優績主義預設了社會財富和職務的分配完全憑借能力及其創造的優績,而與其他因素無關;但在現實生活中,人的能力與才能根本無法完全擺脫其他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優績主義對于社會分配的不平等后果的辯護,也必須依賴預先充分的機會平等;然而,在現實條件下,從來不可能有真正的、徹底的機會平等來充當優績主義的起點。類似地,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也認為,優績主義終究是一場騙局。它本來試圖通過倡導個人能力及其優績而破除繼承性的特權,但是,這種特權卻在優績主義的加持下,通過精英化的教育機制而在代際間得到進一步的傳承和固化——富人的孩子因為在這種機制中獲得更多的投入,成功幾率更大,而窮人的孩子則因此更易被困于社會底層。
與這些反思相比較而言,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精英的暴政》 (The Tyranny of Merit)一書中批評優績主義的角度更為獨特,也更加深刻。他在對社會現實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自己一貫的公民共和主義立場,尤其是基于公共善、公民德性等主張,試圖對優績主義的基石——“優績”——進行重新定義,以突破優績主義造成的各種困境與暴政。
一、優績主義的彌漫
從社會熱點、爭論或重大事件入手,深入展開相關的政治哲學思考,是桑德爾一貫的強項。在這本書里,他首先從 2019年震動美國社會的高校招生丑聞開始,描述了美國家庭如何竭盡全力通過各種正當的和不正當的途徑將孩子送入名校就讀。卷入丑聞的高考咨詢師威廉姆·辛格(William Singer),發明了一種“走邊門”(side door)的作弊方式,通過各種手段——包括修改SAT(“學術水平測驗考試”)答題卡、造假體育特長生等——提升學生成績,以獲得名校錄取通知書。桑德爾沒有停留在對案件本身的思考,而是進一步發問:“為什么人們都要上好學校呢?為什么家長們要不惜重金并冒著損害聲譽,甚至坐牢的風險,一定要讓孩子進入名牌高校呢?” 在他看來,這與我們社會中所奉行的優績主義觀念密切相關,并由此展開有關優績主義的思考。
與此同時,桑德爾結合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現象指出,當前美國各大主流媒體報道和社會生活的各種爭論表明,美國正處于極度分化時期(a deeply polarized time)。政治家和社會公眾在“左”“右”之間爭論、搖擺并相互批評,社會不斷撕裂。這種撕裂源于在全球化進程和經濟加速發展過程中,美國只有富人獲利,窮人越來越淪為社會底層;源于在專家統治式的政治話語中,窮人無法表達自己的聲音;源于成功者變得傲慢自大,失敗者陷入自卑、自責和憤怒。桑德爾進一步把這些憤怒歸結為底層民眾對精英階層的憤怒(anger against elites),并認為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獲得底層人民的支持,恰恰在于他抓住了底層人民內心的這種憤怒。因此,如果將特朗普現象和當前美國社會中的排外現象僅僅看作民粹主義者對日益增長的種族、民族和性別多元化的反擊,或僅僅是一種經濟上的、源自全球化和科技的快速變化所造成的困惑和混亂,那就流于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那么,該如何挽救政治生活中的撕裂危機,重新構建充滿活力和建設性的公共生活?桑德爾認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優績”和優績主義理念的吸引力與黑暗面,結合公共善(common good)的觀念重新界定成功、重新認可工作的尊嚴。
由此出發,桑德爾從對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影響深遠的圣經文化入手,首先細數了優績主義在宗教背景下的發展演化進程,認為《圣經》文化的影響與市場經濟的刺激,都促成了優績主義觀念的盛行。在他看來,《圣經》的世界觀在兩個方面與優績主義密切相關:一是高揚人的能動性;二是對不幸者的冷酷。他以約伯為例表明,盡管上帝的獎懲都源自恩典,但上帝救贖與自救的爭論還是給我們應當自己承擔責任留下余地。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的新教改革讓工作的意義變成頌揚上帝,當“響應上帝召喚而工作的理念轉變為清教徒的工作倫理,人們很難再抗拒其中的優績至上主義內涵,即救贖是人們自己贏得的,工作不再僅是獲得救贖的標志,而且是獲得救贖的原因”。也就是說,新教倫理不僅僅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促生了一種自我救助(self-help)和生命由自己掌控的優績主義的精神。馬克斯·韋伯在發揚新教倫理時便認為,幸運的人想要確信自己“應得”自己所擁有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刺激了優績主義理念的擴張。市場讓人們僅僅基于努力和天賦就能參與競爭,這使得市場產生的結果與“優績”相關——在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市場會給予人們所應得的,這種應得基于人們所取得的優績。由此人們看待成功的方式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贖一樣,我們的成功不是依靠運氣和上帝的恩典,而是憑借自己的努力和奮斗所得。
這就是優績主義的核心觀念,它不僅認可個人自主性、契合個體責任意識,還符合人們對于階層躍升和社會流動性的期望;這是優績主義最吸引人的地方,也鼓勵著人們通過努力發揮自己的才能獲得更多的財富和更高的社會地位。桑德爾還指出,在分配工作時,奉行優績主義理念會帶來效率和公平。這是因為,讓最有能力適合某個職位的人去做這樣的工作最有效率;同時,基于能力或才能,而非家庭出身或膚色去分配職位,是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此外,優績主義還會給人們帶來某種自由感——我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優績主義高揚人的能動性,并帶來一種能夠安慰人心的道德觀念——我們所擁有的都是我們應得的。它不但鼓舞人心,而且具有極強的吸引力。
桑德爾在梳理優績主義觀念形成史的過程中,敏銳地抓住了優績主義的核心觀念及其在增強個體責任意識和階層躍升意識方面所具有的力量,這也正是優績主義之所以能夠盛行、能夠成為鼓勵人們積極努力的精神力量的重要原因。然而,桑德爾所梳理和總結的優績主義發展簡史由于偏重宗教文化背景,而沒有看到優績主義理念之所以彌漫于不同社會的其他一些深刻原因。
首先,正如桑德爾所總結的,優績主義的核心理念在于對德性、才能和努力等要素的認可與支持,基于才能和努力所取得的功績越大,所獲得的社會財富應該更多,相應地社會地位也應得到提升。因此,優績主義理念體現并契合了人們對于德性、卓越性的欣賞、向往與肯定。這種認肯自古有之,早在《圣經》文化影響西方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之前,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然存在,在我國傳統社會亦早已有之。人的本性中存在著一種對于卓越性的追求,當有人具備較高的,甚至是突出的能力與天賦時,我們在欣賞的同時對其所獲得的更高的收入和地位并不會有不公正之感。正如優績主義的推崇者托馬斯·穆里根所主張的,優績主義對于天賦和才能的認可符合了人們的某種直覺——“我們并不會為那些源自基因差異的不平等而感到困擾,因為我們正是基于自然天賦才勾勒出自己的生活計劃,這些自然天賦是構成我們身份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優績主義之所以能夠盛行并影響至深,不僅僅是由于桑德爾所總結的在于認可個人自主性和帶來社會流動性;同時也由于它抓住了人們內心對于卓越性的肯定和追求自我價值、實現自我超越的內在需求,而這恰恰是優績主義理念由來已久、一直悄然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對于個體責任意識的強化、對階層躍升的許諾以及與之相應的有關平等的期許,這是自由主義在當代社會產生廣泛影響之后,人們更容易接受優績主義的原因,但如果只是將優績主義的吸引力局限于此,那不僅不夠全面,還會對我們如何應對優績主義的負面影響產生干擾。
其次,桑德爾可以從哲學上回溯得更加久遠,深入分析優績主義與“應得”之間的關聯及其道德重要性。從優績主義的核心觀念來看,它是一種以應得為基礎(desert-based)的分配正義理念;基于才能和努力而獲得的優績是應得的標準和依據。以應得為基礎的分配理念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分配的公正要基于某種能夠配得”。當代政治哲學有關優績主義分配理念的反思與批評,應當涉及它與應得理論之間的關聯。對此,桑德爾的態度有些模糊不清。他涉及了羅爾斯和哈耶克有關應得的討論,但僅僅局限于借用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對于應得理論的批評和反對,及其有關優績與價值(value)的區分,指出優績主義的分配理念很容易變成基于可用數字衡量的市場價值,優績很容易被理解為對于市場經濟作出了多大的貢獻。然而,優績主義基于應得理論這一點本身是否值得反對?桑德爾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像羅爾斯和哈耶克那樣立場鮮明。相反,如果結合他一貫的公民共和主義立場和對于公共善(common good)及公民德性的強調,他并不反對分配應當基于應得,而只是反對“優績”不應當基于市場經濟來加以界定,并提出要根據公共善來重新界定什么是優績,什么是成功,同時肯定德性以及對于公共善所作出的貢獻應當在分配中相應的分量。因此,桑德爾需要更加深入闡明的是,以優績為分配依據的優績主義及其對于應得的肯定,具有什么樣的道德重要性,這對于他后來提供的解決進路而言至關重要。
二、優績主義的困境
當然,總結優績主義分配理念的吸引力并非桑德爾在該書中的主要目的,他更多的是要加以批判和反思。在他看來,優績主義并非看上去那么美好,相反,它會導致諸多不滿,甚至在政治生活和社會領域造成諸多問題。
(一) 形成對立的社會心態。可以說,對于社會心態的觀察和分析,是桑德爾批評優績主義的獨特角度,也是他貫穿該書的一條重要線索。他通過分析時下各種社會現象,指出社會撕裂的深層次社會心理原因——當各種制度和社會生活未能兌現優績主義的承諾時,當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規則的人無法獲得上升時,他們就會產生一種挫敗感和絕望感。桑德爾進一步推論說:如果優績主義只是一種激勵,那么,落后的人就會譴責這種制度;如果優績主義是一種事實,那么落后的人就會譴責自己,并陷入自卑與焦慮。與此相對應的是,那些成功者認為自己的成功完全憑借自己的努力與才能,因而應得所擁有的一切;這種理所當然的應得觀,會讓他們滋生驕傲自大的傲慢感。同樣,社會在看待成功者與失敗者時也會呈現出截然相反的態度,認為成功者由于付出努力而應得高收入并理應贏得尊重,失敗者則由于懶散或愚鈍而應得落后的下場和鄙視。失敗者與成功者之間的對立心態,以及這種對待成功者與失敗者的不同態度,不僅與人類福祉相悖,破壞社會團結,甚至加劇社會分裂。當前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撕裂正是源于這種對立的社會心態。因為在優績主義理念的引領下,當人們升入好學校、拿到高薪、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品質,成為社會所認可的成功人士時,他們會認為自己的成功完全出于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而忽視運氣、上天恩惠或共同體的支持等因素,并由此認為自己是自足的,也難以學會感激與謙卑。同樣,那些失敗者真的完全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沒有能力嗎?他們很可能是受到原生家庭、生活環境、教育資源或偶然運氣等因素的影響,而沒有獲得成功,甚至只是由于全球化進程而被迫落后。此時他們需要的是幫助,而非成功人士和社會的蔑視,否則他們的自卑與焦慮很容易轉化為對成功人士的憤恨,這也是新民粹主義興起的社會心理要素之一——民粹主義對優績主義精英的反抗,不僅與公平有關,亦與社會自尊相關。
(二) 使精英大學成為固化不平等的主要途徑,并形成文憑主義的偏見。精英高校錄取現狀是誘使桑德爾反思優績主義的動因之一,他通過分析當前美國大學的相關錄取數據和梳理哈佛大學的優績主義精神遺產提出,優績主義的理念不僅是社會生活中的話語,也是當代高校錄取學生的根本價值取向。這是因為,優績主義許諾只要憑借優績就能獲得相應的社會財富和地位,社會階層是流動的,而獲得流動的主要工具就是教育。優績主義所倚重的才能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這就回應了桑德爾最初的疑問——為什么人人都想上好學校?為什么有些富人冒著犯罪的危險風險都要將子女送到精英高校?然而,事與愿違。這種精英教育并不是階層躍升的機會和源泉,反而成為階層固化的途徑。桑德爾通過數據分析得出,SAT成績與家庭財富成正相關關系。家庭收入越高,子女的SAT成績也會越高;同時,SAT成績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密切相關。因此,高校以SAT為標準衡量學生的才能并作為錄取條件,它們的教育就沒有成為社會流動的引擎,反而強化和固化了精英父母或享有特權的父母賦予子女的優勢。“在實踐中,大多數高校做得更多的是鞏固特權,而不是擴大機會。”
更糟糕的是,這種錄取制度讓因才能而產生的不平等正當化,并讓高等教育成為競爭激烈的分類競賽,即依據才能對人們作出分類,并決定誰在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成功,同時也強化前文所提到的公共心態。當高等教育按照才能對人進行分類,那么誰的才華和成就更值得推崇、應得什么,都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公共判斷。由此,當公共話語和高等院校錄取原則呈現出優績主義理念的疊加時,就會形成文憑主義 (Credentialism)的偏見,使得高等教育淪為篩選機器(sorting machine)。
(三) 與專家統治相結合形成優績的暴政、損害民主并腐蝕公共善。這是桑德爾作為當代公民共和主義者最為擔心的。他與最早反思優績主義的英國社會學家艾瑞思·楊(Iris Young)一樣,不僅認識到優績主義可能會造成成功者的自大和失敗者的自卑,更看到了他們與技術專家之間的親密關聯。讓他更為警惕的是,如果堅持認為只有受過高等教育、在價值上保持中立的專家才能最好地解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就會形成技術官僚式自負。讓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治理社會當然是好的,但前提是他們要擁有好的判斷力,并對普通民眾的生活抱有一種同情性的理解,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實踐智慧與公共德性。然而,事實遠非如此。多數大學并不能或并沒有很好地培養學生商議公共善的實踐智慧,因而,持有大學文憑的人并不一定比沒有文憑的人更好地治理國家。因為如前文所述,當畢業于精英大學的成功者認為自己的成功只是源于自己的才能與努力,并認為現在的社會財富和地位完全是應得的時候,這種自足和驕傲難以讓他們學會感激與謙卑,而沒有這些情感,他們就很難真正地關心公共善。相反,如果成功人士認為自己的成就部分源自好運氣、上帝的恩惠或共同體的支持,那么,與他人共享的道德理由也就更強。出于同樣的理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并不比未受過教育的人更寬容,而且他們不會因為自己歧視底層人士而感到慚愧。因此,在優績主義和專家統治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模式中,公共對話和相互理解難以進行,更難實現集體商議,反而會形成某種暴政,傷害民主并進一步加深社會撕裂。
可以說,桑德爾深刻地揭示出當代社會中的諸多問題,他富有洞見地指出,優績主義理念造成了成功者和失敗者之間那種對立的社會心態,并由此導致當前社會政治生活的撕裂。更進一步地,他對當前高等教育的優績主義錄取政策和篩選功能所作出的反思,也引起了普遍的共鳴。當前社會中備受詬病但又難以扼制的“雞娃”現象、各種各樣的輔導班、越是精英越焦慮疲憊的家長,都可以在桑德爾對于優績主義的反思中得到解釋。尤其是他有關美國家長那種“直升機育兒”、侵入性養育方式只會造成不斷跳鋼圈的、身心受傷的贏家的論述,也可用作當前社會中流行的“躺平”文化和“內卷”現象背后的優績主義成因。一方面,正是由于優績主義倫理及其分配正義理念,人們在教育投入和工作量上開始比拼,形成“內卷”。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前文所描述的基于優績主義的文憑主義的影響,一些人好像怎么努力都不夠,于是開始尊崇“躺平”文化或“喪”文化。因此,當一些批評者們在反思各種輔導班、雞娃方式和學歷論時,桑德爾走得更遠,他深入到社會中盛行的優績主義分配理念,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深刻的哲學視角。
然而,基于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思,既是桑德爾對優績主義的反思獨具力度、發人深省并引起共鳴的原因,同時也是他的不足之處。作為當代政治哲學話語體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應該在分析和批評優績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的基礎之上,結合他對自由主義分配正義理論的批評及鮮明的公民共和主義立場,更加深入地反思優績主義作為一種分配正義理論本身所具有的問題。因此,從這一期待來看,桑德爾對于優績主義黑暗面的分析缺乏理論深度。
首先,沒有認識到作為優績主義應得基礎的“優績”在概念上不夠清晰,甚至存在混用。在優績主義分配理念中,優績源自人們的努力和才能;換言之,優績是人們通過努力發揮自己的才能所獲得的成就或功績。然而,“merit”一詞在英文中對應諸多含義,比如優績、優點、品德、特長、才能等;優績主義的倡導者和批評者們對此并沒有加以清晰界定;桑德爾本人亦是如此,他強調其作為優績、功績或成就的含義,但在梳理優績主義觀念形成史,尤其是《圣經》文化影響時,更多側重于“品德”;在考察高等教育錄取政策時又側重于才能、英才等含義。作為優績主義分配理念的分配依據,優績的含義和界定需要清晰明確,否則會造成分配標準的模糊和游移,這也是優績主義分配理念造成諸多問題的理論原因之一。桑德爾雖然注意到了羅爾斯與哈耶克對于“merit”一詞的道德含義排斥,但他在分析優績主義分配理念的問題時并沒有認識到“merit”一詞的多重含義,因此也就沒有更為充分地論證優績主義作為一種分配正義理論所具有的理論問題。
其次,基于公民共和主義政治哲學立場進行的批評不夠深入。我們可以將桑德爾對優績主義黑暗面的分析總結為兩個層面:一是優績主義分配理念與精英教育結合、與文憑主義綁定時,會使由精英父母或家庭而來的繼承性不平等正當化;二是優績主義不但不會促進社會流動性,反而會形成階層固化,甚至與專家統治相結合,損害民主。我們也可以將這兩個層面分別看成優績主義的短中期和長遠的負面后果。然而,桑德爾需要更進一步深入剖析為什么這樣的后果是負面的。當他說優績主義會造成不平等時,優績主義者可能會反駁說,優績主義本來就不曾承諾平等,優績有大小、獲得的相應收入和機會也有所不同;平等不是它的理論訴求和分配目標,而且優績主義理念本身也強調機會平等。因此,桑德爾需要結合當代政治哲學理論中有關平等的分類,尤其是有關公平的機會平等和形式的機會平等的討論,來深入剖析優績主義與平等以及何種平等之間的糾葛,繼而分析優績主義與平等之間的矛盾,是當代社會過于看重平等,甚至將平等看作“至上的美德”而凸顯了優績主義具有的問題,還是優績主義本身長久以來產生的負作用造成當代社會的不平等?
再次,桑德爾并未充分結合自己一貫的公民共和主義立場來解釋為什么我們應當反對不平等和階層固化,并由此說明優績主義的黑暗面。公民共和主義傳統強調公共善和公民參與的德性,不平等、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階層固化會導致公共空間的萎縮,不同階層的人之間沒有公共的利益和活動場域,因此難以形成公共善,也難以讓處于固定的不同階層的人共同參與公共事務并進行有效的商議。這對于公民共和主義所強調的參與自治的民主和公共善而言,都是極大的戕害。桑德爾在擔心優績主義與專家統治相結合會損害民主時,涉及這一點,但缺乏進一步展開,也沒有更深刻地揭示來自公民共和主義傳統且有別于一般自由主義的批評與剖析。
三、擺脫優績主義的暴政
如何才能走出優績主義的困境與陷阱呢?桑德爾認為,最有力的、能與優績主義理念相抗衡的觀念是:我們的命運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們的成功與困境都源于上天的恩惠和變幻莫測的運氣。如前文所述,優績主義對于社會心態的影響,始終是桑德爾關注的重點,也是他對優績主義的剖析與批評比其他批評者更加富有洞見、打動人心,也更引人深思的根本原因;然而,也正是由于過于關注心態的層面,使得桑德爾給出的解決進路雖然具有啟發性,但在某種程度上并不具有理論說服力。
桑德爾認為克服優績主義暴政的有效方式,應該從教育和工作兩個領域重新思考對待成功。“克服優績至上的暴政并不意味著不應該在工作和社會角色的分配中發揮作用。相反,這意味著重新思考我們看待成功的方式。……這種反思應該集中在生活的兩個領域——教育領域和工作領域,優績至上的成功觀念在這兩個領域最為關鍵。”
在教育領域,為了不讓被錄取的入學申請者有那種成功者的洋洋自得感,桑德爾建議,在高等教育的錄取政策當中設定一個基本的合格成績門檻,然后在達到基本門檻線、有資格的人當中進行抽簽,中簽者獲得入學資格。“設置資格門檻,讓機會來決定其余的人,這會讓高中時代恢復一些理智,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學生們所處的困境。……這樣做還能削弱精英階層的傲慢,因為這清楚地表明,在任何情況下,那些登上頂峰的人都不是靠自己,而應把好運歸功于家庭環境和天賦,這在道德上類似于抽簽的運氣。”的確,這種抽簽錄取方式會讓被錄取者不那么洋洋自得地認為,自己之所以被錄取完全是由于自己努力并具備才能。然而,這種方式在消解成功者傲慢心理的同時,也會消解人們在努力奮斗實現自己目標之后所獲得的自我實現感和價值感;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這種自我實現感對于人而言至關重要。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伴有游戲性質的抽簽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會貶低努力、奮斗的道德意義。我的成功到底是由于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能動性、努力發展了自己的才能,還是僅僅由于好的運氣?或者,如果我與競爭者同樣努力,甚至更加努力,但僅僅由于運氣欠佳而沒能被錄取,那么,努力的意義何在?這樣的結果在道德上是公平的嗎?隨之而來的挫敗感、迷茫感,甚至是無力感,要比傲慢心理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更為糟糕。另外,在桑德爾看來,打消成功者的傲慢自足,會讓他們抱以更加謙卑和同情的心理來對待失敗者,更容易關心公共善。然而,即便認識到自己的成功部分地來源于運氣、家庭等偶然因素,也未必會使人更加謙卑,這未必一定是一種正向的聯想關系。相反,成功者可能會認為自己既有能力又有運氣,深受上天庇佑,注定會有所成就,反而更難同情那些失敗者,更難以真正地關心公共利益、促進公共善。因此,如果不從根本上考慮社會等級、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等因素的影響,不涉及當代政治哲學分配正義理論有關平等的種類、道德運氣等話題的討論,僅僅采取抽簽的方式試圖消除成功者的自大與傲慢,難免會不那么具有說服力,同時也會由于其游戲性質而損害努力和自我實現對于人而言所具有的道德意義。
在工作領域,桑德爾要求重新認可工作的尊嚴。在他看來,當我們消解了傲慢自大的心理,懷有這樣的敬畏和謙卑之心時,才能更好地關心公共善、商議公共善。更進一步地,我們應當在公共善的引導下,重新認可各種工作所具有的尊嚴和價值。這不僅需要我們認真嚴肅地回應工薪階層的挫敗感,更要將認可工作的尊嚴作為政治議程的重心。因為一個社會如何尊重和獎勵工作,對于它界定公共善而言至關重要——我們的工作和貢獻并非取決于偶然性的供需關系,也不應該由市場價值加以衡量,而應取決于我們的工作所具有的道德分量和公共價值,也就是對于公共善有多大的貢獻與推動。桑德爾此處援引美國公民共和主義傳統說明,貢獻正義引導我們為公共利益作出貢獻,并由于這種貢獻而應得同胞的尊重,此時我們是最完整的人。與此同時,有關工作尊嚴的討論,也是我們重新思考和界定公共善的一個好的開始,借此我們進一步重新界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公共善,以及我們的共同體所期望的目的是什么。如此,才有希望走進一種少一些仇恨、多一些溫情的公共生活。
的確,依照公共善來重新認可工作的尊嚴,既能關照到底層人民的挫敗感、羞辱感與憤怒感,同時也能幫助我們摒棄優績主義的影響,重新界定和評估成功,并基于人的天賦才能的多樣性,肯定不同種類的工作及其意義,從而重新認識到好生活的豐富可能性。因此,桑德爾所提出的這種進路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對于成功的界定往往較為狹隘,多數人認為成功就在于獲得巨額經濟回報或較高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因此對于一些經濟回報較少,但對于維系和促進整個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行業不夠重視并缺乏尊重。如此狹隘的有關成功的理解,既體現在青年人填報專業志愿和擇業意愿當中,也更明顯地體現在收入分配當中。與各界明星、網紅大V和基金管理人相比,對于社會共同體至關重要的教師等行業所獲的收入更少,那些維系日常生活基本運轉的物流、快遞和服務行業則更是如此,甚至被看作社會底層,被一些傲慢的成功人士鄙視。可見,這種對于成功的狹隘理解與優績主義理念的疊加,是當前一些行業中出現“內卷”的原因之一。因此,商議公共善并以基于公共善的貢獻正義來重新界定成功和認可各種工作的意義與尊嚴,有助于我們突破優績的局限,擺脫“躺平”和“內卷”的怪圈,也有助于我們拓展和承認社會生活與人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然而,桑德爾沒有進一步說明的是,在當代社會多元價值觀成為基本事實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有效商議并形成有關公共善的認識,同時避免強制性?這也是他所復興的公民共和主義傳統在當代面臨的一個主要質疑,是當代公民共和主義者亟須解決的重要難題。
四、未盡的討論
總的看來,《精英的暴政》一書將有關優績主義的討論推進了一大步,使之成為當代西方公共哲學話語中的熱門話題。然而,我們當前有關優績主義的學術研究卻顯得滯后。國內學術界把“優績主義”狹義地理解為“賢能主義”,把優績主義的問題簡單地限定在政治權責和政治資源的分配上,仍是一種常見的做法。因此,我們可以沿著桑德爾所開辟的話題,圍繞優績主義的關鍵議題,至少可以繼續思考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我們需要回應一個日常性的困惑:倘若如桑德爾等人所批評的,優績主義造成了這么多的社會問題,那么,取消優績主義理念,也就是不以人們通過努力發揮自己的才能而取得的優績為基礎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是不是更好?人們付出努力,并期待有所回報,這不僅僅是受優績主義理念影響,也是人們的某種直覺或合理期待。付出了努力、發揮自己的才能,卻并不能獲得相應的回報,那樣反而不符合人們對正義的理解。桑德爾后來區分了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對于優績主義的可接納程度:從個人角度來說,努力、勤勉等品質是令人欽佩、值得鼓勵的;他所擔心和反對的是,這種鼓勵擴大到社會層面、成為社會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標準。然而,桑德爾的這種區分并沒有有效回答以上困惑。這是因為,如果說個人的努力值得鼓勵,那么由誰來鼓勵并肯定?如果個人的努力和奮斗只是得到了來自親朋好友情感和言語上的肯定,而沒有或少有來自社會分配的實際成果,那么,那種情感鼓勵必定是無力且無法持久的。由此個人層面的努力也將受損,如今的“被迫懶散”(forced idleness)或“躺平”,也將成為真正的消極心態。更為重要的是,如果社會財富和權力的分配不以優績為基礎,那么,家庭出身、社會階層、裙帶關系等因素在實際分配過程中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力,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對此,桑德爾等批評者并沒有提供一種完備的分配方案加以替代,優績主義的倡導者也需要認真回應優績主義所可能具有的黑暗面。
其次,如果優績主義理念在某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那我們接下來需要明確的就是,作為優績主義賴以分配的基礎或標準,優績的確切所指是什么?由此需要我們重新定義“優績”的內涵和標準,均衡考慮古典德性論與現代價值多元論之間的張力,奠定優績主義分配正義理論的概念基礎和首要原則。與此同時要思考的問題是:如前文所述,優績主義滿足了對于卓越性的肯定與追求,而在追求平等的社會,如何在分配中平衡卓越性及其帶來的差距與平等訴求之間的關系?優績主義雖然強調機會平等,但因其對“優績”及其大小差距的承認,卻并不強調結果平等。因而,在優績主義的視域中,何種程度的不平等才是合理的或可以接受的,仍是一個具有爭議并亟待破解的問題。因此需要我們考察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在“優績”變量下的復雜關聯,吸收自由平等主義的相關理念,確認合理的或可以接受的社會(不)平等格局,奠定優績主義分配正義理論的運行空間及其邊界。
最后,從分配正義理論體系的構建角度來看,我們需要立足優績主義在收入、財富和機會方面的分配要求及其正當性,承認對機會平等與賢能優先的積極看法,吸收賢能主義政治哲學的相關看法,形成一套既適用于政治權利義務分配,亦適用于經濟收入和社會資源分配的綜合體系。同時借助相關資源,改造吸收“公共善”概念,化解優績主義給現代社會帶來的階層固化、“內卷”“躺平”等社會焦慮和壓力,奠定優績主義分配正義理論的實現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