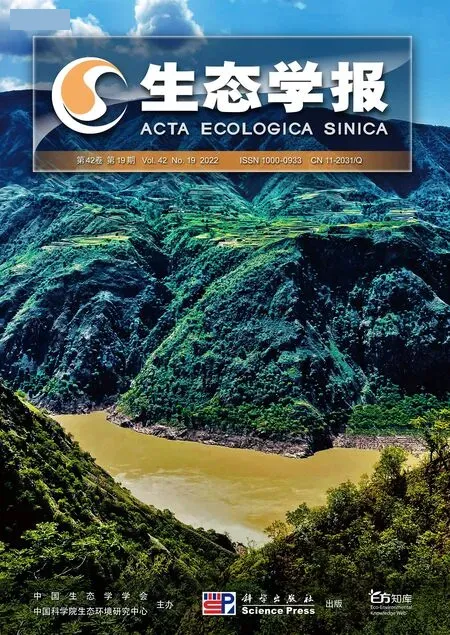水位影響泥炭沼澤土壤有機碳分解的生物化學機制研究進展
徐志偉,辛沐蓉,王鈺婷,劉莎莎,王升忠,*
1 東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長白山地理過程與生態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長春 130024 2 東北師范大學泥炭沼澤研究所,長白山濕地與生態吉林省聯合重點實驗室,長春 130024 3 東北師范大學,國家環境保護濕地生態與植被恢復重點實驗室,長春 130024
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稱,北緯地區10年內平均代際氣溫增幅為0.6℃,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1]。隨著氣溫的升高,降水量及其變異性、干旱頻率及其嚴重程度以及蒸散量預計也會增加[1]。另有研究表明,由于氣候變化和農業、林業及泥炭開采的需要,溫帶、北方地區及熱帶地區泥炭沼澤水位開始呈現下降趨勢,而排水將會使泥炭地水位下降10—50 cm[2],并已經導致全球10%—15%的泥炭沼澤退化[3]。研究表明,排水退化泥炭沼澤溫室氣體(GHG)排放量約占全球人為GHG排放量的5%[4—5],而為了在2100年前將全球變暖幅度控制在1.5—2℃,這一比值將會達到12%—41%[6]。隨著對泥炭沼澤碳儲量的關注不斷增加,人們越來越重視退化泥炭沼澤的復濕工作[7]。退化泥炭沼澤的復濕過程可以立即有效減少或阻止凈碳損失[5],甚至增加碳匯功能[8]。根據《巴黎氣候協定》2050—207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預計需要約500000 km2的退化泥炭沼澤需要進行復濕工作,即平均每年超過10000 km2[9]。2021—2030年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十年計劃必須迎接這一挑戰。
泥炭沼澤占陸地表面積的3%,但其碳儲量估計在530—1055 Gt之間[10—12],約占全球陸地土壤碳儲量的30%[11]。泥炭沼澤對氣候變化及人類活動的響應最為敏感,在維持全球碳平衡及調節區域氣候中發揮著重要的開關作用。水文條件是泥炭沼澤生態系統最重要的環境要素,影響其碳輸入和輸出之間的平衡作用,決定著碳循環各個關鍵過程的作用機制與強度[13]。自然泥炭沼澤的滯水條件限制植物殘體很難被微生物完全分解[14],進而積累了大量的有機碳(SOC),使其成為大氣 CO2的吸收“匯”和 CH4的排放“源”[15]。然而,水位下降加速了土壤SOC的快速分解[16—18],降低其碳儲量,并可能進一步影響全球氣候變暖進程[19]。長期排水作用會改變地表植被類型,使得形成泥炭的物質主要來源由蘚類植物被灌木/喬木所取代[20—21],并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植被對CO2的固定與釋放過程,影響生態系統SOC的輸入[22—23]。此外,SOC分解改變了泥炭的水理性質,導致容重增加、孔隙度和水力傳導率降低、地下水位波動更大,這勢必會影響泥炭沼澤SOC的存儲與分解過程,并使得嚴重退化泥炭沼澤的復濕可能在幾十年內也無法恢復其自然狀態下的生態功能[24]。有研究指出復濕后CH4排放量甚至高于其自然泥炭沼[25]。可見,關于退化泥炭沼澤及其復濕過程中土壤碳排放過程存在爭議[26],這意味著未來泥炭地的碳排放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27—28]。因此,關于退化泥炭沼澤及其復濕過程中碳循環過程及其變化機制的研究,是當前全球變化生態學及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關鍵過程研究中的前沿性科學問題。
微生物是最豐富的土壤生物,強烈依賴于水分,它們通過水與環境相互作用、獲取資源和繁衍[29]。微生物通過兩種重要但截然不同的方式控制土壤碳循環過程,一方面微生物釋放的酶是生態系統SOC分解的重要功能性物質[30—31],在木質素降解、腐殖質化、土壤SOC礦化分解等關鍵生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32];另一方面,微生物將SOC以更為穩定的微生物殘體的形式存儲在碳庫中,進而促進SOC的存儲[33]。土壤胞外酶活性越來越多地應用于預測氣候變化影響的土壤碳循環模型[34—35]。然而,有研究表明SOC的氧化分解和CO2的產生是由于非酶或非生物反應,亦或是生物-非生物機制的耦合過程[36]。研究人員將SOC的分解歸因于鐵和錳等活性金屬中間產物的存在,它們介導了分子氧對大分子SOC的氧化,并已被證明增強了農田[37]、森林[38]和濕地[39]等不同生態系統土壤SOC的氧化分解。目前,有關泥炭沼澤土壤微生物在SOC中扮演的角色及SOC分解的生物或非生物調控機制尚不明確。因此,有必要對現有研究結果進行歸納和總結,以便于更好地把握全球變化背景下泥炭沼澤土壤碳循環過程。
對土壤碳-氣候反饋的未來預測依賴于對控制SOC分解機制的準確理解以及它們如何對氣候變化作出反應。因此,厘清泥炭沼澤水位、鐵化學、酶活性和SOC分解之間相互作用機制,對于預測生態系統-氣候/泥炭沼澤水位管理反饋作用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重點綜述了干旱/排水/再濕對泥炭沼澤土壤SOC組分、分子結構、碳排放的影響,并從酶活性、鐵化學及微生物角度歸納總結了泥炭沼澤SOC分解的生物化學機制,將有助于更好地預測未來氣候變化背景下泥炭沼澤土壤SOC儲量的變化趨勢,為今后深入開展泥炭沼澤土壤SOC分解機制的相關研究工作奠定基礎,并為制定提高退化泥炭地生態系統碳“匯”功能的政策措施提供科學參考。
1 水位對泥炭沼澤SOC循環的影響
1.1 對土壤SOC組分的影響
長期排水作用下泥炭沼澤表層泥炭的好氧分解導致SOC的質量下降,土壤中易分解SOC比例降低而難分解SOC比例增加[40]。通過對雨養泥炭沼澤和森林沼澤的研究發現,長期排水作用顯著降低了底物可利用性和枯落物質量[22,31],限制了土壤微生物的生長,進而導致土壤微生物碳含量降低[41]。研究指出泥炭地排水,導致水位下降,迅速地引起土壤SOC氧化分解,增加了溶解性有機碳輸出生態系統[42],導致泥炭地碳儲量降低。現有研究表明,水位波動、干旱、含氧量、溫度和植被變化是影響泥炭沼澤酚類物質累積的主要因素[43]。排水/干旱作用會通過增強酚氧化酶活性而促進酚類物質的分解,進而降低泥炭沼澤土壤中酚類物質的含量[44]。然而,近來也有研究發現水位降低通過增加維管束植物來增加泥炭沼澤枯落物和孔隙水中酚類物質含量[17]。可見,泥炭沼澤酚類物質對環境變化響應具有復雜性[45],其對水位變化的響應還取決于持續時間及土地利用方式等因素。
1.2 對土壤SOC分子結構的影響

1.3 對土壤SOC分解的影響
水位控制著土壤地表的有氧層厚度,是調節進出泥炭沼澤碳通量過程的關鍵調節因子[52]。因此,泥炭沼澤碳循環對由于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導致的水位變化十分敏感。排水會通過改變土壤理化性質直接影響SOC分解過程。曝氣環境會加速SOC的分解,使得泥炭沼澤成為碳“源”[16—18]。早期研究表明,水位下降或者排水后,由于植被類型、氣候條件及水位變化的差異,泥炭沼澤土壤CO2排放通量將會增加13%—200%[53—55],而土壤CH4排放通量將會減少25%—100%[56],甚至成為大氣CH4吸收匯[57]。研究表明,在60 cm土壤深度內,土壤CO2排放通量隨著水位埋深的增加而增加[58]。然而,排水后泥炭孔隙度、pH、溫度的降低及干旱脅迫對SOC的分解有抑制作用[58]。有證據表明,排水僅會導致富營養泥炭地碳的損失,而對貧營養泥炭地土壤碳排放幾乎沒有影響,甚至降低了CO2排放[59—60]。泥炭沼澤中燈芯草等植物具有發達的通氣組織,這可能會使其在排水后仍舊是CH4的微弱排放源[61]。此外,植被類型的變化也會影響土壤碳排放對排水的響應。研究發現,泥炭沼澤排水造林后,其較高的總初級生產力抵消了CO2排放量的成倍增加,使其仍舊表現為CO2的吸收“匯”[62]。

圖1 氧在土壤有機碳分解過程中的作用的示意圖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ole of O2 in soil organic carbon decomposition process右側虛線箭頭表示“酶鎖”機制中的低氧作用。左側實線箭頭表示增加氧的作用,表示“酶鎖”打開; “+”符號表示刺激(積極)作用,而“-”符號表示抑制(消極)作用(改編自參考文獻[16])
在退化泥炭沼澤水位恢復過程中,水位的升高降低了CO2排放,但只有在持續淹水恢復條件下土壤CO2排放量才出現顯著降低,而周期性淹水恢復對CO2排放量并沒有顯著影響[63]。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水位恢復12年后,泥炭沼澤仍處于CO2凈排放狀態,并占全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33%,其主要原因是凋落物輸入的激發效應促進了SOC分解,而地上凋落物的覆蓋則降低了總初級生產量[64]。同時,研究表明退化泥炭沼澤水位恢復并不一定能夠促進CH4的排放[65]。這一方面是因為恢復初期階段土壤可利用性養分含量較低,限制了產甲烷菌微生物的活性[66]。另一方面,CH4只有在穩定厭氧條件下才能產生,而恢復的初期階段土壤結構、容重等土壤物理性并沒有恢復[66],泥炭沼澤不能有效保持水位,缺乏CH4生成的必要環境條件。此外,產甲烷菌可以直接利用Fe(III)作為電子受體,所以在Fe(III)氧化物存在的條件下,產甲烷菌能夠以Fe(III)作為電子受體,進而抑制CH4的產生[67]。綜上,退化泥炭沼澤及其水位恢復過程中泥炭沼澤SOC分解過程在不同地點和研究中高度不一致[68],進而增加了泥炭沼澤碳循環對未來氣候變化響應的不確定性,并對“缺氧是維持泥炭地碳存儲的關鍵”的傳統理論提出了質疑,其主要原因是針對退化泥炭沼澤及其恢復過程中土壤SOC分解機制尚不明晰。
2 泥炭沼澤土壤SOC分解的生物化學機制
2.1 “酶鎖”機制
土壤氧化酶被認為是影響泥炭沼澤碳循環的關鍵。然而,泥炭沼澤較低的pH[69]、溫度[70]及含氧量[71]環境抑制了酚氧化酶活性和酚類物質的分解速率,導致厭氧還原的泥炭沼澤中積累大量的酚類物質,而酚類物質對葡糖苷酶、磷酸酶和硫酸酯酶等多種土壤水解酶活性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16]。同時,酚類物質可通過減少微生物可利用基質[72]、限制微生物新陳代謝[73]、降低Fe(II)含量[74]進而限制SOC分解。極低的土壤酶活性是導致沼澤環境中SOC低分解速率的重要原因,使得泥炭沼澤積累大量的SOC,這一機制被稱作泥炭沼澤SOC分解的“酶鎖”機制[71]。
長期以來,濕地SOC對干旱/排水的響應主要集中在O2增強胞外酶活性與SOC分解之間的正反饋[16,71](圖1)。泥炭沼澤水位降低,氧含量的增加促進氧化酶活性,通過打開“酶鎖”進一步刺激纖維素類化合物的降解[75]。然而,近期研究人員對這一機制提出了挑戰,有關退化泥炭沼澤恢復過程中水解酶和氧化酶對水位變化的響應規律還存在不確定性。Wiedermann等[76]研究發現土壤水解酶活性隨著干旱/排水作用而降低,而長期再濕的實驗結果發現酚氧化酶活性在高含水量條件下更高[77],有關干旱/排水作用對土壤酚氧化酶及SOC分解的積極、中性和消極影響也均有報道[16,43,77]。同時,泥炭沼澤水位埋深及土壤濕度存在季節及年際變異,并導致氧化還原環境的變化,進而影響土壤酶活性及SOC礦化過程[77]。

圖2 泥炭地退化過程中O2和Fe在酚氧化酶及SOC分解中的作用示意圖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oles of O2 and Fe in phenol oxidase and SOC decomposition during peatland degradationSOC:土壤有機碳Soil organic carbon, 左側為氧在調節酚氧化酶活性和SOC分解中的主導地位,右側為Fe(III)在酚氧化酶與SOC分解中的主導地位;“+”符號表示刺激(積極)作用,而“-”符號表示抑制(消極)作用。(改編自參考文獻[77,92])
在泥炭沼澤水位變化的過程中可能存在除O2以外的其他因素控制土壤酚類物質及酶活性的變化規律。這些問題是揭示退化泥炭沼澤土壤SOC分解的“酶鎖”機制的關鍵。隨著水位的變化,除了可用O2含量的變化,還有生物群落、濕度、pH及養分可利用性的變化。Freeman等[78]研究發現水位下降帶來的氧的供給的增加并非是引起酚氧化酶活性增加和酚類物質濃度變化的必然因素,土壤水分脅迫、pH及凋落物類型也具有重要作用。Williams 等[69]研究發現,泥炭中的酚氧化酶活性受曝氣的影響較小,而受pH和酶抑制劑的影響較大。長期排水會使泥炭沼澤土壤pH值降低[79]。土壤酚氧化酶活性的最適pH值為近為8[32,45],這就意味著酚氧化酶活性會隨著泥炭酸化而降低[45],進而抵消O2對氧化酶活性的激發作用。Xiang等[80]研究發現短期干旱引起的泥炭酸化是酚氧化酶活性降低的主要原因。此外,土壤酸化可抑制土壤脲酶、過氧化氫酶、磷酸酶等多種酶活性[81],并增加礦物吸附有機物的能力[82]。當pH值適宜時,苯酚氧化酶活性更多地取決于濕地植被類型和泥炭的植物成分,而不是氣候因素。研究表明,長期排水后泥炭沼澤植物群落演替為以灌木或喬木為主的木本植物群落。木本植物凋落物會釋放更多的酚類物質[83],進而抑制土壤水解酶活性。
2.2 “鐵門”機制

鐵和SOC通過多種途徑形成Fe-SOC復合體在一定程度上對土壤有機物起到了保護作用[89]。針對不同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碳循環過程的研究結果表明,Fe(III)的存在使富含礦物質的土壤和沉積物中的SOC更為穩定[90—91]。研究發現,Fe-SOC在土壤SOC中的占有重要比例,如沉積物中21.5%的SOC[90]及森林中37.8%的SOC是通過這種方式固定下來的[91]。在濕地氧化還原界面的鐵氧化物對芳烴和酚類物質表現出很強的親和力[89],在O2含量增加時會更多的保護親水型SOC和羧基型碳不被礦化[91]。在富含有機物的泥炭沼澤中,在水位降低后,Fe(II)被氧化為較難溶的Fe(III),Fe氧化通過抑制酚氧化酶活性和促進鐵-木質素結合,在抑制干旱時泥炭沼澤碳損失方面起到“鐵門”的作用[77],這一機制與前述的“酶鎖”機制相反(圖2)。研究表明,以泥炭蘚為優勢植物群落的泥炭地,由于木質素含量和Fe含量低,干旱作用下土壤SOC的分解以“酶鎖”機制占優勢,而以維管束植物為優勢群落的礦質泥炭地,由于其木質素和Fe含量高,“鐵門”對SOC起保護作用[77]。“酶鎖”與“鐵門”機制在泥炭沼澤碳循環過程中同時發生作用,“酶鎖”機制在淹水的初期階段發揮主導作用,而“鐵門”機制在淹水的后期階段發揮作用[93],但究竟何種機制占主導作用及其背后的權衡機制仍是未知。
然而,土壤Fe在生態系統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中扮演多種角色,在保護土壤碳同時也會導致碳的損失。有研究表明在富營養的泥炭沼澤中,干旱作用下鐵可能通過使酚類化合物的沉淀而加速SOC的分解[93]。Fe的轉化是濕地水位變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生物地球化學過程,影響土壤碳的活化和穩定[94]。土壤Fe(III)是濕地生態系統中一種重要的電子受體,它可以在厭氧環境中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發生異化鐵還原過程[95],且是濕地土壤SOC分解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機制之一[77]。厭氧條件下,Fe(III)還原為Fe(II)并釋放過氧化氫(H2O2)進而刺激Fenton化學反應,產生可溶的活性氧(如羥基自由基或超氧化物)來氧化大分子SOC[96]。此外,Fe(II)可以增強苯酚的氧化活性[32],而室內的Fe(II)添加實驗也表明Fe(II)促進水解酶的活性[92],進而促進SOC的分解。Chen 等[97]通過13C標記的可溶性SOC和57FeII標記的Fe添加實驗測定SOC礦化速率的研究表明Fe只有在穩定的水位狀態下,且與可溶性SOC同時添加時對SOC起到保護作用。泥炭沼澤土壤尤其是表層土壤一般處于周期性的厭氧狀態,所以Fe可能對SOC的保護作用是微弱的,而活性鐵需要它們自身的物理化學保護特性來促進SOC持久性。此外,植物根系分泌的有機酸類物質對Fe結合的SOC起到溶解作用,進一步減弱了Fe對SOC 的保護作用[98]。因此,了解研究區的生物和地球化學背景對于理解氣候變化下Fe(III)-SOC的長期命運至關重要[97]。
2.3 微生物機制
微生物是土壤SOC轉化的主要驅動因素,而自然界中土壤Fe的氧化還原過程也是在微生物的介導作用下完成。北方中高緯度的泥炭沼澤,約有25%的CO2是土壤微生物代謝產生的[99]。甲烷氧化作用可以氧化濕地中產生的60%—90%的CH4,然后再逸出到大氣中[100]。泥炭沼澤水位越高,其厭氧程度越大,產甲烷菌的活性就越高[101],而長期排水會減少產甲烷菌的豐度[102],當土壤再次濕潤后,它們恢復得更快[103]。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在泥炭沼澤恢復過程中微生物群落的恢復需要10—15年的時間[104]。因此,在泥炭沼澤水位恢復過程中產甲烷菌并無顯著變化[105],從而導致水位恢復后泥炭沼澤CH4排放量依舊較低。通過對開放水域及其周邊環形濕地以及水位恢復區濕地的研究表明,甲烷排放與土壤產甲烷菌豐度無顯著相關性,而產甲烷菌與甲烷氧化菌的比值和水位動態共同驅動濕地CH4的平衡[106]。水位對甲烷氧化菌的影響存在差異。Kettunen等[107]研究指出 CH4產生量在地表水位20 cm以下出現最大值,而CH4氧化能力是在水位10 cm以下出現的最大值。Sun等[108]發現,當水位在地表下20—30 cm時,濕地氧化CH4的能力大于產生能力。
一般而言,泥炭沼澤營養貧瘠,土壤產甲烷菌以氫營養產甲烷為主,但當干擾發生時,pH值和營養物質增加,產甲烷菌可能從氫營養產甲烷向乙酰分解類型轉變[102]。土壤微生物對環境變化更加敏感、響應更快速。Fierer[109]研究發現土壤pH、SOC質量、氧化還原電位及土壤濕度等因素在決定土壤細菌群落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表明由水位變化導致的植被及群落結構的變化能夠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組成,進而改變濕地甲烷產生與轉化的生物化學過程[110]。土壤產甲烷菌在中性到弱堿性條件下的豐度更高[111],而泥炭沼澤的酸性環境可能會抑制產甲烷菌的生長。Fe(III)是優先于CO2被利用的重要電子受體,從而能夠抑制甲烷的產生,因為鐵還原菌利用乙酸和氫氣的濃度閾值遠遠低于產甲烷菌[112]。此外,產甲烷菌可以直接利用 Fe(III)作為電子受體[67,113],所以在Fe(III)氧化物存在條件下,產甲烷菌能夠以Fe(III)為電子受體,從而減少甲烷的產生[114]。泥炭沼澤退化及水位恢復過程中植被群落及上述非生物因素的變化,將影響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結構、功能基因和代謝途徑等。同時,由于泥炭沼澤垂直剖面微環境的差異使得不同微生物種群的增殖會產生較大的異質性。
3 總結與展望
綜上,泥炭沼澤排水/再濕過程會顯著改變土壤的氧化還原條件,進而改變土壤微生物群落和酶活性,驅動鐵氧化還原過程,影響SOC分解速率[77]。然而,有關退化泥炭沼澤及其恢復過程中SOC分解的影響機制的認識尚不清楚,目前亟待加強的相關研究有以下幾個方面:
(1)泥炭沼澤水位恢復過程中能否提高CH4排放?在排水/恢復過程中植物群落及環境因子的差異可能會影響土壤SOC分子化學組成與結構特征,而這種差異的來源及其對碳排放的影響還未可知。目前,對于自然泥炭沼澤CH4循環微生物特征已有系統研究,但退化泥炭沼澤及其恢復過程中產甲烷菌、甲烷氧化菌豐度及群落結構如何變化,退化泥炭沼澤及其恢復過程中生物及非生物因素對碳排放的貢獻及其對碳排放的影響機制還不清楚。
(2)根據“酶鎖”機制,排水作用會增強氧化酶和水解酶酶活性。然而近期有關排水及干旱對酶活性的影響的相反的研究結果,使得排水究竟能否打開泥炭沼澤“酶鎖”存在不確定性。在泥炭沼澤水位變化過程中,有關氧化酶及水解酶活性是否會對其做出可預測的反應仍然存在爭議。除O2外,是否存在其他競爭或混雜機制影響“酶鎖”機制在泥炭沼澤碳循環過程中發揮作用,需要進一步探索未來氣候變化背景下氧化酶-酚類物質-水解酶活性之間的作用機制。
(3)“全球鐵聯系”研究是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 (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IGBP)的三大研究主題(鐵、碳、火)之一[115]。然而,針對泥炭沼澤Fe-SOC對泥炭沼澤SOC中的地位認識不足。對于鐵在泥炭沼澤SOC分解中的作用還存在爭議,就Fe的泥炭沼澤中的各種功能對土壤碳循環的貢獻存在空白。植物根際及非根際土壤Fe的異化還原能力存在差異[116],而長期排水作用后泥炭沼澤植物群落結構發生變化,應關注由此造成的植物根系活動的差異對土壤鐵的轉化過程的影響。鑒于Fe(III)具有加速和抑制SOC分解過程的雙重作用,應同時關注Fe的氧化和還原過程,探究酶-SOC分解/碳排放-鐵之間的作用機制。未來研究將土壤水分與SOC分解的生物地球化學機制聯系起來,有助于提高預測泥炭沼澤碳儲存穩定性的能力,同時也為退化泥炭沼澤的恢復提供有效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