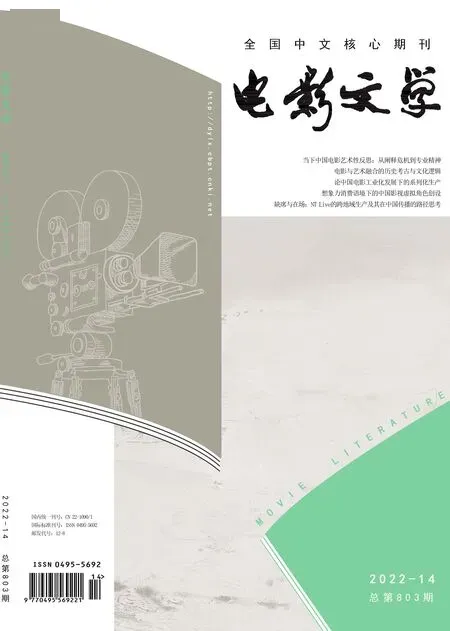《鐵道英雄》:抗日題材電影中的武俠風格
馬卓婭
(周口師范學院,河南 周口 466000)
討論俠客精神這一概念的內涵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在我國歷史中就已經存在非常豐富的有關“俠”的書寫,但從晚清時期出現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俠客小說,卻非常值得研究者關注。究其原因還在于這一時期我國面臨的歷史轉折問題。在眾多晚清文化研究的觀點中,大多都是圍繞西方思想大量進入中國以及中西方文化融合碰撞的角度,但是對當時中國國內政治環境與文化發展之間關系的討論還不夠深入。而武俠小說這一類型的出現和流行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從這一時期“俠”的形象來看,大多數是以民間的正義人士作為主要描寫對象,他們具有一定的反叛精神,個人的戰斗實力在多數情況下也有著遠超常人的表現,而他們所反抗的對象往往是昏聵腐朽的統治階級。這種書寫現象充分說明了“俠”在近代歷史中的出現是一種與政治意識形態密切聯系的現象。表面上看“俠”的出現是對政府無能的控訴,雖然隱含在這一時期的武俠小說還存在明顯的傳統封建觀念,但是武俠人物出現所帶來的社會公平和新秩序的生成卻昭示著文本在創作過程中創作者流露出來的對新的社會規則的渴望。而本質上來說,對“俠”的書寫是一種權力的書寫。在政府所代表的公權力逐漸喪失之后,社會權力需要另一種新的、充滿變革性的民間“私權力”來填補公權力衰弱所帶來的權力空白,因此,“俠”形象的書寫過程其實就是新秩序生成的前奏。而這些新社會規則在以“俠”自命的具體形象中的表現就是這些人物所秉持的“俠義精神”。但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新的社會規則已在政治變革中產生,此時“俠義精神”中對舊政府統治的反叛也就自然而然地與新政權的變革需要結合起來了。電影《鐵道英雄》就是以俠義精神作為文本內核,在原作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武俠類型的文本特征,塑造了充滿英雄氣息的人物群像,向觀眾傳遞出了在抗日戰爭歷史中充滿英雄浪漫主義氣質的精神面貌。
一、武俠人物:正面英雄的塑造與俠客氣質
從表面上看,《鐵道英雄》是一部典型的翻拍電影,在核心要素的表現上和原著小說、原著電影有著密切關聯,但細看之下可以發現這部電影在俠義精神方面表現出的特殊性。首先,在人物的設計上,電影重點表現了若干不同類型的英雄人物,而這些英雄人物在身為革命志士的同時身上也充滿了武俠特質。在電影著重塑造的主要英雄人物方面,最值得討論的莫過于最引人關注的王站長這一形象。這一人物雖然不能被冠以傳統武俠的稱謂,但在個人氣節與個人信念上,卻充滿了“俠”的特質。較遺憾的是,這個人物之所以能夠成為“俠”,在電影的敘事中更多地表現為結果層面的問題,缺少必要的精神發展過程,因此相對而言缺少更為明確的行為動機。比如電影中提及王站長沒有家人,以站為家,甚至在德軍占領時期就已經在車站工作,那么彼時的他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孤膽俠客?如果沒有,那么又如何理解這位渴望為人父的老人視死如歸的堅定決心?如果確如文本暗示的那樣他因喪子而加入了抗日戰斗中,那這個人物身上的俠客精神究竟是國仇還是家恨?這種情感動機又能否與車廂中的入黨儀式結合在一起呢?這一連串的問題不僅讓我們回到了問題的原點,那就是武俠的創作方式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契合革命敘事的內在訴求,但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曾經的大眾化創作方式是否還能夠滿足當代的革命歷史塑造,這將成為同類型作品創作時需要審慎思考的問題。除了王站長外,電影中最重要的正面英雄人物還有洪隊長。這一人物的塑造相對而言最能夠體現出武俠人物的特質。電影一開場,洪隊長率隊暗殺日本軍官,整場行動使用的武器以冷兵器為主,并在最后留下了警示的字條,這些包括蒙面在內的行動都與傳統武俠作品中豪邁正義的武俠人物如出一轍。這位英雄人物的個性和感情線索也接近傳統書寫中的俠客,寡言少語又溫柔善良,在危急時刻有柔弱的女性拯救,在面對叛徒和仇敵時又能夠展現出血勇的一面,對待戰友和善有加同時又能顧全大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部電影作品中對“俠”的理解。
除了這種非常典型的俠客形象外,還有一類人物的塑造就相對簡單了很多。比如電影中出現的其他抗日戰士,他們在文本敘事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甚至在人物出場之后很快就在戰斗中英勇犧牲。但是在文本吉光片羽的敘事中,他們的形象卻恰恰因為這種“少”的現象具有了“多”的可能。在有限的敘事中,這類人物的塑造方式趨于扁平,文本的敘述只抓重點,不及其余。因此抓住了這一類人物的特點,也就抓住了電影對這一類次要英雄人物的塑造方式。在文本的敘事過程中不難發現,這一類人物都曾經表達過自己視死如歸的心聲,在面對強敵時也無所畏懼,但是相比較洪隊長等主要英雄人物而言則勇氣有余而謀略不足,電影如此設計從表面上看應該有兩種目的,首先就是為接受者對電影情感產生共鳴提供基礎,在眾多戰士犧牲時可以間接體現出戰斗的殘酷性,并且加劇敵我間的矛盾沖突;其次,這些戰士犧牲時的無畏與決絕又可以為主人公幸存和反擊提供更深層次的情感基礎。但是,這種人物的塑造方法還是需要進一步反思的。在人物個性方面,這種塑造方法會催生出大量同質化的形象,在整體敘事中,核心人物本就相對單薄,一旦這種同質化形象大量出現,勢必會大大減弱人物群像中的個性表現,從而導致文本更多地向俠義性傾斜,相應失去了個性發展的情感思路。
二、武俠敘事:武俠模式與俠義精神
除人物形象塑造,電影也可通過武俠作品的敘事方式進行解讀。總體上看,傳統武俠文本的敘事都是圍繞著主要英雄人物以及這一人物所堅守的“俠義精神”。而在此過程中,為“俠義精神”奉獻生活乃至生命的信念感,無疑可以同革命敘事中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產生內在的共鳴。這種創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為文本增添了故事性和觀看性,讓文本更容易同觀眾產生情感上的聯系,但這種創作方式很大程度上會使文本流于模式化,降低電影藝術性。作為商業電影,這種敘事方式本身無可指摘,但在實際創作中應當不斷探索類型文本創作的創新。
從情節設計上看,《鐵道英雄》最為核心的部分就是電影的結尾,也是電影在原作基礎上對情節處理最為特別的部分。這處情節圍繞火車展開,是敵我雙方最后的交鋒時刻。在這里兩位主要英雄人物舍生忘死共同擊殺了反面人物,并充滿硬漢柔情地進行生死告別,洪隊長更是瀟灑地蓋住帽子慷慨赴死,這雖然反映出了兩位英雄人物的民族氣節,但從改編角度看,這種處理在強化電影的悲劇性核心和突出故事情節的緊張性之外并未帶來更多的藝術效果,也很難擔負起歷史性的敘事責任,反而因其強調文本的戲劇沖突和英雄的個人犧牲而具有了非常強的傳奇性特征,因此在文本中心的觀感上也難免更加側重對“俠義”的表現。
從文本整體的敘事模式上看,《鐵道英雄》主要沿用著傳統線性的任務型敘事模式,總體上圍繞著“外來反派角色到來—主要英雄行動遇挫—戰勝外來反派角色”的敘事結構展開文本內容。在大多數圍繞中國抗日戰爭這一主題進行表現的文本中,基本上還是沿用歷史性的書寫方式,至少對于大部分抗日題材的經典電影作品,對歷史的還原以及取材于真實的歷史事件是文本創作的基礎。在《鐵道游擊隊》的小說和電影中,都努力地將這種革命事跡忠實地還原出來。但是對歷史事實的書寫并不意味著只有歷史敘事這一種方法,在文學消費、電影消費盛行的當代社會中,在歷史的書寫中添加演義、傳奇的成分無疑可以大大強化文本的大眾化效果。這也是《鐵道英雄》改編的成功之處,雖然在情節上創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再創作,但是基本的敘事模式沒有發生重大變化。而所謂傳奇性的加入正是在于將復雜的歷史問題和敵我關系通過具體的人物表現出來,使兩種政治軍事的對立演變成了兩類人的對立。因此,即使在具體情節的處理上有所不同,但是在敘事模式上電影依舊圍繞著武俠的敘事手法進行展開。
三、江湖話語:空間書寫與民間社會規則
除以上武俠特征外,在電影空間處理中依舊可以發現潛藏在電影文本中的武俠特質。首先在以人物為核心的空間環境書寫中,電影刻畫了非常典型的當代俠客形象。兩位主要英雄人物都以毛呢風衣作為主要服飾,主人公洪隊長的刻畫更是借助黑色的服飾和帽子暗示著他沉穩瀟灑的個性,這種對人物外在形象的刻畫實際上未必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卻可以在整個文本中建立起文本內在的風格體系。除了服飾的表現外,還可以發現電影中主要場景的色調都是以灰色為主,包括決戰也是在夜晚發生的,這一方面是因為電影故事的特殊性,游擊隊的行動本就是夜晚進行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開展故事的敘事空間中,創作者也試圖通過具有抒情性特征的手段,為電影提供更多的文本張力。而在這種空間形式或者說電影場景的安排中,鏡頭語言表現出的形式本身也可以表現出電影的武俠特色。在電影中有一處關鍵場景就是敵我雙方主要人物的初次交鋒,在這次交鋒中雙方的決斗方式同傳統武俠作品非常相似,雙方隔門交戰,都體現出了過人的戰斗實力和戰斗經驗。這場決斗雖然在電影的敘事中非常短暫,卻充滿了武俠小說中高手對決的特色,雙方你來我往、一明一暗,最終主人公負傷敗走,并被少女所救,之后積蓄力量決戰成功,這個過程很難會讓觀眾忽視其中的武俠“味道”。
除了場景傳遞出的武俠特色之外,文本中的另一種空間也讓這部電影與武俠類型緊密聯系在了一起。那就是電影中的“江湖”書寫。《鐵道英雄》這部電影借助對“江湖”的表現完成了對文本空間的進一步深化。江湖的概念一般是某些特定的社會規則和情感模式的集合,本質上并不是一個客觀的空間范圍,同俠客這一概念一樣,江湖的指稱更突出強調的是其民間的、情感的屬性,而江湖的社會規則也有別于普通的社會規則,具有更加豪情、壯烈和快意恩仇的特點。而之所以說《鐵道英雄》這部電影關于空間的書寫具有江湖的特點,正是因為在電影中觀眾也確實可以看到圍繞著洪隊長展開的人物關系也更傾向于兄弟情義,作為空間表現的一部分,人物關系與空間之間的密切聯系自然不言而喻,而電影中正面人物之間的關系顯然相比反面人物更具有人情味,而日軍所代表的偽政權恰恰是主人公們所試圖反抗的、喪失人性的權威,電影中雖然為了貼合原作的主旨專門在決戰前夕增加了在火車上入黨的儀式,但是因為電影的整體空間書寫中一直集中在對個體英雄的刻畫上,導致這段書寫游離于整體的敘事之外,因此,人物之間達成的情感聯系也相對弱化了意識形態的影響,從而在客觀上更加具有江湖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