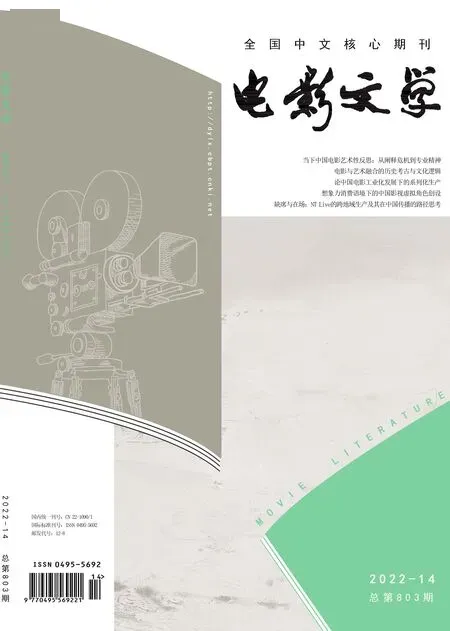寫意·濃縮·注釋:《沙丘》小說電影化改編
葛同春
(哈爾濱師范大學傳媒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沙丘》(2021)是由丹尼斯·維倫紐瓦執導,根據弗蘭克·赫伯特的同名小說《沙丘》改編而成的科幻電影。作為首部同時斬獲了星云獎和雨果獎的最佳長篇小說《沙丘》,被讀者稱為“有史以來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小說《沙丘》擁有恢宏復雜的人物關系、跨越千年的時間歷程,以及保羅模糊性的幻想與夢境、小說形而上的哲學思想等因素,導致小說難以被藝術化改編、難以商業化盈利,也被稱為小說影視化歷史上最難改編的電影之一。2021年,丹尼斯·維倫紐瓦通過寫意、濃縮、注釋式的雜糅方式將小說賦予影視化的特征。
一、小說與電影之“可通約性”和“不可通約性”
小說和電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表現媒介,一種是文字符號,另一種為視聽影像。一種是讀者在閱讀小說文字的過程中攜帶著清醒的意識,通過自己的審美經驗進行幻想;另一種是觀眾在觀影過程中類似于在做“白日夢”,一種潛意識下的心理驅動。由于小說、電影兩者都是時間性的藝術,敘事性成為連接小說和電影的橋梁,小說和電影共有的歷時性、敘事性使改編成為可能。于是創作者們可以充分利用小說進行電影化改編創作,而通過電影化的成功作品也會直接推動原著小說銷售量的提升,吸引更多的讀者閱讀,從而發揮出藝術作品的最大價值。
小說和電影雖同為敘事性作品,但兩者敘述故事的方式有所不同。小說語言系統具有內在的抽象概括性,比較容易地表達頭腦所建立的邏輯思維性;但電影是通過運動畫面來明確的、不可逆性的對物質現實世界的還原。小說可以自由地轉換“十年后”“五年前”等具備模糊性特征的時間,讀者對時間的感知具有強烈的延續感;電影通過物質空間的延續來表現時間,觀影者在“白日夢”所感知的心理時間與影片主人公行動的時間是同步的。若運用字幕表現銀幕時間的來回切換,會容易中斷故事情節的緊密真實感,小說和電影之間的“不可通約性”的敘事差異造成小說電影化改編的不易。20世紀60年代科幻文學界屬于追求風格多樣化的科幻新浪潮時期,這一時期的作品更加關注“內容與思想”,而不僅是硬科幻所具備的“形式、風格或美學”。1965年,科幻巨匠弗蘭克·赫伯特的小說《沙丘》在新浪潮時期問世。由于小說擁有恢宏復雜的人物關系、富有模糊特征的人物心理曲線變化,導致小說難以藝術化改編、難以商業化盈利,《沙丘》的影視化改編道路充滿了荊棘。2016年,傳奇影業獲得了《沙丘》的改編權,交由丹尼斯·維倫紐瓦執導,影片于2021年10月22日在美國和中國同時上映。
杰·瓦格納在《小說與電影》一書中,談及美國流行改編的三種方式:移植式、注釋式、近似式。這三種方式又可以衍生出其他的改編方式,電影的講述是建立在一定的時間內,去把一個故事講述為具有完整意義的樣式。長篇小說《沙丘》中復雜的環境、語言、人物關系等因素,決定了小說不可能通過兩個小時的電影時長講述完整。丹尼斯·維倫紐瓦在拍攝前已確定通過上下部來拍攝《沙丘》第一本小說,根據電影版《沙丘》(156分鐘)所呈現的內容可以看出導演通過寫意、濃縮、注釋式的方法來進行小說電影化的改編理念。
二、寫意式的改編方式:詩意的古典主義廢土新美學
導演對小說電影化改編風格有兩種:一種是再現式,對原著時空完全再現;另一種是導演調動自己的智慧去重新改造的寫意式。作為科幻小說《沙丘》的書迷,維倫紐瓦邀請了喬·斯派茨、艾瑞克·羅斯兩位電影劇作家,三人同時對《沙丘》進行小說電影化的劇本改編。導演根據原著小說的人物與情節,通過自己主觀的、具有濃厚個人色彩的偏好再次闡釋,即“改編式閱讀”。維倫紐瓦運用緩慢的節奏使觀眾沉浸于巨大沉默物體的視覺空間氛圍當中,形成了一種詩意的古典主義廢土新美學,凸顯出強烈的克制、冷靜的個人風格,增添了影片獨特的藝術魅力。
維倫紐瓦對視聽語言擁有天然的直覺性,影片中運用冷色調來渲染高大的建筑群景觀。以冰冷的海洋和巨大的礁石去表現雷托公爵星球家園的環境,以黑暗扭曲的巨大沉默物體來渲染哈克南公爵的府邸,冷冰冰的空洞城堡勾勒出冷漠的建筑文明;巨大沉默的物體凸顯出令人恐懼或著迷的神秘效果。導演通過柔和的暖色調來刻畫厄拉科斯星球沙漠的奇觀,金黃色的光線閃爍著沙漠中的香料;在構圖選取上,影片中天空的畫面占比較小,而沙漠所占的畫面比例極大,廣袤的沙漠以波浪般的身軀曲線,彰顯了厄拉科斯星球中的大自然充滿旺盛生命力的“母性”審美特征。作為美瑯脂的生產者——沙蟲,被原住民弗雷曼人稱為“沙漠之主”,維倫紐瓦運用靜態美去呈現巨大圓柱形狀的沙蟲。影片結尾處,哈克南男爵將保羅和杰西卡流放到沙漠,沙漠中的沙蟲露出充滿尖齒的頭部凝視著保羅和杰西卡;導演通過畫面的沉默去表現“沙漠之主”的奇觀和壓迫感,緩緩的節奏使觀眾沉浸于巨大沉默物體的空間視覺氛圍中,形成了一種“詩意”的古典主義的廢土新美學。這種“詩意”制造了一種視覺上的間離效果,與觀眾保持著審美距離的、陌生化的意境。寫意式的風格將厄拉科斯星球浩瀚的沙漠環境刻畫得極為細膩,使得文本的精神在銀幕上完美呈現,做到了“1+1>2”的效果。
維倫紐瓦運用光影去表現微型獵殺鏢行刺保羅的緊張感。獵殺鏢根據懸浮場進行移動,維倫紐瓦使用全息影像作為光源,昏暗房間內的幾縷白色光束照耀在保羅的眼睛上,成為微型獵殺鏢和保羅眼睛兩者的漸進線;光線既能夠表現獵殺鏢即將刺入保羅眼睛的危險距離,又可以顯露全息影像具有阻擋獵殺鏢的作用。保羅對微型獵殺鏢的直接閃躲,呈現其出類拔萃的冷靜與成熟,也從側面表明了杰西卡對保羅一如既往地秘密訓練。另外,導演對人物角色情感的把握以及對每一句臺詞所體現的細微表情都具有高超的主觀精確度。原著作者弗蘭克·赫伯特根據古希臘神話故事命名厄崔迪家族,以雷托公爵為首的厄崔迪家族源自古希臘的阿特柔斯,阿特柔斯家族的后代都具有命運悲劇的結局。維倫紐瓦運用油畫般的色調渲染雷托公爵赴死時最為壯麗的氛圍,哈克南公爵對雷托公爵的“表兄”稱呼,暗示出哈克南家族與厄崔迪家族具有血緣關系的聯系,體現出骨肉相殘的命運悲劇性。“我來了,必將永世留存!”體現雷托公爵作為一名殉道者對死亡的漠視以及對理想的堅定悲壯感。“夢是來自內心深處的信息”“恐懼是思維的殺手”,貫穿影片的敘事及主題,保羅通過直面夢的預言,主動地選擇與詹米決斗,勇敢面對夢境鏡像,彰顯出人類生命的奧秘在于體驗現實的哲理性思辨,流露出人類個體對自由意識的宣揚。
三、濃縮式的改編方式:“賽博格群像”隱形敘事
小說《沙丘》的背景設定在未來,講述了厄崔迪家族的保羅受到命運的指引,跟隨父親前往滿是黃沙的厄拉科斯星球,并經歷重重磨難成長為英雄的史詩故事。小說恢宏的人物關系以及小說的哲學、宗教等元素導致小說不可能完全被電影化改編。抽取原著中的幾個章節必然會使小說被“閹割”,導演可以通過道具、物件來表現軟科幻“賽博格”的設定,“賽博格群像”的隱形敘事功能來保留小說的完整性,呈現出濃縮式的改編方式。通過電影化的想象,突出小說中的主要事件、主要人物、主要矛盾,并恰當地取舍人物層次,完成敘事上的緊湊,給予清晰的視覺化呈現。
維倫紐瓦運用電影獨特而精簡的畫面語言,巧妙地將煩瑣的背景融入具體的情景中。小說中《沙丘》的故事背景設定是以“后芭特勒圣戰”而展開的,在公會前紀元201年,人類和智能機器之間發動了“芭特勒圣戰”;在“芭特勒圣戰”之后,人類規定禁止使用一切具備思維能力的機器。貴族皇室通過訓練模仿計算機分析能力的人獲取信息,這種類型的人被稱為門泰特。面對恢宏的小說背景設定,維倫紐瓦沒有選擇運用畫外音進行冗長的講述背景,間離觀眾與影片人物之間的情感;而是以門泰特翻轉白色眼珠、用手指觸碰耳朵等一系列動作來刻畫超強的記憶力和認知力。厄崔迪家族的門泰特通過翻轉白色眼珠的動作來測驗厄拉科斯城堡周圍的危險,通過觸碰耳朵的動作來計算皇帝部隊來到卡拉丹所消耗的金錢;哈克南家族的門泰特,通過翻轉白色眼珠的動作來策劃謀略對付厄崔迪家族。
導演運用道具、物件來表現軟科幻“賽博格”的設定,“賽博格群像”的隱形敘事功能呈現濃縮式的改編。后人文主義者把自然與人工物相混合的有機體稱為“賽博格”。影片以兩種形態的“賽博格”來凸顯人物的弧光。首先是以弗拉基米爾·哈克南男爵所使用的“便攜式浮空器”以及保羅的“屏蔽場”為代表的賽博格,這種形態的賽博格機器并沒有直接被植入人體。哈克南通過浮空器降臨在被綁的雷托面前,彰顯出哈克南魁梧的外貌特質以及一手遮天的壓迫感;運用浮空器升到天花板來躲避雷托釋放出的毒氣,勾勒出哈克南謹小慎微的特征;“降臨”與“升空”兩個細小動作濃縮了對哈克南長篇描述。“屏蔽場”具有防御快速武器攻擊的功能,影片中哈克南軍隊偷襲厄崔迪家族,冷兵器與屏蔽場相結合的打斗場景,體現了復古感與科技感的融合;影片借助屏蔽場去表現保羅與哥尼使用冷兵器進行日常訓練的場面,以此使保羅超越了夢境中被詹米所殺的鏡像。第二種形態賽博格是以弗雷曼人攜帶的“蒸餾服”為代表,蒸餾服上帶有鼻塞的一根管子與人體相連接,具備回收水分的功能。保羅通過兩次穿戴蒸餾服的細節刻畫出成長的弧光,保羅首次穿戴蒸餾服是面對凱恩斯博士的疑問,先天、準確地穿戴蒸餾服,暗示出自己就是“天選之人”。第二次是保羅背對母親杰西卡,穿戴各自蒸餾服,表現出保羅已經成年進入象征界,建構主體與社會的關系,不再是依靠母親的孩子時期。影片中兩種形態的賽博格彰顯人物之弧光,具備隱形敘事的功能。
故事性弱、動作性差的《沙丘》小說很難被電影化改編,即使通過濃縮的方式對鴻篇小說進行改編,也會導致小說的次要人物的立體性凸顯平面化的特征。小說的開篇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圍繞尋找家族叛徒的猜疑鏈展開敘事的,保羅在房間內被微型獵殺鏢行刺,其幕后操縱者的身份引起厄崔迪家族成員之間的信任危機。電影對猜疑鏈的省略,直接弱化了公爵和妻子杰西卡之間復雜的情感,消解了哥尼·哈萊克與杰西卡之間的誤會。此外,影片《沙丘》對岳醫生的濃縮處理,弱化了岳醫生內心極其掙扎的狀態。由張震飾演的岳醫生,前額刺著鉆石狀刺青,表明經過了帝國預處理,這一功能表明人忠誠的特質;岳醫生為拯救妻子瓦娜,其自由意志突破了“思想鋼印”的禁錮,因此才會“背叛”厄崔迪家族。影片省略了對于帝國預處理具體功能的闡釋,導致岳醫生背叛的突兀荒誕感。原著小說中岳醫生在出賣保羅之前,通過給保羅一本《奧蘭治天主圣經》,給予保羅信仰,來撫慰自我的良心,體現人性的復雜性。小說對岳醫生的長篇描寫,凸顯人類之間“愛”的永恒與原始神秘性、人類自由意志的能動性。濃縮改編方式雖可以保留小說的完整性,但次要人物的扁平化處理是小說電影化的一個不得不注意的問題,兩者構成了小說電影化藝術改編的悖論性。
四、“注釋式”的改編方式
“注釋式”改編是指影片對原著加了許多電影化的注釋,并對之重新結構,會對作品某些方面有所變動。維倫紐瓦以意識流的閃回,借用不同風格的音樂轉換夢境與現實,通過空間具象化人物內心等視聽方式進行“注釋式”改編,借此表現小說的寫意、心理描寫等富有模糊性特點的文本特征,以及醞釀哲學層面的精神世界。電影是通過片中人物的視點,形而下地展現客觀的世界;而小說當中的哲學、宗教、心理等充斥著形而上特征的語言質感,難以運用電影的視聽語言描述。真正的電影藝術家往往能夠突破常規,自由地控制時間與空間,對電影時空實現超越性的闡釋和拓展。
為了更好地塑造沙丘世界的背景以及恢宏的人物,2021年,維倫紐瓦同時拍攝了與電影版《沙丘》世界觀相同設定的《沙丘:姐妹會》網劇。原著小說中的姐妹會是傾向于對人類精神開發的組織,她們能夠在潛意識層面發出聲令從而控制他人的動作,也可以自由選擇生育的性別。姐妹會預言未來有一位叫魁薩茨·哈德拉克的一位男性引領姐妹會,魁薩茨·哈德拉克的心靈之眼可以進入任何地方,看到過去以及未來。影片《沙丘》中姐妹會的圣母蓋烏斯·海倫·莫希阿姆對保羅進行戈姆刺測驗,來考驗保羅承受痛苦的意志,是否擁有成為魁薩茨·哈德拉克的潛力。圣母將保羅的右手放進一個綠色金屬方塊的盒子里,盒子具有誘導神經的作用,使盒子中的手感受到被燒焦的疼痛效果。保羅測試中首次出現“火”的意象畫面,重現夢境中厄拉科斯的浩劫、未來的圣戰,暗示保羅預知能力的覺醒,隱喻出保羅光明與毀滅的個人復雜命運,也表明厄崔迪英雄家族被悲劇性缺陷性格所困擾的狀況。
當空間作為人物內化的心理而存在時,雖仍具有真實空間的主體感和連續性,卻不是一種物質的現實,而是創造的美學現實。原著小說是根據伊勒瑯公主的手記客觀地敘述故事,大衛·林奇版《沙丘》運用畫外音來闡釋沙丘的世界觀;維倫紐瓦以獨特的視聽語言來隱形地敘述故事,以夢境中的太陽光與現實中臥室的燈光重合的技巧來自由地表現時空。影片開頭以保羅在夢境中的視覺空間展開敘事,夢境敘事過程中暗示出保羅具備預知的能力。夢境中以弗雷曼人契妮的口吻來講述厄拉科斯星球的歷史:哈克南長期統治與鎮壓沙丘原住民弗雷曼人。劇情中保羅通過兩次接觸美瑯脂來閃現未來的夢境,巧妙地凸顯小說的寫意、心理描寫等富有模糊性特點的文本特征。第一次保羅乘坐蜻蜓飛行器采集美瑯脂,畫外音呼喚命運之子——魁薩茨·哈德拉克;導演通過升格的畫面、朦朧感的濾鏡和帶有夢幻色彩的配樂去描述保羅的腦海想象畫面:保羅在決斗中的死亡,但又確定不會死亡的困惑,此時保羅的意識進入想象界層面中。第二次是保羅與杰西卡在沙漠的帳篷中,蒸餾帳篷呈現黃銅色色調,表征保羅成熟的特征,克服了對父親死亡的恐懼;建構著保羅從男孩到男人的成長,其主體結構進入象征界,建構主體與社會的關系。導演借助照明燈這一客觀物件的發光照耀,冷靜地呈現出帳篷內美瑯脂閃爍的特征。保羅吸入美瑯脂再次閃現預知的未來:血液中的美瑯脂濃度飽和度極高,擁有藍色眼睛的保羅帶領弗雷曼人進行圣戰的場面。火焰的意象再次顯現,象征著魁薩茨·哈德拉克預知能力的增強,導演并以緊張急促的音樂來渲染現實中保羅對命運恐懼的氛圍感。注釋式的改編方式再現了寫意、心理等特征,同時對闡釋沙丘世界觀具有承上啟下的結構作用。
維倫紐瓦運用緩慢的節奏使觀眾沉浸于巨大沉默物體的視覺空間,形成了一種詩意的古典主義廢土新美學;通過軟科幻“賽博格群像”的隱形敘事功能,呈現小說中的主要事件、主要人物、主要矛盾,完成敘事上的緊湊,給予清晰的視覺化呈現;以意識流的閃回、空間具象化人物內心、借用不同風格音樂轉換夢境與現實的注釋式改編,表現小說的寫意、心理描寫等富有模糊性特點的文本特征。改編作品和原文之間是一種“共時性”的互動和流變的關系,如何在保留小說完整性、文學性精神的前提下,彰顯次要人物立體性精神弧光,彌補原著動作性差、反高潮的“缺陷”,是下一部《沙丘》影視化進步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