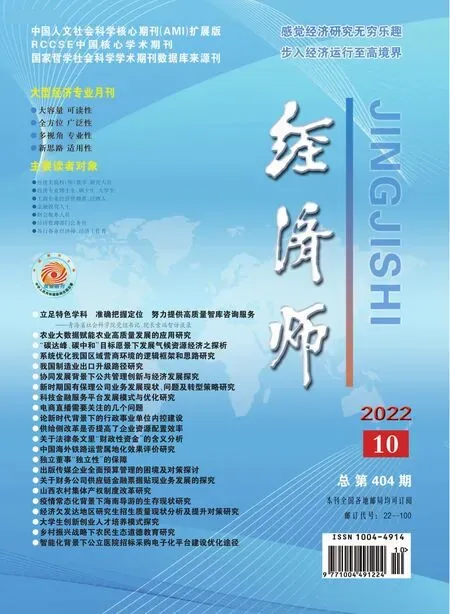山西省收入分配情況研究
●張興毅
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為了“營造激勵奮發向上的公平環境”“拓寬就業渠道”“促進各類社會群體依靠自身努力和智慧,創造社會財富,共享發展紅利”,國務院出臺《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簡稱“《實施意見》”),明確提出“瞄準技能人才、新型職業農民、科技人員等增收潛力大、帶動能力強的七大群體”,實施“七大群體激勵計劃”和“六大支撐行動”。《實施意見》頒布以來,山西省城鎮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就業質量穩步提升,宏觀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優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繼續提高。為了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強化收入分配政策激勵導向,探索開展了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研究,以期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強化收入分配政策激勵導向提供決策建議和參考。
一、山西省勞動收入變化基本情況
(一)勞動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比例逐步提高
2012年到2017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不斷提升。2012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為1.21萬億元,到了2017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增加值1.55萬億元,增加了3415.59億元,年均增長683.12億元。
同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不斷提升的趨勢相似,山西省勞動者報酬也不斷攀升。2012年到2017年,山西省勞動者報酬不斷由5319.18億元增加到7415.66億元,增加了2096.48億元,年均增長419.30億元。
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不斷提升的趨勢和山西省勞動者報酬不斷提高的趨勢高度趨同。2012年到2017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和山西省勞動者報酬變化之間相關系數為0.9739,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的變化和山西省勞動者報酬的變化具有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說明隨著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的提升,山西省勞動者報酬也不斷提高。
在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和山西省勞動者報酬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的背景之下,山西省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也不斷提升。2012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中,勞動者報酬占比43.9%;此后,山西省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穩步提升,2016年,山西省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增加到47.9%。2017年,山西省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16年的基礎上略微下降至47.8%,下降率0.1個百分點;但是,即便如此,2012年以來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不斷增加的趨勢依然沒有根本改變。
從橫向的視角來看,山西省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處于中等水平。2017年,中國內地31個省級行政單位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水平為47.51%;在中國內地31個省級行政單位中,山西省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為47.76%,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在中國內地31個省級行政單位中,排名第19位。但是,盡管如此,相較于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62.77%的西藏來說,山西省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顯然偏低。
(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穩步提高,工資性收入占比占主體
2013年以來,山西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穩步提高。2013年,山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23萬元,到了2017年,山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將近3萬元,為2.91萬元,五年增加了將近1.7萬元。
從山西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結構來看,工資性收入占比處于主體地位。2013年,在山西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占比為65.93%;之后,盡管工資性收入不斷下降,但是,依然為第一大收入來源,2017年,山西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結構中,工資性收入占比依然超過60%,當年工資性收入占比為61.21%。轉移凈收入為山西省城鎮居民第二大收入來源,同工資性收入的變化趨勢相反,轉移凈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步提升,2013年,轉移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足20%,為16.78%;但是,2017年,山西省城鎮居民轉移凈收入占比提升超過20%,為22.89%。經營凈收入和財產凈收入占比長期處于低位,并且,經營凈收入還處于長期下降趨勢,截至2017年底,財產凈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別為7.52%和8.39%。
(三)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穩步提高,工資性收入占比占主體
2013年以來,山西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穩步提高。2013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將近8千元,為7949.47元。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山西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水平分別超過8000元、9000元和1萬元三個關口,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809.44元、9453.91元和10082.45元。2017年,山西省可支配收入進一步增加到10787.51元。
從山西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結構來看,工資性收入占比占主體。2013年到2017年,山西省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分別為52.21%、51.87%、52.06%、51.62%和50.64%,均過半。其次為經營凈收入占比,2013年到2017年五年間,經營凈收入占比分別為27.55%、28.18%、27.76%、27.08%和26.18%。轉移凈收入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處于第三位置,占比分別為18.84%、18.55%、18.68%、19.83%和21.67%。財產凈收入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對最低,2013年到2017年財產凈收入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分別為1.40%、1.40%、1.50%、1.48%和1.52%。
(四)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趨于同步
2007年以來,山西省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波動變化。2009年,山西省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下降至極低值點,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分別在前幾年的基礎上下降至6.7%和3.6%。2009年到2011年,無論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還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均保持上升趨勢,截至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達到15.8%,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提升至18.3%。2011年之后,盡管山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在上一年的基礎上略微提升,但是山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整體均保持下降趨勢;2016年山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分別下降到5.9%和6.6%。
同山西省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的變化趨勢相似,2007年到2017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也呈現出波動的變化。2009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降到5.5%的低點;之后,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又在2010年增加到極高值點,當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13.9%;2010年之后,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整體下降,到了2015年,下降到了地區生產總值的極低值點,當年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3.0%;此后,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有所抬頭,截至2017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提升至7.1%。
從山西省經濟增長和城鎮居民及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趨勢來看,山西省經濟增長與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基本趨于同步。2007年到2017年,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相關系數為0.7098,山西省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相關系數為0.6591,說明山西省經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帶動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并且,2007年到2017年,山西省平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8.7%;與此同時,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0.3%和10.7%,無論是山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還是山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均高于經濟發展速度,說明山西省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較好地享受了當地經濟發展的“紅利”。
(五)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勞動報酬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速
2012年到2017年,山西省勞動生產率變化率和人均勞動報酬名義增長率相關系數為0.9598,二者高度正相關,說明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從現實的數據來看,2012年到2017年,山西省勞動生產率變化率由4.81%增加到2017年的19.17%,平均水平為7.06%;而山西省人均勞動報酬名義增長率由10.5%增加到2017年的19%,平均水平為6.47%。顯而易見,人均勞動報酬名義增長率平均水平高于勞動生產率變化率,說明山西省勞動報酬增長略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從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的結果來看,山西省人均勞動報酬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加。2012年到2017年,山西省勞動生產率由6.8萬元/人增加到2017年的8.11萬元/人,平均水平為7.06萬元/人。與之相應,山西省人均勞動報酬由2012年的2.97萬元/人增加到2017年的3.87萬元/人。
二、山西省收入激勵政策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山西省在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等方面已初見成效,但是由于政策出臺時間較短、政策效果釋放仍需時間等諸多原因,當前仍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一)職工工資水平偏低,城鄉居民增收速度較慢
2017年,山西省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在全國31個省份中排名第29名(倒數第三),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相對較低,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僅為全國工資水平最高省份(北京市)的45.6%,而且近5年職工工資水平增速低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2017年,山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仍占61.21%,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也達到50.64%。工資性收入仍然是山西城鄉居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工資水平偏低是導致城鄉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增收速度較慢的重要原因。2017年,山西省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國31個省份排名中第23名(倒數第9名)。
(二)基層干部、小微創業者、技能人才激勵等群體激勵效果欠佳
從上述結果可以看出,在收入激勵政策初見成效的同時,基層干部、小微創業者、技能人才激勵等重點群體激勵效果不盡如意,受多方面因素影響,這些群體激勵也是近年來各地各部門收入激勵政策實施的重點和難點所在。
(三)政策出臺較多,但政策落地滯后,配套資金投入不足
從《實施方案》印發實施以來,山西省各地各部門圍繞實施方案,根據職責分工,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相關配套政策規定,有力支撐了《實施方案》的落地落實。一方面,政策釋放效果需要一定的時間,具有政策滯后性;另一方面,相關配套政策規定也客觀存在政策“軟環境”制定較多,而相關的必要配套資金投入不足,影響了政策的實施效果。
(四)勞動生產率提升速度慢,約束居民收入更快地提高
如前數據所述,相較于全國范圍內平均勞動生產率而言,盡管山西省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并且于2017年達到了8.8萬元/人的水平。但是,從變化速度而言,山西省勞動生產率增長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并且在2012年到2017年期間,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山西省的勞動生產率還是呈現下降趨勢,從而使得山西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截至2017年,山西省勞動生產率占全國勞動生產率的比例下降到75.85%,同2012年占比達到96.55%而言,大幅下降。
山西省勞動生產率同勞動報酬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598,說明勞動生產率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勞動報酬的增長,山西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推進山西省勞動報酬的提高;但是,與此同時,山西省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偏慢,也約束山西省居民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約束勞動報酬的較快增長,2012年到2017年,山西省勞動報酬增長率平均水平為6.47%,部分年份增長水平更低。
(五)城鄉、城市收入差距問題
山西省城鄉相對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山西省不同城市之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不同城市之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斷縮小,這是山西省居民收入分配的良好局面。但是,與此同時,還應當看到,山西省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全國水平相比,差距依然較大,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國范圍內的排名依然靠后。并且,從山西省內部對比來看,山西省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不同城市之間,城鎮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水平也在不斷增加,這些都是山西省亟需進一步解決的收入分配問題。
三、推動山西省收入分配工作改革發展的政策建議
以持續做好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為基礎,以建立三級聯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體系為抓手,以打造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示范區為引領,全方位開展系列收入分配政策行動,切實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各項政策舉措,深入做好山西省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工作。
(一)持續做好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
持續優化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指標體系,切實提升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指標體系的科學性。不斷完善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機制,著力增強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的適用性。堅持做好年度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充分發揮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對優化山西省收入分配狀況、完善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等推動的作用。以年為周期,編制發布“山西省年度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報告”,觀察、跟蹤山西省每年收入分配政策實施效果以及山西省收入分配最新進展、主要經驗以及進一步優化方向;制定“山西省收入分配年度計劃”,做好山西省年度收入分配工作的部署工作,明確山西省年度收入分配工作目標、主要舉措、預期成效等內容。
(二)建立三級聯動收入分配評估監測體系
在做好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循序漸進推進市、縣兩級政府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形成省、市、縣(區)三級聯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體系。2021年,山西省選擇2個地級市作為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試點城市(地市級),試點開展地市級地方政府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每個試點地級市選擇2個縣級城市,經過山西省政府批準后作為山西省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試點城市(區縣級),試點開展地市級地方政府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分別著力探索地市級地方政府和區縣級地方政府開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的經驗。到2022年,擴大開展市、縣兩級政府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做到“兩過半”,即開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試點工作的地市級城市數量過半,開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試點工作的縣區級地方政府過半,進一步深化探索地市級地方政府和區縣級地方政府開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的經驗。2021年,正值建黨100周年在探索形成地市級地方政府和縣區級地方政府開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全面鋪開市(11個)、縣(區)(包括23個市轄區、11個縣級市、85個縣)兩級政府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做到“兩個全覆蓋”,即開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的地市級城市全覆蓋、開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的縣區級地方政府全覆蓋。
(三)打造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示范區建設
積極爭取國家政策支持,著力打造山西省“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示范區”,充分發揮山西省在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以及收入分配工作中的示范和引領作用。一是建立收入分配示范區規劃體系。圍繞建立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示范區,山西省編制“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示范區建設規劃”和“建設方案”;與之配套,地市級、縣(區)級政府要著力相應編制“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示范區建設規劃(子規劃)”和“建設方案(子方案)”,推動各地以明確路線圖、時間表等形式確保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二是做好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體制建設示范,建立和運行三級聯動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體系。三是做好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機制運行示范,切實做好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著力提升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工作成效。四是建立收入分配激勵政策評議考核制度。將收入激勵政策評估納入市縣地方政府年度考核評價體系,以《實施方案》及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指標及相應指標為基礎和主要量化依據,自2019年起,每年開展省、市、縣(區)政府收入激勵政策實施工作評議考核,評議考核結果向社會公布,強化相關工作的落地落實。五是進一步加大政策宣傳力度,調動群眾參與熱情。充分依托電視臺、報紙、政府網、互聯網等媒體平臺,宣傳重點群體激勵取得的成效,擴大政策的覆蓋面和影響力。通過對重點群體典型案例和增收效果的宣傳,調動更多重點群體主動參與,更好地拉動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六是做好收入分配政策評估監測推進的協調保障工作。加強《實施方案》涉及職責分工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和政策協調,提高各類群體激勵政策信息的利用效率,協同推進各項激勵措施的落實;注意總結提煉增收政策落實中的一些好做法、好經驗加以推廣;給予政策實施效果明顯的部門或集體獎勵,充分發揮工作突出單位的示范效用。
(四)全方位開展系列優化收入分配政策行動
切實加強重點群體激勵措施落地的同時,突出針對基層干部、小微創業者、技術人才激勵等群體目前激勵效果欠佳等措施“短板”,堅持問題導向,有針對性地加強對相關群體的政策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相關政策配套資金的投入。突出以向勞動、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傾斜的“擴張”性宏觀調控政策,以更多實實在在的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獲得感為基本邏輯,來推進實施更為積極地“擴張”性的收入分配政策措施,更好地以收入分配增長帶動消費增長、調動職工積極性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五)加大技能培訓力度、提升人力資本
針對部分人群、部分行業就業需求降低,以及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所產生的新增就業需求,以提高低技能勞動密集型行業、農民工等群體的就業能力為重點,著力在山西省全面鋪開培訓工作,切實提高中低收入群體人力資本水平,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技能水平和就業能力,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最終實現中低收入群體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的雙提升。
(六)堅持和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分配
要充分發揮市場在工資收入分配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在工資收入分配過程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市場評價生產要素、政府彌合市場失靈、員工按照貢獻參與工資收入分配的機制,形成合理的勞動分配份額。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要求,以及山西省關于收入分配的政策舉措,圍繞山西省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深化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制度的試點工作,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全面鋪開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制度,提升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的覆蓋面和持股數量,形成國有企業員工勞動提供者和資本提供者“合一”。積極鼓勵山西省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上市公司積極推進員工持股制度,形成企業員工和企業利益的深度融合。
(七)提升農民工低收入群體保護力度
認清形勢、綜合施策,引導山西省農民工工資合理適度增長。著力構建山西省農民工就業系統化服務平臺,靈活高效調節農民工市場供求。持續構建勞資雙方互利共贏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更好地發揮政府工資調控和引導作用,包括:合理適度調整山西省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山西省制造業人工成本監測制度,加強工資增長、工資價位和行業人工成本信息引導。加強山西省勞動監督檢查制度建設,及時處理勞動違法、違規事件,保障企業正常發放農民工工資,避免因工資拖欠所導致的工資分配差距的產生。
(八)持續完善和發揮社會保障兜底作用
我國社會保險制度設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短交少得、長繳多得”。然而,由于低收入本身工資性收入偏低,高收入者本身的工資性收入較高,所以,社會保險費用“多繳、長繳”者多為高收入群體,社會保險費用“少繳、短繳”者多為低收入群體,從而使得社會保險待遇的享受在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之間存在極大的差距。為此,山西省要積極探索可行的方式、途徑、方法,建立效率和公平并重的機制,適當提高低收入者的社會保險待遇水平,避免社會保險待遇成為新的收入分配差距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