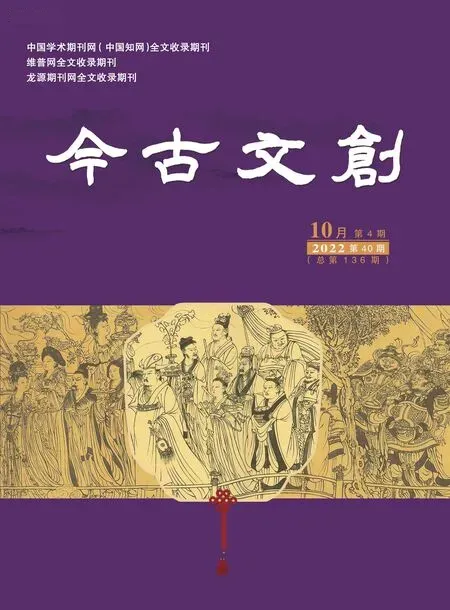虛擬中的真相:華裔女性心理困境再探索
◎王 帆 石軍輝
(咸陽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 陜西 咸陽 712000)
一、齊澤克對拉康三界的闡釋:《女武士》的再探索
《女武士》作為美國華裔女作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代表作,自1976 年問世以來,就引起了美國、中國各社會學術(shù)領域的關注,美國研究、人類學、民族學、女性研究、后現(xiàn)代、后殖民主義時代等研究視角的不斷涌現(xiàn),探索小說所表達的政治、歷史、種族、文化等含義。其中的東方文化符號“花木蘭”時至今日,也是各大電影、電視公司拍攝熱衷的主題和全世界喜愛的形象。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小說中初出現(xiàn)的種種意像表達依然與外界的理解相距甚遠,其間巨大的不可見的創(chuàng)傷也繼續(xù)被掩蓋在娛樂化的幻想之中。
本文將回歸文本之初,借用齊澤克對拉康三界的闡釋,即想象界、符號界和實在界。以此為起點,對小說中想象的虛擬、符號的虛擬和實在的虛擬做出分類分層探索,力求還原不可見的虛擬中的真相。三層虛擬之中,想象的虛擬處于第一層,也是最外層,是賦予虛擬形象在意義上的個人化的虛擬;象征的虛擬處于第二層,意識形態(tài)的權(quán)威或信仰必須在虛擬運作中實現(xiàn)自身;實在的虛擬處于最關鍵的第三層,也是比較復雜的,涉及對于想象實在界、象征實在界、實在實在界(包含:1.意像的創(chuàng)傷;2.伴隨符號層面的朦朧現(xiàn)實;3.對于自身已存在的意識空間預設的未察覺狀態(tài))。從精神分析學的以上這三個層面,再次嘗試探查《女武士》思想深處的精神意識和六十年代美籍華裔女性在思想、文化困境中所遭遇的心靈深處的創(chuàng)傷與掙扎,并嘗試對其中出現(xiàn)的主要東方文化元素,如花木蘭等進行重新闡釋。
二、想象的虛擬:對無名姑姑的個人化描寫與主觀評注
想象的虛擬在小說中主要表現(xiàn)在作者對于遠在故鄉(xiāng)的姑姑的隱秘歷史的個體化描寫與主觀評注上。姑姑早年身故,并未被家族歷史承認,而成為大家共同隱藏的秘密。在無名女人的章節(jié)中,“我”作為對于姑姑這一生隱秘歷史的聆聽者,從自身想象出發(fā)豐富了她的感情和形象,而“我的心理歷史”也通過想象中姑姑的愛欲追求與暴力懲罰中的驚怖中顯現(xiàn)出來,自我的愛欲不得伸展與驚怖不可出口的感受與姑姑的虛擬意像在故事中逐漸編織起來并融為一體。
在姑姑的生前,這種愛欲追求的個人化描寫時常出現(xiàn)在她對于異性的關注中,是她,亦是“我”內(nèi)心的壓抑與渴求:
出于對于形形色色的戒律的恐懼,她的欲望變得微妙、柔韌而堅強。她看一個男人,是因為喜歡看他把頭發(fā)攏到耳后;或者是喜歡看他修長的身軀在肩膀處彎曲、在臀部挺直所形成的問號;因為他多情的眼神、或溫柔的聲音,或從容的步履——僅此而已——幾縷發(fā)絲,一根線條,灼灼的目光,某種聲音,某種步態(tài),為此,她拋棄家庭。(湯, 81)
村里人對于姑姑就是野女人的評價,“我”也表達出不同的聲音:“把她想象成蕩婦并不妥當。我認識的女人中沒有那種人。”(湯,91)在“我”的書寫中,我的姑姑成為一個與眾不同又十分可愛的愛漂亮、愛打扮的女人。拔汗毛、梳發(fā)髻、去雀斑的詳細過程描寫都表現(xiàn)出了對于這位無名姑姑的與眾不同和“我”對她的珍惜之情。她的災禍正來源于欲望與愛牽引之下對自身魅力的展示。那光潔的令人欣賞的額頭、發(fā)髻中飄出的幾縷青絲和優(yōu)美的身姿不僅吸引情人的接近,也在年關的半月里吸引了返鄉(xiāng)探親的叔伯、兄弟、唐兄弟、侄子們?nèi)タ此茐牧舜迩f墨守成規(guī)的“團圓”結(jié)構(gòu)。越軌、懷孕、被驅(qū)逐……她在一項項的罪名中逐步走向死亡的厄運。“……你這鬼,死鬼。鬼啊!我們家從沒你這個人”(湯,157)。我所在的唐人街,即使在幾十年后的美國,也依然延續(xù)著這樣的觀念。在舞會上,當“我在男孩的名字后面默默加上‘兄弟’”(湯,138)之時,“我”心中所生的這股與本土家族文化格格不入的愛欲追求注定也將伴隨著強烈的自我否定被強有力的壓抑在意識之中。而對于姑姑所施加的暴力,母親悄聲對我說:“別告訴任何人你有個姑姑,你爸不想聽到她的名字。她從來沒有出生過。”(湯,186)于是,在家族全員手耳相傳的沉默、順從與共謀中,也將永遠作為秘密被封存起來。
在她飽受折磨、孤獨慘死之后,她無可歸依的“亡靈糾纏著我——她的魂附在我身上……”(湯,195),我那蔓延在內(nèi)心隱秘角落地對欲望的恐懼通過對她的死亡描寫成了形,暴露到了意識中去。她“耷拉著濕淋淋的頭發(fā),皮膚泡得腫脹,一聲不響地坐在水邊,等著拉人下水,好做她的替身。”(湯,195)而真實的姑姑——那個連名字都不被允許留下的女人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樣的……已無可找尋。
三、象征的虛擬:母權(quán)的沉默與英雄續(xù)寫
象征虛擬在小說中生發(fā)于傳統(tǒng)的華人父權(quán)社會對于女性及女性所處位置的忽視和否認。在這樣的傳統(tǒng)文化和美國社會文化觀念氤氳中成長的“我”,獲得了比母親一輩人多一重的觀看視角,在對于作為大他者的父輩的失望與反抗之余,將對于自身存在的肯認轉(zhuǎn)移到了對于母權(quán)的理想化訴求中。
對母權(quán)的理想分為兩個時期表達:第一時期是將母親作為理想化的英雄形象的早期崇拜。作為在家主事的女人,她大膽心細、精明強干,在醫(yī)學院學習的時候,她是與壓身鬼叫陣的女勇士。“你贏不了,你這石頭蛋”“我不會讓步,不論你怎么折磨我,我都受得了。你以為我怕你,那你可想錯了。對我來說,你沒什么神秘的……”(湯,846),母親的理想化形象中同時綜合了男性的勇敢和女性的同情心。然而,一切都在她登上美國的土地戛然而止,走向了“我”目力可及的現(xiàn)實生活。她操持家務、洗衣店、撫養(yǎng)子女,走上了中國女孩所知道了長大要做人家妻子或傭人的人生。母親的這份勇敢僅限于女性群體的框架內(nèi),一旦進入男權(quán)社會,便接受、順從了這威權(quán),從此緘默不語。
在母親的沉默后,“我”的書寫在現(xiàn)實層面也同時沉默了,轉(zhuǎn)而在夢中將自己的理想崇拜對象在寄托“花木蘭”這一歷史形象上,作為象征力量支撐并接續(xù)下去。在夢境的臆想中,花木蘭突破了傳統(tǒng)文化形象所賦予的內(nèi)涵,變得高大、威武,甚至隱隱有了大女子主義者的傾向,對于女子初潮、愛情婚姻和懷孕產(chǎn)子都表現(xiàn)得十分坦蕩直接。故事白虎中木蘭對于初潮的對話描寫就保持了這樣自然不遮掩的態(tài)度:
……老嫗對我解釋道:“你已經(jīng)成年,可以生兒育女了。”接著她又說,“可是,我們希望這幾年你先不要生。”
“那能不能用你教我的抑控之術(shù)止住流血呢?”
她說:“不可。”人總不能不拉屎撒尿吧,經(jīng)血也是同理。隨它流吧。(湯,360)
木蘭與青梅竹馬的愛情和婚姻也與傳統(tǒng)文化中的“男方遠走+女留守”模式完全相反。他在木蘭遠在他處之時與她成婚,后又追隨她去了軍營,為她背上的傷痕哭泣,是以女性為中心的個人化愛情觀與幻想化宗祠社會之間的臆想式和諧聯(lián)系。戰(zhàn)場上的懷孕生子則更是以繁殖為母性力量和以沙場征戰(zhàn)為父性力量的極致結(jié)合與展現(xiàn)。懷孕時“我穿著改大的盔甲,看上去像一個孔武有力的粗壯大漢”(湯,482)。分娩后,“我”將臍帶晾在旗桿上,“那段臍帶隨著旗幟在風中獵獵招展。”(湯,482)
然而,即使在夢境的英雄續(xù)寫之中,作者也無法擺脫男權(quán)作為權(quán)威的影響。首先,英雄的標準是以男性戰(zhàn)士為標準設立的。花木蘭并沒有擁有母性社會女性標志性的豐乳肥臀,強調(diào)生育力的典型身材。正相反,她有著如理想男性一般強壯的身材和英勇作戰(zhàn)的才能等。其次,出征之前,她被允許跟隨父母去祠堂,他們給她背上刻字,讓她不忘為死去的村里人復仇,這也出自傳統(tǒng)文化中男性守衛(wèi)家園的責任。“無論你走到哪里,無論發(fā)生了什么,人們都會知道我們做出的犧牲。”(湯,416)這里的“人們”指家族社會群體,“知道”指他們的承認和接納,也暗合了傳統(tǒng)上男性以傷痕為英勇,以為家國犧牲為榮的傳統(tǒng)英雄文化。最為重要的是,遠征回村后,她壓制住了當?shù)氐牡刂鲪喊裕┙o了族人豐衣足食的生活,成了他們的孝德表率。對于“孝”與“德”的追求,也說明其思想深處期待作為男性展才并被社群接納的渴望。
總的來說,母親英蘭和花木蘭都是作為象征化的虛擬,抗拒父權(quán)壓迫的符號。她們是強大的,也是脆弱的。無論是在現(xiàn)實或夢境中,“我”也只是撿起現(xiàn)實日常中的種種符號碎片編織起來,用已知的男性特質(zhì)包裹在她們和自己身上,來滿足被看見的渴望。長期以來,在話語、意像層面的黑暗與缺乏,使處于困境中的華裔女性很難通過自身去表達,也很難真正走出男權(quán)幾千年來的思想禁錮。當然,因為無法獲得大他者的承認,即便是這樣充斥男性符號的女英雄之夢也無法在現(xiàn)實中開拓出一片空間。
四、實在的虛擬:對現(xiàn)實命運的觀看
實在的虛擬包含了對于想象實在界、符號實在界和實在實在界的虛擬。在想象實在界中,小說中各個章節(jié)中散落的夢境和現(xiàn)實里大量關于鬼的意像加深了思想中對于未知的恐懼,無名女人、花木蘭、蔡文姬、山林中神秘的魑魅魍魎、城市中不斷遭遇的白鬼和黑鬼、鬼丫頭等等。神秘的、歷史的、隱喻的……凡此種種,雖然是來自于想象實在界的虛擬,但延展開來后,卻對于心理產(chǎn)生了斷裂的、實在的影響,十分強烈以至于無法直接面對,形成創(chuàng)傷。
符號實在界中的虛擬主要指伴隨符號層面的朦朧現(xiàn)實,在小姨月蘭的故事西宮外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小姨伴隨著種種本土文化符號來到美國,綠色的花木蘭剪紙、玉鐲子、花卉卷軸和她的本土社群觀念,尋求早已美國化的華裔丈夫的承認。從母親英蘭的口中,可以看出月蘭在本土文化語言符號中作為妻子和母親所處位置的合法性。“……你要去他(丈夫)家,等他小老婆給你開門……你要驕傲地從她(美國妻子)身邊走過去,就當她是個仆人……你要沖他大喊大叫。”“孩子就該歸嫡母,也就是你。母子之間就該這樣。”(湯,1542)然而,這些虛擬的社會法則的作為一種符號存在,其作用是受到本土文化限制的。放在美國社會文化的背景下,非但不能產(chǎn)生任何關聯(lián),反而借由此話語敘說了另一層現(xiàn)實。“你們好像成了我很久以前讀過得書里的人物。”(湯,1925)早已另娶他人,有了兒女的丈夫已站在另一套社會符號系統(tǒng)內(nèi),對曾在作為實在的言語規(guī)則進行了另一番含有諷刺意味的解讀。雙方在彼此的認知里也都成了無法辨識的朦朧鬼影。即便是有花木蘭的剪紙,有姐姐的庇護,月蘭在符號功能錯亂的社會文化沖突中依然垮掉了,成了無法抹去執(zhí)念的瘋子。在精神病院里,她對英蘭說:“哦,你知道,我們這里的人都相互理解,我們說一樣的語言,完全一樣。她們懂得我,我也懂得她們。”(湯,1998)
實在實在界中的虛擬則是一種不可被符號化的,無法被言說地來源于實在界的匱乏的表達。胡笳怨曲中,家庭和學校、社會之間充滿了語言與觀念沖突。在家里,“快嘴快舌,招惹禍災”;(湯,2016)在學校,老師說:“大點聲。”(湯 2050)朗誦時,“我發(fā)出的聲音如同瘸腿的野獸拖著斷腿在奔跑,你能聽到我聲音中有碎骨頭片,還有斷骨間咔嚓相碰相磨的聲音。”(湯,2090)在社會中,“我”是蹩腳的翻譯者,在尷尬中磕磕絆絆地張口發(fā)出支離破碎的聲音。內(nèi)心深處,“我”積累了濃重的沖突和怨念,腦子里總是打打殺殺的故事,做夢也總是噩夢,“我在參天密林捕食人類,我的黑影罩住他們。我眼中滴著淚,獠牙上卻滴著血,那是我本應該愛的人的血。”(湯 2390)在學校,我在陰暗之處,化身成了霸凌者,反復命令那個中國娃娃式的臺灣女孩說話。從一開始言語攻擊,“我要你開口說話,你這膽小的丫頭”(湯,2185)到擰她的臉,拉扯她的兩邊的頭發(fā),對她吼著“說不說?說話!”(湯,2216)一下又一下,最后,卻與她一同哭泣。
你為什么就是不說話呢?……知道嗎、你要是不說話,就是顆植物。你要是不說話,就不會有個性……沒有人會跟你這種人約會的,更別說結(jié)婚了。沒人會注意你。你還得去面試,找工作,當著老板的面說話……我這么做全是為你好,不準告訴別人我欺負你。說話,求求你,說啊!(湯,2259-260)
符號界兩股力量的反復拉扯使得實在界的匱乏感愈加強烈,欲望不斷溢出卻無法找到可以投射的對象。由于符號界的對象空缺,這股莫可名狀的溢出,伴隨極端情緒的宣泄,以無影無形的方式成為超出語言與思想的主導力量,無法消解也無從消解,只能從胡笳十八拍的歌聲中流露出來,在音樂聲中相互聆聽,互相明了。
五、小結(jié)
可以看出,在想象、象征和實在各個層次的虛擬中,自我所受的傷害在故事敘述中都一一暴露出來。男女、種族之間的隔閡、暴力與憤懣都在個體的“我”的心靈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華裔移民所成長的空間,并不僅僅是浮于表面的文化沖突,尷尬一笑并不足以化解。原生文化與本地文化之間并不涇渭分明,而這種難解難分的東方與西方、歷史與現(xiàn)代的交織狀態(tài)使她們的視線常常游移于人鬼之間。不穩(wěn)定,不確信,半人半鬼,不成個樣子。同時,積累在心中的暴力與哀怨也只能停留在潛意識層面,無法以語言的形式一一言明,而現(xiàn)實則是幻滅卻留戀不已的英雄木蘭和衰老盼兒回家的母親英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