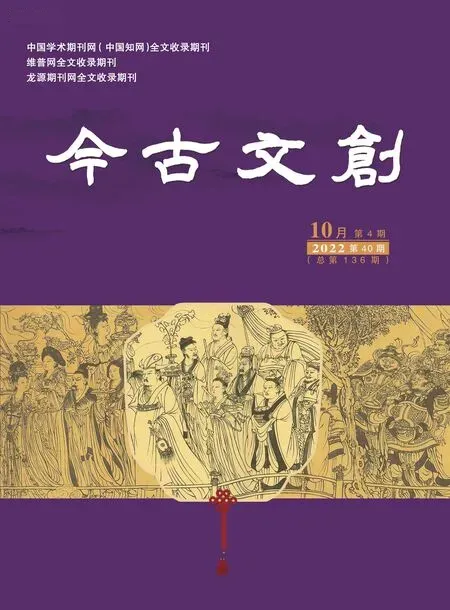板凳龍民俗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傳承
◎駱佳成
(中國計量大學現代科技學院 浙江 義烏 322000)
“總觀人類歷史,任何一個社會要正常運轉,特別要運轉好,是由許多機制維持的,如政黨、法律、軍隊、學校、家庭、民風民俗等等。盡管每種作用大小不一,但缺一不可。”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快速發展使得人民的生活質量普遍提高,然而民俗文化的地位卻在社會發展中逐漸下降。這其中,就包括義烏民俗“板凳龍”。
一、板凳龍在社會發展中的流變
板凳龍是義烏傳統民俗地域文化活動,是農民在長期的觀察和生產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的文化產物。村民們把一節節的板凳鉆孔鏈接,一戶一節,組成板凳的長龍可長達兩百多米,非常壯觀。在古時,板凳龍的組織形式在血緣和集體意識的加持下,形成以宗族為主導的民俗活動。現今,許多村落板凳龍儀式上看到的顏烏藏母的雕刻和繪畫為板凳龍注入“孝感烏傷”傳統道德文化的內涵;義烏民間尚武風潮的價值導向下,板凳龍“出迎”中“游田方”的表現形式也具有體育教育的意義。因此,板凳龍的傳承發展是嚴肅且積極的,是本地區的一個本源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展現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精髓。然而,義烏國際商貿業務快速發展后,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國際市場不斷擴大,城市化進程隨著人口和經濟的激增不斷加快,板凳龍的表現形式也隨著城市化而急劇的異化和簡化。
(一)板凳龍在民間的異化和簡化
龍對中華民族是代表性的圖騰象征,在人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板凳龍在義烏本地也被民俗所隔離并不斷發展異化,在神話傳說中龍的映襯下,龍成為地方性的共性象征榜樣。“崇文尚武”與傳統道德形成一套完整的價值體系為社會穩定和民俗文化傳承提供了先決條件,千年文化傳承的價值體系符合社會發展和百姓需要。板凳龍作為
古時人們心靈的重要寄托及節日的祈福,消解了經年累月的勞作帶給百姓生存的壓力。在千年神權思想的加持下給人以堅定的心靈慰藉,使得人們在物質條件匱乏的古代相信在新年中勤耕苦讀必將得到相應的收獲,從而努力辛勤地投入耕耘當中。正月十五龍皇“出迎”旨在祈求新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子孫平安。在時節上,民俗活動在娛樂的同時也有絕對的嚴肅性,這一嚴肅性也充分體現了老百姓對民俗文化的重視程度,也是板凳龍民俗文化傳承千年的必要條件,可見,板凳龍原本作為農耕生產民俗的產物。在古代思想上,板凳龍的神性與民俗文化觀念綁定,因而具有嚴肅性。然而,隨著義烏逐漸走向國際化,其生產模式與交易形式更加多元化,百姓不需要依靠單一的農業生產來進行交換以博取生存。生產模式的轉變使板凳龍“游田方”等許多民俗特征失去其留存憑證,板凳龍儀式的完整性受到威脅,嚴肅性和觀賞性也已大不如前。社會變遷帶來的思想觀念上的轉變直接使得板凳龍儀式逐漸簡化和異化。在簡化之中,最明顯的體現是板凳龍的軟文化的傳承。大部分青年人對“老東西”興趣衰退,老年人逐漸失去了敘述的對象,傳統民俗文化的接受、傳承相較于過去更加困難,民俗文化儀式開始被簡化,其中蘊含的傳統教育層面上的意義褪去,板凳龍文化內涵的重塑和文化宣傳方式上的推陳出新成為當下維持民俗活動生命線的重要舉措。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的科普教育之下,民眾認知和思想上的局限性逐漸被打破,板凳龍從“娛神”逐漸走向“娛人”,將板凳龍從過去元宵節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上拉了下來。隨著經濟增長,民間對高層次的成長性需求逐漸顯現,代溝隨著不同時代生活層次不同逐漸拉大。經濟發展讓百姓有物質基礎去“鬧龍”,但民俗文化和社會發展必然異變出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民俗文化特征,板凳龍逐漸和社會發展脫節并走向對立。
(二)板凳龍對城市化建設的影響
板凳龍對義烏城市化建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根據義烏市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義烏外來人口眾多,人口流動性極強且每年仍有大量人口流入。在這種情景下,“舊村改造”集約土地建設,打造高效的“耐克區”,成為土地資源高效利用的好方法。新的社區構建使得宗族成員之間的聯系疏遠。溫麗華認為鄉村文化建設面臨著文化建設主體缺位、內容缺失和陣地缺失的難題。以福田社區和銀海社區為例,當地村落建制逐漸淡化被合并為社區,龍燈沒有“出迎”儀式主要放在祠堂供人們祭拜。隨著房屋產業化,社區內住戶幾年一換,生產模式轉型和政策紅利使生產協作逐漸消失,傳統集市逐漸被菜市場取代,宗族成員之間的交流溝通逐漸減少。宗族觀念消退,最直觀地體現就是傳統字輩的淡化,90 后、00 后名字中含有字輩越來越少。
為緩解人口所帶來的交通壓力,高架橋的建設也對板凳龍產生一定影響。舊時龍燈是不能走橋下,車燈是不能照燈頭,走橋下等于燈板被人跨過,都是很不吉利的。蘇溪胡宅村是迎燈大村,由于國貿大道的部分高架橫跨村中的文化禮堂,村前就是主干道,加上一些安全問題的考量,板凳龍“出迎”儀式只能停擺。民俗文化發展如果可以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共同商榷,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更加長遠的均衡方案。
隨著外來常住人口占比逐年上升,外來人口已經成為社區和農村不可或缺的部分,龍燈的迎燈對象也不再局限于本宗族的成年男性,外來人口也成為其中的一員。外來人口和當地居民在日常生活和生產關系上也進一步密切,2016 年以前村莊開始以臨時工的方式聘用外地人加入龍燈隊伍,以擴大村莊板凳龍長度。由于文化的差異,沖突時有發生,給龍燈的安全問題敲響警鐘。
(三)板凳龍對義務商城文化的影響
板凳龍民俗文化是穩定義烏商城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現代市場規模和面向群體的不斷擴大,商城文化內涵也逐漸日趨豐富多樣,但核心問題在于商城文化是以經濟建設為主體,多樣化的商城文化本質上是為經濟建設鋪路,對于正確的價值導向完全依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需要更多輔助形式的。改革開放以來,義烏人民的生活狀況依靠著經濟增長而煥然一新,但是在經濟導向的基礎上難免容易出現短視化、單一化、定勢化的趨勢。在文化建設上,資金流動單一化問題突出。資源上,大規模傾斜于商城文化建設,民俗文化任民間力量發展。商城背景下,百姓思維方式逐漸定勢化,從而使得社會主義價值觀向功利主義偏移。民間力量發展民俗文化從物質角度考量難免短視化,民俗文化內涵的扭曲,表現形式的簡化和異化是最直接的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限于社會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功利化思潮無法深入人心,因此,合理地利用民俗文化補全扶正民眾的價值導向。
民俗文化在民間力量的運作下只要遇到坎坷,民俗儀式必將發生簡化或流變。自2000 年的“三禁”政策和2015 年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責任體系的確立,板凳龍在數量上銳減,長度上被限制小于100 片,后來由于民間熱情也曾有過上漲的幅度,但是,此后龍燈數量和規模搖擺起伏,受監管力度的影響極大。板凳龍在2020 年疫情影響下,全面停擺。2021 年在全國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板凳龍數量上升,但是數量和規模上都已大不如前,元宵民俗形式逐漸向猜燈謎、賞花燈、做元宵上轉移,傳統龍燈的“出迎”儀式只剩下龍頭、龍尾和幾片燈板,甚至是拿車載一圈就當是出迎了。
板凳龍在民間有天然的民眾基礎,然而沒有正確的引導,在功利主義影響下,容易走向錯誤方向,從而加劇與社會發展的對立關系。另外,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但在經濟相對發達的現在,民俗文化在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中的權重需要被重視。
造成板凳龍和社會發展問題對立的根本問題之一是社會治安問題。板凳龍民俗文化首先是一種大規模的群眾性民俗活動,參與者不僅是“迎燈”者還有觀賞者。在元宵節這樣的法定節假日里,聚集觀賞人數眾多,板凳龍的“鬧”也使得治安維穩遭受挑戰。 政策的規制解決了板凳龍“鬧”活動的安全問題,但有時或多或少也挫傷了民俗文化活動的積極性。本土板凳龍文化的多樣性發展缺乏條件,在某種程度上,巨額的擔保金使現有功利主義傾向進一步深化;在責任制度下,不少村落和燈頭會直接放棄板凳龍的傳承。對于板凳龍民俗文化的發展規制是必要的,但完全訴諸高額押金和責任擔保是有待探討與商榷的。社會價值和板凳龍民俗傳統道德的有機結合,通過人的思想轉變和積極民俗文化的指導來引導加速民俗文化正確嬗變并輔以法律手段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二、板凳龍對社會文化發展的現實價值
板凳龍自古就擁有凝聚宗族力量的機能,民俗文化相較于日常的生活生產協作在凝聚力量的動機上更加單純,凝聚更加容易。作為一個外來流動人口數占全市一半以上的城市,維持人口、凝聚人口力量是義烏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環節。
(一)板凳龍有利于地域文化社會的凝聚
板凳龍是吸引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共性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作為一種草根文化相對比較容易被外來人接受,2016年以前制度未落實,當時義烏的外來人員還是以外來務工為主,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關系更多是屬于雇傭關系。在雇傭關系下,板凳龍對于受雇“迎燈”的人來說是一項工作。從動機和主觀意愿上,并不能完全發揮社會凝聚力。
隨著電商模式的成熟及商業化的普及,外來人口結構已經由外來務工向商人轉型,雇傭關系也已經發生改變,義烏新舊居民社會地位、營商環境趨于平等。現在,板凳龍民俗文化相較于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更加開放,更容易使外來人口融入,基于這一種平等的關系也就為社會力量凝聚提供了文化基礎。隨著時代的發展,板凳龍既然無法保留傳承的完整性,在博物館記錄收藏的同時,自身也應該進行革新。允許“出迎”的村落自身屬于城郊,與新居民聚居較多的“老鄉圈”地理上更加接近,因此一些村落或區域會有外地區域性特色。維持人口最重要的就是讓人在主觀意愿上認同這座城市的文化,通過板凳龍這一過去擁有強烈嚴肅性的方式在政府的推廣下,去邀請外地人加入并積極改造。異地文化之間的相互交融,一方面可以再次發揚板凳龍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支撐力量也會不再局限于本地人,另一方面可以發展擁有新居民地域特色的多元化民俗文化特征,再次出現“百村百燈,燈燈不同”的多元板凳龍的創新模式,促進民俗發展多元化。板凳龍可以在新居民的贊同和本地人的接納當中推陳出新,新居民得到歸屬感,老居民也能重拾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相互共贏相互進步,扭轉對立局面促使社會發展和板凳龍民俗文化相互結合。
(二)板凳龍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推動
板凳龍民俗文化中的傳統道德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互結合,可以有效地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入。黨和政府正在積極倡導道德文明建設和價值觀導向建設,在宣傳上,板凳龍作為民俗文化的草根文化屬性易于尋常百姓理解接受;在方式上,節日中的民俗儀式受眾甚廣且深入人心;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詮釋上,義烏的文化故事和古代優秀代表人物也將重新登上舞臺。通常板凳龍文化會以某種實體或者民俗特征的形式呈現出來,這些優秀的人物故事本身就蘊含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的理念,正確地引導闡釋也必然可以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在商城文化背景下,傳統道德文化建設對社會持續發展可以起到補充作用。在經濟相對發達的現在,不可否認不少人著迷于泡沫經濟和政策紅利,價值導向偏差正在逐漸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
板凳龍作為千年義烏從“一無所有”到“點石成金”的親歷者,可以讓人們重新審視勞動價值和自我價值。板凳龍的文化道德傳承蘊含著“仁義禮智孝,溫良恭儉讓,忠孝廉恥勇”的傳統價值觀,有利于提高個人修養從而促進社會持續發展,這些良善價值確保板凳龍千年傳承不斷,也必將繼續成為傳承的依據。目前,板凳龍自身正在面臨文化內涵被曲解從而矯枉過正,這是過去放任民間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樣是重新肅正、詮釋傳統民俗文化內涵,有機結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破而后立,多元化民俗文化發展的好時機。
(三)板凳龍對當地文化教育建設的強化
板凳龍民俗文化教育是國民素質教育的可行且有效的方法之一,可以增加義烏地域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及國際吸引力。經濟轉型需要創新人才,功利化傾向的教育與科技創新和產業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教育的發展偏差和過去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目標的建設是大同小異的,直接影響就是青少年在價值觀養成階段就很容易被引入功利主義,不利于人生的長遠發展。
板凳龍文化的優越性在于,“崇文尚武”素質教育的發展要求、文化教育與家庭教育價值體系的相互補充及寓教于樂的通俗方法。促進當地民俗文化發展、校本課程開發和“雙減”政策有機結合,如道情和畈田朱的小學特色校本課程,青少年可以把空余的時間用到民俗文化當中去,更加深入地去實踐、關注傳統民俗文化,校園課程可以帶動學生個人興趣,從而帶動學生深入學習,其意義在于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深入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建立文化自信。消除青少年與長輩的代溝,推進當地民俗文化創新,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
三、結語
板凳龍民俗傳統文化在后疫情時代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對于扭轉民俗文化和社會發展建設的對立局面,不讓二者此消彼長,融合社會發展需要,將文化力量凝聚互補,應該成為社會文化發展建設的核心議題之一。文化內生機制下,“在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必須建立一種強有力的聯系, 由文化內生出一個推動制度變遷和經濟進步的組織”。因此,板凳龍的穩定發展以及其與商城文化的互補,將是進一步促進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