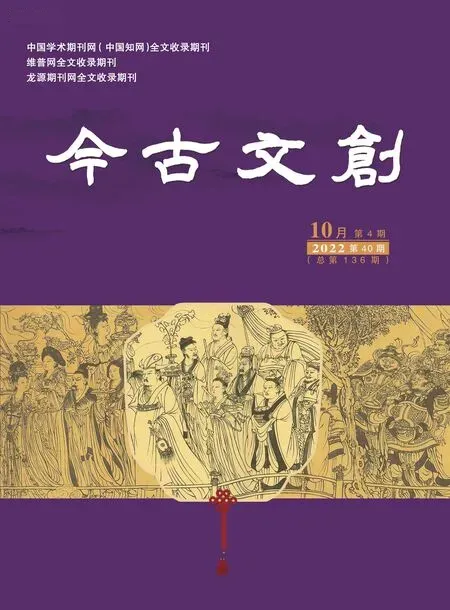電影藝術的類型化與商業化發展(1925—1930)
◎王 澤
(河北師范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河北 石家莊 050023)
20 世紀20 年代之前,中國電影經歷了從誕生到獨立拍攝,再到對短片初步嘗試、對長片進行摸索的二十幾年,這一段時期的努力嘗試都為后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 世紀20 年代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開始進入到了自身的發展期,使得電影業也可以受益于此,發展得格外迅速,這一階段的電影從最初萌芽期的探索中吸取了諸多值得借鑒的寶貴經驗,在經濟、文化的推動下,開始對更深層次的電影藝術進行了探究和發掘。
一、社會背景
20 世紀20 年代后半段,中國正處于戰亂時期,硝煙與炮火彌漫,社會環境極其動蕩,市民情緒也非常壓抑。但電影市場則有著較大程度的自由,20 世紀20 年代是為數不多的電影與政治關聯性較少的年代,這時期的電影不會過多地去表現政治,也并不會成為宣傳工具,所以“避世”的電影成了苦難時期人們排解消遣的一種方式,恰逢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大力興辦實業,發展經濟,因而電影這項事業便順理成章地進入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視線,巨大的商業利益推動著他們去發掘電影無限的商業屬性,使得電影業在此階段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一)電影因“避世”而得到自身的發展
縱觀整個20 世紀20 年代,政局頗為混亂,戰爭頻頻爆發,正常的社會秩序已經被打亂,百姓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里找不到歸屬感,連年不休的戰亂帶給人民的是無盡的創傷與災難。雖然政治的動蕩影響了許許多多產業的發展,也帶給了生活諸多的不便,但對于此時的電影業卻起到了別樣的助推作用。20 世紀20 年代電影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與政治的“不接軌”,它呈現出“避世”的態度,擁有著自由的創作空間,此時段的電影從不反映動蕩社會的不安,而是著重于表現人民樂于接受的元素,充分地發揮著電影的商業屬性。程季華在其著作《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對這段時間的電影評價為“游離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能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相配合,而是走了自己的曲折的歷史道路。”“中國電影事業在混亂的狀態中反常地繁榮起來。”
(二)經濟的發展為電影的發展注入活力
提到20 世紀20 年代的電影,則不得不提到當時電影業極度發達的上海。20 世紀20 年代的中國上海已經發展成了遠東的第一大都市,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對外貿易也因此變得格外發達,造就了經濟空前繁榮的盛況,經商與投資成了具有敏銳嗅覺的資本家們最樂此不疲的事情。他們很快地捕捉到電影這一舶來品是一支有著無限可能的潛力股,可以獲得著豐厚的商業利益與高額的回報,這促使著資本家們開始對電影下了功夫,賺錢是他們的首要目的。
巨大的資本涌入,促使了電影業的騰飛,電影院、制片公司、出版的電影雜志以及各種類型電影在這一時刻全都煥發了勃勃的生機。1925 年前后,上海有各種電影公司141 家,占全國80%以上。至1926 年,全國共計有影院156 座,僅上海一地就有40 座,占全國影院總數的四分之一。同時,大約從20 世紀20 年代開始,電影雜志也為電影業的發展增光添彩,1921 年在上海創辦了《影戲雜志》,此后各類介紹電影的雜志紛紛涌現,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電影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20 世紀20—40 年代中國共出版電影類雜志數量達百種之多。在經濟的支持下,各類與電影相關的產業都開始呈現出了欣欣向榮之勢。
二、電影的商業化特征初現
20 世紀20 年代,是中國早期電影處于探索和創新發展的關鍵年代,也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繁榮期,它基本奠定了20 世紀上半葉出現的各種電影類型的基礎,為之后的電影工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 世紀20 年代的電影具有多元性與復雜性,它繁榮背后的形成原因如之前所述,是多樣的,是有各種原因催生的。諸多電影人不斷地對電影的眾多領域進行探索,為20 世紀20 年代電影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開辟出了一條艱難但輝煌的道路,同時也奠定了這一時期電影多元化的基礎。
(一)電影的娛樂化功能顯露
20 世紀20 年代上海的思想觀念是最為前衛的,這里的文化互融互通,在這里的人們對待新鮮事物亦是非常“包容”,因而享樂主義、物質主義、悅己主義等觀念,早就于不經意間開始萌芽于市民的內心。這種觀念催促著各類娛樂產業的興起,目的是為了滿足市民們強烈的物質欲望,同時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愉悅享受之感。當人們被那些娛樂項目吸引并樂意為其買單的時候,這種娛樂品類源源不斷地供應就成形了,并且開始循環往復,周而復始。
同時,受外來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熏陶下,市民對于電影的審美口味也變得尤其挑剔,他們追求更加新穎、不落俗套的內容,也追求令人眼前一亮的形式。所以不管是風景片、體育片等非故事片,還是《俠女救夫人》 (1928)、《火燒紅蓮寺》(1928)、《梁祝痛史》 (1926)等一系列的故事片,人們都能看到電影制作者在制作時,會刻意追求一些大場面、驚險場景的表現,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大幅度地去表現香艷場景,俊男靚女的演員、夸張露骨的描寫、暴力恐怖的鏡頭、滑稽扮丑的畫面都是這一時期吸引觀眾注意的影像元素。
由于文化氛圍的開放以及想要滿足市民不同觀影需求的這些原因,20 世紀20 年代電影的發展傾向大致如張石川在《敬告讀者》中所提到的那樣:“處處惟興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這樣的“惟興趣”顧名思義是指跟隨著觀眾的興趣,迎合當下流行的時尚元素而進行電影的加工制作;“博一粲”則是希望電影一經播放發行之后能夠讓觀眾體會到觀影的快感,進而更加激發觀眾觀看電影的興趣。周星也在其著作《中國電影藝術史》中,針對20 世紀20年代的電影也進行了自己的總結,說道:“就時代政治與創作思想的關系來說,20 世紀20 年代的電影并不像其他的文學藝術一樣與時代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反而因為現實生活的危難,更加地追逐商業利益,呈現出避世的態度。”
人們能看到的是,早期的電影人大都以觀眾的喜好來制作電影,將電影完全視為一種娛樂大眾的文化來進行創作。同時在觀影的過程中,觀眾投身進去可以忘記現實的紛擾,不論現實生活條件多么地艱苦,外界的戰爭多么殘酷,只要買上一張電影票,進入到電影所營造的虛擬環境之中,便可以逃到無憂無慮的自我世界當中,享受到極致的快樂。所以以情節為中心,以市民的習俗為基準的電影創作成了這一時代的特色,也為日后的電影創作提供了范本。
(二)電影的類型化特征明顯
承繼上文所述,當電影呈現娛樂化特征時,其商業化就會變得明顯。商業化衍生出來的則是電影的類型化。類型電影以商業盈利為目的,類型電影的產生是因為生產商在制造某一類影片上映之后,看到觀眾的反響不錯,進而開始“批量”生產,引得競相模仿的電影。在20 世紀20年代,“生產電影類型化”這一勢頭發展得尤為猛烈,所以許許多多的電影種類開始蜂擁而至,呈現豐富多元景象。
早期中國類型電影的產生一方面是源于追逐高額利益的需要,植根于中國本土的文化發展出了許多的類型如古裝片、武俠片、愛情片等;而另一方面則是受國外電影的影響,這種影響大部分來自美國,受其影響,中國也產生了喜劇片、社會片、偵探片等片種。
受國內文化的影響,中國本土產生了不少的類型電影。古裝片是第一個較為明顯的類型片潮頭,《梁祝痛史》(1926)是古裝片出現的標志,由天一公司創制并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收益,1927 年就出現了各個影業公司競相拍攝古裝片的局面。中國的古裝片大多改編于民間故事和小說,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為古裝片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養料。路見不平,行俠仗義是中國人從古至今一直津津樂道的話題,俠客也是被人們崇敬的對象,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武俠片也在20 世紀20 年代應勢而生,這類型的影片以除暴安良、追求正義為主題,受觀眾的追捧,比較著名的則是張石川執導的《火燒紅蓮寺》(1928)以及其大火之后繁衍出來的“火燒”系列。在《火燒紅蓮寺》上映之后的三年內,“火燒”系列連續拍出了18 集,但后期的影片與神怪結合,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極不相符,因而這個武俠神怪之怪潮到1931 年后也戛然而止。同時,借助國外的元素在中國發展起來的電影種類也在此期間大放異彩。早期中國喜劇片的形成與傳入中國的外國動作喜劇有關,在傳入的過程中與中國本土的文化相結合,出現了國內的第一部喜劇片《勞工之愛情》(又名《擲果緣》)(1922)。中國的社會片受美國的影響也是有跡可循的,在1916 年前后,美國的社會片傳入了中國,1922 年開始大規模地在國內的電影市場放映。中國的電影人和觀眾在觀看之后都有著不同的感受,電影人視社會片為一個商機,觀眾視社會片為一種“心靈和情感上的寄托”,所以社會片也借此在中國扎根,隨后發展了起來。中國的偵探片也是受國外的影響,這類片種首先在國外興起,隨后同偵探小說一起進入中國市場,20 世紀20 年代初期的電影《紅粉骷髏》(1922)可以看作是偵探片的開端。這些片種的產生均是在國外的影響下進行拍攝和制作的。
這些影片在上映之后,觀眾的呼聲很高,制片商也看到了此類類型電影敘述手段上的“高明”,在講述故事方面可以發揮著自己特有的優勢,于是將這些頗受歡迎的類型大量引入和創作,從20 世紀20 年代初期的產生,一直將其延續到20 世紀20 年代后期,乃至未來幾十年電影的創作都離不開這些類型。在20 世紀20 年代后期,這些電影的種類已基本定型出其規模和格局,紛紛開啟了自身的發展之路。
三、主要電影公司及其作品
20 世紀20 年代是電影發展的黃金年代,優秀的文化工作者們積極地加入電影的創作當中,催發電影變成了一項產業,電影公司相繼誕生。這一時期有實力的電影人不勝枚舉,如張石川、鄭正秋、邵醉翁、任彭年、但杜宇、程步高、洪深、黎北海、吳性栽、朱瘦菊等等。而他們的努力,造就了許多有實力的電影公司,如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聯合影片公司等等。在電影界注入新鮮血液之后,中國電影開始了走上了崛起的道路,各個電影公司也開始呈現出了自身的特色。
(一)注重“教化”的明星公司
張石川與鄭正秋于1922 年創辦了明星公司,它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家民族電影企業,其在成立之后,創作的影片主要針對的問題就是“教化”問題,鄭正秋主張讓電影創作“含有改正社會之意義”,因而他們多關注于倫理和家庭,作品貼近當下社會,以期能夠達到教化人生的目的。同時他們在選材上也多關注婦女的生活和家庭的關系,借此對社會問題進行剖析。
明星公司出的影片《孤兒救祖記》(1923)的上映引發了一陣收視熱潮,人們開始重視起對電影社會意義的關注,沿照這條路線,明星公司出品的影片繼續探討社會問題,相繼出品了《苦兒弱女》 (1924)、 《最后之良心》 (1925)、《上海一婦人》(1925)、《空谷蘭》(1925)等等。這些影片都以社會為背景,在各種領域加入自己的觀點而去探討。
最典型的當屬《最后之良心》,該片探討的就是封建社會的婚姻問題,如童養媳、抱著牌位成親等等的陋習在影片里被無情地揭露,充分地表現了在當時的年代,這種封建制度帶給人精神和身體的摧殘,對當時的社會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使得人們在觀看電影的時候也會開始反思并批判這些殘舊的壓抑人的習俗,加強了思想上的深刻性。由張石川執導的《空谷蘭》也聚焦了社會問題,描寫的是中國舊社會豪門家族中一對夫妻悲歡離合的故事。整部影片以紉姝的悲劇命運為主線,以紉姝、蘭蓀和柔云三者間的矛盾關系為核心展開。紀蘭蓀與陶紉姝門第不等但因相愛結為了連理,柔云為紀蘭蓀的表妹卻一直以未婚妻自居,在這段感情中作為第三者身份一直插足,最后紀蘭蓀與陶紉姝和好,而柔云也因為逃跑時馬車翻車,隨即觸底而死。《空谷蘭》原為包天笑根據日本作家黑巖淚香翻譯的英國小說《野之花》改編的小說,曾在當時上海的《時報》上連載發表,鄭正秋等人看中其廣泛的社會影響,于1925 年請包天笑將它改編成電影故事。上映后頗為轟動,票房價值達到13 萬元,創造了默片時代的最高賣座紀錄。
(二)立足傳統的天一公司
邵醉翁與他的兩位弟弟邵邨人、邵仁枚于1925 年的6 月一起合辦了天一影片公司。影片公司成立之初,就明確表示公司所制作的影片要發揚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避免被西方外來文化所影響、所同化,提出“注重舊道德舊倫理,發揚中華文明,力避歐化”,因而其拍攝的影片都立足于傳統。天一公司的電影創作也多選材于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和古典小說,是人們所熟知且耳熟能詳的故事,也更有利于觀眾的接受。
天一影片公司在成立之后,拍出的第一部影片是《立地成佛》(1925),其余的代表作品有《女俠李飛飛》(1925)、《孟姜女》(1926)、《梁祝痛史》(1926)、《義妖白蛇傳》(1926)等等一系列富含傳統意味的影片。尤其是《梁祝痛史》的出現,成功地引領了國內稗史片和古裝片的風潮,其扎根于傳統的制片路線也給“邵氏兄弟”的電影公司打上印記。
1926 年,天一影片公司的《義妖白蛇傳》是根據我國經典民間愛情故事來拍攝的電影,電影人以原故事為主體,在劇情上進行了改編與加工,本應行善積德的僧人變成了道貌岸然的小人,奸佞狡詐的蛇類卻變成了俠義肝膽的英雄,電影借白蛇青蛇姐妹所行的善舉而反諷那些看似有情有義實則忘恩負義之徒,從而來達到警悟世人的目的,讓人們不要以貌取人,而應該發掘人內心深處最寶貴的東西。此類題材是天一影片公司所擅長的,他們善于以人們熟悉的故事做切入點,經過藝術的加工處理,再返送到人們的眼前,規勸人們行善積德,切勿做傷天害理之事,對于當時的社會氣氛起到了一定的凈化作用,用獨特的改編故事、神話的方式開辟了屬于自己的藝術道路。
四、結語
20 世紀20 年代的電影全面飛速的發展,從對電影的初步認識,到逐漸摸索電影,探索電影的不同層面,再到出現電影公司、電影刊物、電影明星,形成一整個電影產業發展鏈,到最后形成自有且多樣的風格,都是在20世紀20 年代中呈現的。而20 世紀20 年代的后半期,從制作流程到影片上映,也都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既定規則。重新梳理這一時期電影的時候,會有許多的發現,同時也有許多可以借鑒的經驗。正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大衛·休謨在《論歷史研究》中提到的:“歷史不僅是知識中很有價值的一部分,而且還打開了通向其他許多部分的門徑,并為許多科學領域提供了材料。”回顧這段歷史,回溯這段記憶,汲取這段營養,開始一段啟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