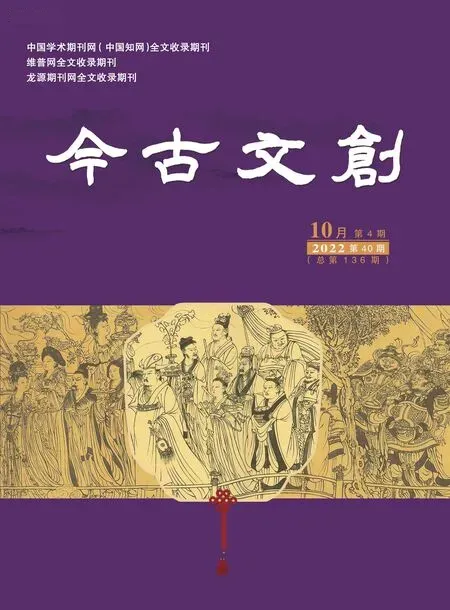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英譯散文譯者主體性解讀
◎周 圳 鄭忠耀
(河南理工大學 河南 焦作 454003)
一、引言
(一)生態翻譯理論的提出
2018 年,胡庚申教授率先在《生態翻譯學解讀》中將生態翻譯學定義為“取生態之要義,喻翻譯之整體,基翻譯之實際”的學科,在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環境下,對翻譯的選材、過程、原則和方法進行描述。其中核心是譯者的“適應/選擇”理論,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先要“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又要根據生態環境的需要對譯文進行“選擇”,這兩個過程都需要譯者能動參與,從而體現了譯者的主體意識性。
生態翻譯學的“多維轉換”翻譯方法主要落實在“三維”轉換上,即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方面的轉換。生態翻譯學關注的是譯者與生態翻譯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關注譯者在翻譯生態中的生存環境和能力發展。文學翻譯活動的順利進行和整個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與譯者密切相關,因為作為翻譯生態系統中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譯者有責任協調翻譯環境、文本生態系統和翻譯共同體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譯者主體性與翻譯
在傳統翻譯觀中,譯者的任務僅為語際轉換,且譯者必須對原作亦步亦趨、頂禮膜拜。譯者在譯文中近乎透明,譯作相對于原作而言就是“寄生的藝術”。人們認為依托原作開展的翻譯活動僅僅是一種“復寫”,原作者文學創作的價值遠大于譯者語際轉換的價值。譯界對譯者主體的研究在“文化轉向”之后進入高潮,由面向源語文化的翻譯理論轉向面向譯入語文化的文化學派翻譯理論。譯界對譯者主體性的研究視角不斷涌現:闡釋翻譯理論、操縱學、解構主義、布爾迪厄文化社會學等。
二、生態翻譯學視域下譯者主體性的體現
(一)譯前生態——譯前文本選擇的主體性
生態翻譯學的核心即為“適應/選擇”理論,譯者的適應和選擇首先是對自身的適應和選擇——對自身需要和自身能力的適應和選擇。譯者的審美需要影響其原作的選擇。根據闡釋學分析步驟,譯者第一步要“信任”原作,與原作產生共鳴才能激發譯者的創造力。正如張培基在前言中所說:“散文最真實,最誠篤,不雕飾,不做作,因而是一種最易令人感到親切的文體。”因此,譯者根據自身藝術氣質和審美判斷選擇翻譯文本。張培基在前言中提到:“……這九十六篇短文裝在頭腦里,是我增加了對英語的散文的興趣,增加了語感,慢慢悟出了寫文章的路子。”可見環境和文化熏陶下影響譯者的原文本的選擇,使譯者在受動性因素制約下得以發揮主體性。
張教授在《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前言中寫道提及其進行散文翻譯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向國外介紹一些優秀的中國現代散文作品”,這則表現了譯者對外在需要——社會文化語境等客觀條件的適應性選擇。一方面,譯者所處的時代語境賦予譯者文化使命。另一方面,譯者早期信仰不斷內化于特定歷史階段的譯者意識結構,形成譯者的“前結構”行為模式,影響并指導譯者的翻譯實踐。
(二)譯中生態——多維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主體性
1.再現原作美感——從語言維度展現譯者的審美創造力
根據美學原理,翻譯遠非單純信息轉換,更是審美再現的過程。譯者首先通過審美感知,從視覺接收到來自原文的信息之后傳輸至大腦。然后在譯者腦中一般感性意象升華為審美意象,并且不斷豐富。譯者成為闡述者之前首先是一個讀者,閱讀時產生的審美感情附著于審美意象之上,這樣譯文才能保留原文中作者的情感。譯者將解碼后的基本信息和融入譯者主觀審美和歷史情境的審美意象重新編碼,最終形成譯文。譯者一方面要盡職于作者,延續和衍生原文。另一方面,譯者需要考慮讀者在語言、語用和文化方面的接受水平。譯者作為翻譯過程中的原作第一讀者,往往是最接近作者美學理論形態的主體,此時譯者讀者通過其審美、想象完成文本意義的完整構建。美學意義的重構摻雜譯者自身的審美理解,因此譯者也是文學創造者,在此過程中,譯者的主體創造性達到峰值。對譯者而言,要想處理好原作、原作者以及讀者等生態翻譯環境下的結構主體之間的關系,必須充分發揮主體性對源文本進行理解、闡釋與再創造。
例1.有時流到很逼狹的境界,兩岸叢山迭嶺,絕壁斷崖,江河流于其間,回環曲折,極其險峻。
Sometimes it comes up against a narrow section flanked by high mountains and steep cliffs,winding through a course with many a perilous twist and turn.
譯者選譯李大釗這篇文章并將其放在第一輯第一篇,其目的不僅僅是傳達原文語言美感和漢語特色,更是處于宏觀翻譯生態環境(社會政治形式或者語言文化環境)下對“譯境”的適應和選擇,以期實現警策激勵的目的。漢語重意合,詞與詞、句子與句子之間的組合往往在外部形態上沒有明顯的標志,而主要依靠意義上的關聯來連接;而英語重形合,句子與詞的組合在外部形態上有明顯的標記,當形態標記不充分的時候,還可用其他語法手段來顯示關系。譯文使用重構法將原文的短句譯為長句,結構緊密,形式緊湊。譯文中,譯者將“極其險峻”處理為“回環曲折”的修飾語,譯為 “perilous twist and turn”,一方面強化曲折程度,并且附帶感情色彩,使讀者切身感受到江河曲折蜿蜒,狹窄逼仄之險、之惡,另一方面,頭韻的使用極大程度上彌補了四字詞語在語言轉化中損失的“音美”,又保持了源語簡潔對仗之“形美”。
2. 打造文化新鮮感與文化共鳴的平衡——從文化維度體現譯者的文化適應與轉換主體性
根據生態翻譯學,文化生態有大小之分:大的文化生態指的是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和諧共生;小的文化生態指的是翻譯文本內各文化要素的和諧關系。Bhabha(1994)提出“雜合化”翻譯策略,他認為“歸化”與“異化”的二元對立之間存在“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內,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被瓦解,弱勢文化與強勢文化語言特性都被保留下來。譯者在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尋求文化的雙向互動,在確保讀者接收原文信息的同時,保持源語文化異域特色,不以“文化輸入”之名顛覆目標文化。一方面,譯者出于對讀者閱讀感受的照顧,在譯入語文化參照系中尋找文化意象。
例2.我出國留學的時候,我父親買了一套同文石印的前四史……
When I was leaving China to study abroad,father bought a set of the Tong Wen lithographic edition of the First Four Books of History**...
“前四史”是對中國四部史書的統稱,譯者選擇直譯能保持形式上的簡潔與通順。但對一些缺乏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的外語讀者來說,直譯可能會造成困惑,造成讀者對文化內涵的不解甚至誤解。因此,一方面為了避免文內過長的解釋造成讀者注意力與閱讀興趣的分散,另一方面為了促進異質文化的輸出,譯者選擇了直譯加腳注譯法。如此,不僅尊重了源語文本,保持了譯文的簡潔通順,又為感興趣的讀者提供了背景知識。
正如譯者在前言中所說,由于先前在缺乏寬松的氣氛中,一些傳統文化未能得到很好的向外推薦機會。而后隨著文化教育的發展和思想意識的積極交流,學者們承擔起文化傳遞以及對外交流的任務。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既受到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又是由自身翻譯動機和自覺的文化意識決定的。譯者對讀者理解原文的作用日益彰顯,因此也就不再隱藏在文本背后。譯者就有權在翻譯倫理的約束下,以源語文本為基礎,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最終以實現傳介異質文化或自身文化的目的。
3.明確交際差異、實現交際意圖——從交際維度展現譯者的適應性轉換主體性
在交際維度上的適應性選擇即譯者發揮主體性作用最大限度保持源語和目的語的交際生態,包括語言的功能、交際意圖、原文表述風格以及敘事角度等,在不損害源語交際習慣與目的的前提下,尋找目的語讀者能理解和習慣的交際方式。作為跨文化交際活動, 翻譯也帶有交際目的。譯入語文本的交際目的,從宏觀看,是為實現文化或者價值觀單向輸出乃至雙向交流;從微觀看,是為傳遞作者自身審美體驗、思想觀念以及信仰架構等。“五四”以來,新文化、新思潮涌入,打破了中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桎梏。寫作內容和寫作風格都是時代政治、社會和文化滋養的產物,展現了變革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極具文化傳播和跨文化交際的價值。譯者在翻譯中采取特定策略也具有目的性,一是對原文及作者交際意圖的順應,二是對讀者語言習慣、接受能力以及主流意識的順應,三是對出版商、贊助人等外部物質因素的順應。刪減、增譯、加注等翻譯策略皆是各種交際目的協商下的語言選擇。
例3. 原文: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著的中國!
譯文:Farewell,China,my beloved homeland!
原句在文章中出現了三次,分別是開頭、中間以及文末,三個短句卻飽含對祖國深切的熱愛以及即將離開祖國的不舍之情。譯者同樣采用三個短句,以一種簡短有力的方式貫穿起開頭處就定下了文章的感情基調,文中又以單句成段的方式再一次出現,更有情感過渡的意味。這既是一種告別,又是對祖國許下的堅定諾言。而在全文最后,簡短的一句話收束全文,激蕩人心,振聾發聵。譯者對開頭此句的處理更是絕妙,原文中首段是由十幾個短句構成的,讓讀者感受到作者的感動與不舍之情源源不斷傾瀉而出。而念及英語語法的限制,譯者不可能將原文十幾個短句的形式照搬過來,只能將該段拆分為數個復雜句處理,這樣原文表達的感情必定有所減損。而譯者將“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著的中國,”處理為“Farewell,China,my beloved homeland!”一來以一個感嘆句提挈全文感情線總綱,二來又與下文再次出現的兩句保持了形式上的一致。另外,譯者將后一個“中國”譯為 “homeland”,而非按照原文譯為 “China”,將作者的愛國之情更加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作者對中國“全心的愛”不是出于別的原因,而是出于深切的對祖國的愛,讀者讀了之后難免也被引起感同身受的愛國之情。
原文是源語生態的一部分,置身于源語文化;而譯文則直面譯語文化。創作與翻譯都是一種人類“行動”,帶有特定目的和任務。作者和譯者的思維活動以及行文方式必然不同,這就會影響到原文與譯文的遣詞造句、表達方式以及結構編排。但作為生態翻譯環境的“中間環節”,譯者顯然不及原作者般瀟灑自如,上述“差異”一定是在策動者劃定的限制之內以及讀者的心理預期和交際需求之中的,否則,這條翻譯生態鏈就中斷了。因此,譯者必定才思超逸如原作者才能重組原文讀者可能產生的反應,而其譯語能力也須足以預估譯文讀者的反應。只有接受者實現交際目的,交際過程才算成功完成。
(三)譯后生態——譯作主體性作用
多數翻譯活動是有目的、有計劃、有一定社會影響的置于人際關系生態系統內的活動。《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的英譯文有的曾在《中國翻譯》以及《外國語》上發表。作為策動主體的翻譯發起者、贊助者以及出版商是譯者為了維持翻譯市場生態系統的整體、關聯、動態、平衡不得不關注的要素。《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被許多院校作為翻譯教材使用,為學習者研究文學作品漢譯英的理論技巧提供范本和參考,實現了推動譯學發展的翻譯之功。在翻譯教育生態系統內,推動了學科建設系統、教材建設系統乃至學校翻譯教育生態系統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以翻譯學研究為核心的跨學科集合體——翻譯本體生態系統的發展,引起了各高等院校以及各學術期刊相關研究的爭鳴,已有不少譯學研究者從不同角度探討《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中翻譯現象的結構和運動規律,通過不斷質疑、思考與交流,使得譯學研究充滿活力與生機。
三、結語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有權選擇翻譯對象、決定翻譯策略、影響譯文質量,但并不意味著譯者在整個生態翻譯系統中起著唯一決定作用。在生態翻譯學視域下,“翻譯主體性”中的“翻譯”不再特指某一具體翻譯行為,而是涉及翻譯中所涉及的所有主體活動。主體性說到底是主體能動性和受動性的辯證統一。譯者主體性受到原文、源語和目的語以及其他翻譯主體的牽制,在生態翻譯環境中譯者確非“中心”,是因為譯前以及譯后生態中涉及的主體甚多,各主體之間相互平衡形成良性生態環境,若有任何一方獨占優勢而致使其他因素處于被“壓制”、被“顛覆”,那么就會打破生態翻譯環境的良性平衡,翻譯活動難以為繼。而在譯中生態環境,翻譯操作為主要活動,譯者是主要施動者,譯者在這一過程中自然占有支配地位,譯者可以選擇翻譯對象以及翻譯策略,因此譯者就是實現平衡源語生態與目的語生態的最積極因素。張培基先生通過早年學習培養起來的文學素養以及對中外散文的深刻了解都確保了譯者既能遵循源語生態規范又能游刃有余地發揮譯者主體性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生態翻譯學所定義的“譯者責任”要求協調翻譯群落中各因素的關系,適應生態環境,在關照生態整體的前提下“創作”出可接受、可傳播的譯文,讓原作的生命通過翻譯延續下去。而這,這正是生態翻譯學中譯者主體的責任。
①**the First Four Books of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