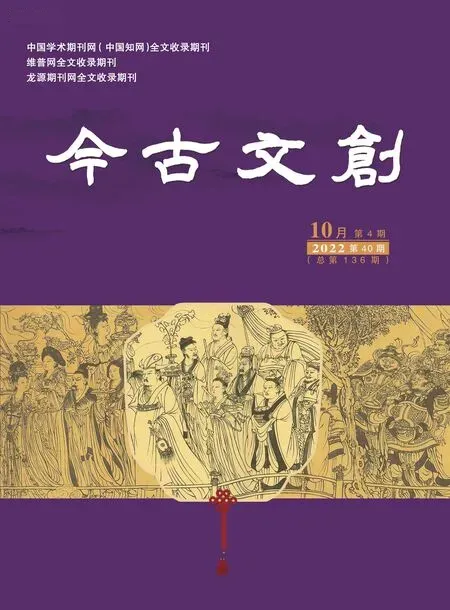試論平城—晉陽地區北齊壁畫墓獨特藝術風格的成因
◎李沛成 魏博文
(西安博物院 陜西 西安 710054)
一、技術處于簡單與成熟之間
北齊,大多普通民眾對其了解程度不高,它處于一個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北朝時期,山西是北魏、東魏和北齊的核心統治區域,是民族融合的熔爐、文化匯聚的舞臺。平城和晉陽地區大量的北朝文物遺存,越千年而熠熠生輝,其中墓葬壁畫頗為引人矚目”。在這些墓葬當中,以徐顯秀墓壁畫、婁叡墓壁畫、九原崗墓壁畫和水泉梁墓壁畫為代表,其墓葬規格、壁畫工藝水平和內容特點也是相對較高的。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當中,由于戰爭、工藝以及保護難度等很多原因,致使能夠保存下來的地上壁畫相對較少,所以墓葬是目前能夠留存古代壁畫的一種較好形式。據考古發現,中國的墓葬壁畫最早出現在西漢時期,分別有河南永城芒碭山柿園梁王墓、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隨著時代及王朝更迭,到魏晉時期,隨著北方鮮卑拓跋一族的崛起,到南方定居并建立王朝,民族的匯聚造就了多種文化的交融,而北齊就處于這樣一個時代。
目前存世的繪畫作品最早可追溯到顧愷之,承接有到唐代閻立本、張萱等,在魏晉到唐代之間存在一種實物留存的斷代,作為銜接的南北朝畫家有陸探微、楊子華、張僧繇等為代表,古代畫評家謝赫、張彥遠等都對他們有過褒獎,遺憾的是,他們皆無存世作品,目前可以參考的資料有現存在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的宋人摹本《北齊校書圖》以及考古挖掘出的墓室壁畫及文物等。而墓室壁畫為僅有遺存,在其藝術風格上的判斷更為可靠。這些墓室壁畫代表有婁叡墓壁畫、徐顯秀墓壁畫和灣漳墓壁畫等。它們一經發掘,便引起了國內外的巨大轟動,彌補了我國南北朝時期繪畫的空白,可以為后世研究古代繪畫的發展和傳承提供很好的資料。那么是何種原因使北齊繪畫能夠在中國繪畫歷史當中獨樹一幟呢?筆者在下文闡述以下幾個原因。
這些墓室壁畫的畫風與早前完全不同,與后世唐代、宋代的表現也不同,早期魏晉時期現存的壁畫線條簡單,而且大多數以平涂的方法來表現,“漢末中原古墓壁畫圖像多表現出一種沉靜肅穆的風格,線條簡潔概括,敷色以平涂為主,造型端莊。河西魏晉十六國古墓壁畫圖像沿襲漢末中原傳統”。而北齊墓室壁畫所采用的是一種“凹凸法”,這種方法可從南朝畫家張僧繇“疏體”風格中溯源,“按唐宋人的說法“疏體 ”是張僧繇在吸收了印度岌多藝術因素后加以變化而成的人物畫風格”。其特點就是對形象的描繪更為立體,染色不再是平涂,而是隨形象的五官和形體起伏而設色,線條更為靈動,粗細變化,尤其是婁叡墓和徐顯秀墓壁畫中的形象和用色,通過“染低不染高”的方法,將人物表現的立體形象,整個壁畫以土紅,土黃色為主基調,使壁畫整體統一,“水泉梁壁畫顏料色彩運用非常豐富,可明確辨識者有紅色、綠色、藍色、黃色、黑色、白色、灰色七種顏色,其中紅色顏料按不同部位的色相又分為暗紅、大紅、土紅、朱紅、淺紅五種”。可見,其用色非常豐富,能夠將顏色巧妙運用在描繪物體應有的位置上也確實體現了畫師的畫工,鉛白、朱砂及孔雀藍在古代礦物質顏料中更加珍貴,因此只在一些關鍵部位稍加點綴,如覆蓋力較好的鉛白多出現在墓主人的腰帶部位;高飽和度的朱砂出現在嘴唇處,而臉部運用淺紅稍作暈染;而孔雀藍則只出現在墓主人的衣服裝飾部位。
二、多民族交融的時代
北齊處于中國古代政權交疊紛爭的南北朝時期,每個朝代的時間都不長,多民族混合交融,這正是文化與藝術交流的土壤,北齊繪畫就受到了胡文化的影響,“以繪畫而言,東魏北齊時曾流行一種傳出于中亞的繪畫,其畫法與中國傳統的繪畫十分不同,是用特別煉制的胡桃油調顏色來作畫,以色彩表現見長,近似于今天意義上的油畫。 因其傳自西域,故稱之為‘胡畫’。能掌握這種‘胡畫’技藝的文獻見有祖挺、徐之才、平鑒等人。北齊書·祖挺傳》”。
在現存北齊墓葬壁畫當中,可以看到所描繪的故事,基本包含了墓主人的現實生活、死后升天的場景,描繪的是現實以及宗教題材等,一種基于現實的和靈體、精神的表現。那時,人們對于星象、鬼怪都還敬畏有加,如忻州九原崗北朝壁畫墓,墓室第一層為升天景象,以祥云為背景,繪有神怪異獸、風伯雨師等形象;第二層以郁郁蔥蔥的山林為背景,北段狩獵圖描繪了眾多武士騎馬放鷹驅狗、追逐圍獵的宏大場景。南段為備馬出行場景,西壁侍者中有胡人形象;第三層、第四層依舊以山林為背景,繪有隊列出行圖,各將領、儀衛均佩帶武器。墓道北壁繪有一座規模宏大的木結構建筑,廡殿頂,復雜的斗拱、重復的額枋、特殊的瓦釘、彩色鋪地磚,表現出很高的等級。屋頂正上方繪一博山爐,左右兩側各繪一獸首鳥身的怪獸。
我們可以從同一時期的其他文物古跡中找到其受“胡”文化影響的根據,北齊處于我國公元4—6 世紀,政權交替,民族遷徙,提供了文化、貿易、宗教、社會等一系列交流的契機,從地理區間上看,目前已發現的文物古跡多處于東西向的絲綢之路上,從波斯地區,延伸到中亞粟特地區,直到我國的古龜茲、河西走廊,往東延伸到中原地區,直到東北高句麗壁畫古墓,在這一條漫長之路上,本文所探討的山西北齊古墓葬壁畫就位于中原地區的鄴城——晉陽墓室壁畫區位中。
北魏拓跋氏一族經由大興安嶺到今天山西大同,再遷都到洛陽,“從北魏墓室壁畫風格和色彩搭配看,仍是延續兩漢以紅黑色為主的色彩體系,并未出現新的突破”。我們可以從北魏時期的墓葬中發現,如大同沙嶺壁畫墓,這是目前勘探發掘出的最早的北魏壁畫墓,壁畫分布于甬道及墓室的四壁之上,壁畫內容為墓主人夫婦、出行、宴飲、伏羲女媧等內容,其顏色使用赭石色,并在外形處,使用黑色線條進行勾勒,明確地分辨出所描繪的人物、動物、建筑等形象,繪制的方法也主要使用平涂、暈染和勾線等技巧。同樣可以看到運用此方法繪制的古墓還有大同云波里路壁畫墓葬,在畫面當中依舊使用了赭石這樣的主色調,用線條勾勒出山水及人物、動物的動勢,可見在這一區域,北齊的墓葬壁畫,其主色調是繼承了北魏時期的主色調,這也體現了該區域的藝術特點。
那么我們再把目光投放到同時期的西域。公元4—5 世紀,龜茲古國成為絲綢之路上的佛教文化中心,也是中國佛教石窟壁畫藝術的重要發展地區,龜茲處于中亞與中原的銜接處,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重要地區,“德國瓦爾德施密特(E.Waldschmidt)根據龜茲石窟壁畫色彩應用和藝術風格,將其劃分為兩種畫風:一是以紅色、黃色、淺棕色為主的暖色調,石綠色作為輔助色;二是在前一種畫風基礎上增加藍色(青金石)使用,強調色彩對比和裝飾性,并使用暈染法描繪人物”。而俄國的亞·伊·科索拉波夫將其分為三種風格:“第一種風格(5—6 世紀)的色譜基本上與希臘主義時代壁畫一樣,以暖色調為主,并加入綠色形成鮮明的對比;第二種風格(6—7 世紀)是以藍色、綠色與橙粉色(肉色)搭配組合的色彩;第三種風格是唐征服龜茲之后,壁畫受中原地區藝術影響”。可以看出,山西北齊壁畫墓與龜茲壁畫的第一種風格,在用色上非常相似。
除上述外,筆者還要列舉克孜爾石窟這一典型,根據碳十四同位素測定,克孜爾石窟可分為三個階段,宿白先生認為:“第一、二階段應是克孜爾石窟的盛期,最盛時期可能在 4 世紀后期到 5 世紀這一時期之間”。而在其早期壁畫中,整體使用的亦是暖色,多見于赭石、土紅,冷色采用石綠,在盛期藍色的使用增多,并占據主導,使畫面的色彩沖擊感更加明顯,在表現手法上,也多采用暈染,使描繪物體的顏色有明顯的變化。受中亞文化藝術影響的還有西安北周安伽墓、敦煌石窟等,“敦煌十六國北朝時期壁畫以紅色為背景的暖色調,帶有明顯的外來特征,布哈拉古城瓦爾赫沙壁畫也是以紅色地仗為背景,兩者使用色彩習俗相似”。
可以通過上述看到,在山西北齊墓葬壁畫中所使用的顏色與我國西域地區壁畫使用的顏色基本相同,在北魏時期的墓葬壁畫中使用的還是較為簡單的黑、紅色,而在東魏北齊時期壁畫當中,經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顏色的使用受到了西域影響,色彩的豐富程度遠勝于之前,在文化的表現上也趨于一致。
三、民族性的影響
草原民族,對于騎射、捕獵和戰斗都異常熟練,如北齊婁叡墓壁畫內容以游騎、出行、宴飲、神話及星象等為主,整個墓室分為墓道、甬道及內室,在內室中,設計者將壁畫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為天空星象、鬼怪異獸等,下部分為墓主夫婦宴飲圖,在墓道兩側則分為四部分,自上而下為升天圖、狩獵圖、儀衛及出行圖。在整個墓室中,所描繪的馬匹就有兩百頭,更加出彩的是,這些馬匹描繪的都非常寫實,這在中國古代早期繪畫當中是不多見的,更為驚艷的是狩獵和出行圖中,馬匹和人物之間的組合關系不是平行單一的,而是運動的,人與馬匹之間是互動的關系,這種構圖、組合關系讓筆者聯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烏切洛的繪畫《林中狩獵》,他們在描繪中運用了同樣的方式。多梅尼克在階梯醫院當中的壁畫《孤女的撫育和婚嫁》 描繪了當時醫院撫養棄兒的場景,壁畫中心描繪的是院長將孤兒交給乳母,左邊為修女給棄嬰擦洗和喂食,右側為醫院給棄嬰舉辦婚禮,從孩子的出生、撫養到長大成人的婚事,醫院全部包辦,充分顯示了教會醫院對于信仰的踐行,在一幅壁畫當中,將多個場景和故事組合,這與北齊壁畫的表現形式上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前文也已闡述,北魏繼承漢代的畫法,到北齊墓葬壁畫的發掘出現,在繪制方法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受到了中亞藝術的影響,有學者指出,我國中原墓葬壁畫的藝術風格與中亞粟特人有關,粟特人信仰拜火教,而其主要使用的色彩為紅色,除此之外,經由絲綢之路,該民族將其文化信仰帶入中土,與本地的文化進行了融合,其繪畫技法也與本土相結合,因此在色彩及方法上出現了類似于西方立體塑造的特點。
那么既然這一時代處于承上啟下的時代,我們也忽視與北朝相對的南朝,除上文提到的,在北齊壁畫墓中找到非常明顯的中原本土繪畫傳承,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明顯受南朝影響的案例。
謝赫在《畫品》中提出品評好的藝術作品有“六法”:“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跡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聞見也”。通過徐顯秀墓中的出行圖,我們來分析一下,在整個繪畫布局中,儀仗隊的中心在于傘蓋以及之下的馬匹,人物呈三階梯式分布,可簡化為梯形看待,這三個階梯是由人物組成的隊列來區分的,同時,傘蓋將畫面的中心位置突出,表明傘蓋下的馬匹非常重要,亟待主人乘騎,此外,為了將布局不經營的過于死板,畫師在創作的過程中,有意使用旗子以及大蒲扇,將上半部分分割,并使用裝飾性紋樣,將整體構圖表現出左簡又繁的畫面,因為整個畫面人物都是面向左面,在該壁畫右側的是墓主人圖像,因此將空白留于面朝部分,體現視覺上的空曠性。而整體的用色就是我們在前文提到過的,主色調為暖色,在一些裝飾上使用了綠色,而畫師很巧妙地利用“賦色”,主觀的將人物和其他事物區分開,形成一種“間奏”。
而在描繪形象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中國傳統的用線方式,通過勾勒輪廓邊緣,來體現所描繪對象的基本動作,同時也使用色塊來區分形體,由于線條基本使用黑色,在物體上描繪形狀的時候,色塊則采用了較淺的顏色。
北齊墓葬壁畫作為魏晉及隋唐之間的銜接,技藝從簡單的勾線描繪和顏色平涂到粗細變化的線條、隨形體變化“染低不染高”的凹凸法,形象的刻畫由平面轉為立體,這種成熟且受西域影響的畫法,使北齊繪畫藝術形成獨有的風格,謝稚柳先生曾經深有體會:“當年我在莫高窟對隋唐之際的畫風突變,如無源之水,看不出從何而來當婁叡墓壁畫的風規所示,開始發現隋唐之際畫風的突變,其與顧愷之的淵源將不是直接的,直接的是北齊。”可以很明顯地得出,其繪畫方法是兼容南北方以及西域流傳相結合的方法,因此,在我國眾多流傳的中原壁畫當中顯得尤為獨特,此外,雖然山西北齊墓葬壁畫受到了西域繪畫的影響,但還是繼承保留了非常多中國本土繪畫的創作技法,這種兼容并蓄的方式,正也體現了山西北齊墓葬壁畫的民族性特點。
四、結語
南北多個政權的統治,外來民族的遷徙,使多民族互相交流,中原藝術呈現多姿多彩,兼容并蓄的面貌。從北周到隋唐風格轉變過程中,除了融合南北風格以外,也經歷了復雜的取舍過程,壁畫中明顯的本土風格始終保留。“由此可知絲路沿線古墓壁畫的風格演變是多時空,多維度的”。北齊墓葬壁畫在我國藝術歷史上除了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更開創了藝術的新風格,使隋唐之后的繪畫在繼承中又得以發展。
①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乾坤:山西北朝墓葬壁畫藝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
②?王江鵬:《絲路沿線漢唐墓葬壁畫的藝術演變與中外文化交流》,《美術》2016 年第1 期。
③⑤羅世平:《北齊新畫風——參觀太原徐顯秀墓壁畫隨感》,《文物》2003 年第10 期。
④胡文英、王岳:《拉曼光譜在水泉梁北齊墓葬壁畫顏料中的研究分析》,《硅谷》2012 年17 期。
⑥⑧⑩李海磊:《4-6 世紀中國北方地區壁畫色彩技術及應用研究》,上海大學2019 年學位論文。
⑦常書鴻:《新疆石窟藝術》,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年版,第43 頁。
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文物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 頁。
?(南齊)謝赫、姚最,王伯敏標點注譯:《古畫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 年版,第1 頁。
?謝稚柳:《鑒余雜稿》,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