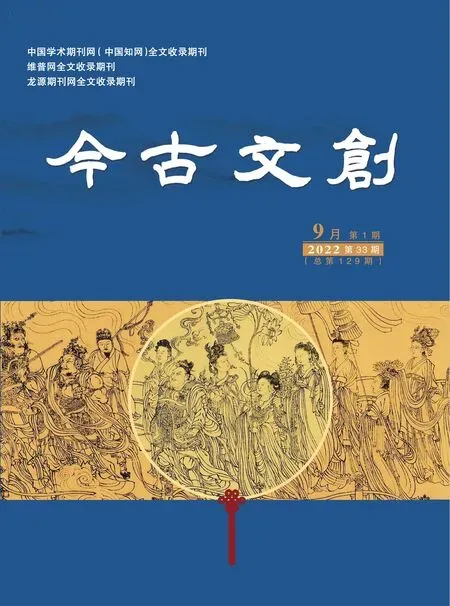清代寧夏籍名將俞益謨研究綜述
◎賀靖懿
(北方民族大學民族學學院 寧夏 銀川 750000)
俞益謨(1653-1713),字嘉言,號澹庵,別號青銅。祖籍明代北直隸河間府,因曾祖父參軍,遷居寧夏西路中衛廣武營,遂入籍寧夏。康熙十一年(1672)中武科解元,康熙十二年(1673)中武進士。俞益謨曾歷任大同總兵,湖廣提督等職,著有《青銅自考》 《辦苗紀略》,并與高嶷編著有(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俞益謨在清初有很大影響,文獻評價其為:“一代名將,千古文人。”
一、俞益謨家世與生平研究
俞益謨作為寧夏地方名人,清代許多地方文獻中都收錄有其小傳。如,(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上卷《鄉獻志》記載:“俞益謨,字嘉言,號澹庵,別號青銅。君輔子,有文武才。以進士隨征……才兼文武,堪應總督之任。生平不蓄私囊,所得俸金,隨在整軍裝,犒士卒,建衙署,修教場,崇整文武圣廟,更以所余,瞻顧鄰里鄉黨,浚渠設塾,在在有記。歷任具有祠祀。性好讀書,政事之余,手不釋卷,著有《青銅自考》 《道統歸宗》 《辦苗紀略》等書行世。”而(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上卷《武階志》則記載:“俞益謨,由武解元進士,初任柳樹澗守備,歷升達州游擊,郁林參將,兩江督標中軍副將,大同掛印總兵官。提督湖廣全省軍務,統轄漢、土官兵兼軍衛土司,控制苗彝,節制各鎮總兵官,左都督加六級。事功見《鄉獻》。門人馬見伯等紀實編次,梓有《青銅君傳》。”(乾隆)《寧夏府志》中也列有俞益謨小傳,記載了俞益謨前往湖廣處理苗族事務,“奉命辦理,恩威并施,苗悉就撫。在任多所建白,皆合戎政機宜”,以及他“談兵料敵,言無不應”的事跡。此外(乾隆)《中衛縣志》和(民國)《朔方道志》中也收錄有俞益謨小傳,內容與(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和(乾隆)《寧夏府志》記載基本一致。另外,(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中還收錄有編修俞長策所撰俞益謨《墓志銘》一文,文章論述其一生作為,并肯定了俞益謨的功德事業。但(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在收錄《墓志銘》時有缺失,(民國)《朔方道志》中錄文更為完整。
俞益謨本人文武兼才,官至湖廣提督,當代學者對其生平及家族的研究已有較多成果,胡迅雷《寧夏歷史人物研究文集》中《清代廣武俞氏家族》《清代名將俞益謨》兩篇文章,都是以俞氏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曾文俊《俞益謨生平事略》,按照時間順序對俞益謨的為官經歷進行了論述。田富軍《清代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生平考》則以俞益謨本人著作為參考,對其一生的經歷進行梳理和考述。楊學娟、田富軍《清代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家世考》一文,對俞益謨的家族關系進行了研究,不僅梳理考證了其祖上以及子侄的關系網絡,還用大量篇幅介紹了其子俞汝欽、其侄俞汝翼的著作情況。付保珂《清秦慈君墓志考略》一文,對出土的秦慈君墓志石碑進行了考證。此碑主人秦氏是俞益謨的副室,其墓志也是由二人之子俞汝亮所撰。田富軍博士論文《寧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中也有專門的章節對俞氏進行介紹,包含其生平、主要著述、詩文創作及其他族人的著述等方面的內容。
俞益謨也常進行詩文創作,一生共有131首詩流傳于世。(乾隆)《寧夏府志》記載:“少英敏,即為官,益務折節讀書,雅近文士。能詩文,軍中每手草露布,詞理可觀。”這些詩文可以說是俞益謨內心世界的表露與抒發,因此也有學者對其思想進行研究。田富軍、葉根華《試罷吳鉤學詠詩——代清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詩詞的思想內容探析》一文,對俞氏所作詩文進行分類,并從中選取典型詩文進行詳細剖析。王茜子《清代寧夏詩人研究》中以俞益謨家族為例,探究了寧夏本土詩人詩文創作的成就和價值。而《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散文創作簡論》是對俞益謨所作散文進行的整體研究。
俞益謨休致回鄉后,致力于發展家鄉教育事業,“常購書貯學宮,資后進講讀。”且慷慨出資加蓋校舍,“廣武堡社學……學舍十間,學田四十二畝”,皆為俞益謨所置。因此俞益謨的教育思想,也引起了學界關注。彭新媛《清代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教育思想探析》即是對俞益謨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他對待軍事教育的態度進行了探究。文中總結出其教育思想的三個特點并分別考述,肯定了他的教育觀點。
二、俞益謨著述整理與研究
俞益謨有多部著作,如今傳世的主要是(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青銅自考》及《辦苗紀略》三部。近年來學術界對其著述的整理與研究有較多成果發表。
(一)(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
此書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俞益謨和高嶷共同編撰完成的地方志書。上卷38目,下卷28目,共三萬字,不僅詳細記載了廣武地區的地理風貌與屯田戍守情況,且用大量篇幅記載了俞氏家族的“文武功德”,是研究俞益謨及其家族的重要參考資料。因此,許多學者都對(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進行了專題研究。馬力《〈朔方廣武志〉與俞益謨其人》一文,首先介紹了“廣武營”的歷史沿革及其重要的防御地位,之后對此書的內容、修志緣由、編修始末以及參修人員等進行了簡單的介紹,最后肯定了其突出的類目特色。吳曉紅《康熙〈朔方廣武志〉考》一文也對(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進行了專門的研究。高樹榆《寧夏方志錄》和《寧夏方志評述》兩篇文章,則對其進行了提要式介紹。胡玉冰在整理出版(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的前言中,也對此書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不僅對整理與研究現狀進行了評述,還細致的考訂了此志編修的其他人員。
(二)《青銅自考》
此書是俞益謨根據自己的別號進行命名的作品集合,收錄了俞益謨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間的大部分作品。全書分為12卷,914篇,內容涉及題奏條議、恣呈移會、檄行文告、啟集、尺牘、傳記引、序祝祭文和詩詞對聯等八個類型,是考證其生平的直接材料。《青銅自考》現有四種版本傳世,但內容不盡相似,因此有學者專門對此書的版本和內容進行了考訂研究。
田富軍是最早對《青銅自考》進行點校出版的學者,《清代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青銅自考〉版本論略——兼論臺灣抄本的價值》就是對《青銅自考》各種版本的集中考述。作者在文中詳細分析和對比了四種版本的異同,并總結出各個版本的優缺點。《清代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青銅自考〉卷十一校勘札記》一文,是將《青銅自考》抄本和刻本內容進行比較,并以康熙四十六年刻本的第十一卷作為底本進行校勘,考辨兩種版本中出現的異誤。
(三)《辦苗紀略》
《辦苗紀略》也是俞益謨本人所著,涉及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間,有關俞益謨在湖南境內處理苗族事務的相關記載,不僅詳細直觀地記錄了這次事件的始末,在許多擬定發行的條約和規定中,也可以看出俞益謨杰出的軍事領導才能。另外,此書中還有許多康熙的批語,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現有研究成果中,《清代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著述考》一文以俞益謨的存世著述作為主要的考證對象,集中梳理了《青銅自考》《辦苗紀略》 《振武將軍陜甘提督孫公思克行述》三部文獻。另外,作者在文中也對俞氏一些單篇作品的收錄情況進行了詳細討論。
(四)其他作品
除俞益謨本人作品外,傳世文獻還收錄有他人為俞益謨所做的傳記,即《青銅君傳》。關于《青銅君傳》的內容,(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武階志》中記載:“門人馬見伯等紀實編次。”事實上,該文先由其好友黎宗周記載其生平事跡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由王基進行續寫完成此傳,最后由俞禮和張禎等刊刻成書。《青銅君傳》僅留存孤本,藏于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內,是了解俞益謨生平的重要資料。田富軍《康熙年間孤本〈青銅君傳〉考述》一文,就詳細考訂了成書過程和主要經歷的三個階段,并考述其版本情況,指出《青銅君傳》有著較高的版本和文獻價值。
此外,各地方志也有關于俞益謨事跡的記載。如,高平《道光本〈大同縣志〉康熙帝巡幸篇糾誤》中指出《大同縣志》“康熙帝巡幸篇”中的幾處舛誤,考證了康熙欽賜俞益謨“焜耀虎符”牌匾是在康熙四十一年巡幸五臺山時,而不是康熙三十五年巡幸大同期間。
三、對俞益謨研究的思考與展望
目前,學界對于俞益謨的研究,成果豐富,基本上涉及了俞益謨本人的大部分信息,比如生平、家世、著作、文學成就以及休致后的回鄉生活等。但是,作為寧夏籍名人,筆者認為還可以深入開展研究。
第一,關于俞益謨的家世研究,雖然已有楊學娟、田富軍的《清代寧夏籍湖廣提督俞益謨家世考》,但該文研究還是僅限于俞益謨的直系親屬范圍,對于其他的一些親戚,像親家、岳父等等這種姻親關系基本沒有涉及,甚至背后涉及的家族交往、利益聯系也很少有人關注。(康熙)《新修朔方廣武志》中記載:“始祖伏四……居咸寧。越五世,曾祖諱大河贈君,遨游西夏……生祖諱天義贈君,積善慶余,生子三:仲諱君佐公,早殤;季諱君宰公……伯即榮祿大夫封考也,諱君輔……原配趙氏大君……生一子,諱益謨……”這是對俞益謨祖上關系的記載,且志書中也有關于其本人及子侄關系的記載。如,“張氏夫人,俞都督妻,汝欽之母。”俞益謨與側室秦氏有子俞汝亮,秦氏的父親為秦應晨,母親為鄭氏。此外,俞皋謨與妻陳氏有子俞汝翼,即俞益謨侄子。而關于俞益謨的兩個兒子所娶妻子,盡管目前還沒有搜集到有確切記載的資料。但《青銅自考》序祝祭文集中有一篇《祭永寧參將邦達王親家》,是俞益謨寫給親家王邦達的祭文。文中稱:“快友道之弗替,遂聊姻之新訂。”由此可證二人結為親家之實,但具體是俞氏哪個兒子娶王家之女,文中未有提及。此外,《青銅自考》中還收錄有俞益謨母親過世時,他因無法回鄉奔喪而寫給妹夫和姐夫的尺牘,即《致黃欽錫妹丈》和《致賀劉二姐丈》,這兩篇文章可作為考證其郎舅關系的依據,但由于文章內容較短,能提供的信息有限,所以需要在今后進一步搜集相關文獻進行研究。
第二,俞益謨在朝任職多年,與官場許多同僚均有往來,研究其交游情況,也是人物研究的重要環節。首先,俞益謨與寧夏鎮臺葉蘭亭關系很好,《青銅自考》中收錄了許多其寫給葉蘭亭的詩文,多是朋友間交流近況,但也有特定類型的文章。如,祝壽類《壽蘭亭葉年兄》、送別類《壽蘭亭葉年兄兼送之任全州》、祭文《祭寧夏鎮臺葉年兄文》等。此外,逢年過節時,二人也會互相寫信祝福。其次,俞益謨在湖南境內處理苗族事務期間,與欽差席而達、湖廣總督喻成龍以及湖南巡撫趙申喬等人共事良久,之后也有不少書信往來,迎賀類如《致湖廣喻制軍》《致偏沅趙撫軍》,祝壽類也有《祝湖廣喻制軍》《祝偏沅趙撫軍》等多篇,皆收錄在《青銅自考》中。最后,志書中評價俞益謨:“其談兵料敵勝負,言無不應。一時趙勇略,王奮威諸宿將并稱其智能。”而俞氏本人除在入川進剿吳三桂時與勇略將軍趙良棟有來往,其私下也有較多往來,并有俞益謨為趙良棟祝壽文《祝勇略趙將軍》和悼文《祭勇略趙將軍文》傳世。且趙良棟的孫子趙之增,“聘寧夏鎮葉公女”,也就是俞益謨的好友葉蘭亭。俞益謨所作《振武將軍陜甘提督孫公思克行述》一文,是俞益謨在與孫思克相處的過程中,感嘆其品格高尚,因此記述其事跡與品德以表對振武將軍的敬仰。此后俞氏還寫了《祭振武孫將軍文》,表達其哀思之情。田富軍在《清代寧夏籍湖廣總督俞益謨生平考》中提到俞益謨與當時很多著名文人、達官顯貴都有詩文交往,比如韓菼、禮部尚書查升以及刑部尚書吳嗛等。通過俞益謨對待朋友的態度,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他的人品和性格,此方面研究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第三,俞益謨是一代武將,重視帶兵操練。在擔任大同總兵和湖廣提督期間,提出了許多整飭軍隊的措施。《青銅自考》中許多作品都是俞益謨基于軍隊整改意見的上奏,如《省馬增步》是俞益謨認為軍中馬多兵少,馬匹無人顧養以致疲累,因此請求裁馬不裁兵,調整軍營構成。《提補標營將備》是俞益謨向上舉薦可用之才。《請改舉劾》則是俞益謨提議將對武臣的舉薦從兩年一次改為兩年半,這些意見都得到了康熙的賞識。俞益謨曾與趙良棟一起進剿吳三桂,在湖南處理苗族事務,以他的軍事思想為主題進行考述,不僅可以全面了解其軍事謀略,對于研究清代時期軍隊的設置與給養、訓練等都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