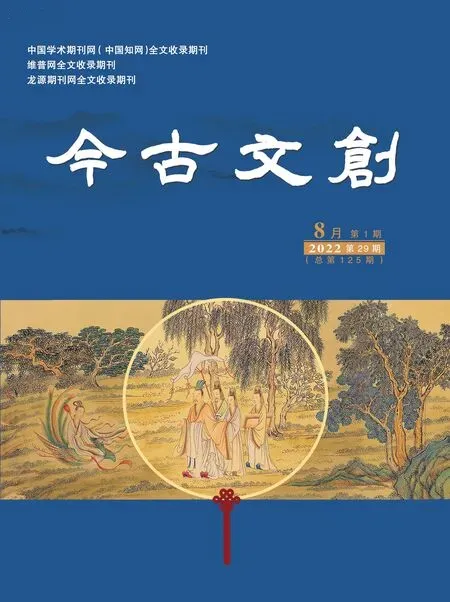青年黑格爾實證性思想的研究
——基于《青年黑格爾》的文本解讀
◎張 彤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盧卡奇的《青年黑格爾》于1948年得以問世,這本書凝結了盧卡奇對哲學史和當時的哲學現狀的研究成果。在導論中,盧卡奇曾指出了德國古典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重要性:“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德國古典哲學的起源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但尚未解決的難題。”他認為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但在其逝世后,黑格爾學說的學術價值被忽視,他和他的辯證法被叔本華和一些新康德主義者貶低為“一條死狗”。即使之后黑格爾的理論在部分新康德主義者和新黑格爾主義者的著作中有一定程度上的復興,盧卡奇認為這種復興也是走錯了方向的,具體表現為對黑格爾學術地位的貶低和對其辯證法進行非理性化和神秘化的歪曲。前者表現為“把德國古典哲學的整個發展歸結到康德的水平上”,后者則在狄爾泰對青年黑格爾理論的論述中有所體現。
盧卡奇認為上述貶低之由均源于他們對黑格爾辯證法中經濟思想的忽視,以至于更看不清經濟思想與辯證法之間的關系。本書分為四個部分,其中關于實證性的概念貫穿其中,能看出盧卡奇對早期黑格爾的思想中的辯證法的成分的追溯和研究,在研究中也堅守了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宗教觀。此書中盧卡奇將青年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的發展歷程和觀念分為了兩個時期:“實證性”時期和“外化”時期,“實證性”時期是“外化”時期的雛形,因此對黑格爾的實證性問題的探究是建立黑格爾完整的思想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展現了黑格爾對其認識的不斷加深的歷程。
一、黑格爾對“實證性”概念的首次提出
盧卡奇在此書中將黑格爾的思想發展史分為四個階段:伯爾尼階段(1793-1796)、法蘭克福時期(1797-1800)、耶拿第一時期(1801-1803)和耶拿第二時期(1803-1807)。第一部分盧卡奇論證的是伯爾尼時期的黑格爾。
盧卡奇指出黑格爾在這一時期經常使用“實證性”這一概念。究其含義,黑格爾給出的答案是:“主體的道德自律的中止”即人受制于外在的、強制的信仰而喪失了自身的自由和尊嚴,這種信仰成為與主體相對立的客觀的、不容違背的精神。他指出:“宗教的問題是黑格爾在伯爾尼時期所闡述的中心問題、特別是基督教的‘實證性’……對于青年黑格爾,實證的基督教支撐著專制和壓迫的進行,而非實證的古代宗教則是自由與人類尊嚴的宗教。”黑格爾的思想發展受到了德國落后的政治環境的制約,黑格爾在圖賓根神學院主修神學和哲學,于是也對宗教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作為具有政治抱負的左翼民主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想要“他想要創造一種社會條件,在這種條件下,專制和奴役的宗教可以重新為古代范型的自由宗教所代替。”這一時期的黑格爾將恢復古代宗教視為自己的任務之一。
盧卡奇認為黑格爾主要在對宗教的分析中使用“實證性”這一概念,企圖以人道主義的方式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黑格爾曾說過:“一種實證的信仰,是這一系列的宗教命題,它們所以對我們來說是真理,乃因為它們是被當做戒律由一種吩咐給我們了,而我們又不能不使我們的信仰聽從于這種權威。這個概念,首先表示這樣一系列的命題或真理,這些東西的真假不被我們左右,總得視之為真理,它們即使從來沒被人認識過,即使從來沒有人承認它們是真的,也仍然是真理,而且,它們雖然時常被稱為客觀真理,現在也必須是為我們的真理,主觀真理。”盧卡奇認為這個定義實際上說明了黑格爾意義上的實證性指的是首先人作為主體,卻失去了自身的尊嚴、意志自由和獨立的思考能力,尋找獨立于人之外的信仰所依托存在,而這種信仰是作為一種客觀的、必須予以遵循的精神力量與主體相對立。黑格爾認為當時的德國社會的毒瘤源于基督教,基督教對人的統治方式是以恐嚇加權威的姿態呈現在教徒面前的,它利用信徒的悔罪感對其進行統治,在這種悔罪感的影響下,信徒的內心變得灰暗,變成了病態的人。在此基礎上黑格爾闡述了實證性在宗教中的意義。實證性在基督教中表現為外在的客觀的宗教教義對人進行壓迫,信徒只能無條件的服從。作為一種外在的、與人的主體相對立的實證性的宗教,它不允許人們不相信它,同時也不允許人們自由地相信它,就這樣宗教成為異己的力量扼殺了人的理性。黑格爾認為在實證性的宗教統治下人沒有實現自由的可能,所以他比同時代的任何哲學家們都更想清除近代基督教對人們的統治。
盧卡奇認為青年黑格爾認為道德律的這種外來的“被給予的”性質乃是實證性的最重要的標志。他說由道德主體本身來制定道德規律乃是實證性的最重要的標志。他說,由道德主體本身來制定道德規律,乃是任何道德規律的本質;“基督教教義宣稱,道德規律是外在于我們的,被給予的東西,所以它必須努力通過外來的途徑使人尊重這個規律。實證性的宗教的道德律是外在的強加于人的律法”。從黑格爾關于宗教實證性概念的論述中可以明晰地看出青年黑格爾已經在自覺地思考辯證法問題之前就有了辯證法意識的萌芽。
盧卡奇對黑格爾的實證性觀點的評價很高,認為其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表述有三。首先他贊揚了黑格爾實證性概念的歷史性,表現在其將實證性概念與宗教相結合,使實證性概念獲得了豐富的歷史感。其次盧卡奇指出:“實證性決不是某種從外部引入到人類歷史中的去的東西”,表明了他對黑格爾的實證性觀點加以肯定,并認為這是現代社會發展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最后盧卡奇認為黑格爾實證性概念是對唯物主義思想的肯定:“從對早年黑格爾如此關鍵的實證性概念中可以看出唯物主義的優先性”。
但其作為黑格爾早期的理論觀點,不免也有一定的缺陷。盧卡奇認為在黑格爾的表述中,實證性概念是一個自明的概念,所以并沒有對其加以闡述,也導致了其概念的模糊性。通過分析他對戰爭、政治權力等方面的描述也可以發現他是立足于從社會現實本身去闡述近代宗教的實證性起源的,只是當時他還沒有對經濟生活進行系統的分析,也是其實證性概念模糊的根源所在。
二、在對市民社會的分析中尋求克服實證性的道路
盧卡奇繼而對法蘭克福時期的黑格爾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黑格爾放棄了對實證性概念的思考,盧卡奇甚至認為實證性問題仍是黑格爾這一時期的核心問題。他寫道:“‘實證性‘這個老問題作為一個中心問題在這里重新出現了,但比起伯爾尼時期來,它被賦予更復雜、更矛盾和更富于歷史感的處理。這個問題現在引導黑格爾更深入地去研究活躍在市民社會中的主導力量:它導致了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可以說黑格爾經歷了從伯爾尼時期側重于研究法國革命到法蘭克福時期側重于研究經濟問題,尤其是針對英國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研究。
盧卡奇認為這時黑格爾的學生對其政治經濟學與辯證法的關系的認識不甚深入,甚至連黑格爾自認為最理解自己的羅森克朗茨也沒有重視到二者的關聯。由于黑格爾的親傳弟子對經濟問題并不重視,導致了其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理論的一手資料大多失傳。據羅深克朗茨的記載,黑格爾在這一時期主要是對英國的經濟問題感興趣,同時熱衷于對經濟理論進行研究,其中斯圖亞特的經濟理論和亞當·斯密的勞動理論引起了黑格爾的高度重視。
盧卡奇指出這時的黑格爾雖然仍將實證性問題置于問題中心,但他對其的考察基點已經發生轉變:在伯爾尼階段黑格爾是從對近代宗教的分析批判中對其進行闡述,而在法蘭克福時期的黑格爾將對實證性問題的研究范圍擴大即開始思考如何克服這種實證性。他從市民社會出發,著手于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關系。盧卡奇認為黑格爾在對市民社會的剖析中建立了總體性的視野:“我們不應忘記,黑格爾的思想在法蘭克福時期不管走得多么遠,他始終從總體上來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并把這一社會理解為一個過程。”這種總體性視野的確立包含了對抽象的實證性的揚棄,為青年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增添了更豐富的歷史現實感。
黑格爾此時的宗教觀主要是在批判近代基督教,當時基督教是社會的主流,黑格爾的批判也有著較大的影響。但他對基督教的批評逐漸趨于緩和,更多的是以歷史的發展眼光來看待基督教,實際上這一時期的黑格爾的宗教理念在內涵上是與近代基督教相似的。但他此時并未放棄實證性問題,而是對其重新加以認識。
這一時刻的黑格爾認為任何的宗教的存在均具有真理性,它們是按照人們的根據現實的想象力被構建起來的。盧卡奇曾在文中指出“青年黑格爾把實證性這一概念……放置到中心地位上,他實際上已經向著他后來的辯證歷史觀走了不自覺的第一步。”
三、對實證性概念的創新發展
在對黑格爾的耶拿第一時期的理論思想的分析中,盧卡奇認為這一時期蘊含著盧卡奇與謝林的浪漫主義分道揚鑣的趨勢,對現實的把握促使黑格爾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更加深入,在這一時期寫成了《倫理體系》和《實在哲學》,這其中包含了黑格爾對勞動問題的探討。盧卡奇認為黑格爾對亞當·斯密的不少理論都實現了超越。
黑格爾看到了勞動分工所擁有的利弊。首先,勞動分工對提高勞動效率有極大的幫助,進而推動了社會財富的增加。同時黑格爾還指出了勞動分工帶來的弊端:“勞動的價值與勞動生產率呈反比關系。勞動慢慢地變得沒有活力,同時機器使工人的自身技能水平受到制約,也導致了工人的意識也處于非常鈍化的水平。”對工人勞動的產物后與工人自身相對立的闡述是黑格爾在對市民社會的分析中對實證性的折返,在隨后的分析中他也發現了實證性概念不明的問題,于是他對其加以總結深化并以新的概念取而代之即異化概念,表現了實證性概念在黑格爾的思想根源中的重要地位。
這一時期的黑格爾克服了對實證性靜止性的解釋,找到了“從人本學走向歷史主義”的道路,處在實證性時期的黑格爾更傾向于二元論模式,法蘭克福時期的黑格爾已經開始試圖擺脫絕對否定,開始對傳統的二元論哲學中辯證的、歷史的方法進行突破建立一種更為歷史性的具體性的辯證法。
四、對“實證性”概念的超越即異化理論的提出
耶拿第二時期的黑格爾繼續向前,徹底完成了對實證性概念的超越即異化理論提出。盧卡奇說:“在理解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時,最重要之點是,辯證法的現象不是一般的生活的一種功能,而是社會和個人生活的資本主義的‘外化‘和異化的產物,也就是說,自我意識只能達到自己,并只能把自己看作這一異化中的客觀實在的一個部分。”這體現了異化概念在這一時期已成為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概念。
為了更深入地說明“外化”概念是對“實證性”概念的升級,盧卡奇追溯到了外化概念的語義學源頭。盧卡奇認為“alienation”在社會契約論中翻譯為“原始自由的喪失”,異化和外化也都是英語的 “貨物出售(alienation)”的德文翻譯。費希特眼中的外化指的是“主體的外化表現為客體的建立”。可以看出盧卡奇的外化概念在德語語境下與異化有共同的語義基礎,在他看來異化和外化本就是同源詞。
此時的盧卡奇并沒有對異化和外在化進行嚴格的區分,認為均可翻譯為英語的alienation(異化)一詞。按照盧卡奇對異化的劃分,黑格爾的異化理論主要富有三層含義。第一,異化涉及復雜的主客體關系,包括勞動和其他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等。黑格爾對主客體關系的辯證論述是對舊唯物主義的拋棄主觀性空談客觀性的克服。第二,這里的異化主要指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對物的無限崇拜的現象。黑格爾的異化觀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到的“拜物教”概念有相似的含義。但二人對此理解的角度不同,馬克思主要是從階級對立方面進行分析,黑格爾主要是從人本主義方面對其進行分析。第三,黑格爾的異化概念指的是自然和社會都是人類精神的異化的產物,對自然的歷史性的否定體現了其辯證法的不徹底性。
盧卡奇認為實證性是與主體相對立的,具有僵死的和絕對的客體性,而與這種客體性相對應的是與古代社會相對立的一種實證性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基督教精神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而“外化”階段時期的黑格爾對實證性的理解更加深入和辯證,這一時期的黑格爾更加辯證,更加關注現代社會的具體的歷史性,從非此即彼的對立中走向了更具體的、更具有歷史性的揚棄模式,致力于達到主客體之間的真正統一,一直到1805年—1806年在講稿中“外化”概念被替代,即“外化”階段是對“實證性”階段的升級。實證性概念的非此即彼性在向外化時期的過渡中逐漸被揚棄,實證性概念在法蘭克福時期之后就天然地包含了外化的含義即“在人的社會實踐里,原始的直接的東西、天然的東西被克服掉并且必然被克服掉,而在這個過程中由人的實踐通過他自己的勞動創造的一系列產品所替代;而這總勞動不僅創造這些社會客體,并且也創造人的主體,因為它也揚棄主體里原始的直接的東西,從而主體就異化了自己”從上述論述可以發現這種實證性的概念是通過勞動作為中介的對象化過程而向異化狀態機進行轉變的。在這個過程中“外化”“勞動”“對象化”等概念逐漸組成了與辯證法相關的概念群即“在這個過程中,外化和異化就逐漸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占據主要位置。
綜上,盧卡奇在《青年黑格爾》中糾正了對黑格爾的研究的偏離問題,這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復興和其自身哲學素養的提高有著較大的作用。但由于其對勞動和異化的研究不夠深入,導致了他對異化的概念、根源的“自明性”的肯定,對異化和對象化之間的界限的模糊不清等問題均有出現。但其對黑格爾和馬克思均將經濟思想與哲學相聯系的思路的學習促使盧卡奇形成了其理論研究的基本態度,成了其批判理論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