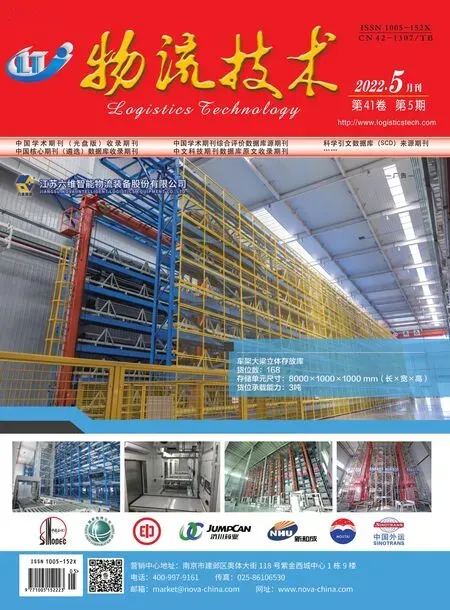秦代主要“物流”成就及其影響概述
湖北物資流通技術研究所 艾 振
武漢紡織大學 周興建
前四期里,我們就先秦時期有關倉儲和運輸的部分內容做了簡要介紹。這一期我們將從“物流”的視角重新了解一次秦代,講述這個朝代的先輩們與“物流”的淵源,總結他們在各個歷史時期運輸措施、倉儲戰略的部署和成就,并反思其對國家發展的影響。
1 因交通起家的秦代先輩
史料中,關于秦建國之前一千多年的記載多與交通運輸有關。
舜帝時期,在表彰大禹治水之功時,大禹回答:“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大費因此受到舜帝的嘉獎—娶了舜帝給他挑選的妻子,并開始輔佐舜帝畜牧。
夏末時期,大費的五世孫費昌,因不愿跟隨夏桀而“去夏歸商,為湯御”,隨后以商湯專職駕駛員的身份協助商湯在鳴條打敗夏桀,
商朝時期,大費的另兩個五世孫孟戲和中衍駕駛技術出眾,商王太戊“聞而卜之使御”。此后,中衍的子孫們也世世代代為商王駕車,為此很多嬴姓人逐漸身居顯位——“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
商朝末年,中衍的五世孫蜚廉和他的兒子惡來,因“善走”,“俱以材力事殷紂”,算是
進入西周,蜚廉的另一個兒子季勝有一個著名的曾孫名叫造父,長于識馬用馬,精通駕駛,因此“幸于周繆王”。他曾為繆王駕車西游三萬里;在徐偃王作亂時,又“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為表彰造父
惡來的后代也因造父受寵而得趙氏。他的一個五世孫叫做非子,善于養馬。因此“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閑,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翳(大費)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而恢復嬴族祭祀則意味著嬴族一姓十四氏及更多的平民從此有了共同的領袖,。
要知道,先秦時期車和馬都是最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大到禮儀、戰爭,小到日常生活,可以“載重致遠”的車、馬承擔著人員和物資轉移的重任,幾乎意味著整個陸上交通。它們的發展水平甚至直接影響或代表著國家形象和實力,其地位遠非現世可比。而秦之所以贏得自己的姓氏、封號和各種榮譽,之所以能逐步壯大并統一全族,無不因他們的先輩們在養馬或者駕駛領域的突出貢獻。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
2 從“物流”角度看秦國的崛起與統一
2.1 武裝押運的超級回報
非子得秦地后,秦人一直在與西戎的糾葛中慘淡經營,終于在秦襄公時迎來一次翻身的機會。公元前771年,慣用“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城破被殺。幾經波折之后,周平王掌權。面對戰后破敗的鎬京和西戎的襲擾,平王決定遷都洛陽。政治嗅覺敏銳、在周朝救亂中表現積極的秦襄公得知消息后立即響應,“。偌大一個國都長途遷徙了。大宗伯抱著周朝的七廟神主乘車在前,平王御駕隨后,各類物資綿延不斷,車隊一眼無邊;數不清的百姓攜老扶幼,帶著自己的家當車拉肩扛的跟在其中…。公元前770年,立穩腳跟后的平王論功行賞:“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秦襄公成為了諸侯,秦國也在襄公手上正式建國!順帶著,秦國還被賦予了奪取岐山的正當理由,為秦國日后的崛起奠定了物質基礎。秦國在這次“武裝押運”活動中,獲得的回報“不可計矣”。
周王室的東遷讓秦國獲得了更大的戰略發展空間,但秦國并不滿足于此,他們需要考慮如何向中原的政治中心進一步靠攏。所以,處理與擋在東邊的強鄰晉國的關系成了長久以來秦的政治大事。好在在和親等政策達不到預期的情況下,機會一再垂青著秦國。
晉公元前650年,晉獻公死后,他流亡在梁國的三兒子夷吾承諾以河西八城作為酬謝,請求秦穆公送其回國繼位。秦穆公欣喜的命重臣百里奚率隊,全副武裝、小心翼翼的把夷吾從秦都雍城護送回晉國當上了晉惠公,秦國再次當上了大國之君歸國繼位的護送者。
歷史繼續往前。晉惠公的繼任者晉懷公不得人心,晉國決定迎立晉獻公的二兒子重耳回國。在外顛沛流離十幾年,歷盡人間冷暖的重耳出于各種原因同樣選擇了求助秦穆公。公元前636年,秦穆公一次性將自己的五個同宗女子嫁給重耳,又派公孫枝率領三千人護送重耳渡過黃河,讓他帶著秦穆公的無限“恩惠”回國當上了晉文公。就此,秦穆公坐穩了晉國第一救星的交椅。與政治聯姻相比,秦國從更高層次上涉足了晉國政治的同時,也通過晉國把影響力滲透到了中原大地。
其實,在那個動蕩的時代,各國互換質子盛行,類似的武裝押運事件在秦國還有很多,在其它各國也時有發生。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哪個史學家把它們作為軍事行動來看待為此,我們不禁可以思考:秦國派出的那些不以戰斗為目的,只為保護受托目標安全送達,從而獲取高額回報的武裝隊伍,算不算現代服務于金融等機構的那種押運業務,和前朝那種武裝送貨軍——鏢局的前身?
不管怎樣,秦國抓住難得的幾次機會,用長途護送這種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提升了自己的地位,穩固了與鄰國的關系,并向諸侯匯集的東方嘗試著邁出第一步。
2.2 秦國的通道建設
我們先用一個案例來說明掌握運輸通道對秦國的重要性。
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戰國策·燕策二》
秦國正告楚國:秦國占住水運通道,就可以輕松出兵到你城下,即便你人才再多,也來不及反應,就問你服不服?!楚國深以為然,因此屈服于秦國十七年。同樣的,秦國以切斷運輸通道、占領關鍵運輸節點為要挾,讓韓、魏國等國被迫“事秦”。
東向主要有崤函通道、晉南豫北通道及商洛、南陽通道三條;南向主要有金牛道、褒斜道等棧道。
,鎬京(今西安)和洛邑(今洛陽)之間的一條古老道路,全長400里。西連關中平原,東接中原大地;南北是高聳的秦嶺和山西高原。最窄處“車不并轅,馬不并列”,僅容一人通過;兩側高崖陡峭,其中有十五里,“絕岸壁立,崖上柏林蔭谷中,殆不見天日”,險要至極。“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函谷關、潼關,黃河沿岸的風陵渡、太陽渡和茅津渡等重要渡口都分布其中。崤函通道在東周初期即被晉國占據,但它又是秦國東出的必經之路。為此,這條通道成為長久以來秦晉關系的核心。為了打通這條通道,秦國不惜與晉國及后來的魏國戰斗了300多年,直到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打進洛陽后秦國才實現了對它的完全掌控。
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兵者,以此故也。—清·顧棟高
憑借此道,秦國不但實現了東出中原的夢想,還有效防止了它國入侵。事實上,單是通道上的那個函谷關,六國就拿它沒有任何辦法。
于是六國之士…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賈誼《過秦論》
西起陜晉邊界的臨晉(今陜西大荔),蜿蜒向東北,到達邯鄲所在的冀南平原,連通了秦國和趙國。它依群山、傍黃河,占據著天然之險,又在緊要處建有臨晉關,秦國掌控此道之后,諸侯各國無一次敢通過此道攻秦。
起于咸陽,向東南穿秦嶺、過武關進入南陽,最后延伸到楚郢都所在的江漢平原,是秦、楚之間的核心通道。通道上的武關與函谷關一樣險要,素有“關中鎖鑰”、“三秦要塞”、“秦楚咽喉”之稱。更是被清朝的顧祖禹評價道:“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而輕重分焉。”公元前505年,秦哀公助楚昭王復國之后,拿到了楚國贈送的六百里商於之地,武關道也隨之歸秦所有,楚國此后數次想要討回未果。通過此道,秦國多次重創強楚。它一面見證了秦國的崛起,一面目睹了楚國的衰亡。
,又稱石牛道,是最早見于史書的古蜀道之一。秦惠王伐蜀時,為了打通通往巴蜀的道路,以運送“夜能糞金”的石牛給蜀王為由,騙蜀王遣五丁力士在大、小劍山、五丁峽一帶峭壁處,日夜劈山破石,鑿險開路打通了1 200里的懸崖棧道。隨即,惠王沿此路滅蜀。對秦國而言,它戰略價值極高:此道一開,“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
,又稱“斜谷路”。古時巴蜀通秦川的主干道路,重修于秦昭襄王時期。它在懸崖絕壁之間穴山為孔,插木為梁,鋪設木板以聯為棧閣,讓原本極其難走的小道成為可通過軍隊和輜重的驛道。南起褒谷口(漢中市大鐘寺附近),北至斜谷口(眉縣斜峪關口),蜿蜒穿越秦嶺之間,穿褒、斜二谷,全長500 里。《史記》里評道:“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
秦國攻下巴蜀的一個原因在于:拿下巴蜀就等于控制了長江航道的上游。這樣就形成了對下游楚國的戰略威懾,降低擊敗楚國、進而統一天下的難度。
(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華陽國志·月志》
于是才有了“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之類的諸多勝利。
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任水利專家李冰為蜀守,歷時14年,耗費無數人力、物力在岷江上筑建了世界水利史上集防洪、灌溉、運輸于一體的驚世之作—都江堰。自此之后,岷江改道成都,進出巴蜀的水路暢通,上游汶山的木材可順江而下,運往成都,并在這里直接打造成船,裝載運輸。岷江之上,飄滿了運載輜重的船舶。成都也成為秦國真正的集散中心。制約秦軍兵馬、糧草補給效率的重大短板得到了很好的彌補。
例如,公元前289年他們一口氣打下了黃河沿線包括魏國軹邑(今河南省濟源縣)在內的62座城,只為保護黃河水道的運輸安全。
這個“四塞之國”不但在秦穆公時貢獻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水陸聯運壯舉—“泛舟之役”,我國見于史載的首座黃河浮橋竟也由秦國建設。
這些陸上和水上通道一起,織就了秦國擴張的供給網絡。
2.3 大國的倉儲戰略
儲糧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無需多言,有著宏大志向的秦國統治者們當然更加明白。
。公元前659年,出使秦國的西戎人由余感嘆秦國的倉儲:“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站在由余的角度,秦國的儲蓄之多無異于勞民傷財—即使鬼神來做,也要花費很大力氣;要是讓人來完成,則必定有很多百姓受苦。但它無疑又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秦國的倉儲規模有多驚人。十二年后,秦國能輕而易舉的救濟飽受饑荒的晉國(指泛舟之役),還熬過了第二年自己的大災之年,同樣佐證了這一點。
在形制上,秦國的倉儲形態基本有囷、倉、窖三種。一般來說,囷的容積較小,倉的容積較大,都建于地上;而窖則建于地下。這與其它諸國類似,屬于時代的特征。
在等級上,秦國糧倉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大類。都城設有太倉,各郡縣設有縣倉,鄉又設有離邑倉。分別由內史屬官、縣嗇夫、倉佐等職官負責,等級嚴明,便于管理。
在管理上,秦國頒有《倉律》,內容全面而細致。糧食以“積”為單位隔上荊笆,設置倉門。地方倉庫一萬石一積,舊都櫟陽二萬石一積,都城咸陽十萬石一積。入倉時由縣級主管和具體經辦人員共同驗視、共同封印。所有糧食編有“倉籍”,記上數量、經辦人員等信息,供年底或出倉時核對。如發現糧倉漏雨、倉儲虧空、庫房門閂不嚴、有鼠穴、有糧食朽敗等,都會視情節輕重對管理人員給予不同程度的處罰…正如盧鷹所說:“倉政管理法的嚴密性和系統性都是歷史上少見的。從糧食的入倉,貯藏保管與使用分配的每一道程序都制定了具體詳細的法令。”
此外,《效律》等處規定了如何晾曬、如何防火、如何處理“不當籍者”和檢斤計量等各種問題。《金布律》、《廄苑律》、《田律》等也對特定物品的倉儲管理有一定的涉及。
這些措施,從法律層面保護了秦國的倉儲安全和運行上的高效,保證了秦軍的后勤補給。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鐵質農具開始被廣泛使用和牛耕的方式逐步得到推廣,農業的發展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秦國的統治者們看來:糧倉建的再大,制度定的再好,如果沒有穩定的糧食來源,也都是枉然,相較那些等級分明,遍布全國的一個個“人為之”的具體倉庫,他們更看好的是更高層面的東西—“天府”。在此基礎上,秦國各個歷史時期的
為了確保自己的糧倉能源源不斷的供給國家用度,他們不惜用兩代君王的鮮血奪取了“岐豐之地”這座天然糧倉;他們不惜延緩統一步伐,花費10年時間修建鄭國渠用于灌溉;他們拿下巴蜀,并耗時14年建成都江堰,讓秦國從此“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收獲又一座“天府”…更重要的,他們于困境中選擇了商鞅變法,一方面重農抑商,逼迫全體國民參與耕作;一方面“廢井田,開阡陌”,鼓勵人人開荒,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同時,他們還用優厚的政策招攬它國流民來秦從事農業生產,并將戰俘和罪人發配到新打下來的地盤種田,以增加收成…
在這一系列操作之下,秦國沒用多少年就從“諸侯卑秦”的狀態蛻變為諸侯皆畏之的超級強國。從秦孝公開始,及至始皇,充足的糧食支撐了秦國統一過程中大大小小108次戰爭。他們“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終于完成千秋大業,實現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一統!
3 秦統一后的“物流”成就概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合天下;前206年秦三世子嬰降于沛公而秦亡。549年打下的天下就存在了15年,…但這15年里,大秦在“物流”上的成就仍然可圈可點。
國家統一了,秦代在法令、度量衡、生產領域甚至思想上都嘗試統一標準。在交通上禮儀上,他們定下“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車同軌”。只可惜,司馬遷等史學家并沒有描述什么是車同軌,它的具體內容和形式因此成為兩千多年的歷史謎題。
西方道、巴蜀棧道、武關道、東方道、濱海道、臨晉道、上郡道、北方道和秦直道等9條馳道組成了秦國的主干交通網。作為始皇帝主要的歷史貢獻之一,馳道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和修建標準。
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等于現在的69 米寬),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書·賈山傳》
秦始皇派兵南征百粵時,為解決軍餉轉運困難的問題,“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公元前214年作為秦國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靈渠修成。它溝通了湘江、漓江,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為秦王朝統一嶺南提供了重要的保證,靈渠鑿成通航的當年,秦兵即攻克嶺南。
秦代在道路的修建形式上有了較大的突破,他們修建了多處“上下有道”的復道,也就是我國早期立體交叉道路,意義重大。還在道路兩側夯土筑壁,修建甬道,以提高人員轉移和物資運輸的隱蔽性和安全性。
另外,秦始皇的也對秦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有極大的提升。
比如為了漕運東方的糧食以充實長安,“秦建敖倉于成皋”,在秦漢之后都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再如,“始皇帝四年七月,立長太平倉,豐則糴,歉則糶,以利民也。”(《太平御覽》)等等。
4 反思及歷史啟示
我們沿著“物流”的視角簡單回顧了大秦的歷史,“物流”在大秦的各個歷史階段可謂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其“基礎性、戰略性、先導性”的地位在兩、三千年前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我想,我們一定還會從中收獲其它更多的反思和啟示。這里,不妨把它留作“思考題”,等后面幾期多了解幾個朝代之后,我們再來做個對比和總結。我相信,從這些舊歷史中,我們會對物流有一個全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