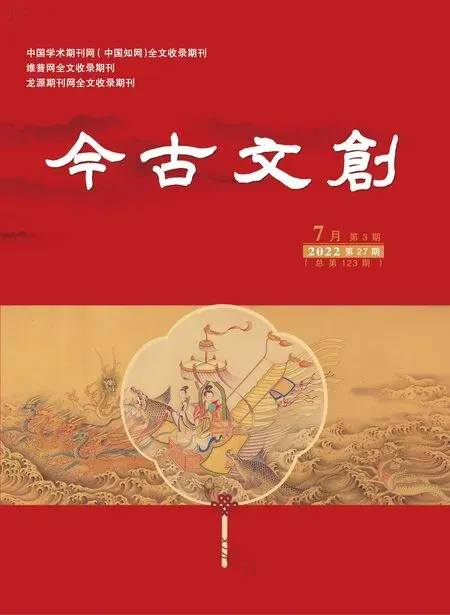約翰·福爾斯作品女性神秘特質的構建手段研究
◎張曉華
(貴州商學院大學外語教學部 貴州 貴陽 550014)
一、作為人類存在本質的神秘特質
神秘,或未知,是動力。一旦被闡釋,神秘就不再是動力之源。如果我們深入探究,就會接近解決神秘的頂點。而神秘被揭開則意味著被扼殺……事實上,因為未知是上帝,我們不可能脫離最基本的存在的神秘。神秘是所有疑問的動力,因此也是所有行動和選擇的根源所在。
福爾斯《智者》
神秘是福爾斯每部作品的主題。福爾斯認為,神秘是人類認知和無盡追尋的基本動機。神秘是一種力量,是基本的推進力,把人置于最佳的未知境地。受神秘的刺激,人類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去了解未知和未確定之物。神秘創造張力,促使人去發現被掩藏的奧秘。“就像黑夜里一道閃電,它向人類展現了現實,也照亮了前進之路。”在追尋過程中,人類會遇到各種危險,透視生存的意義,感受存在的意義。“我們通過分析、理解和陳說世界以及世界的構成要件來感知自己的存在,從而證明這些方面從根本上有幸不為我們所知,雖然事物之偶然性在我們的生活中越來越無足輕重。”
福爾斯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大病癥即總是試圖運用現代科技解決所有的神秘,從而破壞了神秘的真正內涵。福爾斯通過把他的主人公設置在個人追尋的一系列迷宮中來強調神秘的重要性。他的故事的氛圍總是神秘莫測,充滿了實現自我、認知自我的可能性。其中的人物總是受好奇心驅使去深入探索迷宮,然后卷入一系列事件。他們首先要經歷身體的折磨才會從心理上得到啟蒙,然后才能獲得自我意識。
為了讓他的故事保持神秘性,福爾斯并沒有給故事設計明確的結局,由此來凸顯人類存在在本質上的不確定性。通過延遲某些關鍵細節對故事產生的影響,以及故意對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內心世界的忽略,福爾斯解構了意義的確定性。因為,在福爾斯看來,女性是神秘的主體,利用神秘來吸引男性走出受傳統觀念束縛的烏木塔,進入完全未知的領域。當男性接受了存在的神秘本性,他就作為“優等物種”實現了自身的進化。
二、通過男性書寫構建的神秘另類女性
盡管以女性作為小說題目,但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的主人公絕對不是法國中尉的情婦薩拉,而是查爾斯這位在尋求自我過程中經歷不尋常的紳士。女性只是擔當了男性質變的催化劑。
女性人物薩拉的第一個特點是神秘。她的來源是神秘的,源于作者福爾斯1966年秋季偶然夢到的一位神秘女性:
在機場休息室里,那個女子從不向窗外凝視……那女子的面孔模糊不清,也并不是很能代表女性的特點。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她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她背轉身,代表了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嘲諷。一個邊緣人物。(Fowles,Wormholes,14)
利用對這位神秘女性的傾慕,作者運用各種手段寫成了一部十分成功的作品。薩拉的神秘表現在她的具有異域風情的外貌、她的衣著、她的不合時宜的行為以及她的復雜的內心世界。小說以一個身份不明地拿著望遠鏡觀察萊姆海灣的當地旁觀者的講述開始,以全知的外視角描述事件。他像一個偷窺者,看到薩拉遠遠地站在防波堤的盡頭,身穿一件破舊的式樣簡單的男式外套,帶著一種抗拒一切傳統的神秘和怪異。在當地男性旁觀者的眼中,她與她所在的維多利亞時代格格不入,就像一個外來者侵入傳統社會,像一個被拋棄的佩戴著代表恥辱的紅字的女性。
第二,從男性聚焦者的角度來看待薩拉,她的另一個特征是陰郁。她身著暗淡的黑衣,是一個黑色的影子。她的黑色外套看上去很怪誕,她蔑視那個年代的時尚,故意以衣著的簡樸和破舊來標榜自己與眾不同,給男性帶來強烈的視覺震撼和新鮮感,喚醒男性去發現野性之美,并迫使他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存在。她顛覆了傳統的語言習慣,使萊姆鎮變成了一個不能用敘事來表述的地方。她被人稱為“悲劇”,“棄婦”,這些稱謂把她籠罩在一種桀驁不馴、否定傳統的敘事當中。
第三,從男性角度來看,薩拉是智慧的象征。根據世俗觀念,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女性都應該內心單純乏味,像天使一樣不諳世事。薩拉的精明使她與她生存的社會環境隔絕開來。她像一位道德法官,“能從空洞的辯論中、虛假的學識里、受偏見左右的邏輯方法中,發現人們的矯揉造作和弄虛作假”。在人們喜好對一切事物進行歸類劃分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傾覆了范例和系統所設定的框架”。
第四,薩拉具有歇斯底里癥的病態特征。小說中,格羅根醫生毫不掩飾自己的性別優勢,帶著男性的、種族的和醫學的優勢去診斷薩拉的病例。女性在他的眼里是低等的異性,是缺乏正常智力的生物。他列舉書中有關歇斯底里癥的描述,并讓查爾斯去閱讀有關片段,使查爾斯不知不覺地用書中所描述的癥狀來判斷和預測薩拉的行為。這樣,病例文本變成了歷史,歷史被用來指導人的行為。
第五,神秘女性薩拉成為了女性的符號。無論是從一個男性旁觀者的角度,還是從一個男性作者、男性讀者的角度,薩拉的神秘感以及由神秘引申出來的性感被無限放大,她身上的其他元素都被無限虛化了。女性的身體被簡化為一個象征著女性的符號。從她的眼神,她的頭發,到她的聲音、神態,男性所能發現的,全部是從男性欲望本身出發的被理想化、陌生化了的女性的某個方面。
三、男性作家敘事操控下的女性人物
在《法國中尉的女人》這部小說中,男性作家福爾斯運用有限全知視角、人物之間的相互映襯和解構主義手段操控文本,形成了特殊的效果。通過塑造薩拉這個神秘女性,作者肯定了女性引領男性的積極作用,但“強化了在場的男性敘事者和男性作家的權威”。因此仍然未能擺脫從男性角度來描寫女性時所帶的性別偏見。
首先,作者運用了對人物聚焦的控制手段,成功通過有限全知視角、外視角等方法塑造了薩拉的神秘特質。除了針對薩拉之外,福爾斯在處理所有人物的時候都運用了傳統的維多利亞小說中的全知視角。而標題人物薩拉 “基本上沉默不語, 直到作品的最后,仍然不夠強勢”。針對薩拉的心理活動,作者失去了對于人物內心無所不知的能力,一直堅持從外部、從一定的距離來描述她獨特的氣質。薩拉成為一個脫離作者意識之外的產物。比如,在小說的第十二章,他這樣寫道: 誰是薩拉?她來自哪里?我并不知曉。我現在講的故事只不過是我的想象。我創造的這些人物存在于我的意識之外。
作為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小說家,他蔑視維多利亞時代對作者全知的關注,同時又對現代理論所奉行的意義的闡釋和結構的虛幻性提出了挑戰。他通過展示小說情節的構建過程和所用手段來強調情節的虛構本質,通過表現人物的人工雕琢痕跡來表現自己對小說創作和人物塑造的困惑。此時的作者并非是傳統意義上的作者,而是由敘事者、作者與福爾斯本人,以及人物查爾斯結合起來形成的三位一體。這三個要素之間在不同程度上相互重疊、互相映襯,共同締造了一個神秘女性薩拉,從而凸顯了小說的虛構性和小說的現代性,使整個小說就像一個現代小說家在書中回到維多利亞時代旅行一樣,通過把虛構人物的命運和眾所熟知的近代歷史聯系起來,并展現書中人物的后代的現代生活,來消除現在和過去兩個時間段之間的疏離。
第二,男性作家通過帶有性別偏見的男性敘事視角,塑造了神秘女性薩拉。作為神秘的化身,薩拉的世界一直在男性作者的操縱下未向讀者展示。所有對于薩拉的描述都是通過旁觀的當地人外視角和男性人物查爾斯、醫生格羅根先生和男性作者的視角交替、根據對她的外部觀察做出的,這些觀察者都帶著某種程度的優越感高高在上地審視這位神秘女性,把薩拉的外表和行為都打上了男性審美的烙印,并用醫學知識去診斷薩拉的行為。受男性霸權的影響,對薩拉的刻畫帶有明顯的性別偏見。
由于薩拉的內心世界一直未能被讀者了解,神秘成了她的標簽,令她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并給自己、查爾斯和作家本人提供了存在主義的選擇的自由。男性人物查爾斯深深被她的性感、神秘和不可知性所吸引而進入她的領地,并被迫經歷了如夢蘇醒、自我否定的過程,最終達到了對自我的認識。從這一點上來看,福爾斯在對待男性權威和女性主體性上存在著一種悖論:雖然女性人物是低等的和病態的他者,但是,女性卻是男性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
第三,虛實結合的敘事手段強化了薩拉的神秘特質。為了與主要人物相互映襯,作者又塑造了另一個薩拉,一個倫敦妓女,來影射女性或為貞女, 或為妓女的雙重性,同時也使小說似乎具有一定的宿命論色彩。在倫敦,查爾斯發現一個妓女的眼神與薩拉十分神似。通過對比,此薩拉與他所認識的薩拉有諸多相似之處:她所從事的職業是薩拉差點不能避免的命運;她也是被一個軍人拋棄,并生有一個女兒,這一點與萊姆鎮的薩拉完全吻合。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男性作家福爾斯實際上另外一種三位一體:法國中尉模糊先生(筆者譯)、查爾斯和藝術家若賽蒂。男性人物查爾斯陷入了停滯狀態,只有神秘的女性才可以帶他們走出困頓,讓他們重新獲得科學家和藝術家的敏感。可見,男性的進化永遠是福爾斯關注的核心。他的作品無一例外都是探討男性的變化,女性至多是引導男性進化的催化劑。女性的內心以及女性的命運,并不是查爾斯去探討的主題。
第四,薩拉的神秘和不確定性是福爾斯運用解構主義方法來創作小說的結果。福爾斯首先書寫了薩拉的故事,然后再進行擦除,從而凸顯了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他設計薩拉來編造自己的經歷,然后予以否定,把薩拉包裹在神秘氛圍之中,同時也給予作者和讀者自由,去根據自己對薩拉的理解來解釋薩拉的行為。關于薩拉的一切,沒有任何一點是確定的。從她的身份、她的講述、她的行為,到她的心理,都是他人的語言建構,或者是薩拉自身語言建構的結果,或者僅僅是作者猜測形成的。敘事變成了一種游戲,剛剛被建構的敘事被下一個情節所解構、所擦除,直到作者甚至懷疑薩拉這個人物是否實存在。但是薩拉對于男性的成長卻是有益的。可見,作者創造然后涂抹女性人物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促進男性的自我意識,并以此敦促男性的成熟。
四、結語
神秘是福爾斯所要展示的人類存在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福爾斯小說人物探求未知的動力。通過對神秘的探索和試圖解釋神秘現象所作的努力,人類逐漸獲得對自我的認知和對奇妙的宇宙的更多了解,并逐步建構、完善知識體系。 “認知—神秘張力為人類自我的存在提供了一個綜合性語境,也為我們對不確定、不可知的自我進行探索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受神秘女性的吸引,福爾斯的男性人物從未停止探索生命意義、認知內在自我的腳步。通過小說創作,福爾斯體現了對人類存在本質和人類認知的深刻思考。
然而,福爾斯對于神秘的理解未免有些偏頗。在他的小說中,男性人物進入神秘世界去探索未知世界的奧妙,這種神秘性一般集中表現在女性人物身上。這種被簡化的神秘特質在女性身上多表現為女性身體的遙不可及和女性內心的深不可測。同時,女性的神秘又常常被福爾斯賦予色情的意味。把女性的神秘等同于色情或許是福爾斯看待女性的一種特殊方式,但在這種觀念背后依然可以看到根深蒂固的男性等級思想。在某些男性作者的眼中,女性的神秘為男性的成長提供一個認知的領域,是男性自我走向成熟的一個媒介,而男性,永遠是作者關注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