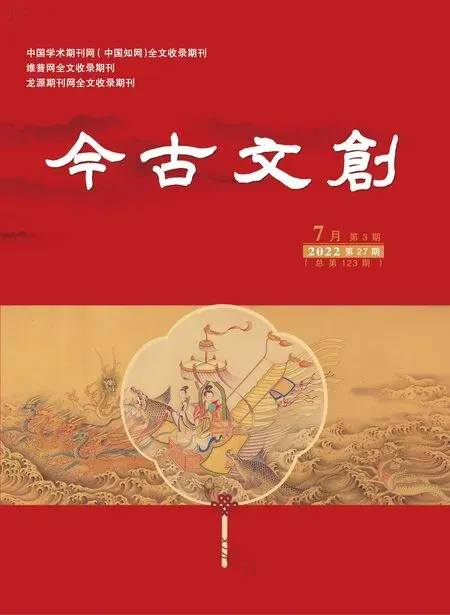《水滸傳》英譯本中的翻譯普遍性研究
◎李冰茹
(河北工業(yè)大學(xué) 天津 300130)
一、翻譯普遍性的提出與發(fā)展
早期的翻譯研究主要集中在語言學(xué)研究和理論研究,學(xué)者們更多關(guān)注的則是理論的提出與發(fā)展。在這一時期,涌現(xiàn)出一大批語言學(xué)家和翻譯家。隨著電子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翻譯學(xué)家的目光轉(zhuǎn)向了語料庫翻譯研究。語料庫翻譯研究是 20世紀(jì) 90年代才興起的一種全新的翻譯研究范式。Vanderawera(1985)選取了五本丹麥語寫成的小說的英譯本作為語料庫,經(jīng)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小說的英譯本的語言特點與原文本的語言特點存在一些相似性,這主要表現(xiàn)在文體、選詞、句子結(jié)構(gòu)、篇章結(jié)構(gòu)甚至標(biāo)點等方面。Baker在Vanderawera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語料庫研究的。她于1993年發(fā)表了一篇名為“語料庫語言學(xué)與翻譯研究:啟示與應(yīng)用”的文章,這開啟了語料庫研究的新篇章,而語料庫翻譯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對翻譯普遍性的研究。
Baker(1993/1996)提出翻譯普遍性,她認(rèn)為翻譯文本具有自身的語言特征,這一特征不同于原文的語言特征。借助語料庫的幫助,Baker認(rèn)為翻譯普遍性特征主要包含簡略化、明晰化和規(guī)范化和整齊化。并且此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簡約化、明晰化和標(biāo)準(zhǔn)化三個方面,對整齊化的研究較少。胡顯耀(2004)也對這一問題進(jìn)行歸納總結(jié),他認(rèn)為翻譯普遍性是“譯文而非原文中的典型特征”, 主要表現(xiàn)在簡略化、明確化、規(guī)范化、整齊化和集中化等幾個方面。柯飛認(rèn)為翻譯普遍性是指譯文中表現(xiàn)出的有別于原文的一些典型的、跨語言的和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征。(柯飛,2005)
二、《水滸傳》的英譯
隨著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到來,中國經(jīng)濟(jì)迅速崛起,國家軟實力也穩(wěn)步提高。典籍英譯是對外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它有助弘揚(yáng)民族文化、促進(jìn)東西方文化融合。《水滸傳》是中國傳統(tǒng)四大名著之一,先后被翻譯成多個國家的文字版本。水滸傳的英譯本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賽珍珠和沙博理的譯本。賽珍珠,美國著名作家,人權(quán)和女權(quán)活動家。她是第一位將《水滸傳》全譯成英文的作家。賽珍珠在中國生活多年,由于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她的譯文則是盡可能原汁原味地傳遞原文中所蘊(yùn)含的信息,整體翻譯趨向于直譯。直譯就導(dǎo)致了譯本中存在一些錯誤。沙伯理的譯本晚于賽珍珠的譯本。他的譯本語言風(fēng)格很接近目的語讀者,語言簡潔質(zhì)樸,目的語讀者的接受性更高。但他在翻譯的過程中比較大膽地對原文進(jìn)行了刪改,所以原文中的有些信息并沒有進(jìn)行準(zhǔn)確傳達(dá)。
三、《水滸傳》中的語言特點
《水滸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瑰寶,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用白話文寫成的章回小說之一。全文通過塑造108位梁山好漢,生動地展示了封建社會的階級壓迫和他們奮勇力爭的大無畏精神。水滸傳成書于元末明初,書中存在大量的特殊句式,文中用語也十分考究。在翻譯的過程中對這些句式的處理也是一個關(guān)鍵點,不同譯者的處理手段也有所區(qū)別。水滸傳的用語具有以下特點:一、由于水滸傳受眾廣泛,所以書中語言具有典型的口語化特點,文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粗俗語的使用;二、水滸傳屬于長篇章回體小說,所以其用語也符合章回體小說固定用法;三、水滸傳中摻雜一定的古文用法,用語復(fù)雜。這些特點導(dǎo)致水滸傳在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難度。翻譯時也需把握這一點。譯者所做的只有針對書中的語言特點選取合適的翻譯方法。
四、譯本中的翻譯普遍性特征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許多學(xué)者對翻譯文本都存在一些偏見,根本原因是翻譯文本中使用的語言是區(qū)別于源語言的,譯語與源語的背景文化與語言結(jié)構(gòu)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常稱譯本為翻譯體,對其認(rèn)知也存在偏頗。但隨著語料庫研究的進(jìn)展,人們通過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譯本中存在一些普遍特征。而這些普遍特征的發(fā)現(xiàn)是使譯本的質(zhì)量有所提高。
(一)第一個翻譯普遍性特征為簡約化。簡約化也譯為簡化,指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下意識地用簡化的語言進(jìn)行再敘事或者對源語的內(nèi)容進(jìn)行去繁從簡的處理,或者兩者兼而有之。(Baker,1996:176) 翻譯文本的簡略化傾向主要表現(xiàn)為用上義詞代替下義詞,用常用詞匯代替源語中的不常用詞匯。所以簡約化體現(xiàn)在句式的長度,詞匯的選擇等方面。
1.水滸傳中武松與潘金蓮的初次見面時展開了一次日常對話。對話中潘金蓮問叔叔青春幾何?兩位譯者都對句式進(jìn)行了分析處理。古文中的青春一詞可以得知為年齡的意思,但此處賽珍珠的譯文中把“青春”二字直接翻譯為green spring-times并且答語中的“武二”也通過插入語的形式進(jìn)行翻譯,拘泥于原文的語言格式 而沙博理的譯文則簡化為我們?nèi)粘5挠谜Z。用How old are you?Twenty-five.這一簡單問答來代替。更加簡潔易懂。但在用語簡單的同時則不利于原文文化信息的傳遞。忽略了當(dāng)時叔嫂二人見面時那種緊張的氛圍。而賽譯的版本則更加具體地把信息表示出來,雖然青春一詞翻譯存在問題,但原文的句式結(jié)構(gòu)更有利于整個環(huán)境的再現(xiàn)。
2.水滸傳為了平衡句式 文中會出現(xiàn)一些語氣詞來平衡一下音節(jié)如“也好”“便了”等詞匯。這類詞匯并不具備其他的作用。在翻譯過程中賽譯則是盡量把這一內(nèi)容都進(jìn)行了展示,如“也好”賽譯便譯為“l(fā)et that end it”,這一表達(dá)原汁原味,但讀者可能并不是很清晰明了,而沙譯則是簡單地把基本內(nèi)容進(jìn)行翻譯,省略語氣詞的翻譯,譯文讀起來簡潔明了。
(二)第二個翻譯普遍性則體現(xiàn)在語言的明晰化。明晰化也稱作顯化,指翻譯時用明確易懂的語言對源語中隱含、晦澀的意思進(jìn)行再敘事(Baker,1996:180)。明晰化也通常發(fā)生在詞匯,句式,語篇等方面。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的傳播離不開語言的使用。《水滸傳》的故事發(fā)生于宋朝,書中存在許多文化負(fù)載詞,這些文化負(fù)載詞往往帶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給讀者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難。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需重視這一類詞匯的翻譯策略,必要時要對這些語言要素進(jìn)行明晰化處理。如以下幾方面:
1.書名翻譯。典籍英譯中書名的翻譯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關(guān)注。書名整體概括了全文中的主要內(nèi)容,也可傳遞一部分中心思想。書名也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英文的書譯名往往體現(xiàn)一位譯者的翻譯風(fēng)格。水滸傳這一名稱中“傳”代表的就是一本人物傳記,翻譯的難點在于水滸二字。這一詞匯不具有實際內(nèi)涵。因此在翻譯時需進(jìn)行一定的明晰化處理。因此賽珍珠在此借用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這一表達(dá)進(jìn)行翻譯,譯為All Men are Brothers借此表達(dá)水滸傳中的兄弟情。沙伯理在此譯為Outlaws of the Marsh代表沼澤里的草莽英雄,這一表達(dá)更為直接。
2.社會文化負(fù)載詞的翻譯。在近代武俠小說中頻繁出現(xiàn)“江湖”一詞,江湖在中國文化中有多重引申的含義,在水滸傳中這一詞匯也常常出現(xiàn)在正文中,它通常指的是不受朝廷約束,行俠仗義的一個環(huán)境。水滸傳中的江湖指的就是梁山好漢所生存的社會。文學(xué)作品中關(guān)于江湖的翻譯也具有多個版本,在此沙博理將其譯為“the gallant fraternity”代指這一群英雄好漢,通過這樣的翻譯可以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江湖這一詞匯的社會意義。賽珍珠選擇直接翻譯為江和湖“On rivers and lakes”這容易造成讀者的理解錯誤。
3.綽號的翻譯。水滸傳中人物的塑造離不開綽號的使用。書中的典型人物都有其自身的綽號,頗具代表意義。綽號的使用可以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水滸傳中的綽號往往根據(jù)其自身特點確定,十分具有代表性。水滸傳中塑造了很多印象深刻的人物,如神行太保戴宗,及時雨宋江,花和尚魯智深,豹子頭林沖等。提起每個人的綽號這一形象也躍然紙上。如神行太保(戴宗)這一綽號則與其特長相關(guān)。戴宗因為學(xué)過道法,所以將神行甲馬拴在腿上,可以日行八百里,因此稱他為神行太保。賽譯為“The Magic Messenger”雖沒有將原文的意思完全傳達(dá)出,但信使這一詞匯至少體現(xiàn)了他的特長,而沙譯將其翻譯為“The Marvelous Traveler”戴宗的身份就定義為“traveler”這一詞匯重點突出了他是一位旅行者,并不能生動形象概括這一人物特點,有失于原文。而花和尚(魯智深)這一綽號十分符合他的身份。魯智深他行伍出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后為躲避官府出家當(dāng)和尚,迫于無奈逼上梁山。花和尚說明他首先是一個和尚,其次花和尚說明他與傳統(tǒng)和尚不同,他不受清規(guī)戒律所束縛。賽譯為“The Tattooed Priest” 沙則譯為“The Tattooed Monk”,賽譯對“和尚”翻譯為“priest”,在西方并沒有我們所指的和尚,“priest”通常指的是天主教的神父,職位等同于中國的和尚。沙譯的僧人“monk”更符合中國和尚的表達(dá)。青面獸(楊志)為楊家將后人,此人武藝高強(qiáng),孔武有力。因為他的臉上有一大塊青色胎記,所以人稱青面獸。賽譯為“The Blue Faced Beast”沙譯為“The Blue-Faced Beast”兩位譯者的翻譯幾乎相同,“beast”在西文化中代表野獸,十分兇猛的意思,所以這一詞匯無明顯問題。“青面”一詞本因臉上胎記使面色發(fā)青,兩位譯者翻譯成“bluefaced”這稍微有一點夸張,但目的語讀者也可以準(zhǔn)確理解此綽號的含義。
(三)第三個翻譯普遍性原則為規(guī)范化,不同的學(xué)者對他的稱呼也有所不同。它指翻譯文本對目標(biāo)語語法,表達(dá)和結(jié)構(gòu)特征的順應(yīng),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犧牲源語的創(chuàng)造性語言,代替以規(guī)范的表達(dá)。實現(xiàn)規(guī)范化的手段也多種多樣,但整體是使得譯文比原文可讀性更強(qiáng),組織結(jié)構(gòu)更加清晰明了,如下文所示。
1.水滸傳中塑造了108位英雄好漢,書中人物之間銜接緊密,人物關(guān)系復(fù)雜。在介紹文中典型人物時往往使用了大量的報道性動詞。報道性動詞的使用使成文更加緊密。報道動詞代表的是語言和思維的連接,也暗示著作者對轉(zhuǎn)述內(nèi)容及觀點的視角和態(tài)度。故報道動詞的使用整個語篇更加連貫。水滸傳中出現(xiàn)很多報道性動詞。如林沖道,那婦人道等用法。第八回林沖道:“謝得照顧。”這一句在翻譯的過程中賽譯為Ling Chung said, “I thank you for this protection.”在翻譯的過程中用said一詞突出說的方式。沙伯理的譯文中則直接翻譯為“Thanks for your protection”, said Lin Chong.這一句中的said 位于句中隱含的進(jìn)行表達(dá),這也比較符合西方讀者的英語習(xí)慣。
2.水滸傳屬于長篇章回體小說,在長篇章回體小說中,套語的存在必不可少。開始時,作者會使用“看官聽說”這一類詞匯,在每章結(jié)束時,作者會用“欲知后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這樣的套語將故事引入到下一章節(jié)。對比賽珍珠和沙伯理的譯文,兩位譯者關(guān)于套語的譯文十分固定,其中賽珍珠將這一句統(tǒng)一譯為“Pray hear it told in the next chapter.”而沙譯則是譯為“Read our next chapter if you would know.”兩者的表達(dá)都體現(xiàn)了這一語言特點,但賽譯版的“pray”一詞使文中感情色彩更加濃厚。
五、總結(jié)
通過分析沙伯理和賽珍珠兩位譯者的譯本,可以發(fā)現(xiàn)兩位譯者的語言風(fēng)格存在很大的差異,這取決于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兩位譯者的譯文也都存在一些普遍性特征。明晰化特征的出現(xiàn)使整個譯文所傳遞的信息更加詳盡,我們往往在此對不明晰的表達(dá)進(jìn)行補(bǔ)充說明,這有利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規(guī)范化則使整個譯文的用語表達(dá)更加規(guī)范,譯文可讀性提高。簡約化也是譯文的一個普遍特征。但有時候不是非得進(jìn)行簡約化處理,簡約化可能會把原文中隱含的信息刪去,不利于文中信息的傳達(dá),所以譯者在使用時需要考慮自己的翻譯目的,選擇合適的翻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