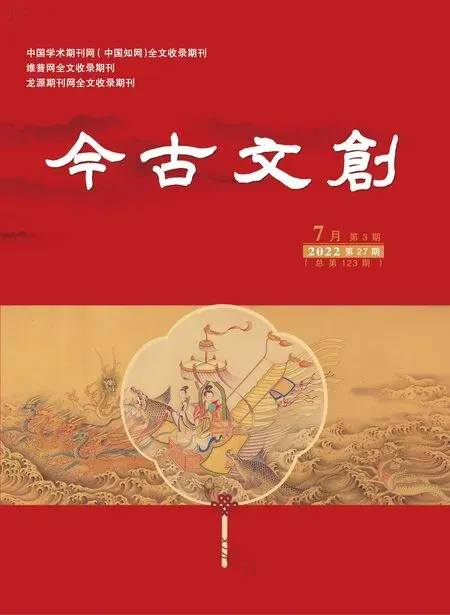《金枝》中的兩種神話—儀式主義
◎朱睿卿
(山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 山西 太原 030036)
神話與儀式是許多學科的共有領域:除去民俗學之外,還有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以及文學涉及這一主題。各個學科在這一問題上視角各有不同,但早期對這一主題的研究幾乎總是建立在這兩者與宗教的關系之上;由此而來的批評一般被稱作“神話—儀式主義批評(mythand-ritual criticism)”,并在其基礎上形成了在20世紀20—60年代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一個學派,即神話—儀式主義學派(the myth-ritual school)。這一研究途徑的主要研究內容是從文獻當中尋找潛在的神話和儀式的模式,而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英國學者則是其主要的理論和方法論的來源,其中包括以簡·艾倫·哈里森(Jane Allen Harrison)、吉爾伯特·穆雷(Gilbert Murray)為代表的“劍橋儀式主義學派(Cambridge Ritualists)”,以及對這一學派有著重大影響的英國學者,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作為神話—儀式主義的核心人物,弗雷澤的學術思想經歷過許多階段性的轉變,并且也受到過許多同時代的其他學者的影響,他所提出的兩種不盡相同的神話—儀式主義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
本文意在對弗雷澤在他的著作《金枝》中提出的兩種神話—儀式主義進行梳理,并對弗雷澤受到的來自其他學者的影響進行分析,以求更好地理解弗雷澤的學術思想。
一、早期對神話—儀式關系的研究
歐洲對儀式的研究在開始的時間上大致相同。被譽為“人類學之父”的愛德華·博內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71年發表了他里程碑式的著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泰勒對于神話—儀式的關系觀點主要基于文化進化論,并且建立在原始宗教與現代宗教的對立上:他認為神話是科學在遠古時期的對應物,只是一種通過故事的形式進行表達的信條,并將其視作一種對自然界的解釋,因而能夠獨立于儀式運作。
換句話說,在泰勒的認識當中,神話是儀式的先決條件,他認為神話既是解釋世界的手段,同時也是解釋世界的目的,而儀式則只是對神話知識的一種應用:“當一個在智力上處于神話創造階段的人被任何現象或者傳統——尤其是沒有任何明顯原因的現象或者傳統——吸引了其注意力時,他就通過創造出一個故事、并且講述這個故事的方式來解釋它。”
因而,神話的解釋比儀式的控制更加重要,神話也就由此在宗教當中具有了比儀式更加重要的地位。從這一基礎出發,泰勒認為現代宗教中并沒有神話和儀式的位置,因為現代宗教的主要內容不再是對自然界的認識和解釋,而是一系列倫理和哲學的組合。
在大約同一時期,閃米特學者威廉·羅伯特森·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也發表了他的《關于閃米特人宗教的講稿》(Lectures on 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1889)。與泰勒相類似地,他認為古代宗教與現代宗教不同,古代宗教并不存在信條,而是以習俗和實踐為主,而神話則承擔著信條在現代宗教當中的職責。因而,與泰勒相反地,他認為神話完全來自于儀式,只是儀式的理由在宗教發展過程中被忘記之后的產物,并將神話、儀式、宗教之間的關系劃分為了五個階段。
總體來說,史密斯認為神話完全地來自于儀式,并且只能在儀式的語境下進行解讀,而同樣由于這一點,儀式消亡的過程也并不會受到神話的影響:“只要神話包含對儀式的解釋,它們在價值上就是次要的,并且能夠從所有的方面說明神話來自于儀式,而非儀式來自于神話;因為儀式是固定的,而神話是可變的,儀式是一種義務,但對神話的信仰卻是信徒的一種創造。”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對弗雷澤的研究有著深遠影響的德國語言學者、民俗學者威爾海姆·曼哈特(Wilhelm Mannhardt),他在19世紀后半葉開始了尋找有關植物、谷物和樹木精靈習俗的調查,并發表了他在宗教與儀式的關系這一問題上最重要的幾部著作:《黑麥狼與黑麥犬》(Roggenwolf und Roggenhund,1865—66)、《谷物精靈》(Die Kornd?monen,1868),以及兩卷本的《森林與田野崇拜》(Wald-und Feldkulte,1875)。由于當時德語世界民族主義的影響,曼哈特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近現代習俗中保留著的古代宗教崇拜元素,并且與同時代的學者一致地試圖將現代民族志與民俗學同古代傳統聯系在一起。
曼哈特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對材料和證據的大范圍使用,這一點對弗雷澤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就像弗雷澤本人在《金枝》第一版的序言當中所寫的,“我使用了許多威爾海姆·曼哈特近期的研究成果,如果沒有他的研究,這本書很可能根本無法寫成”。
二、弗雷澤的兩種神話—儀式主義
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Golden Bough,1890)奠定了19世紀神話—儀式主義研究的基礎;但這部作品只是他一生的眾多著述之一。除去這部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之外,他還發表過《保薩尼亞斯的〈希臘道里志〉》(Pausanias’s Description of Greece,1898)的翻譯和五卷本的批評,以及《早期王權史講稿》(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Kingship, 1905)、《圖 騰 制 與外婚制》(Totemism and Exogamy, 1910)、《舊約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1918)等多部著作。
《金枝》最初是從對一場儀式性的決斗的解釋開始的:這一決斗發生在羅馬外的一個名叫阿里基亞的小鎮,而在附近的內米湖旁的林地中,一個被稱為王的“祭司”隨時等待著其他人前來挑戰他的權威。決斗的規則是這樣的:任何成功逃跑的奴隸只要殺死這名祭司,就可以獲得自由,但也必須同時成為新的祭司,等待下一次決斗的到來。弗雷澤認為這一決斗的習俗不能完全(或者完全不能)按照羅馬宗教的角度來理解,而是必須通過比較的方式來進行分析:“如果能夠表明像內米的祭司繼承一樣的野蠻習俗在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如果能夠找出發展出這種制度的動機;如果能夠證明這些動機廣泛存在,或者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并且在不同環境下產生了大同小異的制度;如果能夠證明這些動機,以及由此而來的制度,的確存在于古典時期,我們就能證明這一點。”他隨后通過其他原始社會中的例子主張祭司同時也是王,而這一“祭司王”則是社區富足的保障,因而社區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障祭司王的健康,其方式多種多樣,涉及到禁忌、巫術、獻祭等等,以免他們的王染病或者死去。
弗雷澤援引了許多古代地中海地區宗教中的神話和儀式來支持他的主張,如阿提斯、阿多尼斯、歐西里斯、狄俄尼索斯,并將與這些神相關的儀式視作“死亡與重生的輪回”,以及促進豐產的儀式。而這些神祇則作為人類共有的一種與植物有關的、戲劇化的儀式當中具有神性的主人公出現。
內米的決斗本質上只是弗雷澤用來引出他的理論當中支配著原始思維的法則的引述;他認為,雖然我們無法直接接觸原始人的思維方式,但這種思維方式仍然可以通過他(曼哈特)的“相似律”來進行解釋:當不同的社會當中存在著相似的習俗時,這些民族當中產生這些習俗的動機就很有可能具有相似性。受到19世紀的比較宗教學和比較神話學的影響,弗雷澤接受了曼哈特的觀點,認為原始的“雅利安人”思維方式仍然存在于現代歐洲的農民階層,因為他們的思維尚未受到現代思維的影響,并且進一步地將這一觀點擴展到了那些“現代的原始人”(即不發達地區的氏族社會)身上,認為同樣可以將他們與古代世界的社會進行比較,并且從中研究那些支配原始思維的法則。
弗雷澤在《金枝》中的觀點,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來自當時具有主宰地位的文化進化論的影響。在這一基礎上,他還進一步地提出了人類的巫術、宗教、科學的三個階梯式發展過程,而這部作品中主要的內容,則是對宗教與科學之間的調和階段的討論:對弗雷澤來說,只有在這個仍然古老并且原始的階段中,巫術與宗教才能共同作用,因而也就成為了他的神話—儀式主義的土壤。
而就是在上述的這些理論的基礎上,弗雷澤提出了他的神話—儀式主義思想:他認為所有的神中最重要的就是掌管豐收的植物神,神話描述的是這位植物神的生死循環,而儀式則是為了復現這一神話中對植物神死亡與重生的描述。這一儀式建立在弗雷澤巫術原理的“相似律”之上,也即是“可以通過模仿來實現任何希望達成的效果”。
因為人類雖然將季節的年度變化主要地歸結為在他們的眾神身上所產生的對應變化,但他們仍然相信能夠通過舉行某些巫術儀式來幫助他們那位作為生命原理的神,來對抗那位與他敵對的、作為死亡原理的神。他們想象自己能夠為神補充逐漸衰弱的能量,甚至使他起死回生。他們為了這一目的而舉行的儀式,本質上只是一種自然進程的戲劇式的表現,目的在于促進這一進程的發生;因為巫術的信條就是可以通過模仿來產生任何想要的效果。
因而,按照弗雷澤的巫術原理,這一儀式操縱的是植物神而非植物本身,是通過植物神的變化使得植物本身隨之變化,王在這一儀式過程當中扮演的只是神的角色,而非神本身;因而,對弗雷澤來說,植物受到植物神的控制屬于一種宗教觀念,但能夠通過巫術控制植物(即使是通過對神的控制這一中介的方式),則是一種巫術的觀念:“宗教理論就是通過這種方式與巫術實踐混合在一起的,這種組合在歷史上十分常見。”
但是,阿克曼與西格爾都曾指出,弗雷澤在神話與儀式的關系上持有的觀點并不連貫。在上述的第一種神話—儀式主義當中,王的身份對扮演神的祭司來說并非必要條件;但在弗雷澤的第二種神話—儀式主義當中,王就不再只是通過巫術原理的“扮演”來以模仿的方式影響神、并獲得自己想要的效果,而是本身就具有一種神圣的性質。按照弗雷澤的認識,他們是具有人身的神性(human divinities);或者說,神性寓居在他的體內。而就像植物神能夠控制植物的生長,王的健康狀況也會產生同樣的影響:“王和祭司被認為擁有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是神的化身,而與這一信仰相一致地,自然的進程也同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響,因而惡劣的天氣、農作物的歉收,以及類似的災難也都同樣要被歸咎到他的身上。”
而為了能夠穩定地獲取食物,社區就必須在國王陷入年老或者疾病導致的衰弱之前將他殺死:“避免這些災難的方法只有一個,人神必須在他表現出自己的力量開始衰弱的癥狀時被殺死,他的靈魂也必須在被衰老的威脅損害之前轉移到一個強壯的繼任者的身上。”弗雷澤本人將這種神話—儀式主義總結如下:(原始人)相信王的生命或者靈與整個國家的繁榮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如果他染病或者衰老,牲畜就會生病、失去生育能力,農作物會腐爛在田野中,大眾也會死于瘟疫。因而,在他們眼中,規避這些災難的唯一方式,就是在王仍然強壯時將其殺死,以使他從前任身上繼承而來的神圣的靈在仍然強壯的狀態下被轉移到他的繼承者身上,以免被疾病和年老帶來的衰弱所損害。
弗雷澤的第二種神話—儀式主義的理論范式,一般被稱作“神圣王權(sacred kingship)”,在發表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人類學和宗教學的領域內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與弗雷澤提出的第一種范式相比,神圣王權的理論范式在神話與儀式的關系上并不那么清晰:這一儀式的本質目的僅僅只是靈魂的轉移,有關植物神的神話也不再需要通過儀式復現,被殺死的王也不再是通過相似律進行模仿,只是為了避免他體內具有神性的靈魂被他的衰弱所影響的原因才在他仍然強壯時將其殺死。
弗雷澤在觀點上的這種不連續性并不是偶然的:《金枝》一共發表了3個版本,第一版中的副標題是“比較宗教學研究(a study in comparative religion)”,但第二版則改為了“巫術與宗教研究(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他著名的“巫術—宗教—科學”的人類發展進程也同樣直到第二版發布后,才成為他理論體系當中的一部分。
在弗雷澤的多版《金枝》當中,事實上同時出現了至少三種并不相容的理論:這些理論包括歐赫墨羅斯主義、理智主義和儀式主義。弗雷澤在觀點上的這種變化同樣也反映了許多同時代的學者對他的影響。從他的研究框架出發,弗雷澤最初受到來自史密斯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第一版的《金枝》事實上就是一部出于“感謝和景仰”而獻給史密斯的作品。一方面,在史密斯(以及曼哈特)的影響下,弗雷澤將儀式當中的表演元素視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點體現在許多他對模仿植物神的神話的分析當中;另一方面,史密斯在他的研究中使用了許多當代貝都因人的文化來解釋希伯來圣經當中的元素,弗雷澤也同樣大量地使用了這種方式,試圖通過對古代文獻與近代農民階層的習俗、觀念和儀式的對比,來構建出一個人類共有概念的參考系。除此之外,史密斯提出的任何宗教都不是從零憑空產生的看法,以及他對精英宗教與大眾宗教之間對比的評論,都可以在弗雷澤的研究當中找到相關的影子。
弗雷澤與史密斯同樣認為神話是為了解釋儀式的意義;但就如前文所述,史密斯堅定地認為神話來自于儀式,弗雷澤的觀點則逐漸轉向了泰勒:他接受了泰勒將神話視作“對自然界的解釋”這一觀點,也即是將其視作——按照他們的說法—— “原始人的科學知識”,并且就像他所提出的三個階段一樣,他認為這種偽科學最終會演變為科學的思考模式,而儀式只是一種對這種“偽科學”的應用。
簡單來說,巫術只是一種對自然規律的虛假認識,一種錯誤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種偽科學,一門無用的技術。被視作是自然律的體系的巫術,也即是一整套能夠決定世界上的事件發生的順序的法則,可以稱作“理論巫術”;而那些被視作人類應當遵守的一系列戒律,以求達到特定目的的巫術,則可以被稱作“實踐巫術”。
在這一基礎之上,弗雷澤同樣強調了這些巫術對原始人來說總是具有實踐的天性,并且始終未被作為科學對待過:“原始人巫師只能夠知曉它在實踐上的性質,他永遠不會分析他的實踐是建立在怎樣的思維過程之上,也永遠不會反思他的行為當中蘊含的那些抽象原理。”
三、結語
弗雷澤的這種將神話視作原始人的科學、將儀式視作對這種科學的應用,以及兩者由此不能與現代科學共存的觀點構成了19世紀和20世紀神話研究的基礎。但是,由于弗雷澤在理論上的不連貫,以及他在方法論上的缺陷,對弗雷澤本人的評價也一貫有著兩極性的傾向:一方面,海曼稱他的影響“永遠地改變了古典學領域,使之獲得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他同樣也是20世紀的學者主要的批評對象,其中尤以維特根斯坦的措辭最為激烈:他認為弗雷澤所做的一切只是“要讓那些與他有相同想法的人相信它們(他對異族習俗的論證)”,并且認為弗雷澤的研究都只是基于“錯誤的物理學,或者可能是錯誤的醫學、技術等等”;阿克曼也同樣認為弗雷澤的處境在現代的人文學科中“十分尷尬”,因為他的理論“完全地只是產出自圖書館”,并且他本人也“缺少對作為整體的文化的觀念”。但是,他的研究奠定了19世紀關于神話與儀式關系的基礎,就像西格爾指出的,20世紀的神話理論完全可以被視作是對弗雷澤和泰勒的反駁;即使拋開神話—儀式主義學派不論,他也仍然影響了許多學者:如馬林諾夫斯基,作為弗雷澤的學生,就曾多次在他的著作中公開表達過弗雷澤對自己的影響,并且也常在他的著述中提及弗雷澤,如他的《巫術、科學、宗教與其他論文集》(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中文節譯本見《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
弗雷澤的研究盡管存在相應的局限性,但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都與他所處的時代脫不開關系:一方面,達爾文主義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勝利使得任何以進化論作為其前提的學說,都具有了一種不言自明的正確性,而就像弗雷澤(以及泰勒)所認為的那樣,如果人類的思維同樣按照這種線性的進化趨勢發展,那么從巫術到宗教再到科學的發展路徑,顯然是對人類思維真實演變過程的一種合理解釋;另一方面,只有在19世紀這一歐洲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處于鼎盛的時期,歐洲才有機會真正地接觸到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氏族社會,并進而引起相關學者的興趣;也就是說,弗雷澤與泰勒一致地,是第一代能夠通過世界范圍內的資料來第一次對宗教行為進行真實可信的人類學研究的學者。
盡管現代的人類學者更多地強調田野調查,因而就像阿克曼所指出的,并不推崇弗雷澤式的“安樂椅學派”的研究方式,但他對比較方法的大量使用仍然還是為他在宗教史、文化史以及文學批評等領域,贏得了極高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