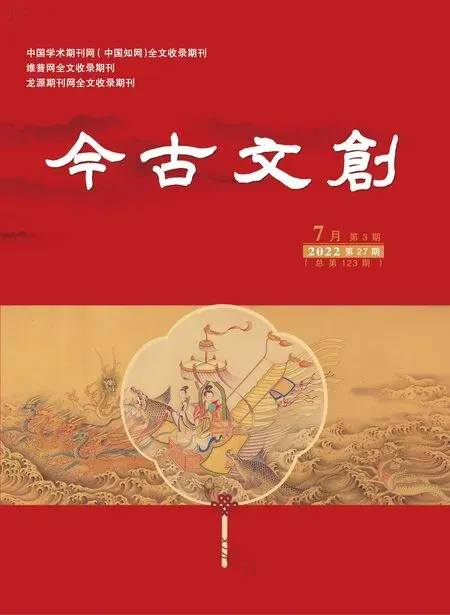淺析《古船》中的家族敘事以及與啟蒙敘事的交織
◎楊 丹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00)
家族是中華民族傳統的親屬集團,對于社會而言起到穩定發展的作用,對于個體而言也承載著親情倫理。在中國,作為大能擴延至國家和社區、小能濃縮到個人家庭的“家族”,它已然成為不可或缺的社會中介組織。宏觀來看,“家庭本位”是我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家國同構也是中國傳統社會政體的基本構成形式;微觀而言,家族觀念以血緣為信賴基礎延續至今,家族內部的各成員都對其承擔管理責任并受其管轄。又因為家族文學是我國傳統文學的理論基礎,因此家族書寫在我國文學創作中始終是個永恒的話題。
早期的作品繼承了前代作品中家族敘事方式的文化傳統,對于家庭生活解讀與親情倫理的詮釋又邁上了新的臺階。當代家族小說也在文化啟蒙的語境中,在多元文化的探索中達到了豐滿。“80年代長篇小說的主題是豐富的,但基本上是啟蒙敘事的不同展開。”
《古船》這部小說彌漫著濃厚的家族意識,本文將深度解構作品中的家族敘事,以解讀家族敘事的傳統性和現代化特點,以及文本中啟蒙敘事與家族敘事有機交織的靈魂。
一、家族敘事的傳統性
家族延續以血緣為紐帶,在宗族制度的深遠影響下,傳統家族的凝聚力團結性都是現代社會所無法匹敵的,而且這種帶有血緣紐帶的神秘力量則可以支配著家族的個體。小說《古船》具有中國傳統的以“家”隱喻為“國”的家庭敘事特點,它隨著家族的歷史文化發展與演變,以冷靜而切實的口吻書寫了一個關于洼貍鎮三大家族在時代洪流中的興衰故事,也重點講述了這個曾經繁榮輝煌的小城是怎樣逐步走向分崩離析的。
故事發生在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小城——洼貍鎮上,這里的靈魂從家族的土壤中生長出來,又被宗族精神所灌溉。鎮上的人們祖祖輩輩在同一片天空下勞動生長,多年不變的環境古樸而又封閉,傳統的家族觀念是其延續的濫觴,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封建式族長專制——老趙家的族長四爺爺趙炳。小說中,趙炳憑借自己最高的輩分而非能力或是年齡,成了趙家的實際掌權者,也成了洼貍鎮的領袖。作為長者,“趙炳是融革命領導與鄉村族長、集體利益與家族意志于一體的專制家長”。小鎮上的人對他有種莫名的敬畏與服從。比如小說中地震了,人們驚慌失措,趙炳說地震不會再來了,于是大家不再害怕,當即安安靜靜地在家里待了一夜;他若一生病,全城都為他倒下了。洼貍鎮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受到封建宗法家族觀念的影響,即使新中國成立,鎮子上擁有了新的領導新的指揮者,四爺爺趙炳依然享有絕對權威,甚至可以與鎮長共同議事。
在傳統家族敘事視野中,家族的基業與聲望是家族綿延不絕的物質與精神基礎。所以當家族受損時,每一個家族個體都理應奮不顧身為家族奉獻。隋見素就是在這樣的思想環境中長大的,也造就了他濃厚的傳統家族復興的使命感。曾經的隋家是洼貍鎮上首屈一指的大戶,家族產業龐大,有最大的粉絲工廠,還在各地開了粉莊錢莊,并且由于家主隋迎之是公認的開明紳士,家族名聲顯赫。隋見素有過如此富裕的童年,自然在家族衰敗后心有不甘。隋見素深受傳統家族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對于隋家的家業與聲望有著很深的執念,家族復仇的信念支撐著他,使他一次又一次為了光宗耀祖而爭奪家業爭奪粉絲廠。雖然隋見素的舉動有些極端與不妥,但他是為了家族的重新輝煌而奔走,他心中一直懷著家族復興之夢。立足于傳統家族意識與宗法觀念,隋見素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理解的。在他身上,人們看到了家族個體為了家族復興而付出的努力與恒心,符合了傳統的家族敘事邏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傳統農村社會中家族統治的政治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但后來成立的農村生產隊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構人們內心的宗法家族觀念。經過幾千年的沉淀,“家”已內化為人生理想的終極和一種集體無意識,家族中心主義與近兩千年的傳統文化體系神話般地融合在一起,成為所有價值觀念的基點。正是基于此基點,族長至高無上的權威與統治權能夠與家族中心主義融合并延續。而又源于血緣紐帶連接支撐的家族內部使得洼貍鎮的每一個個體都會產生血緣使命感,以此延續發展家族觀念。
二、家族敘事的現代性
作者張煒通過《古船》呈現出小城洼貍鎮的盛衰史,以其獨有的生命體悟解讀家族闡釋苦難,其中特有的現代意識更是給作品帶來了不一樣的生機。他在《創作隨筆三題》中說:“一個優秀的藝術家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忠于他的感情、思索,忠于他所熟悉的一切”“清醒地自覺地尋找與這個世界對話的角度和立足點,使自己與面前的這個世界構成某種關系”。基于這樣的創作理念,他筆下的家族可能已經跳出了體制意義上的家族,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家族,即不同的家族各有其血緣性與一貫性,在現代性視野下亦可解讀出寄托的人文情懷與道理理想。
趙家的命運是與政治運動密不可分的,其在運動中充當了歷史的打手從而改變了家族的弱勢地位。趙炳從族長到整個鎮子上的靈魂人物,趙多多也從無人問津的小混混到備受尊重的團長,身份地位的陡然變化刺激并放大了人性中的殘忍與暴虐。趙炳以施恩者的姿態對受害者的零星寬容也被美化,人們因此對他感恩戴德,為其披上了虛偽華麗的外衣。然而這樣的感恩并不能滿足趙炳心中無盡的欲望,他想要的是人們麻痹思想與情感,變成一味地服從,這其實是人性變相的壓抑,正如隋含章與趙炳扭曲的性關系。在經濟轉型時期,趙家象征為個體意識覺醒的障礙,終究會被歷史淘汰。
李家的命運始終離不開科技,李其生和李知常都是洼貍鎮為數不多的研究科技相信科技的人。小說中機械化的科技讓鎮上的人感到驚慌,李知常不知疲憊地為粉絲廠設計“變速輪”,即使并不被身邊人理解,但他心中科技的信念支撐著他,他認為自己就是注定做這個事的人。就像小說中李知常念叨的“不能停,都不能停——不能停住機械化”,現代性科技力量以勢不可擋的姿態入侵洼貍鎮,李家只是被歷史選中的使者,歷史的車輪始終會向前駛去,那些停滯不前故步自封的人終究會被歷史風塵掩埋,留下的是時代的前沿者與開拓者。小說中,李家幾代人相繼追隨科學的身影是洼貍鎮現代化的風景,也成就了其家族開拓創新的家族精神,成為使洼貍鎮上的民眾擺脫傳統重壓的希望。
隋家的關鍵詞應該是苦難。作品中父親的死去和繼母茴子的服毒自殺,讓隋抱樸、隋含章兄妹陷入了懺悔與贖罪的深淵,他們繼承了家族留下的苦難,繼而在內心自我壓抑懺悔。相較而言,次子隋見素更多是將苦難轉化為家族復興的動力,但動力中承載著難以排解的壓力與沉重的負擔。隋家三兄妹就在這樣的苦難中痛苦掙扎著,展現出那個時代下傳統家族中的個體在自我認知與家族意識沖突矛盾時的掙扎與現代意識的覺醒。
作者筆下的隋含章更多承擔了母親的角色,當家族命運的歷史責任壓在她的肩上時,她選擇肩負起這一切,忍受著心理與生理、靈與肉分離的煎熬,毅然投身趙炳懷抱,默默為家族利益獻身。她希望通過犧牲自我來保衛隋家,即使自己擁有的只有年輕的肉體,但她依然勇敢地站在了哥哥們的身前,以守衛者的姿態承受著趙炳的凌辱。隋含章雖然到最后都未能打破趙炳的“國度”,但她依舊舉起復仇的剪刀公開宣告了自己不屈的抗爭和對趙炳的決絕斬斷,同時也揭露了趙炳的無恥行徑,為洼貍鎮的和平安寧貢獻了力量。
“苦難在現代以來的思想,以及文學藝術中作為人類生活的本質,這與基督教的原罪觀念有關。基督教把人生來就視為有罪,因此把現世生活看成贖罪。”作者將“原罪”的注解體現在隋抱樸的身上,在隋抱樸心中,自己家族曾經壟斷財富的行為是罪惡的,這是導致窮困人民痛苦的原因,所以他有意識地將自我置于精神的苦痛深淵中懲罰自己。“贖罪”是隋抱樸生活的全部,而與此同時不可避免的是人性的欲望被抑制,故而隋抱樸的苦難主要在于其精神世界中欲望與理性的矛盾沖突。隋抱樸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審判與懺悔,他通過三本書籍找到了自我思想的出口,也開始理解新型國家政權的執政思想。在了解了《共產黨宣言》中的基本理論“消滅私有制”后,隋抱樸意識到粉絲廠并不是隋家獨有的,也不是屬于趙家的,而應該歸屬于人民大眾,屬于洼貍鎮的每一個勞動個體。所以他每一次都盡心盡力地解決粉絲廠“倒缸”問題,幫助其渡過難關卻不求回報,在他看來,隋家的家業與聲望都不是自己應該追求的東西,對他來說反而是一種原罪與負擔。然而隋抱樸是傳統家族的長子,是理應承擔起復興家族的使命的,但他卻選擇了放手與懺悔。思想與身份立場的矛盾也彰顯了文本家族敘事的現代性特征。隋抱樸最終意識到人類應該用人性的“愛”與“善”逐漸消除或減弱人性的“惡”,體現出被苦難打壓的人在逆境中重生從而擺脫束縛與桎梏的頑強。
而隋家除了長子隋抱樸的現代性思想與行為,另外叔侄倆的出走也為文本現代性敘事增添了亮色。隋不召在年幼時便與大哥隋迎之不同,他不愿用功讀書,而是喜歡在碼頭上閑逛,表現出其內里反叛與另類的一面。面對父親隋恒德的管教與約束,隋不召依然不屑一顧,死死盯住父親。可以說,隋不召的“出走”意識從小就深藏心底。隋不召是作者有意識塑造的現代生命的典范。一方面,他與洼貍鎮長期遵循的傳統道德相違背,形象放蕩不羈;另一方面,他對人類力量和智慧始終保持愿景,對于航海事業的執著便可以看出。
與隋不召從小萌發的叛逆不同,隋見素的反叛主要源于家族的衰敗與自己多年心血的付之東流。他年幼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家道中落后便積極承擔家族復興的使命,傾注畢生心血,一心想從趙家手里奪回原本屬于隋家的粉絲廠,并試圖破壞趙家的管理與經營,無奈以失敗告終,最后選擇了出走。隋見素的出走行動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但同時預示著他在尋找新的生機。隋見素立足于家族與現代的交匯點,他面對家族曾經的輝煌以及現在的衰敗,難以與現實和解對話,選擇出走漂泊人生,期望走向自己的夢想圣地。“出走”是具有現代意義的行動元素,是對個體生命完整性的追求,是對傳統家族觀念的反叛與離棄,展現了年輕人在追求理想時自我意識的覺醒。
三、啟蒙敘事與家族敘事有機交織
總體而言,小說采用的是全知敘事視角即零視角,但敘事者“不但置身事外,且亦置心事外。他仿佛站在一個山岡上,對腳下爭斗著的人物一無偏護。他犀利的目光直射歷史和人物的內心深處,并客觀冷靜地講述著他的發現。”在張煒的筆下,隋家不再是那種剝削人民、道德墮落的典型民族資產階級,而是有文化有節操的家族。一家之主隋迎之是公認的開明紳士,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長子隋抱仆的性格,隋抱仆從父親那里承襲下憂患意識與原罪意識,以至于隋抱仆前期被強烈的負罪感裹挾,處于壓抑與懺悔中,后期在精神世界中獲得解放。
對于趙家這個搭上了時代順風車的家族,敘述者并沒有因其農民起家為革命階級的代表而一味美化其形象,而是揭露出由于地位身份巨變而膨脹的家族內在的狹隘復仇意識。小說并沒有把四爺爺趙炳塑造成臉譜化的壞人,他并不是扁平人物,敘述者以旁觀者的態度展現出他圣潔外表下的自我放縱以及對正義的扭曲。他作為長輩,卻長期以干爹的身份在隋家小姐隋含章身上滿足自己的占有欲。反觀隋抱仆、隋見素這兩個曾經的貴族子弟,失去了曾經的富裕生活,淪落到了壓抑人性、自我遏制的地步。隨著社會發展歷史變革,經濟改革與思想解放的潮流無意間又為隋家的復興提供了機會,家族個體的命運始終與時代洪流息息相關。
面對當代鄉村社會的歷史變革,不可否認的是家族主義對人們根深蒂固的影響,革命者正義的行為背后可能含有一定的家族復仇動機。張煒在《古船》中從人道主義立場與人性關懷的角度重新審視農民革命,他發現,一方面農民翻身解放的歷史合理性與推翻封建政權斗爭的積極性,同時他們濃厚的家族觀念與家族復仇的強烈欲望則暴露出獸性的泛濫,家族意識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人們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階級意識與家族觀念交織在一起造成歷史與人性的悲劇。即使封建大家庭在歷史中瓦解,但人們的家族觀念與家族意識依然存在,以血緣為紐帶的親屬集團對個體、家庭都有著天然的吸引力與感召力,讓思想還未解放的人們不自覺遵從。人們難以脫離家族觀念,導致幾十年都沒有走出宗族集團統治以及族長統治的傳統。盡管工廠改變了管理制度條例,但家族主義家族觀念生長的溫床已存在多年,如果沒有成功啟蒙農民的思想,實現其個體意識覺醒,那么改革就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
“這個敘事者用一雙悲天憫人的眼睛俯視著人間的苦難,這雙眼睛絕不是冷漠的,而是布滿血絲的,從眼睛里放射出的目光,有著灼人的熱量,這雙眼睛里有著憂愁,更有恐懼和震驚……這個敘事者用一雙悲天憫人的語調訴說著人間苦難,這種訴說也絕不是冷漠的,而是同時包含著這樣的質問:人間為什么會是這樣?人間為什么要有這樣多的苦難?人對人為什么會如此殘忍?”
在《古船》中,敘述者的現代性啟蒙立場使文本內涵超脫于家族恩怨情仇,而在傳統鄉村家族復興與復仇中開闊視野進行探究。敘述者立足于人道主義,將洼貍鎮上家族的苦難上升到民族的苦難,廣闊的悲憫情懷增添了文本的現實內蘊。同時,作者的現代化啟蒙思想和人道主義情懷,充滿了人性的同情和憐憫,使小說具有了難得的思想深度和歷史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