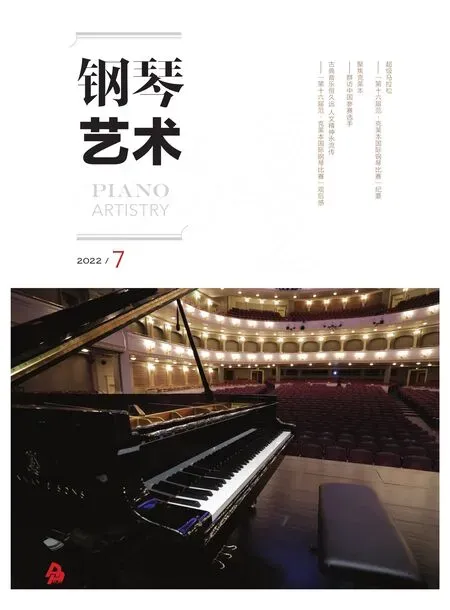“心敏達聰,內外兼修”
——淺談器樂協作鋼琴初級演奏技巧
文/謝貝妮
隨著器樂協作鋼琴專業在各大音樂學院的設立及學術界對協作鋼琴這一專業的日益關注,越來越多鋼琴專業學生對這個領域展現出濃烈的興趣。他們在此之前都有著多年的鋼琴獨奏學習經歷,其中不乏具有相當音樂才能和技術水準的演奏者。但與鋼琴獨奏所不同的是,協作鋼琴作品從讀譜階段的準備期開始,就需要鋼琴演奏者將合作者的音樂內容納入思考與設計的范疇。這就意味著即使面對著樂譜中熟悉的鋼琴音樂語匯,協作音樂鋼琴演奏者也需要使用與獨奏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技巧演奏方式來彈奏。通過近幾年器樂協作鋼琴的教學工作,我逐漸產生了一些心得與想法,希望借此文能與大家分享。
在進入合作階段之前,鋼琴演奏者首先需要完成鋼琴聲部中技巧部分的設計及練習。這部分的工作不僅包括準確彈奏出譜面上的音符、節奏、運音法(articulation)等方面的“顯性”內容,還需要鋼琴演奏者根據作曲家的創作風格、作品創作時代的演奏習俗、作品情感的表達內容,以及演奏者自身的個性解讀,就音色、音量、觸鍵、鋼琴內聲部平衡、速度等方面的“隱性”內容做出更深層的判斷和選擇。粗看以上內容,其過程似乎與我們學習鋼琴獨奏作品時沒有不同。但是,在鋼琴與器樂協作作品中,由于另外一種或幾種完全不同門類樂器的加入,就使得鋼琴在整個音樂作品中的角色地位和演奏思維方式不同于鋼琴獨奏作品。為了兼顧其他樂器的器樂特性、音色特點,鋼琴演奏者需要對以上提到的“隱性”內容做出有別于鋼琴獨奏作品演奏方式的調整。
對于經驗不足的器樂協作鋼琴演奏者來說,可以通過作品中一些較為固定的織體形態,尋求一些協作鋼琴聲部演奏的基本規律。
一、鋼琴聲部的“內向”演奏技巧
鋼琴“內向”技巧,主要指演奏鋼琴聲部時,鋼琴演奏者自身需要解決的演奏技巧。
1.鋼琴聲部中“經過型”樂句的基本音色和分類
在大量鋼琴器樂協作作品的鋼琴聲部中,時常會有一個聲部的織體為時值單位較小的快速樂句。它們以級進音階、分解琶音、二度或三度甚至六度級進等不同形式,通過迂回、盤旋的線條行進方式來填充整個作品的聲部空間。這種類型的音樂內容在古典時期的器樂鋼琴協作作品中尤為常見。在這個時期,鋼琴聲部與合作樂器的關系還未變得極為緊密,聲部關系還相對簡單。因此,鋼琴演奏者能通過對此類內容的學習,尋找到適合協作作品中鋼琴聲部的音色及音樂氣質的基調。依照古典時期鋼琴音樂審美的特點,無論譜面上的力度為強或弱,鋼琴演奏者都需要使鋼琴的音色富有光澤并具有一定的“顆粒感”。這需要演奏者在演奏過程中減輕大臂的重量,更多地依靠來自掌關節發力所產生的快速擊鍵,手指尖的觸點集中,以及手腕略微地帶動來完成樂句的演奏。但是,為了兼顧與其合作的弦樂樂器音量、音色,以及演奏方式,在協作鋼琴作品的快速樂句中,對鋼琴音色的清晰度及輕盈感的要求要比同時期獨奏鋼琴作品要更高。因此需要鋼琴演奏者盡量減少鋼琴較容易產生的余音混響,并適當柔化鋼琴音色的亮度。
在古典時期的鋼琴器樂協作作品中,“經過型”樂句多位于鋼琴聲部。因為相較于弦樂樂器,尤其是大提琴或中提琴,鋼琴更善于演奏并表現這種持續、快速、密集音型的樂句。同時,這些作品的創作者本身多為具有極高演奏能力的鍵盤演奏家(特別是莫扎特和貝多芬,擅長演奏當時的各類鍵盤樂器),因此他們除了熱衷創作數量極多的鋼琴獨奏作品之外,還毫不吝惜地在鋼琴器樂協作作品中為鋼琴聲部譜寫了可以展示鋼琴演奏者各種技巧的樂段,它們可以根據織體形式及聲部功能分為以下幾類。
(1)和聲功能類
這些片段中,鋼琴聲部通過音階、音程分解琶音、雙手交替琶音等織體形態,在演奏過程中完成或“夯實”樂句的和聲和調性。
例1中的第1、3、5、7小節,鋼琴聲部在弦樂和鋼琴左手聲部休止的狀況下,以和弦轉位琶音和音階的樂句形式,完成了從F大調到d小調的調性轉換。但是,在實際演奏過程中,鋼琴演奏者是否需要將經過樂句中的每一個音符都以同樣清晰、通透的方式演奏呢?當然不是。考慮到作曲家在此處的力度標記和此樂句在整個聲部構造中的功能屬性,鋼琴演奏者只需要將轉位琶音中每組十六分音符節奏型的首音略微著重,而隨后的三個和聲性音符使用略微分離的、干凈而富有光澤的音色演奏即可。而第7小節的音階則要有“一蹴而就”的效果,鋼琴演奏者不必糾結于每個單獨音符的清晰度,而是著力突出位于第7小節的第一、第三拍和第8小節的d小調主音D音,以強調樂段中最終調性的確立。

例1 貝多芬,《大提琴奏鳴曲》(Op.5,No.1),第一樂章
在譜例2中第1至4小節,旋律聲部位于小提琴聲部,雙方樂句的目的都是為了凸顯和強調D大調的主、屬和弦功能,以強調作品的D大調調性。小提琴聲部是附點節奏織體形態,鋼琴是十六分音符琶音織體形態,都為力度f,并且位于同一音域。在同時考慮這些因素,以及鋼琴聲部僅作為和聲功能的情況下,鋼琴演奏者需要將自己的音樂地位依附在小提琴聲部下,跟隨小提琴演奏者的氣息,使用可以烘托弦樂聲部的音量,同時依舊保持十六分音符音色的清晰度和亮度。請特別注意位于每一拍首音的四分音符,這里莫扎特通過延長音符時值的方式,意在提示演奏者使用“手指踏板”的奏法,從而與小提琴聲部形成縱向和聲。因此鋼琴演奏者在此時應當慎用踏板,同時在時間上將四分音符與十六分音符之間做出極細微的分割,從而使“和聲支柱性音符”和“和聲填充型音符”獲得區分。

例2 莫扎特,《小提琴奏鳴曲》(K.306),第一樂章
(2)旋律功能類
自從意大利作曲家多梅尼科·阿爾貝蒂(Domenico Alberti,1717—1740)創作了分解和弦形態的伴奏音型,這種既保持和聲性又富有流動感的織體就在鍵盤作品中被作曲家們廣為使用,并被稱為“阿爾貝蒂低音”(Alberti Bass)。在古典時期及之后的音樂歷史長河中,這種新的鋼琴語匯不僅應用廣泛,還被作曲家們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改變。我們可以看到各類分解琶音變形織體、多種音程度數的分解音程上下行織體,以及回旋式音型織體。在這些類別織體的鋼琴演奏中,演奏者需要從建立“立體”音響層次的角度出發,將單聲部音型的織體結構衍化成多聲部層次的織體,即在演奏中將和聲主干音(通常為正拍節奏位置,或音程突然大跳的位置)剝離出來,并前后形成橫向樂句走向,而剩余音符作為主干旋律音的和聲填充,起到帶領音樂平穩行進,或趨向緊張,或趨向松弛的作用。
在例3中,鋼琴右手聲部為三連音分解琶音下行織體。此時鋼琴左手聲部位于整體音響的低音區,大提琴聲部位于中音區,同時在節奏律動上與鋼琴左手聲部形成相互填充和呼應,這兩個聲部的音樂行進方式都是對相對穩定和堅定綿長的。但鋼琴右手聲部,自小字三組音域起直至小字組低音區,通過主干音旋律(每組三連音音型的首音)始終強調c小調的屬和弦和主和弦關系,輔以密集、快速的和聲音符填充,猶如利刃穿透了大提琴與鋼琴左手聲部營造的穩定狀態,讓整個音樂情態呈現了排山倒海之勢。

例3 貝多芬,《大提琴奏鳴曲》(Op.5,No.2),第二樂章
在例4的第1至2小節中,大提琴聲部和鋼琴左手聲部都是同樣的節奏律動,音樂行進平穩且和聲變化簡潔。而演奏者可以通過譜例里的方框和圓圈,看到鋼琴右手聲部的十六分音符織體中,旋律主干音被分割成了高、低兩個聲部,這些旋律主干音巧妙地穿插在穩定的大提琴及鋼琴左手正拍旋律律動中,為樂曲的律動帶來了“弱拍向正拍傾向”的變化。尤其在第4至7小節中,鋼琴右手聲部的旋律主干音還發生了不規律的節奏變化,這些主干音可以清晰地幫助演奏者體現這個片段中由g小調—F大調—f小調—V/降E大調的整個調性轉換。同時,整個樂段處于p力度狀態,且鋼琴右手聲部位于整個作品音響的高音區,音樂情緒處于由繁至簡、由動至靜的過程中,因此需要鋼琴演奏者在弱奏力度的范圍中,使用掌關節支撐并近乎貼鍵地快速觸鍵,從而使旋律主干音能從這些和聲填充音中穿透出來,同時又不會過于明亮,而破壞了此處接近夢幻的情境。

例4 貝多芬,《大提琴奏鳴曲》(Op.5,No.1),第一樂章
2. 鋼琴聲部中起“和聲性”樂句的演奏
在這些初級技巧階段所涉及的音樂片段中,除了前文中提及的,鋼琴以“快速”樂句的形式為協作音樂的整體音響構架起到“填充”作用之外,通常還需要擔任整體音響構架中和聲支撐這一角色。在古典時期奏鳴曲中,鋼琴聲部會以單音、柱式和弦或八度音程的方式來實現音樂中的和聲支撐。在鋼琴獨奏作品里表現和聲支撐時,為了體現鋼琴自身音響的空間感,演奏者通常會特別突出低音聲部,以凸顯琴槌擊打在粗制琴弦上所產生的轟鳴感,甚至會增加一些踏板以延長琴弦的震動。但是在協作作品演奏中,鋼琴演奏者就需要極為謹慎。因為此時的鋼琴聲部僅作為“通奏低音”的聲部角色,更多的是體現和聲在情緒表現中的功能,而非和聲在音響表現中的功能。由此,對于八度音程織體的低聲部,演奏者不要刻意突出根音,僅僅從增加音響厚度的角度出發即可;對于柱式和弦織體的低聲部,鋼琴演奏者可以聆聽和感受弦樂合作者拉和弦時的狀態,觀察他們演奏和弦時手臂發力、收力的方式,要追求鋼琴音色發音的“蓬松感”,尤其避免演奏時在“音頭”上產生“剛直感”。在此要提醒大家的是,對于這樣的低音聲部演奏,踏板的使用要極為謹慎。由于現代鋼琴的規模、制式、體量與合作弦樂樂器差距過大,因此鋼琴本身的共鳴在音響平衡中就需要有所收斂。所以,演奏者可以更多地通過手指延音或踏板“淺點”的方式來控制音符的時值和共鳴。同時,在柱式和弦的演奏中,可以適當調整內聲部的音色、音量,在減輕音柱效果厚重感的同時,依舊可以保持其和聲內部聲部橫向進行的清晰度。
在例5中,鋼琴右手聲部與小提琴聲部以三連音節奏型交替進行呼應,而鋼琴左手聲部以分解八度音程織體強調D音功能,因為此時音樂正處于由D大調至G大調轉調的“糾結”階段(鋼琴右手聲部堅持C音,而小提琴聲部堅持C音,可見雙方在調性上的“爭奪”)。考慮到鋼琴右手聲部音量、音色與小提琴聲部的平衡,以及作曲家標注的p力度記號,雖然左手聲部在第1至4小節中既作為D大調主功能,承擔著G大調屬功能,也只需要強調其中的低音聲部(即每一拍中的正拍音符),將高音聲部(每一拍的后半拍)作為和聲余音的補充,而不需要將每個音“實打實”地演奏出來。

例5 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Op.96),第一樂章,第172至180小節
二、鋼琴聲部的“外向”演奏技巧
與鋼琴獨奏相比較,在協作演奏的過程中,鋼琴演奏者感到的最大不同在于需要與同伴進行大量溝通,共同制定音樂藝術成果的最終目標,并彼此做出協調,甚至在某些時候需要做出讓步。優秀的協作鋼琴演奏者要懂得與合作者一起根據樂段的需要迅速變換角色,或主導、或跟從。如果演奏者們對誰主誰從沒有清晰的意識,那么在演奏中,音樂的勻稱感、節拍,以及樂句的走向和形態都會產生沖突。
1. 鋼琴“對位旋律”聲部的演奏
在協作鋼琴作品中,音樂的發展更加著重于樂器之間的交互對話,每個樂器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都會主導旋律線和節奏動機。這都需要演奏者對作品進行深入的分析,尋找并定位各聲部的主次關系。前文中提到,鋼琴聲部中存在著大量時值單位較小的快速樂句。在很多時候,這些樂句看似精彩和華麗,但卻并非為主導聲部,因此需要仔細聆聽主導聲部的發音、音色和速度,并做出相應的調整。
在例6中,大提琴聲部處于旋律主導地位,節奏律動綿長且包含跨小節連線和切分節奏,由此引發了重音位置的重置,從而使音樂在下行方向進行中具有相當的緊張感。而鋼琴聲部以均勻律動的級進上行樂句與大提琴聲部形成反向移動,更增強了音樂情緒的“擠壓”。鋼琴演奏者在彈奏這個片段時,不可孤立地沉浸在自身聲部的音樂情緒中,否則很容易不由自主地隨著音域的上移產生漸強甚至漸快的音樂效果。反而要遵從大提琴聲部的發音規律和音色特點,通過指腹觸鍵,演奏出濃稠的連奏效果,尤其在第5小節后鋼琴聲部成為八度織體之后,更加要減少音頭發音時的瞬間觸鍵感,著重于突出緊張、綿延的音樂情緒。同時要仔細聆聽合作者的演奏個性,維持住與反向大提琴聲部之間的平衡,避免“頭重腳輕”的現象。

例6 貝多芬,《大提琴奏鳴曲》(Op.69),第一樂章
在例7中,雖然鋼琴右手聲部擁有最繁忙的聲部線條,但卻并非是這一樂段的主要聲部,整體音樂的走向和框架反正是由鋼琴聲部的左手聲部和小提琴聲部共同構架(見例7中的直線指示)。它們共同組成了切分節奏句型(第1至4小節),以及交錯式向上級進的對話樂句(第5至7小節),因此在整體的音樂呈現過程中,演奏者們需要讓聽眾抓住這些框架聲部和它們的發展方向。因此,鋼琴演奏者需要從音量、發音、樂句的展開程度等方面出發,與小提琴合作者進行良好的合作。而對位旋律聲部則要在第1至4小節中處于和聲性的從屬地位,只需要勾勒出調性音(圓圈音)。此處鋼琴聲部的觸鍵一定要小心控制,由掌關節發力,保持指尖觸鍵瞬間時的集中度和速度,使整體音色即有調性音符所構成的外部樂句輪廓,而剩余經過音符又能產生和聲烘托音效。尤其是在第5至7小節中,鋼琴右手聲部也通過大跳、休止符的手法,產生了與另外兩個框架聲部相呼應的節奏型,并穿插其中,具有相當的趣味和競奏感。隨著音樂的發展,鋼琴右手聲部最終在第7小節獲得了音樂的主導權。同樣,在第6至8小節的演奏過程中,鋼琴演奏者也需要通盤考慮,兼顧合作者。盡管右手聲部最終會獲得主導權,但在第6、7小節中,其本身所處的音域與小提琴聲部相比就更加容易被聽眾注意,因此反而要有所收斂,并小心音樂“膨脹”的幅度。而此時則應當更加留心左手聲部與小提琴聲部之間的匹配度,因此對于鋼琴演奏者來說,各聲部之間的取舍是需要做出精密安排并以極好的技巧來予以支撐的。

例7 莫扎特,《小提琴奏鳴曲》(K.380),第一樂章
2. 鋼琴“平行和交替旋律”聲部的演奏
在古典時期的鋼琴協作作品中,鋼琴聲部時常以相同音高、相差八度、間隔三度或六度音程,或以復調等方式與合作者一起演奏一段旋律,或鋼琴聲部只演奏旋律的某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交由合作者完成。當旋律線在不同樂器演奏者之間接力時,每一位演奏者都要做到角色的無縫轉換。與“對位旋律”聲部在整體聲部中的次要作用不同,“平行旋律”聲部一定是作品整體聲部中最重要且最需要凸顯的聲部。但當“平行旋律”聲部由鋼琴和其合作者共同完成時(或同時進行,或交替進行),此時鋼琴演奏者最需要考慮的則應當是如何處理與合作者之間的關系。
在例8中,鋼琴右手聲部與小提琴聲部完全一致。在第1至8小節中,鋼琴聲部位于小提琴聲部上方八度小字二組音區,第9小節后,兩者進行了交換,鋼琴聲部被置換到小字一組音區。按照弦樂樂器的發音特點,它們會在其樂器音域的低端產生極富特質的美妙音色(例如小提琴的G弦、大提琴的C弦)。但是,由于樂器體量的限制,這種音色的發音能量與現代鋼琴相比,也是極為懸殊的。因此,在這個片段第1至8小節的演奏中,鋼琴演奏者盡管位于更重要的上聲部,但為了保持與小提琴聲部的平衡,就不可按照獨奏時的音色處理,而是要根據合作者的音色特點,對鋼琴的音量和音色稍加控制。尤其在第9小節音域變更后,鋼琴演奏者更加要降低右手聲部音色的“濃度”,而對于左手聲部,則要按照“對位旋律”聲部來進行處理。這些音量、音色的控制都需要鋼琴演奏者具有極度敏銳的聽辨能力以及強大的演奏控制力。

例8 莫扎特,《小提琴奏鳴曲》(K.302),第二樂章
在例9中,鋼琴聲部在第1至3小節與小提琴聲部進行了“交替旋律”的聲部演奏,這三次進入分別為A大調的V級、Ⅲ級、Ⅰ級,因此演奏者雙方都應當遵從和聲的緊張度來安排各自的情緒和演奏處理。尤其是鋼琴演奏者很容易將注意力放在第3小節的右手聲部中,而忽視了該小節極為重要的左手調性主功能聲部,從而造成整體音效“頭重腳輕”的效果。與此同時,此處鋼琴右手聲部sf音也不可以過于尖銳,要協調小提琴合作者的發音速度和特點,形成協調的三度和聲效果。

例9 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Op.12,No.2),第三樂章,第72至79小節
在例10中,鋼琴的左右手聲部與大提琴聲部展開了一個充滿糾纏、競爭且彼此合力的音樂過程,這對鋼琴演奏者來說,委實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樂段。由于大提琴的音域始終被包裹在鋼琴的左右手聲部之間,因此鋼琴演奏者就必須經過審慎的分析,來選擇恰當的演奏方式。第一個樂節位于第1至2小節。在第1小節中,鋼琴右手聲部在高音區以比大提琴聲部滯后一拍的卡農方式進入。而第2小節時,大提琴聲部停止,鋼琴聲部則進行了旋律延展。盡管作曲家在兩個樂器的聲部中都標注了f力度,但根據大提琴聲部先行進入的重要性及音量的局限,鋼琴演奏者在第1小節中,右手聲部要相對控制,以保證大提琴聲部進行的清晰度,而在第2小節后才可以達到真正的音量。第二樂節位于第3至7小節。大提琴聲部依舊位于鋼琴左右手聲部之間,并且與鋼琴左右手聲部以反向行進方式來“抗衡”。因此鋼琴演奏者更加要控制音量,尤其是與大提琴聲部音域重合的左手聲部,否則此處極易蓋過大提琴的旋律。在第4、5小節中,鋼琴右手聲部以同音方式銜接并發展了大提琴聲部的旋律元素。因此在演奏重疊音時(第4、5小節第二拍),鋼琴聲部更要配合大提琴聲部sf的發音方式,以調整自己的音色和音量。

例10 貝多芬,《大提琴奏鳴曲》(Op.102,No.2),第一樂章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學習協作鋼琴的初始階段,需要鋼琴演奏者從“內向”和“外向”兩個方面來提升自己的技巧水平。一方面,針對鋼琴自身的演奏內容,鋼琴演奏者要建立一些與鋼琴獨奏狀態下有差異的聲音概念,并就相應的音樂類型調整自身演奏所使用的技術手段和演奏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在演奏中增加了其他合作樂器類型及演奏個體,音樂的進行方式就由單一體的持續型方式轉變成多量體的層疊、交替型方式。所以,鋼琴演奏者就需要更為靈活地根據音樂形態的變化、合作樂器的演奏特點、合作個體的演奏習慣進行實時、實地的調整。相較于協作鋼琴演奏“內向”技巧,這種充滿變數的“外向”技巧,更需要鋼琴演奏者具備過硬的鋼琴技巧能力、強大的聽辨審視能力以及內心對音色想象力的儲備,才能與合作者一起完整地呈現出自己對作品的藝術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