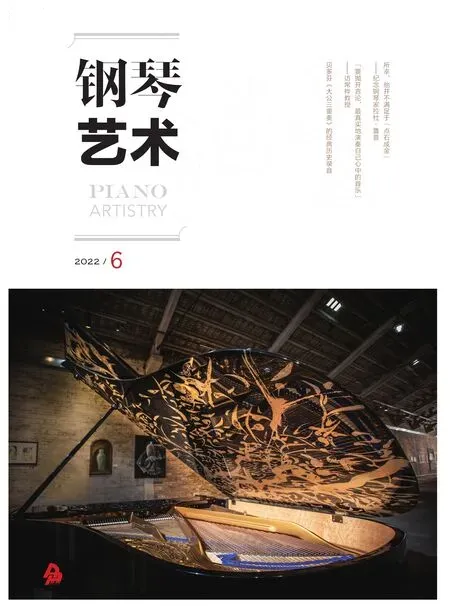『要拋開言論,最真實地演奏自己心中的音樂』
——訪常樺教授
訪談者/郭 煦

訪者按:2021年10月在“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中央音樂學院常樺老師的多位學生入選了這項重大賽事,并且以各富特點、極具個性的演奏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常樺老師是我國著名鋼琴教育家,她從教二十多年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培養了一大批鋼琴專業人才,學生們從附中畢業后考入了中央音樂學院、柯蒂斯音樂學院、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漢諾威音樂學院等世界名校。“柴科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的決賽現場臨危不亂的安天旭,及在“肖邦國際鋼琴比賽”、2017年“范·克萊本鋼琴比賽”中因其突出的藝術個性而廣受關注的孫榆桐已經活躍在世界各地鋼琴舞臺,成為鋼琴演奏領域的佼佼者。這樣驕人的教學成果,不禁讓人好奇:常樺老師在鋼琴教學中到底有什么獨特的方法或秘訣?帶著這樣的問題,我采訪了常樺老師。

Q(郭煦):在剛剛結束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您有多位學生入選了這項賽事,并且每個學生的演奏都有其鮮明的個性和閃光點。這與您為他們所打下的堅實基礎是分不開的。在教學當中,您是怎樣在幫助學生打好扎實基礎的同時,挖掘學生的藝術個性的呢?對于學生的培養有什么具體的方法呢?
A(常樺):嗯,的確是的。在這一屆備受矚目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比如你們三位——郭煦、孫榆桐和王紫桐,都是曾經從附小到附中一直跟隨我學習的學生,有些人開始的時間甚至更早,從很小就跟隨我學習,每個人大概都有六到八年的時間。看到你們在這樣的比賽場上展現自己的藝術個性和音樂才華,我感到非常高興,而且,我自己也很有收獲。如果說到打基礎,我覺得很難條理化地總結出一二三,因為教學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過程。但是我想對于每位老師來說,學生在附小到附中的學習階段,也就是八九歲一直到十七八歲的這幾年是非常重要的。從老師的角度來說,我是要為學生打下所謂的“基礎”,主要指“技術”和“音樂”這兩個方面,力求讓這些年幼的學生有一個非常扎實、穩定的基礎。
從技術角度來說,要盡量開發每個學生的手的運動能力。雖然每個學生手的先天條件各不相同,但是作為老師,應該讓孩子們手的能力在這個階段盡可能地得到充分發展,通過幾年的訓練培養,把手指的機能——就是最基礎的運動能力,最大化地挖掘出來。那么當他(她)未來進入到本科,由下一位老師接手時,也會覺得這個學生的手是能力強大、訓練有素的,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目標。
關于技術方面,我還想補充一點,就是我自己在教學過程中特別不喜歡在學生之間進行技術及手指條件的比較。我不認為某一種技術是所有人都必須要達到的,反之,要找到每個學生自己的技術特點,發展自己的演奏,這才是最為重要的。比如,對于一個先天手小一些,或者身體相對男生來講弱一些的女孩子,在彈奏和弦或八度的時候,不像男孩子那么方便,那我就要給這個女孩子的技術找一條路,要把她的優勢,比如跑動和靈敏度發揮到極致。還有些學生可能彈奏李斯特練習曲比較吃力,但他(她)可能極其適合彈奏德彪西的練習曲,因為聲音色彩和想象力非常出色。總之,每個人都是有路可走的,最重要的是最大化地把他們的潛能和技術優勢發揮出來,而不是“力求”每一個人都變成技巧全能的類型,更不需要因為“技術”而煩惱。
第二個方面就是音樂層面,我認為這個階段的教學要同時走兩條路,一條是廣泛涉獵,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曲目都要學習,盡量多彈。在這個前提下,第二個重點是要在這個廣泛學習的過程中去發現學生所擅長的曲目類型,感受每個學生自身的藝術特性。當遇到重要的場合時,比如比賽、音樂會等,就要揚長避短地選擇曲目。
Q:也就是說分為兩方面累積和學習曲目,既要廣,又要精。這讓我想到,準備一次這樣的大賽所需要的曲目量是十分龐大的。您覺得,對于參加這種比賽的選手來說,應當用一種什么樣的方法和方式去備賽呢?
A:我認為參加比賽要有計劃,要提前知曉并了解今年或明年有哪些比賽,這一定不是臨時想起來才決定的,這種習慣要在附小、附中時就開始養成。大多數比賽都有一個固定的循環周期,比如兩年一次,或是一年一次等。一個小型比賽,通常只有一輪,雖說只需要準備十多分鐘的演奏曲目,但是最少也要提前三個月就開始計劃。再比如說,上半年的時候就要開始計劃下半年參加的比賽,下半年就要計劃明年的比賽。臨時做出參加比賽的決定,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剛才我們談到的是小型比賽,對于像肖賽這樣的大型比賽,就更應早做準備。在當今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大家都知道幾年之后有哪些比賽,那么可能好幾年前就要開始進行相關曲目的學習。比如說當你中學的時候學過的很多肖邦作品,可能將來長大進入大學,或18歲以后參加成人的肖賽時,以前的曲目幾乎都是用得上,這個積累是很重要的。通常,比賽所選用的樂曲,大多數都是相對成熟的,就是我們所說的“學習過的舊曲子”。但是,并不是意味著在比較長時間的練習和演奏當中一成不變,它其實一直是在變化、在“成長”,舊曲子仿佛有“生命力”。我自己的感覺是,這種成人的大型國際比賽,可能曲目當中起碼有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應該是比較成熟的“老”曲子,新曲子的數量是相對少一些的,這樣的話,這個人在舞臺上會比較心里有底。現在很多成人國際比賽那么難,像“肖邦”“柴科夫斯基”“利茲”等這些比賽,每四年,甚至五年一次,有很多人可能會參加兩次,那在這個過程中就較少會全部用新的作品了。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他(她)仍然是有收獲的,每年彈起來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我在教學時,如果覺得這個學生適合參加下一屆的某個比賽,那我就會有意識地結合比賽章程來學習一些曲目,等到兩年之后,這個比賽真的來臨了,積累的曲子就是用得上的了。因此我想說,比賽總是要早準備,心里要有數,永遠都要有計劃。
Q:確實,我在這次比賽當中演奏的很多曲目其實在附小、附中時期就跟您學習過,例如肖邦的《船歌》等。還有孫榆桐在比賽當中有很多曲目也都是在附小、附中時期就跟您學的。我還記得您當時跟我說“每過幾年再回來演奏同一首曲子時都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這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您能進一步講一下這個問題嗎?
A:我也記得非常清楚,肖邦《船歌》是我們在小學六年級升初一的那場考試時學習的。這其實也是我的一個教學習慣,提前準備一些將來能夠“用得著”的曲目。比如孫榆桐這次在肖賽的一些曲目,還有他參加的克萊本比賽(2017年),從初賽一直到半決賽三輪的演奏視頻中,我特別高興地看到有好多首曲子都是我們以前積累的,比如利蓋蒂的《魔鬼的階梯》、巴托克的《奏鳴曲》、肖斯塔科維奇的《前奏與賦格》(No.24),等等。看完你們的演奏,我覺得當年的教學是有成效的,當時在附中參加比賽已經拿出來用過并且獲獎,但是現在,在這么難的克萊本比賽和肖賽里面再彈,又是煥然一新,更上了一個臺階。所以,積累是特別有用的。當我在聽孫榆桐彈巴托克《奏鳴曲》和你彈《船歌》的時候,我覺得有一些處理和感覺跟我自己腦子里面構想的是不一樣的。所以反之,你們今天的演奏,對我也有很多新的啟發和體會,我覺得可能這個就是師生之間的一種“交流”,也是我們所說的教學相長吧。這反映了隨著演奏者自身的成長、成熟,相同的曲子會煥發出新的光彩、新的生命。不過,也有相當多的學生變化不大,聽他(她)演奏的感覺仿佛和年幼時差不多,這就是“人長大了,音樂沒有長大、沒有成長”,演奏還是學生味兒。

直到今天我也仍然保留這種教學習慣——就是我在給所有的學生選曲目的時候,都希望這個曲子既具有學術性和教學上的意義,同時我也會想到,這個曲子有一天他在什么場合是能用得上的。另外,要非常留意哪些曲目適合參賽。我記得以前學生出國比賽,我都請他們幫我帶一份比賽的冊子,我就是要注意一下別的選手都彈什么曲目,尤其是特別會留意一下那些獲獎的選手彈什么曲目。當然現在不存在這個問題了,因為網絡上遍地都是關于比賽的信息,冊子就沒有以前顯得那么重要了。
Q: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過您的著作《〈肖邦練習曲〉教學與演奏指南》,在這次肖賽中,對鋼琴演奏者具有挑戰性的一項就是要演奏四首肖邦練習曲(海選視頻和預選賽兩首,正賽第一輪另外兩首),并要求每輪兩首練習曲必須緊挨在一起演奏。這對于演奏者的手指機能和音樂素養都有著很高的要求。而我觀察到并不是每一位選手都可以完整并出色地將兩首練習曲完成好。您覺得肖邦的練習曲跟其他作曲家的練習曲相比,有什么特殊性?在演奏方面具有什么樣的挑戰性?
A:肖邦練習曲兩首連在一起彈真的是很難的。你也說到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完成得很精準。雖然肖邦有24首練習曲,但是在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特別擅長的一條或者兩條,那這一兩條也許在前一輪的預選賽里面就用完了,而等到正賽開始的時候,他(她)不得不換成另外兩首可能沒那么有把握的練習曲。所謂練習曲的技術,我們絕對不是指那種最膚淺的“手指運動”,而是指“控制力”。演奏者在舞臺上是否穩定,取決于他(她)對手指是不是能夠“長期”控制得很好,而不是取決于偶然性。偶爾有一次控制得好,并不是真實的,所以練習曲是一個“危險”的項目。當然每個人狀態不一樣,心里想法也不一樣。我個人認為練習曲特別見功夫,尤其見這個人小時候的功夫。也就是說在年幼的時候,訓練腦子里想什么手就能控制什么是特別重要的,大概八九歲到十八九歲這幾年,是大腦和手結合的最佳年齡。假如小時候比較弱,長大以后就要加倍刻苦地練習,才能夠彌補一些不足。另外,如果要想一直在臺上有出色的表現,除了小時候的功底外,在成長的過程中也一天都不能落下,要持之以恒地練習,心里才會完全有底,手才會一直保持最好的狀態。

至于說肖邦練習曲跟別的作曲家的練習曲有什么不同?我想,可能是因為肖邦實在太出名了,他有他特別固定的音樂風格。所以即使演奏的是練習曲,尤其當把它放在肖賽這樣一個背景下,觀眾也還是希望能夠欣賞到他的詩意和浪漫。而相同的練習曲放在別的國際比賽時,可能感受就沒有那么強烈,只要彈得準、彈得漂亮就可以了。恰恰由于是放在肖賽上,使它擁有了更多對聲音的想象、節奏的把控等要求,音樂上也要更有了趣味。因此,我認為即使是練習曲,當技術問題解決以后,也應該用彈奏樂曲的那種細心和對細節的處理來看待,也就是要把練習曲的音樂性展現得更多一些。
建筑組團分區景觀及中心環路景觀: 各建筑組團分區周邊,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分區置景,統一中有變化,變化中有統一。建筑組團景觀與中心環路景觀結合形成園區特色景觀區。
Q:看到很多鋼琴家會選擇完成全套肖邦練習曲,您覺得這是有必要的嗎?
A:我自己覺得這個選擇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的。主要看這位演奏者的目的是什么,比如有些演奏者是想把肖邦成套的練習曲作為音樂會奉獻給大家,那這個意圖是很明確的。這個意圖就像彈全套的24首肖邦“前奏曲”或巴赫“平均律”一樣,是一個“藝術性”的目的。如果是單純地想要證明手的技術能力,我自己覺得并不是非常的必要。當然,一位年輕的演奏者如果24首肖邦練習曲都能高質量地完成,這足以說明他的手具有非常強大、非同一般的能力。但是絕大多數人是不可能達到這個水平的,大部分人會有幾首是自己很擅長、很拿手的,我覺得這也足夠了。比如有些人手特別的小,那他彈第一條(Op.10,No.1)這樣大跨度的,或者“雙八度”(Op.25,No.10),是完成不了的;可是也許雖然他手小,但是卻極其靈敏的,那么他可以彈第二首(Op.10,No.2)或者是“雙三度”(Op.25, No.6)。另外,練習曲Op.10之4、8、12等,都是非常精彩的作品,掌握其中任何一條,都足以代表演奏者的水平。總而言之要有自己的一個方向,這是很重要的。
Q:不只是在這次肖賽中,您的學生極富個性及感染力的演奏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上一屆柴賽中,您的學生安天旭更是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安天旭臨危不亂的心理素質。我想,參賽經驗和心理素質對于一位鋼琴演奏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您在教學當中如何培養并訓練學生這方面的能力呢?
A:關于一個人在舞臺或比賽場上的狀態,有兩個因素起決定性的作用,一個是先天,一個是后天。首先是一個人天生的心理素質,這個應該起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用。有些人天生就是要登上舞臺的,而且是“大舞臺”,從小就展現出來他具備的這種才華,這個是前提。如果不具備這種能力的人,那他的表現就要稍打些折扣,所以先天放在第一位。比如,在中央院附小、附中選進來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在這方面具有優異素質的。
有了先天的基礎,第二個對演奏者未來在舞臺上起作用的要素,就是他是否可以持之以恒、踏實且專一地學習音樂,以高度的熱情和集中的狀態學習,解決要克服掉的所有困惑,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每個人心里的想法都不一樣,首先要自己覺得解決得八九不離十了,然后再上臺,穩定性就會很好。第二個要素中,學生一方面自己要非常勤奮,另一方面還要跟老師有愉快的配合,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音樂上的問題,老師能夠盡他所能的幫助學生解決掉很多學習道路上遇到的困惑,這樣學生就會慢慢成長起來。但是我想如果在舞臺上遇到“突發狀況”,在這樣極端情況下,更多的是這個人先天本能的反應,登上舞臺的次數越多,經驗就會越豐富。
我自己的教學中,比較習慣在比賽或考試前,較早地讓學生把這一套曲目連續地演奏,“連貫地演奏”是很起作用的。當學生把曲目中的細節基本掌握后,就需要重視完整性,重視“演奏的感覺”。
既然說到安天旭這個例子,我自己當時看到直播,就是覺得他心理素質特別的好,還有他手底下的功夫足夠好,才不會被這種突如其來的狀況干擾到,這是我當時非常直觀的感覺。
A:這樣的評論的確是存在的。讓我們假想一下,如果我是一位30歲以下的年輕演奏者,而且這些年我有很多比賽要參加,那么我要盡量避免受到這些評論的干擾。這些評論應該說還是比較客觀的,也沒有惡意,但是確實這樣或那樣的言語和評論會影響到一些演奏者。我覺得參賽者要有特別強大的心理素質,不管人家說什么,我就把我自己表現出來,不要受到這些評論干擾。
同時,如果我是一個參與評論的人,是用除選手和評委之外的第三方視角來看比賽的舞臺。從客觀來說,每一個比賽有它比較特定的氣質和要求,有些比賽偏“學術”,而有些比賽則注重選出未來的演奏家人才。不過如果真是有這樣的說法,我覺得這兩者:“比賽型”或“音樂會型”,不完全是矛盾的。因為無論是在音樂會還是在比賽,一個人的演奏都是情感的一種表達,打動人的情感是不可以條理化的,因為它就是一瞬間出來的東西。任何情況下,只要藝術是打動人的,那就是好的。這里我想強調的是,評論歸評論,演奏歸演奏。作為演奏的人來說,要拋開這些對你有影響的言論,永遠都要最真實地彈你自己。就是會有些人喜歡你,有些人不喜歡你,這是一個絕對存在的事實,要堅持自己的想法。除非有一天你發自內心的認為需要做改變,那是可以調整的,而對于自己不愿意調整的,也完全沒有錯,需要堅持。就是要尊重自己的內心,真實的表達才會是最自信、最順暢和最圓滿的表達。不要被語言上的評論束縛住,永遠都不要。
Q:是的,這太重要了!各種各樣的評論其實也反映出這次肖賽在國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這不僅對于參賽者來說是件好事,更加促使很多音樂愛好者、琴童,甚至之前從未關注過古典音樂的人有機會接觸并關注到重大的鋼琴賽事,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A:肖賽現在確實是一個大熱門。我覺得可能隨后的一些其他比賽,也還是會很受關注。因為現在網絡太發達了,所以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網絡其實就是擴大了一個比賽的宣傳面。這種事情我覺得對選手來說是把雙刃劍,無論演奏得好或不好大家都知道你了,這對演奏者來說既是宣傳也是壓力,比賽一輪一輪的淘汰,面對輿論和結果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我是一個演奏者,我會提醒自己避免在參賽的過程中過多關注大家的評論;那如果我是一個旁觀者,我很有興趣去看大家的評論,好的我會吸收,但是不贊同的,我也會堅持自己。總的來說,我覺得這個現象帶來的益處肯定是更多的。
Q:您如何評價此次比賽中國選手的表現呢?
A:我確實熟悉這個比賽當中很多的中國選手,有些人很小的時候就在比賽中聽過,過很多年一看,覺得真是長大了,現在彈琴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我覺得在這里最重要的是有些人成長非常快,而有些人成長不夠快。所謂成長不夠快,就是指這個人彈琴大眾化——盡管技術漂亮,音樂表現卻比較中規中矩,可能小時候光芒四射,但是十年過去了他還沒有成為他自己;而另外一些選手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在藝術上、在音樂上成了他自己,并且有他非常獨到的藝術魅力,這種展現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說明這個人在藝術上完全成熟了。所以我在想,這種成長得非常快,并且在演奏方面有他獨到之處的人,這些年是沒有白白學習的,這個學習的過程每天都很踏實。但是有更多的人,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對待音樂沒有像小時候那樣專注,那么他演奏出來的音樂也就趨于平庸,很難脫穎而出。這里我想強調的是,從小到大學習的過程很漫長,很多人是堅持不住的。在這個過程中受到社會環境、生活環境各種影響的時候,他能不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專注于自己對藝術、音樂、和對鋼琴的熱愛?絕大部分人不是的。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人早晚有一天要成為自己,那么作為老師來說,我也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學生彈出的音樂完全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靠著模仿別人的演奏——這是我很欣賞的。
Q:通過您剛才講的,一個成熟的鋼琴家是來源于成長道路上持之以恒的堅持與專注,這讓我想到,一個演奏家的成長過程當中,每一個階段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您覺得學生在學琴的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側重點應當是什么呢?例如,在業余階段,在附小、附中時期,在大學之后,等等。您在教導不同階段的學生時教學上各有什么樣的側重點?
A:學琴道路上的每一個階段肯定還是有區別的。比如在教業余學生的時候,可以非常敏感地感覺到,有些孩子是絕對具有音樂素質的,但是更多的孩子呢,他就是業余學習。所以像能夠進入專業院校附中、附小的孩子,就是從這些非常有音樂素質的孩子當中冒出來的。在平時教學時,他們的進度就會比較明顯地比別人快,老師教的東西他能夠領悟得到,并且做得到。當然我也會在學生要參加比賽這個過程中,給他略微難一點的曲目,來觀察這個學生的能力。這絕對不是指拔苗助長——你發現他擁有這個能力以后,還可以再退回來補充更多的東西,讓他更扎實。
在教授專業學生時,整體來看附小三年和附中六年加起來的九年當中,我感覺在初一到初三這三年是一個產生質變的時期。一些孩子在這個階段,藝術上會變得逐漸成熟起來,但是這些也都是少數,應該是“天賦型”加“勤奮型”的學生。這些相對成熟的孩子音樂表達更豐富,開始對音樂有自己個人的一些理解。但是更多的孩子呢,還是勤勤懇懇,老師教什么他就彈什么,比較孩子氣或學生味兒,所以我覺得初中這個階段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大學以后,又是一個新的臺階,應該是從學生轉變為未來的藝術家的年齡,那當他再次出現在大型比賽場上時,曾經的孩子就已經蛻變成音樂家、藝術家了。可是這也是少數,更多的人應該只能算是質量不錯的,或高質量的學生在演奏,我覺得這是有區別的。很多人到了大學之后也僅僅就是一個學生,他對自己沒有想法,別人說什么他才干什么。包括對于比賽的設想,或什么時候該做哪些事,完全是聽老師或家長的安排。
所以,其實我剛才談的也不能完全算是教學方法,就是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其實教學很難分出條理化的一二三,哪個階段應該怎么教,這些都是滲透在點點滴滴當中的。觀察學生和觀察自己一樣,需要拉開距離,才能看到你的教學或者是學生的努力,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這是一種既模糊又清晰的感覺吧。拉開距離,或者是很久沒有看到他彈,再次看到的時候,你再去回想,就會知道他成長得怎么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