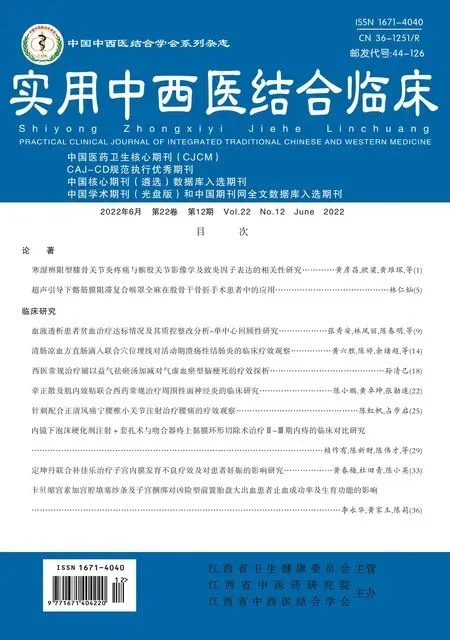脾部分切除在脾臟良性病變中應用初探
彭正 陳之強 劉海洋 楊琦
(北京市順義區醫院 北京 101300)
脾臟良性病變較為常見,包括脾囊腫、脾膿腫、脾血管瘤等。脾臟良性病變早期多無明顯癥狀,隨著病情進展會對脾臟功能造成影響,體積增大還會壓迫周圍器官組織,誘發相應癥狀,因此及早明確診斷、予以相應治療尤為重要[1~2]。臨床對于體積較大的脾臟良性病變多行手術治療,但傳統手術方式多以開腹手術為主,切除病灶的同時對機體傷害較大,不利于術后機體恢復[3~4]。腹腔鏡全脾切除術(LTS)為當前脾臟良性病變重要手術方式,具有創傷小、出血少等優勢,通過切除全脾達到治療目的。但臨床隨著對于脾臟的深入研究發現,脾臟為機體重要臟器功能,與血液系統、免疫系統等存在密切關系,全脾切除后易引起諸多并發癥,降低患者生活質量[5~6]。腹腔鏡脾部分切除術(LPS)僅切除部分脾臟,能夠保留部分脾臟功能,但關于LPS具體療效仍需深入研究。本研究分析LPS在脾臟良性病變治療中的應用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醫院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脾臟良性病變患者64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兩組,各32例。對照組男19例,女13例;年齡34~67歲,平均(51.85±7.12)歲;病變直徑5~7 cm,平均(6.02±0.47)cm;疾病類型:脾囊腫12例,脾血管瘤8例,脾淋巴管瘤7例,脾錯構瘤5例;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10例,初中14例,小學8例。觀察組男20例,女12例;年齡33~68歲,平均(51.91±7.17)歲;病變直徑5~7 cm,平均(6.05±0.43)cm;疾病類型:脾囊腫13例,脾血管瘤9例,脾淋巴管瘤6例,脾錯構瘤4例;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9例,初中14例,小學9例。兩組一般資料對比無顯著差異(P>0.05)。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SYYY20181201)。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于體檢時發現脾臟占位性病變;經CT等影像學鑒別為良性病變;病灶直徑≥5 cm;行腹腔鏡手術治療;凝血功能正常;本人及家屬對研究內容知情,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肝、腎等功能障礙;心肺功能欠佳;嚴重精神障礙;多發病灶;惡性病變。
1.3 治療方法 兩組均完善術前檢查,明確病變部位,并經脾動脈血管重建明確脾葉血管走行。對照組予以LTS治療:全麻后,大字位分開患者雙下肢,術者及助手分別立于兩側,扶鏡者立于兩腿中間。先建立氣腹,維持腹內壓12 mm Hg,之后臍右下方穿刺作為觀察孔,并于腹部左右兩側各穿刺兩孔作為手術操作孔;先于胰腺上緣后方尋找脾動脈,明確后分離并結扎,待脾變軟變小后,分離脾門,將胰腺尾部、脾蒂血管顯露;之后以直線切割吻合器將脾蒂切斷,解剖并結扎剩余胃短血管、脾周韌帶,之后自臍部切除取出標本;脾窩留置引流管,逐步退出器械縫合切口。觀察組予以LPS治療:手術麻醉及穿刺孔同對照組,先精細化分離脾門,以Hem-o-lok夾閉通向脾上極或下極血管,待脾缺血線明顯出現后,在缺血線內側5~8 mm處以超聲刀離斷脾組織,之后電凝止血,并沖洗創面,維持良好術野;隨后用超聲刀將脾周韌帶、粘連切開,自臍部切口取出切除標本;常規脾窩留置引流管,退出器械并縫合切口。兩組術后均予以營養支持、抗感染等。兩組術后隨訪3個月。
1.4 觀察指標 (1)手術情況:比較兩組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術后排氣時間、術后排便時間、術后住院時間。(2)免疫功能:術前及術后4周,采集兩組3 ml空腹血,離心處理后,以流式細胞儀測定CD3+、CD4+、CD8+及CD4+/CD8+水平。(3)生活質量:術前及術后3個月,采用世界衛生組織生活簡易量表[7]評價兩組生活質量,包含心理、生理、社會及環境4個領域,各100分,分值高生活質量佳。(4)并發癥:包括血小板增多癥、感染等。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以(±s)表示,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表示,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手術情況對比 觀察組手術時間較對照組長,術中出血量較對照組多,術后排氣時間、排便時間及住院時間較對照組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手術情況對比(±s)

表1 兩組手術情況對比(±s)
組別 n 手術時間(min) 術中出血量(ml) 術后排氣時間(d) 術后排便時間(d) 術后住院時間(d)觀察組對照組32 32 t P 145.62±10.28 133.41±10.15 4.781 0.000 215.42±18.96 178.96±16.54 8.197 0.000 1.52±0.24 2.02±0.29 7.514 0.000 2.11±0.37 2.89±0.42 7.883 0.000 7.12±1.05 8.54±1.13 5.208 0.000
2.2 兩組免疫功能對比 術前兩組免疫功能對比無明顯差異(P>0.05)。觀察組術后CD3+、CD4+、CD4+/CD8+水平較對照組高,CD8+水平較對照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免疫功能對比(±s)

表2 兩組免疫功能對比(±s)
CD4+/CD8+術前 術后觀察組對照組組別 n CD3+(%)術前 術后CD4+(%)術前 術后CD8+(%)術前 術后32 32 t P 55.41±6.29 55.37±6.22 0.026 0.980 51.59±5.38 45.87±5.21 4.321 0.000 41.75±5.12 41.59±5.04 0.126 0.900 34.75±4.23 30.36±4.17 4.181 0.000 28.42±4.16 28.18±4.12 0.232 0.817 29.14±4.26 33.75±4.45 4.233 0.000 1.47±0.25 1.48±0.27 0.154 0.878 1.19±0.22 0.90±0.19 5.643 0.000
2.3 兩組術后生活質量對比 觀察組術后生活質 量各領域評分較對照組高(P<0.05)。見表3。
表3 兩組術后生活質量對比(±s)

表3 兩組術后生活質量對比(±s)
環境術前 術后觀察組對照組組別 n 生理術前 術后心理術前 術后社會術前 術后32 32 t P 71.54±5.47 71.39±5.38 0.111 0.912 86.51±7.25 80.33±6.89 3.495 0.001 65.79±5.12 66.05±5.23 0.201 0.841 84.41±6.93 78.52±6.27 3.565 0.001 75.74±6.15 74.32±6.28 0.914 0.364 89.73±7.34 82.41±7.22 4.022 0.000 70.13±6.58 70.07±6.49 0.037 0.971 92.21±6.25 85.41±7.82 3.843 0.000
2.4 兩組并發癥發生情況對比 對照組發生血小板增多癥6例,感染2例,并發癥發生率為25.00%(8/32);觀察組發生血小板增多癥1例,感染1例,并發癥發生率為6.25%(2/32)。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有統計學差異(χ2=4.267,P=0.039)。
3 討論
脾臟良性病變病因復雜多樣,早期多無明顯癥狀,多于體檢時發現,需盡早診治,減輕疾病對機體造成的損害。手術為治療體積較大良性病變患者重要方式,既往受限于手術器械、技術等,臨床多以開腹全脾切除術為主。該術式創傷較大,術后并發癥多,不利于機體恢復[8]。隨著微創技術的發展,腹腔鏡手術逐漸應用于臨床,僅需于腹部作幾個小孔即可開展手術操作,且鏡下視野清晰,亦可滿足手術精細化操作要求,從而減輕手術創傷,減少出血量,有利于術后機體恢復[9~10]。
LTS為當前治療脾臟良性病變的常見術式,借助腹腔鏡視野開展脾臟全切,能夠在達到治療目的的同時減輕機體創傷[11~12]。但臨床隨著對脾臟的深入研究發現,脾臟為人體重要的淋巴器官,在人體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能夠幫助機體對抗感染等多種疾病,且脾臟具有造血、儲血、濾血等多種功能,一旦進行全切則易誘發血小板增多癥、感染等多種并發癥,降 低 術 后 生 活 質 量。CD3+、CD4+、CD8+及CD4+/CD8+為反映機體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標,當開展手術操作時可對機體免疫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且脾臟與機體免疫關系密切,切除后可促使免疫處于低下狀態,故監測上述指標變化有助于評估不同術式對機體免疫的影響。本研究中,相比對照組,觀察組手術時間長,術中出血量多,術后排氣時間、排便時間及住院時間短;術后CD3+、CD4+、CD4+/CD8+水平更高,CD8+水平更低;術后生活質量各領域評分高于對照組,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提示LPS治療脾臟良性病變效果更佳,能減輕免疫功能損害,降低并發癥發生風險,縮短術后住院時間,改善術后生活質量,但手術時間較長,出血量多。分析原因為,相較于LTS,LPS術中僅切除部分脾臟組織,操作方面更為復雜,需嚴格執行精細化操作,故手術時間相對較長,且脾臟血供較為豐富,術中操作易引起創面出血,使得出血量較多[13~14]。脾臟具有一定再生能力,LPS術中脾臟保留僅需達到原脾體積的1/3即可維持脾臟正常功能,故術后免疫功能恢復更快,并能夠降低血小板增多癥等并發癥發生風險[15]。但LPS對手術操作要求極高,不僅需嚴格把控適應證,還需術者熟悉脾臟結構,并充分掌握腹腔鏡操作技巧,保證手術操作輕柔,精細分離脾二級脾蒂血管,從而提高保脾成功率。
綜上所述,LPS在脾臟良性疾病治療中應用價值高,能夠縮短術后恢復時間,減輕免疫功能損傷,降低并發癥發生風險,改善患者術后生活質量。但臨床仍需注重精細化操作,避免出血量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