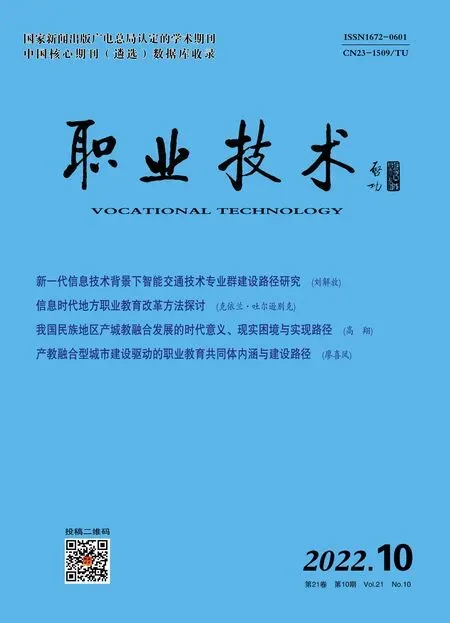理工科課程混合式教學中課程思政的社交化實施及表現性評價
付 英,劉貴彩,王嘉斌,張新瑜,張 剛
(濟南大學 土木建筑學院,濟南 250022)
0 引言
眾所周知,理工科思維和文科思維是有本質區別的。傳統的文科思維,主要特征是忽略量化的概念,特點是善于形象思維,并擅長橫向聯想;而理工科思維強調的是邏輯嚴密性,[1]具體而言,可以認為理工科思維具有邏輯演繹、線性思維、問題導向三個最主要特征,即內容未動,框架先行。
在世界教育史上被尊稱為“教育科學之父”“現代教育學之父”的德國哲學家、心理學家、教育性教學的首創者赫爾巴特認為“道德普遍被認為是人類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2-3]蔡元培先生認為,教育應以道德教育為中心,以世界觀教育為終極目的、以美育為橋梁,使學生德智體美和諧發展。因此,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提出的教育的本質包括兩方面:一是使學生認識和理解客觀世界,二是表現學生自身內在的本質。很顯然地,理工科思維注重的是前者,而往往忽視了后者。
落實到教育單體,概括而論,教育的基本功能有兩個:育人和育才。育人關注的是三觀培養,即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育才關注的是創造力、分析力和領導力。[4]育人是核心靈魂,育才是外在的殼;若沒有魂,殼只是一種有形存在,若沒有殼,魂也就沒有了依附,所以育人和育才是唇齒相依的關系。一般意義的人才包括兩層含義:人是社會的主體,人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5]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針對人和人才的教育過程是剝離的。人類所有科技發展的最終服務目標,以及社會、經濟、政治等方方面面的進步都是為了人及人的幸福生活。因此,“育人比育才更關鍵、更根本、更重要”的說法是不容置疑的。[3]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12月召開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關系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6]。2020 年教育部印發了《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7],提出要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8]在全國高等學校全面推進課程思政建設,這種教育理念正好與赫爾巴特教育思想有機契合。
在高校全面推進課程思政的當下,如何高效地實施課程思政,并能夠對其效果進行合理評價,是高校教師和學者探索的重要課題。對于理工科課程而言,若要基于課程思政根本任務及其本質(立德樹人)有效地開展相關工作,同時也為較好地踐行具有“兩性一度”特征的金課建設,則需要結合理工科思維及課程體系的特點,進行較為長期的探索和實踐,方能緩解目前學校教育教學育人與育才相分離的矛盾,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文章結合理工科核心課程在混合式教學中的建設實踐,基于混合式教學所具備的獨特的時空特點及授課方式特點,創新架構了課程思政的社交化實施(IP-SI)和表現性評價(IP-PE),并進行了探索和總結。由于IP-SI需要一定時間的課下準備、課中辯論及討論、課后反思和總結,因此在混合式教學中,IP-SI的進行是合理的,即時間充分、空間自由、形式適度。下面針對混合式教學背景下的IP-SI和IP-PE進行具體的闡述。
1 理工科課程混合式教學中課程思政的社交化實施(IP-SI)
社交,即社會上人與人的交際往來,是指人們運用某種方式傳遞信息、交流思想,為達到某種目的而開展的活動。顯然,人類的社交活動具備擴散某件事情的能力,同時也具備傳播或交換某種思想或觀點的能力。課程思政的社交化實施(IP-SI)即基于此概念而來。課程思政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而“立德樹人”主要是依賴于思想或觀點的傳播或交換來完成的。區別于采用其他方式實施的課程思政,IP-SI達成的目標是獲得思想或觀點的實質性內化,IP-SI秉承的原則是內化思想或觀點所進行的路線、方式、手段等要合理有效。利用混合式教學獨具的時空特點及上課方式,IP-SI要傳播或交換的思想、觀點可以來自老師,也可以來自同學,因此能很好地達成社交化實施的目的。
若要有效地進行IP-SI,需要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思政元素的挖掘與數量的關系,二是教師思政意愿和能力的自我判斷。IP-SI具體的路線設計如圖1所示。
1.1 課程思政社交化實施(IP-SI)的前提條件
首先是思政元素的挖掘與數量的關系。IP-SI需要稍長一些時間才能夠完成,這就要求思政元素的挖掘與數量需要具有一定數量的比例關系,不是盲目挖掘,也不是多多益善。
對高校本科學生而言,若要獲得學士學位,需要修完本專業規定的學分,這就要求學生至少完成四五十門課程的學習任務。對于每一門課程,思政元素的挖掘都需慎之又慎,需要所有教師齊心合力,共同研討所負責課程的思政元素的著眼點。而且每一門課程應以某一類核心思政元素為主體,即“思政主元素”,以其他思政元素為輔助,即“思政輔元素”。否則在一些教師的思政能力還未達到一定高度的情況下,會出現類似“廣告效應”的嫌疑。例如:對于理工科課程而言,“趕超先進技術的家國情懷”是常見的思政元素,尤其對于目前我國存在一些“卡脖子”的技術難關,許多課程可能都暗含著這類思政元素。這就可能導致多數教師都在課程教學中滲入該元素,當教師不具備高水平的思政能力和創新的教學方法而強行融入該元素時,學生就會大概率地出現厭煩心理,教學效果則適得其反。如果一個專業能夠統籌安排,針對某一門課程或幾門課程,以某一類核心思政元素為主(思政主元素),以其他思政元素為輔或微量滲入其他思政元素(思政輔元素),則會避免某類思政元素在多門課程中一再重復出現。如果教師還能夠在教學中輔以恰當的思政元素實施方式和方法,學生在修完這門課之后,就很容易深度內化該門課程的“思政主元素”,同時又輔助性地接受了其他思政元素。經過大學四年的深度熏陶,學生就接受并內化了至少四五十類思政主元素。若再銜接起小學、初中、高中的教育體系,基本實現了全程育人的最佳效果。

圖1 IP-SI的具體路線
其次是教師的思政意愿和能力的自我判斷。IP-SI的引導者是教師,因此,若要成功且有效地進行IP-SI,教師需要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都說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請悄悄問問自己,你是否做到了“最光輝”?第二,赫爾巴特認為“在教師與學生之間,不需要第三者的加入,就能夠成為偉大而精選的伴侶”,你是否有資格成為這個“偉大而精選伴侶”的另一方?只有先回答好這兩個問題,并且得出一個定性的答案,才能夠說明教師具備了思政能力自我判斷的依據。
教師思政能力的自我判斷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問題:是否具有守好自己“責任田”的強烈意愿(樂于做),是否具有較佳的意識形態把控能力(善于做),是否具有較佳的課堂把控能力和隨機應變的思維能力(能夠做),是否具有承擔被反駁、被否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理性做)。
1.2 思政元素在教學中的引入及滲入的依據原則
基于不同的思政元素類別、思政內容及其與知識點的結合方式,以及不同的課程思政的實施方式,思政元素在教學中的引入及滲入的依據原則為“隱式”或“顯隱結合式”,可以認為這是一種高階思政的有效方式。例如:如果采用學生討論/辯論式,則有時需要教師進行適度的點評或總結,其中學生討論/辯論過程可能是“顯隱結合”的過程,而教師點評或總結則為顯性過程。
1.3 課程思政社交化實施(IP-SI)的方式方法
對于“思政主元素”和“思政輔元素”,其滲入手段可分別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而IP-SI主要是指“思政主元素”的滲入方式。
如圖1所示,對于“思政主元素”,主要采取辯論式、案例/討論式、綜述/匯報式、蜻蜓點水式。蜻蜓點水式就是觸點零星式滲入,是指課程進行過程中,對某“思政主元素”進行觸點零星式的融合,屬于開放式滲入,目的是為辯論式或案例/討論式的主滲入方式打下基礎,使它們最終達到實質性內化。辯論式、案例/討論式、綜述/匯報式的進行是在課程結束之前,采用小型辯論賽、案例/研討法或綜述/匯報法等多種形式,使學生達到知其言更知其義、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效果,同樣也是開放式內化的過程。通過課程進行時與課程結束前的有機結合和良好銜接,如竹筍剝皮,層層深入,達成了“思政主元素”深入內化的主要目的。
對于“思政輔元素”,主要采用問題牽動式、聯想式、探問式(特指思政小問題)、拋磚引玉式、討論/點評式等,或者任意兩種方式的有機結合。
下面針對辯論式闡述IP-SI目的的達成。
辯論的實質是博弈,而博弈是一種平等水平上的對話,實質是不同思想之間的碰撞與交流。IP-SI的辯論采用的是合作性博弈:要求參與者從自己及合作者的觀點出發,與其他參與者達成觀點協議,博弈雙方的觀點利益都會有所增加,至少另一方觀點利益不會受到損害,結果是整場辯論的參與者及旁觀者的觀點利益均有所增加,即產生一種觀點利益的合作剩余。具體言之,辯論的過程(即合作性博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過程。該過程中,一方若要申明自己的觀點,即表現為力圖完勝對方,則必須學會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即換位思考,所以辯論過程的實現需要具有全局觀念。積極思考是辯論過程最重要的特征,而通過自己主動思考過的觀點才能獲得更深刻的理解,即內化的效果是事半功倍的,而這也是“金課”中高階思維的內生需求。高階思維是指發生在較高認知水平層次上的心智活動或認知能力,它在布盧姆教育目標分類學中表現為分析、綜合、評價和創造,而高階思維是高階能力的核心,主要包括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思維能力、創造思維能力和決策能力,體現的是當今知識爆炸時代對人才素質培養提出的新要求。課程思政中對于高階思維的訓練,也十分有利于學生對于專業知識的掌握及在解決復雜問題上的運用。
辯論過程的本身就是極具思政意義的一種行為,包括換位思考、協作與合作、獨立意識、理性思考、邏輯思維、批判思維,以及語言表達、穩扎穩打、未雨綢繆等,這些本身就是極佳的思政元素。通過辯論過程的實施,這些附加的思政元素對學生的影響是深遠長久的,甚至貫穿其一生的發展,而這種思政元素的內化效果是課堂上通過講解、提示等其他思政元素滲入方式所不能替代的。
此外,對于青年學生來說,好勝心與生俱來,辯論能夠極大提高學生的參與積極性,能充分調動課堂氛圍。
從發展的眼光看,對這些與理工科課程知識完全不同的思政元素,教師是作為首代傳播者出現的,通過社交化實施,學生在較大概率下會成為二代傳播者,所以該過程實為一種幾何式增長的過程。
2 理工科課程混合式教學中課程思政的表現性評價(IP-PE)
課程思政表現性評價(IP-PE)原則是盡量關注學生的發展,而不是聚焦于結果,即關注過程、弱化結果。
表現性評價是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興盛起來的一種評價方式,是指根據已定的規則,對學生在復雜任務情境中的過程表現與結果進行評價的一種方式,[9]主要是運用先前學過的知識來解決某個新問題,或應用于解決復雜問題,或創造某種事物,其目的是考查學生對所學知識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及水平,以及對于實際問題、實踐問題或復雜問題的解決、交流合作/協作、批判性思考、創新性思考等多種復雜能力的發展狀況。因此該評價方式注重的是過程評價及發展評價,在促進學生發展其基本認知技能的同時,還是對學生綜合能力的一種評價。所以,表現性評價屬于對高階思維能力評價的范疇,評價的是分析能力、綜合能力、批判思維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和合作溝通能力,可以認為表現性評價是形成性評價的一部分,但不是終結性評價。
表現性評價分為兩種形式:限制式表現性評價和開放式表現性評價。前者對評價任務和目標均有明確要求,并對學生行動確定了限制范圍,比如閉卷考試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限制式表現性評價。而后者是對學生不做限制要求的一種評價方法,用于課程思政的評價上,適度性、實用性、現實性均較好,操作性較強,內化度較大。
IP-PE需要解決的兩大問題是評價主體的確定和評價規則的制定。而評價主體的構成與評價規則的內容因課程不同和IP-SI不同而異,如圖2所示。

圖2 IP-PE構成示意圖
如圖2所示,評價主體包括教師和學生,其中學生參與度較高的評價方式主要體現在學生參與度較高的實施方式中,如辯論式、案例/討論式、綜合/匯報式、討論/點評式等。IP-PE需要有學生評價的參與,原因如下:首先,可以避免教師單純性評價的局限導致的結果偏頗;其次,可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性,對于開放性答案,本無對錯之分,所以主體構成成分越多,則評價結果越客觀;最后,受限于師資力量,如由教師全程評價會導致操作性難度增加,而由教師與學生共同構成評價主體則降低了操作性難度。但是針對這種IP-PE模式下的評價主體,評價規則的制定就需要具備明確、清晰、公正、公開、客觀、操作性強、框架精細等特征。
學生參與度較低的評價方式則主要體現在學生參與度較低的實施方式中,比如蜻蜓點水式、問題牽動式(特指思政小問題)、拋磚引玉式等,這里的IP-PE中的評價主體由教師一方承擔即可。評價規則基本為開放性答案,涉及學生參與的評價,開放性答案則較為復雜,因課程而異。對于開放性答案,IP-PE實際屬于一種行為性評價,[10]學生只要參與,答案不過分偏離主題,則可根據學生參與過程的認真情況、積極性、態度等進行直接評價。
3 結語
作為包含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工程、天文及其各種運用與組合的一個廣大的學科領域,理工科的發展關乎人類社會進步,理工科課程教學則關系到我國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的進展,因此理工科課程思政建設及推進勢在必行。
文章基于思政元素的挖掘與數量的關系、教師思政意愿和思政能力的自我判斷,結合理工科思維特點、課程思政的基本任務和目的、混合式教學獨具的時空特點,對社交化實施(IP-SI)及表現性評價(IP-PE)進行了初步探索和實踐,以期我國高校在理工科領域相關課程中盡快實現育人和育才目標的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