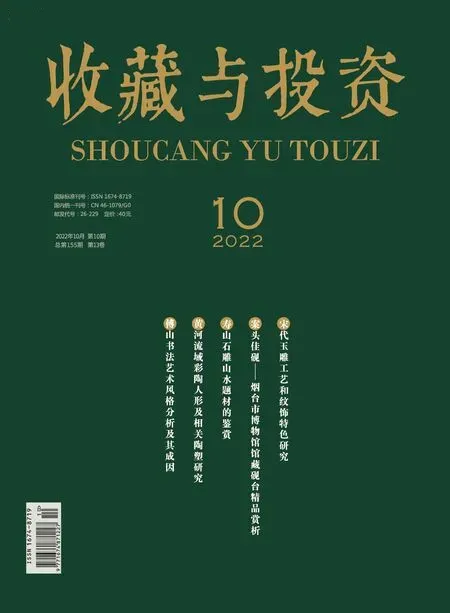詭形怪狀 任情肆意
——張旭狂草藝術分析
劉佳佳(陜西理工大學 人文學院,陜西 漢中 723001)
張旭,號稱“張顛”,世稱“張長史”,他作為在唐朝時期頗具盛名的書法家,在當時就已經被譽為“草圣”。張旭工書法,精通楷法,但是以狂草最為出名,也最受推崇,多見于諸家詩文。張旭的狂草藝術顯示出書法審美的“形”與“意”層次:“形”的審美是書法審美中最基礎直觀的部分,張旭將曠達灑脫之情寄于狂草藝術,其狂草藝術之“形”彰顯出極致的變化之態,但仍處在漢字的結構框架之內,最終達到整體和諧之美;透過表象形式可以窺見“意”的審美層,張旭的筆墨揮灑中蘊含著縱逸狂放之情與動態之美。
一、張旭狂草“形”與“意”形成背景
在中國書法史上,唐朝是無法逾越也不可逾越的一個時代,“大唐盛世”“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在歷史與文化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穩定的社會使人民追求精神生活,促進了藝術文化的發展。同時唐太宗鐘情書法,還將文字學知識和各種書法演示納入科舉考試之中,“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1]。必須要兩者兼及才能書科及第。除科舉考試外,書法也是考核與任官的必要條件,因此促進了書法在唐朝的發展。
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與創作者主體性的審美取向是密不可分的,作品獨特性顯示出對象本身的特征,對象的特征和創造者的主體性相互聯系。中國古代詩、畫、書三者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張旭的詩歌中蘊含其審美取向,傳世的詩歌僅有十首,其中,《全唐詩》收錄六首,《全唐詩拾補》中收錄四首,其詩與自然有著緊密的聯系,張旭在進行創作時將目光投向自然,追求清新脫俗、閑適淡雅,這使得他在書寫時呈現狂草的極致自由之勢。
張旭處于整個社會崇尚書法的氛圍之內,加之唐朝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時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張旭鐘情于自然萬物,自然在他心中引發自由灑脫之感,于萬物中體悟書法,其狂草中的“形”與“意”在受唐朝影響的同時更是其審美取向的結果。
二、張旭狂草的“形”—外質審美
張旭的狂草有其鮮明的特點,漢字在線條中建構所具有的空間性,決定了書法藝術的空間性。張旭在狂草中將較為穩定的空間造型打散,使得字形得以突破。但無論其形如何使空間造型改變,整體的均齊依舊存在,同時字的整體框架結構不會因狂草字形的變化而從狂草藝術中消失。
(一)形—變
杜甫在《飲中八仙》中寫道:“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2]草書藝術對于楷書穩定的框架結構和字字獨立之形進行了突破,張旭的狂草藝術在此基礎之上又對于章草與今草之形也有所變化。章草與今草都表現出“字字區別”的態勢,字與字之間區別仍分明可辨,張旭的狂草則更多為牽上引下,字與字之間相互勾連,一行無所間斷。劉延濤在《草書通論》中稱:“狂草者,草書中美藝品,創始張旭,由狂僧懷素得名,而以詭奇疾速為其特征!”[1]詭形怪狀是張旭狂草最為明顯的特征。
張旭的《古詩四帖》是詭形怪狀極致的書寫,以其屈伸變化之勢最為突出。對于草書的書寫,其他書法家一開始的書寫都略顯嚴謹,但張旭不被拘束。《古詩四帖》開首即為狂草,“東明九芝蓋,北燭五云車”十個字可以說字字連而不斷,兩詩句形成一筆書,到“車”字的末尾以枯筆為收筆,停頓之后再另起筆鋒進行下一句的書寫。“芝”字順峰落筆,幾經曲折,極具張力,然后引筆順勢而下至“北”字,上緊下松,整體的和諧仍存其中。“登天”二字與“泉”字其形在簡化的基礎之上,線條奇肆,形雖變神依存,篇尾“隱”字順承“仙”字右落之筆,彈性的伸展可以由此窺見。“隱”的右旁空間雖小,但筆畫盤踞之中,形折而不亂,如神龍騰天潛淵之勢,至“不”頓字筆勢結束,筆結意不結,之后又另為起筆,“別”字以環繞成圓的態勢現于紙上,如龍盤踞之勢,氣勢昂揚,“可”字上屈下伸,上部曲繞使態勢較為緊,上部空間筆畫被壓縮,下部得以伸展,順意延長,“其書非世教”左旁屈右旁伸,“世教”二字又上伸下屈,形成對比,“其人必賢哲”是完全的伸展態勢。短短幾行就蘊含了多樣的屈伸變化,可以說態勢的屈伸在張旭的狂草中隨處可見,但其狂草中字態的伸展是完全不可預測的,在字形簡化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賦予字形變化的態勢。
張旭的狂草將外形框架進行最大限度的突破,運用變形、夸張手法,字形跌宕起伏,使字形隨心而變,無論是字構、線條還是筆法,都具有舞動之感,不為前人拘束,以無法為有法,“如神騰霄漢,夏云出嵩、華,逸勢奇狀,莫可窮測”[5]。
(二)形—不越矩
書法是以文字為載體而存在,它對于漢字的“音”與“義”有所擯棄,但漢字的“形”對于書法來講是不可分離的。書法雖脫離文字之后其形雖仍具有美感,但書法的實用功能就喪失了,人們在面對不可完全識別的“書法”時,對于其美的欣賞在失去可參照物時就喪失了一部分。狂草能夠最大限度地擺脫漢字框架結構,但狂草終究不能脫離一切,漢字第一形式的框架性依舊在其中。
姜夔在《續書譜·草書》中云:“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5]。”以張旭的《古詩四帖》為例,《古詩四帖》中的“仙隱不別可?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其書寫連綿如山,體勢飛動,字字皆無法辨識,而其仍不逾矩。“字之梗概”可見于其中,仙隱二字,“仙”字疏而“隱”字密,二字之間雖有所牽連,但整個方塊結構仍存,“隱不”二字,以“不”字之上筆畫作為“隱”字之下筆畫,使得二字相連,但是“不”字內部又是連中有斷,使得二字“同中有異”,二字各具體勢,“不別”二字,“不”字的收尾細輕而“別”的起筆粗重,二字的區別也是一眼可辨,“別其”二字也是上字收尾輕細而下字起筆粗重,同“不別”二字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書非”連筆與點畫之筆具有粗細變化,于流動之間見其形,“世教”二字則連筆處較粗,但仍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其人”“賢哲”皆是連而不斷,其密疏布局,框架仍可見。張旭的狂草不僅是線條的藝術,更是點畫的藝術,點畫的運用使其更增變化之勢。“下”由三點構成,猶如墜石,“雨”字將兩點半包圍其中,“應逐”“登天”在連續的線條結構之中加以點畫,起畫龍點睛之筆,無論狂草如何使得字形變化,其框架與點畫都仍可見。
狂草在對字形框架突破上作了最大的嘗試,將書法向自由方向最大限度地延伸,但整體仍處于漢字的框架結構之內,豐富的線條韻味與詭奇的形態變換相互依存,同時張旭對于時間與空間的把握恰到好處,流動的時間在線條與節奏之中得以體味,在有限的空間之中構建無限的韻味,內美外美皆寓其中。
三、張旭狂草的“意”—內質審美
書法是由線條所匯聚而成的藝術,書法、繪畫與音樂之中的線條,雖都具表情達意的功能,但書法表情達意的功能更上一層樓,書家細微的情感變化都可映于線條變化之態中。蔡邕在《筆論》中曾加以論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5]
篆、隸、形、楷因受到法度約束更強,因此抒情性就會被削弱。張旭的狂草以無法為法,灑脫之情映照在其筆墨中,從字的疏密大小之變可以感受到張旭情感的變化。《古詩四帖》開頭即是狂草,可以體會到張旭情緒的欣喜之感已經生發,此后情緒不斷激越上漲,至“齊侯問棘花……南宮生祥云”,其字形大墨濃,情感激昂至極,狂放自由之態更為凸顯,至“一老四五少”情緒略有舒緩,至最后“必賢哲”戛然而止,但書盡而意無窮,情意仍留于其中。
“中國的書法本是一種類似于音樂或舞蹈的節奏藝術。它有形線之美,有情感和人格的表現。”[4]書家或疾或緩的運筆中蘊含著豐富的節奏韻味,將筆墨揮灑于紙上,濃淡潤枯更不相同,這一切賦予書法以音樂的節奏感。張旭在狂草的書寫中通過運筆的疾緩、點畫的輕重、結構的疏密將節奏加以表現,行行之間的間隔并非整齊劃一、整篇不變,字與字之間并非字字分離。或緩或快的運筆使得狂草具有連綿不斷的勢態,字字相連為常態,使書法節奏更具有連續性。緩時,如潺潺流水;疾時,如瀑布傾瀉。正是這種緩急變化,加強了狂草的節奏意味。《肚痛帖》大小字穿插其中,參差錯落中又具有整體和諧性,第一行“忽肚痛不可堪”六字,前三字濃墨粗筆,厚重穩定,忽然之間,后三字輕筆連綿,順勢而下,極具藝術夸張的形式美,用筆飛動流暢,變化莫測。張旭在自由肆意之下所書狂草,其體勢的平衡被打破,書法的靜態空間也隨著打破,其 “形”表現出回環往復的態勢和線條的飛動變化,時間的動態美在張旭的狂草中得以充分體現。
張旭在狂草中以無定法為法,意欲達到法度的極限與無定的極限。其落筆書寫之時,筆墨自由奔放,隨胸臆自然而發,線條具有流動美,在狂草中可以體會到張旭的詩酒情懷及其豁達的生活態度,體味其奔放激昂的生命體現,形意相存。張旭將這一切寓于狂草之中,在節奏中流動,在字里行間流淌,奏出對自由靈魂的贊歌,體現出生命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