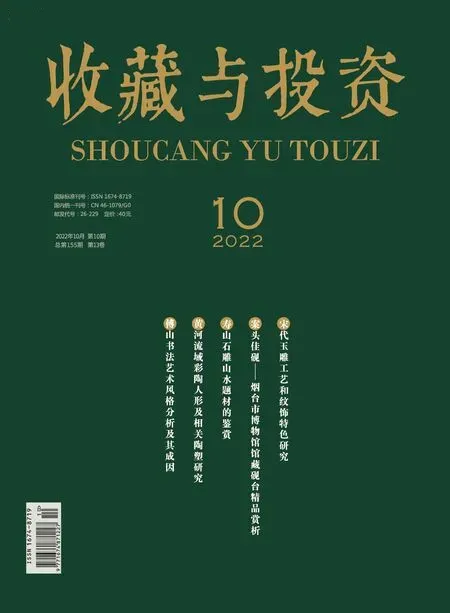傅山書法藝術風格分析及成因
韓 敏(山西博物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太原段帖》(以下簡稱《段帖》),為明朝著名書法藝術家傅山之學生段繒收集并匯總的關于傅山晚年書法藝術作品的刻帖集。在當今書法藝術界中,《段帖》占據了極其崇高的地位,并為后繼的書法藝術家和學者提供了真實且可靠的臨摹、學習和研究材料。對此,本文以《段帖》為例,研究傅山的書法藝術風格及成因,論證其作品的代表性、真實性、藝術性和創新性價值。
一、傅山的書法藝術風格分析—以《太原段帖》為例
(一)《段帖》各單元書法藝術特征之詳析
《段帖》以青石為整體質地,分刻“元”“亨”“利”“貞”等單元[1],并附有段繒本人所作的序言,故共有二十五方內容。其中,傅山的楷書作品集中于第一單元,而行書、草書主要分散于“亨”“利”“貞”等單元之中。由此可見,《段帖》內有關隸書和楷書的內容相對較少,主要收錄的是傅山在行書、草書上的創作成果。但從微觀角度分析,《段帖》內的小行草以飄逸和秀美為主體特征,因而又區別于傅山以往一般性的行書和草書作品。也就是說,《段帖》中傅山的書法藝術風格具有更高的區分度和更明顯的特殊性,因此更具有研究價值。
在“元”這一章之中,傅山的楷書接近漢朝風格,其是在吸收漢朝隸書風格并加以創新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具體而言,傅山從鐘繇的楷書作品中汲取創作靈感,并呈現為更方正的字形、更平直的線條以及更圓潤的筆觸,因而其也具有更加生動靈活的表現效果和多元化結構,同時也具有更豐厚的古拙氣韻。章炳麟曾評價傅山不同書法作品的不同特征:楷書透有古意、草書生動蒼莽。隨著傅山思想和價值取向的道化轉向,其楷書和草書作品竟有融合之勢,大氣而凜冽的草書風格也逐漸轉向更為平穩溫和的楷書風格。隨后,因傅山開始推崇顏真卿的書法藝術風格和為人處世的態度,故對于顏體書法的臨摹和創新不斷深入,凸顯出更端莊的字體筋骨、更平穩而謹慎的落筆著墨以及更強烈的古樸之韻。盡管如此,傅山的草書作品依然保留了原真狀態,具有與本性一致的飄逸風格。
在“亨”這一單元之中,《段帖》收錄了傅山部分隸書作品,雖不足50字,但卻是反映傅山風格轉換和心境意識最重要的部分。具體而言,該單元開篇寥寥幾字之線條筆觸以典雅、古樸為主要特征,但在尾章數字,筆尖在峰回路轉之際又凸顯輕盈靈活之姿,線條筆觸以流暢、靈動為明顯特點。該單元雖以小行草為基本形式,筆觸之間并無勾連之處,字里行間各字以獨立姿態存在,但總體上看,前后文間字體字形在氣韻方面明顯相通,故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并能夠將書法靈魂的氣韻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呈現出傅山“氣在理先”的哲學思想體系。在筆觸綿延串連之處,百余年來的社會動蕩和風雨侵蝕仍未能將其痕跡抹除,字與字之間的連接印記仍舊清晰明顯,故而更深刻地體現出段繒的高水平篆刻技術和對傅山書法作品關鍵特征的準確把握。
最后,以“貞”為例,該單元著墨側重于“按”,即在點與劃等筆順的勾勒上有更為厚實的力度。另外,“貞”這一單元與其他單元的輕盈和靈活字形存在顯而易見的差異性,具體而生動地表現出傅山在易代動蕩之際心境和思想意識的明顯變化。
總而言之,《段帖》雖為書法作品刻本,卻能力透紙背地展示出傅山書法藝術的多元內涵和蒼茫大氣之韻,因而具有極高的欣賞、研究及收藏價值。
(二)《段帖》書法藝術風格規律之詳析
從整體上看,《段帖》中收錄的傅山書法作品具有質樸和高雅的古韻,是傅山長期秉持的“大巧若拙”理念中的應有之義。從《段帖》內容來看,傅山也常臨摹古人古字、借鑒古人的書法藝術風格。
技法上,其書法作品與顏真卿相似,均有正直而不拘一格、莊重但不肅穆的共通之處。小楷作品中,傅山書法以穩重著墨、清勁筆法、疏密有致的字體布局為獨特風格[2];隸書作品中,樸素而富有古意是最為顯著的藝術風格,而堅韌甚至力透紙背的落筆則是其獨特藝術風格的展示形式。至于傅山具有強烈反差性的草書和行書作品風格,一氣呵成與剛柔相濟是主要的規律。
盡管傅山善于模仿和借鑒,甚至其作品多追求“顏筋”,但其并非一味盲目地追求古韻,反而是在融合古字筋骨和古人氣韻的基礎上凸顯自身獨特的書法藝術風格。聯系傅山坎坷的生平經歷,可知其所極力追求的古樸古韻之風,不僅是其對于自身書法藝術風格和境界的要求,更是其對于人生境界的追求。
此外,從《段帖》中傅山的書法作品內還能夠發現自然、流暢、輕盈、靈活的藝術風格規律。書法藝術史中不乏清新自然的風格作品,這是古代文人抒寫胸臆的主流風格。
受老莊清靜無為的自然思想影響,加之傅山一生歷經坎坷,他于紛紛擾擾的塵世之中曾數次目睹易代背景下普通百姓的顛沛流離。這種特殊的體驗使得傅山在潛移默化之中形成了順其自然的處世理念[3],秉持清靜無為的人生態度,后期更將上述價值取向滲透于自身各類書法作品中,最終使得其晚年時期的書法藝術作品呈現出渾然天成、自然清新的風格。
《段帖》中,傅山的書法作品還具有差異性、轉換性的藝術風格規律。在早中年時期,傅山的書法藝術作品以大行草為主要形式,并凸顯出恢宏、大氣、蒼莽及飄逸豪放等藝術風格。然而在《段帖》中傅山的晚年書法作品之中,楷書后來居上,成為主導性的書法藝術形式,其以平穩、溫和、輕盈、靈巧為主要風格。追根溯源,這種具有一定徹底性的差異性、轉換性藝術風格的出現,歸因于傅山長達一生的顛沛流離遭遇,因此反映出其對靜謐、和平生活的向往,表現出傅山在歸隱生活中追求自在清明的“居留地”。
二、傅山書法藝術風格形成原因
(一)時代背景的影響
傅山出生于1607年,正處于明末清初的易代之際。九歲時,傅山步入傳統的書學道路,學習臨摹晉唐和趙孟頫的書法作品。受傳統書學經歷的影響,傅山相當重視書法字體之“正”,尤重恢宏氣勢與超凡脫俗,具有“壯”意。明朝滅亡之時,傅山正處于中青年時期。經過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臨摹和積淀,其書法藝術風格體現出傳統性和虛靜狀態,并且表現出對晚明搖搖欲墜的社會及政權的隱隱擔憂。這是傅山書法帶有“悲”意之始。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的社會動蕩和戰亂背景為傅山的思想轉型創造了大時代環境,家國分離、山河破碎的悲痛結局為傅山狂放而不羈的性格奠定了客觀條件。該歷史時期正是傅山書法呈現出悲壯風格之始。
明亡入清,傅山的平靜轉向悲憤與抗爭,其書法藝術風格也進一步呈現“奇”的特征。生逢亂世,社會思潮紛亂復雜,各派思想或碰撞或交織,許多文人掀起了反傳統、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潮流。山河破碎之悲和顛沛流離之痛激發了傅山的藝術創造潛力,生命價值與書法藝術的詩性融合在思想的碰撞和交匯中日益豐滿。對社會現狀的焦慮和憤懣充分流露,更為放縱且不羈的連筆草書應運而生,悲壯和反抗的情緒張力油然而生,自然而然地體現在該階段的書法藝術風格之中。總而言之,朝代更迭為傅山藝術風格轉型創造了契機。
清朝中后期,社會逐漸穩定,文教緩慢復興,傅山本人也于此時迎來晚年,進入其書法藝術風格的升華階段。此時相對平穩的社會背景為清代書法藝術家追求理性和求學鉆研創造了有利環境,習漢魏北碑和樸學之風盛行[4]。經歷起伏的一生、面對無法逃避的死亡,傅山對于人生與生命形成了更通透的認識,并逐漸達到大徹大悟、平和安寧的人生境界。在此時代背景和自身境界的影響下,傅山的書法藝術風格大有回歸傳統和古韻、升華至崇高人生境界的趨勢,并增添了幾分嚴謹和理性的克制,達到了收放自如、穩定平衡的狀態。
(二)思想觀念的轉化
社會意識形態往往從潛移默化中對個體施以影響,因此在分析傅山書法藝術風格的形成原因時,我們應當綜合考慮社會思潮和主流價值觀的影響和作用。
自漢以來,儒學長久地占據社會主流思想地位。朝代的更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部分內涵和形態,但儒學的核心亙古不變。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學成為思想領域的主導者,推崇“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和強烈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的樹立。但僵硬的倫理主義和內在修養淡化了經世致用的價值,弱化了個人自由的追求,導致教條主義思想的盛行。隨后相繼更迭的明、清二朝進一步加固了程朱理學的絕對性地位,使個體的思想更為僵化,因而引起一批思想家的強烈不滿,并由此而掀起了一場帶有反封建、反傳統、反理性束縛特征的思想解放潮流。
李贄等人對于僵化的程朱理學的思想批判為彼時的書法藝術界提供了創作理論基礎,尤其推動了傅山的思想觀念轉化。傅山書法藝術風格轉向“拙”之特征,大有針砭時弊、響應反傳統和反理性束縛思想的意味。
(三)人格力量的升華
傅山論書法首重人格,因此其書法藝術風格中往往表露出升華的人格力量,并通過筆力的控制、“奇字”的設計、率性和疾速的落筆淋漓盡致地呈現[5]。青年時期的傅山處于國破家亡、明清易代之際,受傳統書學教育和儒家思想的渲染,其內心深處對前朝的忠誠、對異族統治的憤懣、對遺民人格的捍衛情緒迸發而出,因此,無論是為人處世抑或是書法創作,其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愛國主義精神和升華的人格力量,并凝聚成其獨特、剛強、富有骨氣和骨力的書法藝術風格。以《段帖》中收錄的傅山楷書作品為例,堅韌甚至力透紙背的落筆足見其剛毅倔強的人格力量。
三、結語
綜上所述,從收錄傅山晚年書法藝術作品的《段帖》中來看,在該歷史時期,傅山的書法藝術風格兼具質樸和高雅的古韻、輕靈和流暢的自然、顯而易見的差異性和轉換性等特征。回顧傅山所處的歷史時期,可知其書法藝術風格的形成受到時代背景、思想觀念以及人格力量的共同影響,三者的合力也因此滲透在傅山的書法藝術作品之中,成為研究傅山本人或其書法藝術作品史的重要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