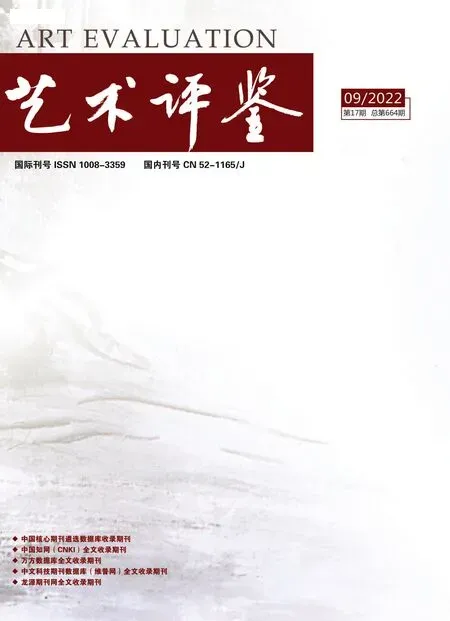中國民族管弦樂隊的發展及“交響化”探析
孫冉 山東藝術學院
20 世紀20 年代,我國出現了一個新型的民族樂隊,即:民族管弦樂隊。一些學者,如汪毓和、梁茂春、喬建中等,都對我國民族管弦樂隊的改革與發展展開過深入探索。
一、民族管弦樂隊的發展概覽
20 世紀,一些從事民族器樂演奏的民間音樂團體陸續出現在城市中。如1920 年,鄭覲文等人秉著“傳承古曲和傳統器樂合奏曲進行傳承與培訓”的宗旨,在上海發起并創辦了大同樂會。其設立了研究部、編輯部等機構,后來組建了我國第一個具有三十多人的新型民族樂隊,這可以視為我國民族管弦樂隊的萌芽。在那個年代,設置樂隊時以傳統絲竹樂隊為基礎,即建立以簫、塤、笙、鐘、磬、七弦琴、瑟等樂器組合的雅樂樂隊為先,在此基礎上又設置了吹管樂、拉弦樂、彈撥樂、打擊樂四個聲部。從這里可以看出,這個樂隊提出了民族管弦樂隊的設想,分為吹管樂器、拉弦樂器、彈撥樂器、打擊樂器四個樂器組,且對樂器音色、音量的組合問題也有考慮,在此基礎上也對一些民樂合奏曲進行了整理排編。再如,“滬江國樂社”在作曲家譚小麟的指導下,也探索了新型民族器樂合奏問題,譚小麟在民族樂隊的配器上運用樂器分組的原則,在其創作的《湖上春光》一曲中有初步體現。此外,“中央廣播電臺民樂組國樂隊”在這一時期的中國民族樂隊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35 年在南京成立的這個樂隊形成了大型民族樂隊的基本體制,實現了“南北合流”的樂隊編制,其是在廣東音樂和江南絲竹樂的基礎上,吸收了北方打擊樂的形式。樂隊鼎盛時,開始設有專職指揮、作曲,采用改良樂器,樂隊的表現力有了新的發展,演奏的作品也開始表現當時社會戰斗的新內容。
可以看出,20 世紀20—30 年代的作曲家們在擴大、豐富我們民族樂隊編制的想法中,開始有意識的探索并學習西方交響樂的特點。
20 世紀50 年代以后,社會上逐漸形成了一些新型的民族樂隊,一些大型民族樂隊的新作品也應運而生。其中以上海民族樂團、中國廣播民族樂團、上海電影樂團民族管弦樂隊、前衛歌舞團民族樂隊等民族樂隊較為突出。這些民族樂隊大多采用了從20世紀30—40 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吹、拉、彈、打四個樂器組為基礎的編制,也從西洋管弦樂隊編制中吸取了成功經驗。樂隊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絲竹樂隊為基礎,如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和上海民族樂團;另一種是以吹打樂隊為基礎,如前衛歌舞團民族樂隊。20 世紀50 年代的民族樂隊作品多數是根據古曲、民族樂曲改編的,也有的是從管弦樂隊作品移植而來的,因為當時專業作曲家鮮有參與,多數作品是由民族樂隊的指揮家、演奏家所作,所以作品略顯“業余”。這時的樂隊設置追求當時西方已形成的大樂隊體制,作品更多的是盲目吸收西洋管弦樂隊的經驗,生搬硬套的追求“交響性”。
可看出這一時期民族樂隊的發展,成就主要集中于大型樂隊建設方面,顯示了“遍地開花”的良好形勢。但是中國民族樂隊在“文革”時期也是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和摧殘,直到20 世紀80 年代,民族器樂才開始進一步恢復、發展。
20 世紀80 年代以后,民族管弦樂隊的發展有著“困惑與繁榮同在,艱難與興旺并存”的特點。困惑在于,這時期的樂隊工作者們在大型民族樂隊的建設、排練、演出等方面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從而有許多阻礙。但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再度崛起,專業作曲家開始加入民族樂隊的創作中,努力從民間音樂中發掘“戲劇性”“交響性”因素,將民族樂隊的作品推向了一個繁榮高峰。20 世紀80 年代以后,專業作曲家的加入使得創作的大型民族樂隊作品水平更高,推動了民族交響音樂的發展。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李煥之的箏協奏曲《汨羅江幻想曲》、高為杰的民族管弦樂合奏《蜀宮夜宴》、何訓田的《達勃河隨想曲》,以及劉文金的二胡協奏曲《長城隨想曲》等。
這一時期的民族樂隊出現了多元化的特點,由于專業作曲家的加入,使得作品創作不再迷茫和僵硬,作曲家開始注意民族樂隊自身的色彩,找到適合發展民族樂隊自身的規律。可以說20 世紀80—90年代是民族管弦樂隊的一個豐收時期。
通過對民族管弦樂隊發展的概覽,我們看到雖然民族管弦樂隊在發展的幾十年間道路蜿蜒,但在學者們不斷的探索實踐下,創作出來的作品質量越來越高。
二、樂隊“交響性”創作理念的變遷
任何改革都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創新,所以要真正做到民族管弦樂“交響化”,其“交響化”的創作思維是必不可少的。
通過以上梳理的民族管弦樂隊的發展階段,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族樂隊的改革是以西方管弦樂隊的模式為標準的。中西音樂文化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民族管弦樂隊無論是在樂隊編制、音色的協調與音響效果的統一等方面,還是在表現戲劇性的張力,矛盾的對比、沖突,以及內心情感刻畫等方面,與西方管弦樂隊相比都有不少差距。因而,中國民族管弦樂團的改革重點在于對樂器的改良、樂隊的編制、樂隊的作品及樂章結構。
音樂家在了解到中國樂器的特殊性后,通過改變樂器的材質、形制等,進而對樂器進行改革,使音色趨近,便于音響效果的統一。在樂隊編制上,加入低音樂器,加強民族管弦樂隊的中低音聲部,達到寬廣樂隊音域的目的。在創作作品時,作曲家們為使音樂具有復雜的、戲劇性的表現力,開始追求作品的多樂章結構或單樂章作品采用大型曲式結構,在表現復雜的情感變化和細膩的內心獨白中采用多聲、復調的表現手段,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有哲理的思想內涵。
總之,作曲家們在創作上開始追求氣勢磅礴的樂隊,追求具有豐富音色的演奏效果,追求創作對比強烈、變化多樣、思想深刻、內容廣泛的樂隊作品。
三、樂隊的形成與發展原因
民族管弦樂交響化探索不僅需要創作思維和技術手段的綜合運用,樂隊編制也是民族管弦樂“交響化”的一個必然要解決的問題。在我國民族管弦樂探索的過程中,對于樂隊編制的探索也是逐步深入的。
最初,我國民族樂隊大多是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傳統的“江南絲竹”等模式。后受到西方樂隊模式傳入的影響,我國民族樂隊開始參照西方的構建方式進行“交響化”探索。西方交響樂隊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其樂器的種類、樂器的數量、各種樂器的分組、樂隊演出時的座位排列等,均因時代的變遷、作曲家及創作風格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這種樂隊模式是以相對穩定的形式傳入的,所以在民族管弦樂隊交響化的探索中,也有出現過一些生搬硬套西方的管弦樂隊模式、忽視我國民族樂器固有特點的錯誤,比如不加實踐的讓二胡演奏小提琴聲部、讓嗩吶代替吹小號的旋律等,這也說明我們對“民族樂隊交響化”的認識不夠全面,改編重點有所偏頗。
隨著時間的推移,作曲家們的創作水平有所提高,作品中表現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對傳統文化及民族樂隊“交響化”的認識也更加深入,我們的民族樂隊創作在揭示傳統文化的底蘊方面越來越成熟。在樂隊編制上,作曲家對樂器的運用更為靈活,在固有模式的基礎上考慮民族樂器的特殊性,根據音樂表現的內容和情感,靈活地選擇樂器。例如,錢兆熹的《和》,樂隊中除了有常規的拉弦樂組、彈撥樂組和吹管樂組外,還大量運用了打擊樂器,除了一般常見的打擊樂器,如堂鼓、鑼外,還運用了彈板、風鼓、搖風器等不常見的打擊樂器,豐富了整體的音響效果,增加了樂曲感染力。值得一提的是,彭修文在民族樂隊“交響化”的探索中取得了顯著成果。他以西方管弦樂隊的組合方式為參照,在結合中國傳統民間樂器特點的基礎上,運用和聲、復調、配器以及樂器制作原理和技術,對樂器進行革新,進而構建了以“吹拉彈打”為基礎的中國模式的管弦樂隊,這一構建方式也被稱為“彭修文模式”,在之后的一些民族管弦樂隊中廣為應用。此外,部分學者依舊認為,我國民族管弦樂隊編制不用急于固定下來,仍有繼續探索的空間。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樂隊編制的探索道路也是曲折蜿蜒的,但在探索過程中也收獲頗豐,民族管弦樂隊也呈現出繁榮發展的趨勢。那么,民族管弦樂隊形成及逐漸興旺的原因是什么呢?
20 世紀初,當時一些知識分子大力提倡“學習西方”,因此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開始學習西方的模式。我國民族樂器具有不確定性,發展形式呈多樣化,因而有著很強的包容性。在當時,一些民間音樂團體進入城市,為了發展自身,這些民樂團體吸收了西方的音樂文化,因此使我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發生碰撞,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必定會產生一種新型模式,因而為以后民族管弦樂隊的成立做了鋪墊。最初音樂文化并不受社會重視,所以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及音樂的社會地位,我們可以看出民族管弦樂隊形成初期并無政府參與。
學堂樂歌的活動,使人們意識到音樂教育的重要性。當時有很多留學日本的人士,如沈心工、李叔同等,他們在日本學習,考察音樂教育,并在回國后致力于音樂教育的發展,因此逐漸提高了音樂在社會中的地位。音樂社會地位的提高,促進了音樂文化的發展,進而也推進了民族管弦樂隊的形成。建國后,社會環境相對穩定。為了振興文藝事業,國家提出了新的方針政策,許多文藝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開展了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工作。為了適應時代條件的變化,以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政策方針的指領下,全國廣大音樂工作者以豐富音樂創作為中心,全面推動新中國各項音樂事業的協調發展。在這些方針政策的指引下,民族管弦樂隊也得到了極大地發展,一些民間藝人開始加入樂團,進入學校學習,各地紛紛組建新型民族管弦樂隊。同時為了滿足樂隊演奏的需要,開展了樂器的改良工作,因此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民族管弦樂作品,但樂曲創作大多是“比著葫蘆畫瓢”,即盲目的將西方樂隊模式套入中國民族樂隊中,加上企業的介入,使得樂曲創作受到限制,因此作品雖多但是質量不優。
到了20 世紀80 年代,樂隊編制基本形成,民眾的接受和欣賞能力也逐漸提高,專業作曲家的加入也提高了樂曲的創作水平。因得到政府的支持,1985年左右,民族管弦樂得到普及,一些民族管弦樂隊開始以講座的形式深入學校進行傳播,如香港中樂團,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民族管弦樂的繁榮興盛時期。
社會在變遷,時代在進步。在這不斷發展的時期,止步不前只會面臨淘汰,所以推動民族管弦樂隊的形成與發展,可以說是對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繼承與發展的重要策略,其逐漸繁榮的趨勢也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四、典范“彭修文模式”的再思考
“彭修文模式”是一種獨具民族特性管弦樂的新方式,其音源結構特征是彭修文先生按照晚清時期傳統器樂領域的分類(即吹、拉、彈、打)為基礎,并在傳統管弦樂隊模式的基礎上,探索適合中國民族音樂特點的音源結構,使得他創建的民族管弦樂隊不僅可以演奏西方模式的管弦樂,還可以演奏中國的古典作品。彭修文創作具有三個特點:一是注重傳統的音樂風格;二是借鑒西方古典音樂;三是根據實踐經驗自我創新的寫作方式。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創作、編配民族管弦樂作品時保留了傳統的音樂風格。彭修文不排斥西方的理論知識,他也借鑒了許多西方的和聲寫作、曲式結構等手法,只為將中國的民族管弦樂創作的更加成熟。“彭修文模式”得到推動的一點也是因為其在運用、吸取國外寫作模式的基礎上,保留了中國的傳統風格,將優秀的國外創作技巧融入中國民族管弦樂中,推動了中國民族管弦樂的發展。彭修文采用中西結合的方式走出了自我創新的新道路,這種對傳統模式的保留、對借鑒西方技法后自我創新的思考模式,對當時的民族管弦樂來說是極具開拓性的一步。
“彭修文模式”可以說是在對傳統音樂的繼承和將西方音樂本土化的實踐過程中催生出來的,這個模式促進了中國民族管弦樂的發展,不僅為專業的職業樂團編制奠定了基礎,也為今后民族管弦樂的發展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因為這個模式的成功,所以成為民族管弦樂的傳統范式,但這個典范模式被其他各個樂團借鑒和模仿,使得民族樂團在一定時期內的形式逐漸趨向“大一統”,對于其民族管弦樂多樣化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因此,20 世紀80—90 年代“新潮音樂”作品的出現,比如郭文景的《蜀道難》、朱踐耳的《納西一奇》等,為民族樂隊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華民族是一個團結的民族,在很多方面都力求團結一致,跟風也成為了一個普遍現象。“彭修文模式”作為民族管弦樂交響化的成功范例,引起很多其他樂隊的模仿。但藝術作為一種不定性的文化,應該保持它的多樣化,才能煥發出新的活力。在對成功的事例進行參考時,也需在保持自己獨有特征的基礎上,借鑒汲取其中的一部分內容,跟隨大眾、力求同化、盲目模仿只會使這種藝術逐漸泯滅在歷史的長河中。藝術是開放的、多樣的,只有多種個性風格相互碰撞,才能產生出新的火花,進而不斷進步。
五、結語
通過上文對民族管弦樂形成與發展的梳理,以及對創作思維、樂隊編制、彭修文模式等分析與思考,可以看出我們的民族管弦樂隊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但也暴露出作品單一化、對民族樂器不夠了解等一系列問題。對此,筆者有如下看法:
我國民族器樂的發展經歷了很長時間的歷史積淀,從先秦到清代,民間的器樂合奏形式始終以不同形式表現在中國的土地上。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和影響,以及一批作曲家開始主動學習西方基礎理論,對于我國傳統音樂的演奏形式有了更深刻的思索,開始有了借鑒西方樂隊、豐富民間樂隊的意識。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思想也逐漸變得更為復雜和深刻,在作品中表達思想和一些含有哲理性、觀念性的內容成為了一個新的趨勢。那么,樂隊作為呈現音樂作品的一個載體,“交響化” 成為民族樂隊前進道路上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反觀西方交響樂的發展,從最初較為簡單的結構發展到浪漫主義時期,再到20 世紀承載著復雜思想性的大型交響樂作品,也是從無到有逐漸探索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們的民族樂隊也需要跟隨潮流、發展自身,從中西結合中探索契合中國民族樂隊的交響化。在探索交響化的過程中,我國也形成了不少有所成就的民族管弦樂隊,如香港中樂團等,而且也相應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如由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演奏的《秦·兵馬俑》、香港中樂團演奏的《秋決》,此外還有《靈山梵音》《豐收鑼鼓》等樂曲。這些樂曲的成功演出,說明我們的民族樂隊可以進行交響化創作。
“民族樂隊交響化”是將我們的本土與西方兩個音樂文化融合在一起進行創作探索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提升的過程。那么,如何進行交響化也成為一個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我國音樂家在探索和實踐過程中,也出現過生搬硬套西方交響樂隊編制的情況,但我們的民族樂器相比西方樂器更為個性化、特殊化,以至于器樂合奏中的融合性相比西方較弱一些,單純采用西方的樂隊規制且僵硬地套在中國民族樂隊上是不合宜的。在創作上,我們需要深入學習和挖掘中國優秀傳統音樂,加強對民族樂器的了解,以使音樂整體和諧的同時發揮本民族的樂器特色,并能靈活地選擇樂器、編排樂隊。在思想上,我們要在保留自己民族性和地區性的基礎上,有目的的吸收外來音樂文化,在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找到適合中國民族管弦樂的發展道路。
民族管弦樂的發展道路是充滿挑戰的,它需要我們不停地實踐,反復摸索。過程雖痛苦但前途光明,在音樂家們的不懈努力下,我國民族管弦樂的表現力及藝術成果也逐漸令人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