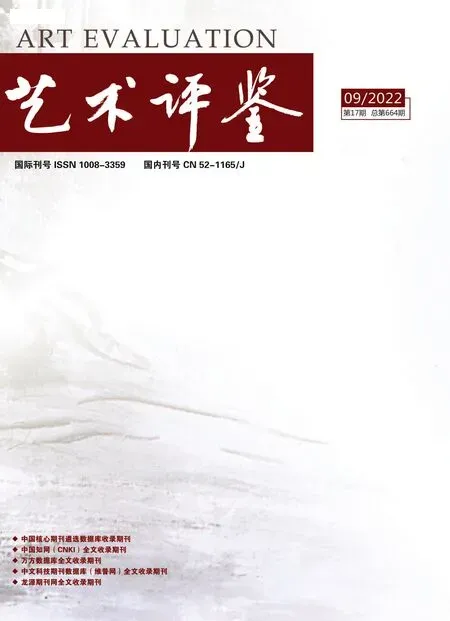從藝術本質論“藝術終結論”的哲學反思
何茂碧 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
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其在《美學》中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黑格爾說美是理念,美與真是一回事,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是建構在“絕對理念”辯證發展的理論體系上的。美是理念或現實物象的一種表現形式,指的是形式、內容、意蘊,藝術是表現具體物象或當下時代觀念的載體,當藝術對歷史環境的發展貢獻到一定的程度,哲學將代替藝術,藝術必然終結。
一、藝術終結理論
黑格爾哲學體系中藝術的“終結”不表示“停止”或“消亡”,時移世易,這個光輝時代正在悄然隕落。從哲學思維的深度提出藝術終結,在絕對理念中分為三個階段:主觀精神、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藝術、宗教和哲學是絕對精神的三個發展階段,其中包含兩個維度,時間維度和精神維度,對藝術本身而言,是表現一個時代精神的合理呈述形式,環境的影響帶來的社會反思和自我覺醒的變遷,精神概念產生出來的形態觀念,對最初表象式的本質和它的自我性有一種互不關聯的內容意識的變化。思想觀念的停滯不前,同時鎖死了藝術形式的進步。丹托的藝術終結論理念剝脫了外在形態,而處于歷史的維度,因歷史環境萌芽出的藝術品而被賦予不同的詮釋意義。當《布洛里盒子》出現時,一切架構都在具有一定藝術理論和藝術史上。當藝術產生本質的思考方式的結晶在概念中辯證,探究其價值和真理的追問,是藝術品與普通物品的差異,只有哲學可以展示該差別。生于西方文藝復興發展時期的“藝術終結論”,保留了前面人文主義學者演化成的“藝術家”,主張自由發展平等和自我價值的揮發,藝術呈現的一種精神時代和社會風俗某一特征的體現,揭示了人的自我覺醒的意識。所以時代的藝術形態必然隨著歷史泯滅,藝術始終在傳統藝術和當代藝術的規律中來回更迭,藝術最終走向終結。
二、從藝術本質論藝術終結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柏拉圖設有畫家、造床匠、神造三種床,神制造的床只有一個,這是本質的床,造床匠制造的是世界理念中的床,而畫家是模仿造床匠制造的床。一個是創造者,一個是制作者,制作者是創造者的影射,畫家是對影像的模仿,模仿的產物不需要知識和見解,其主要靠被模仿產物的某一個角度進行繪畫,藝術家有著技藝高超的畫功就可以騙過一些“笨人”和小孩,距離真實世界隔著三層真理,將藝術衍生到藝術實在的絕對實體領域,理性驅逐了感性,藝術是影子的模仿,世界是“理念”世界的縮影,存在于客體的精神世界,這些理念基于柏拉圖唯心主義理論。唯心主義理論是把人的意識從具象物體中剝離,把相對獨立性的意識凌駕在萬物主宰之上,隔離出存在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東西。觀念理論是柏拉圖哲學的核心基石,注重意識與實在的自身協調的統一。
摹仿說在西方藝術界仍占據著一定地位,美學歌德在《關于藝術的格言和感想》中論述:“假定特殊表現了個體,不是把它體現為夢或影子,而是把它表現為奧秘不可測的一瞬間的生動的顯現,那里就有了真正的象征”。在不可知論的真理中顯現,使我們在相對獨立剝離出來的東西中認識這個理念世界的存在可能,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是普遍的真理內容本質,是在某種具體現象中顯現的感官,對藝術與現實看法的共知,人們可以領悟到更高層次的存在,洞察現象的本質,了解具體特殊的對象與普遍一般的觀念統一。在《自然的單純模仿·作風·風格》,歌德將藝術創作分為三個階段,最初的階段是藝術家追求忠實,精確地臨摹自然表面的世界景象,再者藝術家本身對事物的心領神會,進而創造出的一種語言表達形式,最后是藝術的風格,藝術家要基于精湛的知識依附事物的本質進行創作,即接近物體的真實性又體現創作者的精神理念,不是單純地臨摹,是創作者自我消化,將內在情感解放和理論認知的對象特征遵從事物具象和探索現象本質投射出的概念表達,藝術作品與藝術形式達到統一,使特殊對象隸屬于一般概念,以區分差異。《論德國建筑》里,歌德提出了特征概念,一個民族精神特征的獨特性格。
從時代與藝術的角度來看,黑格爾講述:“藝術卻已實在不再能達到過去時代的,滿足了過去人們在藝術中尋求的精神需求,而這些精神需求只能在藝術中找到,至少滿足了與宗教和藝術最密切相關的精神需求,希臘藝術的輝煌時代和中世紀晚期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現時代的一般情況是不利于藝術的”。維科的《新科學》采用了“時代”的概念,他理解的時代是像季節一樣,具有循環連續性,是歷史必經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神的時代”,產生神話的粗野、自然原始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英雄時代”,歌頌戰爭和騎士英雄史詩的時代;最后一個階段是“人的時代”,人發現理性的時代(啟蒙時期)。現代藝術不斷推翻精神上與藝術的邊界,有些藝術品給人第一視覺形象感到不適,拋棄這件作品的視覺表象,轉而去思考這件作品的本意是什么,擯棄了理性意識世界的反映,是主觀世界的表現對客體實物的現象分析和綜合,是最早出現的印象派。
莫奈的《印象·日出》是其創作的一幅法國印象派油畫,同時也是印象派風格的開創,這幅畫是在日出晨霧時的港口描繪的,描繪了光的運作軌跡和光的幻覺,展現了日出港口下的景色,帶著輕快跳躍的筆觸,描繪了寬廣海面上的光線折射和物象幻覺的生動景象。以瞬間的印象作畫,不依靠已有知識創造,抓住一個具體物象的側面進行生動刻畫,迅速畫出的產物呈現的是多慮的畫面效果,作品缺乏修飾,對歷史內容的描寫表達的繪畫形式減少,富有創造力的形式狀態勝過對世界客體現實的本質,與已知傳統決裂,是一種理念和形象不和諧的階段,精神內容模糊,自我創新而顯現出的藝術。黑格爾所處的時代正是古典主義文化與文藝復興的過渡時間,認為藝術是一種精神滿足,當時周圍環境個人私欲膨脹,物質享受,奢靡泛濫,學術思想自由斷裂,人道主義趨于淘汰。藝術內化為外在形式,意味著近代藝術的發展丟棄了傳統理念,主張“個體”,藝術已經意識性質的表現,任何物體都可以是“藝術”,用哲學的方式去思索藝術是什么,以及帶來的價值,不再有“敘述結構”的藝術形式,終結一切意識形態,整個時代精神文化以“偏重理智”的社會情境感染周邊盛行的風氣,并擴大和強化觀念本身,讓藝術趨向觀念,并轉移到世界觀念中,喪失了人類對藝術的精神需求,不再實現現實自身藝術的價值,“思考”占據藝術,不再滿足過去民族“時代精神”的需要。
歌德聯合席勒所指出的辨別在《說不完的莎士比亞》一文中提出區分古典主義與近代主義:古典的是質樸的、異教的、英雄的、理想的、必然的、責任的;近代的是觀念的、基督教的、浪漫的、現實的、自由的、志愿的。藝術是人類追求精神自由的重要途徑之一,真正的藝術,可以使人獲得情感體驗,并回歸內心的自然和精神上的自由,古典藝術是“對終極理想主義的追求”,是一種和諧的理想美,古羅馬通過政治和戰爭不斷探索世界,古希臘有很多以人為形象的雕塑,古希臘人基于對人體結構的觀察,對自然和市民社會相結合的詮釋,推理探尋世界最本質的現象。在古羅馬的神話中,米洛斯的維納斯是愛與美所誕生的女神。斷臂的維納斯讓人追求極致永恒的真實,自然修飾的痕跡,追求最本真質樸,外在美和精神完美地內化需求一致,呈現出一種古典主義的理想美,是古希臘美術過渡藝術成熟時期的至高境界的作品,沿襲了古希臘的人文主義精神,看到了“希望”和“愛”“存在”與“生命”,是理念浮現的感性美,古希臘的人文主義精神是最貼近自然的藝術,正是古希臘人對自然奧秘的探索發展路程,所以才孕育了哲學思想的種子,充當了精神需求的象征,這種最本質的物質個體形象表現了概念化,藝術講求現實物象的本質,追求外在形態的真實,注重人的思想,強調個性及內心的表達,引起人的思考和反思。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敘述到:“最高的藝術和審美體驗即使和最初的生命力的融合,擺脫個體化原則,讓生命本身噴薄欲出的熱力讓藝術創作者和審美者體驗到。”尼采堅信,藝術必然作為宗教和哲學的替代品給予人審美的和形而上的享受,借以讓深陷苦難的個體渡過茫茫的人生之海。藝術拋棄主觀常態意識,正視欲望,與欲望保持緘默,基于個體的自我為塑造的原型,擺脫個體的自我意識和欲望的枷鎖,當藝術以這種形式賦予價值,使現實藝術具有了實際意義。
三、追溯“藝術終結之后”的反思
“哲學往往姍姍來遲,作為世界的整體思想內核,它只出現在現實完成了自身的發展并結束了整個過程之后,只有在現實達成之后,真理才會顯現出來,與客觀世界對抗,繼而整個世界被理念重建,成為一個全新的充滿智慧和顯現了本質的世界,當哲學在灰色之上擦涂悲哀的灰色,生命也隨之衰老,哲學并不能重煥青春,只能認識到生命如斯,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到來才會進行起飛。”黑格爾意在說明哲學是一種反思活動。西方近代的人道主義的探究得到人們普遍性的關注,各類流派和藝術風格的涌現,造就了“形而上學”的局面。但丹托認為藝術的形式是作為不同的載體進行另一種新形式的闡述,時代文明的進步、個體的自我意識化、社會的變遷、理性的個體化,反而是藝術不再需要哲學的外在形態進行敘述,是哲學對藝術的剝離,不是藝術形式本身給人類帶來思想上的碰撞和啟發,是人類從自身引發的觀念進行探索,思考自然奧妙和真理,追尋藝術內在帶來的理念化和真理化,藝術就是“哲學發展”的本身,哲學是藝術上的思維發展,也是另一種形式上的“藝術”終結,是新的形式、新的思想,藝術得到了解放,思想引來了僵化,以想象力作為支撐,藝術搭建出形而上的結構作支架,人類懷著最本質的生命的理念去思考。蘇格拉底問畫家帕拉西奧斯,當畫家畫人物時,因為一個人不容易表現出美的不同方面,畫家從許多人物中提煉出最美的部分,使整個畫面顯得極其美麗。蘇格拉底再次提出,是否也能描繪出心靈的性格,比如:扣人心弦、令人喜悅的可愛性格,還是這種性格根本無法描繪,帕拉西阿斯這樣回答,怎么能描繪出這種無可度量,沒有色彩的,沒有一種形式的,看不出并觸碰不到的東西。古希臘的雕塑正達到了這種形式,通過外在形態便把人物內心的活動表現出來,使人的精神世界和內在心靈進行藝術闡釋,歌德的特征概念中,他一方面強調創造想象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想象力須依靠感覺力、知解力和理性。藝術家在創作中,基于自身的觀念理論認知和想象力,在黑格爾體系中,想象力具有生產力,人類個體創造出的想象力也是具有生產力的,是便于從感覺經驗和知識理論的框架里構建出人類理解事物的一種建構,想象力本身沒有實際知識做支撐,并不能直接涵蓋和解釋某些觀念,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知識建構的意識。
黑格爾的《美學》里追求的是一種藝術能夠反映絕對精神的構造。藝術通過理念使其具象化的表達,從而揭示絕對精神的表達形態,藝術的表達就是為了證明這種精神理念的存在而形成的性質,在這種絕對理念中,所有實體的具象都能夠施展自身的價值,使精神理念與歷史意義的存在通過藝術得以體現出來,同時也是一定的理論文化知識通過其自身藝術使人理解和施展,不僅是事物本身的存在,也是具象化的運行機制的軌跡,是藝術本身體現了某種思想、某種理論,也是主體與客體的一種特殊關系,主體對客體的形式,主體的存在進而更加了解客體的理論精神和充滿表象的物質世界最本質的含蘊,使這些理論浮現于世,并通過藝術了解和實現自身,所以藝術是一種詮釋絕對精神的工具,也是詮釋絕對精神的一種解釋的載體,更是對這一過程的結構實現。歌德指出近代側重理智的文化對藝術不相宜,“當下的這個世紀在理智方面固然是很開明了,但是極不善于把明晰的感覺和理智結合在一起,而真正的藝術作品卻只有憑這種結合才創造得出來。”藝術具有感官性、實體性,具有物質表象的實體形態,隨著歷史的與時俱進,不同階段的思想變化和理論認知,藝術的物質形態逐漸減弱,在概念與精神層面逐漸深化,主體心靈的需求轉到了內在化、理智的觀念世界中,也就是藝術的形態只是一種表達手法,內在理念的認識更加強烈,個體的理論達到一定知識儲量才得以理解,脫離物質形式,脫離感官世界,客觀的存在趨向理性觀念、概念化發展,更具有自我意識的覺醒,更自我意識化,呈現出一種更理想化的存在。
鮑桑葵指出的歌德特征論理論征象,強調有內容的形式,一個民族的性格就是其特征,藝術家必須刻畫出這種特征,才能達到一種典型性,特征就是一種有內容的形式,人們能夠通過這種形式洞觀到藝術的精神。古羅馬建筑、哥特式的教堂,精致的雕花和內部結構的功能,規模的宏大、建筑物質外在形式都在顯現出宏偉的氛圍,以及功能和形式的統一。黑格爾講述,“這個時代的思想和條件不利于藝術的發展,藝術已經達到其頂峰,以后也不會被超越”。歷史的運動軌跡順著自然規律進展,進而推動歷史前進,而時代建筑的建造和形象都無不彰顯著這個時代的精神理念和它存在的運行功能機制,建筑本身涵蓋了精神意義,強調了整體的生命力,建筑整體形式表現自然而然生長的生命力,感性的顯現,是去材質化的形式表達,建筑代表歷史意義,是歷史成就而創造的不朽作品,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藝術則凸顯了歷史客體形式和時代精神的載體形式,是宏大的敘事鋪墊,統一了絕對精神形式概念的顯現,非物質化的呈現一些概念,是直觀的和客觀的,歷史精神理念賦予了藝術一定的價值。
歌德認為只有兩種結合的一致才會被引到真實和現實的領域,感覺力把繕寫清楚的形象交付給它,知解力對它的創造力加以約束,而理性則使它具有完全的確實性,不是通過戲弄夢的幻象,而是根據觀念。兩種概念的結合在實體物質的協調性讓這種美得到了統一和具體化,視線上直觀豐富了人類精神世界的理念,對絕對精神的意識更加普遍化。古典主義階段中,古典雕塑使人類的形體可以展示出一種精神意義,形式和理念巧妙地協調在一起,完成精神的統一,通過本身物質展現。在某種意義而言,藝術更加真實,使絕對精神在藝術形式上得以彰顯,在浪漫型階段,黑格爾認為藝術在發生轉變,從物質世界轉向理念化,這是個“偏重理智”的時代,意味著藝術的終結,不代表藝術迎來了死亡,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但過去民族精神的偉大藝術已成為過去,客觀存在的物質已經不足以彰顯和詮釋絕對精神,脫離了真理的性質,轉向一個純粹的視覺現象和表象的物質形式,轉向宗教和哲學的范疇中。藝術結束了,但藝術創作仍還在繼續,藝術形式是依附于其他的理論知識和文化而存在的理論框架圖。
四、結語
藝術透過世界規律分享自己的認知和對事物本質的蘊涵,標志著一個民族精神的特征,是為了滿足對主觀缺陷情感寄托的一種形式表達。歷史藍圖的背后是歷史理念在支撐,時代的理念精神通過對客體物質世界的反映塑造出來,藝術就是時代特征對理想特征塑造出來的產物,個人精神內涵沒有形成的主體意識,必須通過客體塑造出現實物質世界的主觀意識。人自身的意識化,當“內在理念”超越了“外在形態”,從而使真正的“藝術”終結亦或是藝術迎來新的轉型,藝術承載著與歷史息息相關的理性信念,特殊和個體形式達到統一。當藝術采取巧妙的描繪手法創作以達到人類的精神需求和審美基礎,采用推理的方式,用純描述的形式講解藝術,觀念擴入藝術,情感成為了藝術最直觀表達的主觀意識,呈現于視覺感官的印象,歷史的建構表明藝術的發展并非連續性的,歷史的發展進程讓藝術不斷靠近一種新的認知和新的表現形式,某種意義上的歷史維度到達了一定限度,藝術以一種“超前形式存在下去”,藝術的存在價值便不再賦有歷史觀念,當這種認知成為實際,藝術迸發出的觀念和哲學也隨之出現,這時的“藝術”意味著藝術家個體的自我認識和個人情感的獨特性的表達物,不拘泥于本質的現實具體物象的形式,當理論成為絕對,客體存在的現實物質的減弱,理性觀念的逐漸深化,藝術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