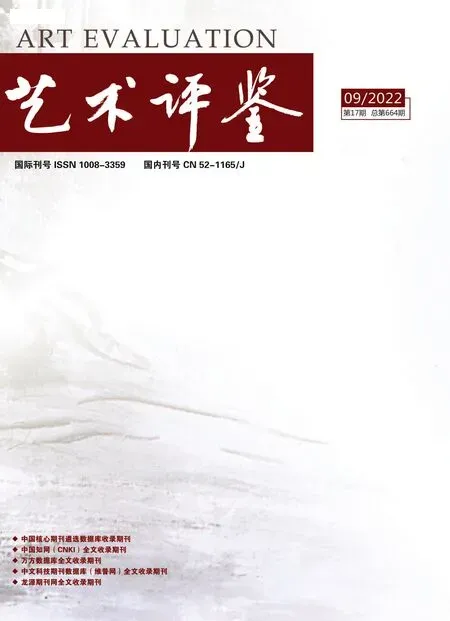論后戲劇劇場的政治性
白璟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
自從20 世紀80 年代的戲劇觀大討論之后,可能再也沒有比“后戲劇劇場”更能引起中國戲劇學界如此廣泛爭鳴的問題了。對于后戲劇劇場,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不絕于耳,而其招致批判的主要原因,是有人認為該種表演方式“以自我指涉的能指表演取代歷史現實指涉性的美學邏輯”,進而“意味著政治性的實際缺失的”,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新興的舞臺藝術模式,后戲劇劇場放棄了傳統的劇本中心制度,轉而以舞臺表演為主導,用對自身的指涉代替了對現實的指涉,因而缺乏明顯的社會—歷史與政治意義,是一種具有唯美主義傾向的形式游戲。然而雷蒙·威廉斯曾經指出,對形式的分析必須扎根于對該形式形成過程的分析中,特定藝術形式的興起不僅與文學創作本身的發展流變有關,也同樣與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相關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經強調事物之間存在著的普遍聯系與相互作用,是故文學藝術和政治之間的關系也并不是分置在相互隔離的抽屜中的機械組合,而是時刻水乳交融的,共同構成了社會生活的有機整體。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要求我們要用歷史與美學結合的方法評判文藝作品,這不但要求我們要關注文藝作品形式上的特征及其帶來的審美效果,還要將其返歸到它生成的社會歷史背景中,考察這種形式特征及其審美特質是怎樣形成的。因此,形式不只是藝術外在的存在方式,它和內容一樣,都能反映出一定的政治觀念。本文將圍繞后戲劇劇場的形式問題,分析其形式所承載的政治性含義。
一、戲劇形式的政治內涵
現代主義文學誕生前,“真實性” 曾長期是傳統文學,尤其是戲劇與小說的最高追求。盡管英語中小說本身就有“虛構”之意,而戲劇也具有“扮演”的意味,但這從來沒能阻礙傳統小說家和劇作家為營造真實性時所做的努力。19 世紀的藝術家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甚至有將文學藝術直接與科學等同的傾向。巴爾扎克將他的皇皇巨著《人間喜劇》系列分為風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部分,顯然是以社會學家自居;左拉更是直接表示藝術家應當像科學家一樣,在文學作品中實驗、觀察、分析,以獲得社會的真理。而為了強化文藝作品的真實感,藝術家會采取各色各樣的藝術手法,例如將故事情節置于真實的地點、以社會中確實發生的事件作為創作素材、不厭其煩的細節刻畫等等。小說家致力于營造的虛擬世界只見于筆端,讀者也僅是在想象中將這種“虛擬真實”還原出來;但戲劇不但見諸紙面,還需要搬演于舞臺上、呈現在現實世界——因此,戲劇家對真實感的追求往往比小說家更加強烈。
德國戲劇學家彼得·斯叢狄指出,我們現在通行的“戲劇”體裁產生于文藝復興時代,其特點在于:戲劇中唯一的內容是人與人之間的間際關系,而 “對白”是構建這種關系的媒介,作家和觀眾在戲劇中都是“不在場”的;“演員與戲劇形象必須融合成為戲劇人物”,扮演關系絕不能顯現出來,與之配合的是鏡框式的舞臺形式;戲劇的時間性質永遠是“當下”的,其時間發展是一個絕對的“當下”系列,并且每個瞬間都包含著未來的萌芽。通過這樣的方式,戲劇最終在舞臺上虛構了一個與現實世界隔斷了一切‘物理’聯系的、完滿自足的‘鏡像’世界,將對真實性的追求推至了頂峰。
盧卡奇認為,藝術體裁是某種世界觀的表達和實現,其體制和特征是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具體制約中生發出來的,是某種社會話語的體現。藝術形式不僅僅是外在的框架,它和內容一樣,同樣可以體現出某種社會、歷史、政治的觀念,而戲劇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體裁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如此追求真實感的戲劇究竟體現出了一種怎樣的政治觀念呢?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一書被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家和學者奉為圭臬,其理論也構成了戲劇文體的哲學基礎。亞里士多德認為,每種藝術的本質都是摹仿自然,各藝術門類之間的區別在于摹仿的具體對象不同,而悲劇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門類,它摹仿的對象是“動作”。一連串的動作形成了情節,因此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情節便是形成悲劇的諸要素中最為重要的一種。亞里士多德對情節提出的要求是必須具有“整一性”,即摹仿一個“完整”的、“具有一定長度”的行動。具體來說,“完整”就是意味著情節必須是一個由一系列因果邏輯組成的、嚴絲合縫的邏輯整體。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對悲劇提出了時間須限定在一晝夜之內等建議。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經由卡斯特爾維屈羅等學者的闡釋和發揮,最終演變成了“三整一律”原則,其成為了古典主義戲劇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雖然浪漫主義作家對其大有批判,但三一律的生命力其實相當頑強,不僅 “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的著名的四大“社會問題劇”符合三一律,甚至常被歸于后現代主義文學的《等待戈多》和《禁閉》等作品也體現出了三一律的特點。
雖然亞里士多德以“情節整一”為戲劇的最高原則,但同時他也認識到,現實生活中真實的自然狀態并不是邏輯分明、條理清晰的。所以亞里士多德同時指出,一個人所經歷的事件有的“缺乏整一性”,而一個人經歷的許多行動也往往“并不組成一個完整的行動”——因此,亞里士多德所強調的事件其實并非自然的原初狀態,而是經過人類理性“加工”過的、能體現出因果邏輯關系的“自然”。也正因此,亞里士多德認為詩能夠表現更帶普遍性的事,比歷史更賦哲學性、更嚴肅。換句話說,亞里士多德的“情節整一”思想,體現出的其實是對人類以理性把握世界的能力的信任與推崇。同樣地,時間與地點的整一律對戲劇構建“鏡像”世界的行為來說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時間和地點的整一保證了戲劇更大程度地對現實世界的摹仿,能夠防止觀眾因為演出過程中頻繁的時間、地點的切換而產生不真實感。而在這方面,時間整一原則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斯叢狄認為戲劇的時間發展是一個絕對的“當下”系列,并且每個瞬間都包含著對未來的萌芽,換句話說,戲劇每個“現在”都是“未來”的伏筆。這也就意味著,戲劇的時間序列其實同時也是一個邏輯序列,它和情節結構一樣,都體現出了戲劇家運用理性能力、以因果邏輯解釋世界的意圖。
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凱瑟琳·貝爾西指出,經典現實主義戲劇和小說最重要的兩個特點就是營造真實世界的“幻覺”和塑造因果邏輯閉合的敘述。貝爾西還借鑒了阿爾都塞的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認為經典現實主義文學通過以上兩個特點 “質詢”了讀者,使讀者在潛移默化之中接受了其所承載的資產階級理性主義意識形態,從而不由自主地成為了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理念的理性式主體;在理性主義者看來,人不是某種超自然力量的傀儡,而是自決的、具有自由意志和自覺行動的主體,并且作為主體的人也是世界的中心,為世界賦予意義。
戲劇的情節結構并非真正的“真實”,而是創作者將一定意識形態觀念加諸自然狀態的產物,通過這種方式反映創作者對人類、世界、社會和歷史的某種想象性的把握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戲劇文體所承載的政治觀念。
二、后戲劇劇場的政治內涵
19 世紀中后期,西方思想界開始普遍出現一股懷疑主義的風潮。馬克思、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單個作為主體的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弗洛伊德致力于探索自我意識之下那個幽暗深邃、不可捉摸的無意識世界,人不但不是自由、自決的,反而時時刻刻受到無意識暗中的掌控。尼采在運用譜系學方法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之后,對始于蘇格拉底的西方理性思想體系發起猛攻,高呼要我們“重估一切價值”。戲劇體現的主體觀念及其背后的理性主義的思想支柱開始變得搖搖欲墜,而這種深重的思想危機也自然反映在了文藝之中,現代作家也對理性主義傳統產生了懷疑。前文說過,經典現實主義藝術手法所營造的“真實” 并非真正的“真實”,而是創作者對人類、世界、社會和歷史的一種想象性把握,是資產階級理性主義意識形態觀念加諸自然狀態的產物。因此,現代主義之后的藝術家逐漸將創作的重心從鏡像般描繪外在現實,轉向了展露文學自身的表現技巧,即用自我指涉替代了他者指涉——戲劇家在這場風潮中自然也不例外。
德國戲劇學家漢斯-蒂斯·雷曼是“后戲劇劇場”一詞的提出者,他的同名專著《后戲劇劇場》久在戲劇學領域聞名遐邇,自我指涉性是后戲劇劇場最大的特點。后戲劇劇場的自我指涉性主要體現在文本、空間、身體三方面。正如前文所述的斯叢狄的觀點,對白是傳統戲劇的核心內容,但在后戲劇劇場中,承載對白的劇本卻失去了中心地位,成為了和聲音、光照等要素齊平的舞臺元素之一。在后戲劇劇場中,語言文本不斷體現出差異性和重復性,以不同的語調和節奏出現,也時常不再表達清晰連貫意義。通過這種方式,文本不再專為塑造人物、建立對白、構建沖突服務,也不再是唯一的意義載體了。如此,情節便失去了整一性,最終使得觀眾拋開對語言意義的追求,轉而關注語言文本本身的形式特征,顛覆了傳統的理性思維,
空間也是后戲劇劇場致力于探索的劇場元素之一。傳統戲劇往往采用鏡框式的舞臺結構,這種舞臺的基本空間特點是與觀眾席完全分離,以便隔絕戲劇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系。通過這樣的舞臺框架,觀眾看到的是一個封閉、原生的世界,它是現實世界的反應,好像鏡中的倒影一般,演員的演出是“自然而然”的,他們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舞臺上生活一樣。后戲劇劇場的藝術家反對這種相互隔絕的觀演關系,他們嘗試采用種種手法,發掘空間本身的存在意義。后戲劇劇場中,“現場性”尤其成為了戲劇藝術家們追求的目標。20 世紀初以來影像技術高速發展,其描摹現實的能力深深震撼了戲劇家,使他們產生出一種“影響的焦慮”,迫使戲劇家反思戲劇的本質特征,而他們最終思考的結果是,戲劇藝術不同于影視藝術的最大特點就是現場性。正如艾麗卡·費舍爾-李希特指出的——戲劇始終強調演員和觀眾是同時在場的。因此,后戲劇劇場的交流重心從舞臺內部轉移到了舞臺與觀眾席之間。經典現實主義戲劇中的觀眾只不過是消極的旁觀者,但后戲劇劇場中,戲劇家開始有意識地利用演員、燈光、音響等舞臺元素與觀眾互動,打破戲劇世界的封閉狀態,從而激發觀眾的能動性,使其主動參與到戲劇意義的構建系統中來。這樣的演出空間所構建的不再是過去鏡框式舞臺所呈現的保守、封閉的世界,演員不再是單純為觀眾“凝視”的鏡像,觀眾也不再是被隔絕于舞臺世界之外冷漠而單純的旁觀者——他們平等相待,共同參與演出,在后戲劇劇場的舞臺空間里營造出一種“狂歡”的效應,從而把人們的思想從現實的壓抑中解放出來,發揮他們的創造性思維,重新審視變化中的世界和人類社會。
另一個體現出后戲劇劇場自我指涉性特點的維度是身體。經典現實主義戲劇以“情節整一”為核心,演員的身體不過是戲劇角色的“容器”,角色的動作與情感及由其體現的情節才是表現的重心。但隨著文本中心制和情節整一原則從戲劇的王座上跌落,觀眾首先面對的便不再是虛構的角色,而是真實演員的身體。后戲劇劇場的演員身體失去了目的性與意義性,從而使得單純的姿勢性顯現出來,不僅如此,后戲劇劇場藝術家還常常使用病患、反常、殘缺的身體使得觀眾產生恐懼與不適,以求更大限度引起觀眾的注意。對身體的強調使得演員不再是承載文本抽象意義的載體,而獲得了自身具體的存在意義,演員與角色的分離也破壞了傳統戲劇大力營造的真實性,使得抽象性的身體轉化為具體性的身體,揭示了被理性主義所遮蔽的人類生存的物質性。
劇場的“政治性”不等于直接將政治觀念或政治事件作為主題的戲劇。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與曹禺的《雷雨》《日出》等經典名劇均以家庭和社會問題為主題,但都體現出了鮮明的政治關注和政治態度,同時對社會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絕不能說這些作品沒有政治性。同樣的,政治性也可以不體現于藝術內容中,而呈現在藝術形式上。后戲劇劇場藝術家通過文本、空間、身體等多種方面的自我指涉技巧,暴露了自身的虛構性,顛覆了傳統戲劇對真實感的追求,使得觀眾無法沉迷于戲劇構造的鏡像世界,解構了劇場幻覺和經典現實主義的“真實”,揭露出現實主義也無非是一種戲劇技巧而已,從而抨擊了現實主義的“文化霸權”,突顯了戲劇程式所制造的“自然”“逼真”幻象之后隱藏的資產階級理性主義意識形態。在此基礎上,后戲劇劇場通過對打破“第四堵墻”,將觀眾和演員融為一體,共同參與和完成戲劇的演出,這打破了傳統戲劇演出模式中的等級觀念,重新建立了一個平等的共同體。
三、結語
“自我指涉”這個術語常常引起人們的一種錯覺,仿佛后戲劇劇場僅僅強調劇場藝術的表現手段,已經完全放棄了任何社會—歷史追求,因此常招致“反歷史”“非政治”的批評。然而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后戲劇劇場雖然不直接體現社會—歷史內涵,但是卻借由文本、空間、身體三方面自我指涉的手法,揭示了傳統戲劇“真實”背后隱藏的意識形態控制,間接起到了政治效果。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戲劇家布萊希特認為,“資產階級戲劇對生活的表現,總是從調和矛盾,制造虛假的和諧,把事物理想化出發”,因此他別出心裁地提出了“間離”理論,并系統應用于戲劇文學的創作和戲劇舞臺的演出中。布萊希特通常將情節設置在觀眾不熟悉的遙遠古代,戲劇中時常出現告示、字幕提示劇情,演出中不斷換幕,且毫不避諱傳統上需要盡量隱藏的舞臺裝置和幕后人員,直接將其展現在觀眾眼前。情節曲折,出人意料,且結構不符合傳統“開端—高潮—結局”的三段模式,甚至演員時常脫離人物,直接向觀眾對話、評論劇情。通過以上種種手法,布萊希特希望通過暴露戲劇虛構性的方式,為觀眾營造一種陌生化的觀劇體驗,阻止觀眾沉溺于劇情中,從而引發他們對劇情理性、獨立的思考,進而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不公與壓迫現象,萌生出參與社會改造的政治愿望。布萊希特是西方現代戲劇史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不難看出,后戲劇劇場自我指涉的特性正是承續并發揮了其間離思想的產物,而布萊希特獨特的戲劇形式所承載的社會—歷史觀念和政治追求,也必然由后戲劇劇場的嶄新形式所繼承。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可以說:后戲劇劇場就是后布萊希特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