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修斯時刻與卡夫卡式的佯謬
涂險峰 曹曉龍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卡夫卡的“奧德修斯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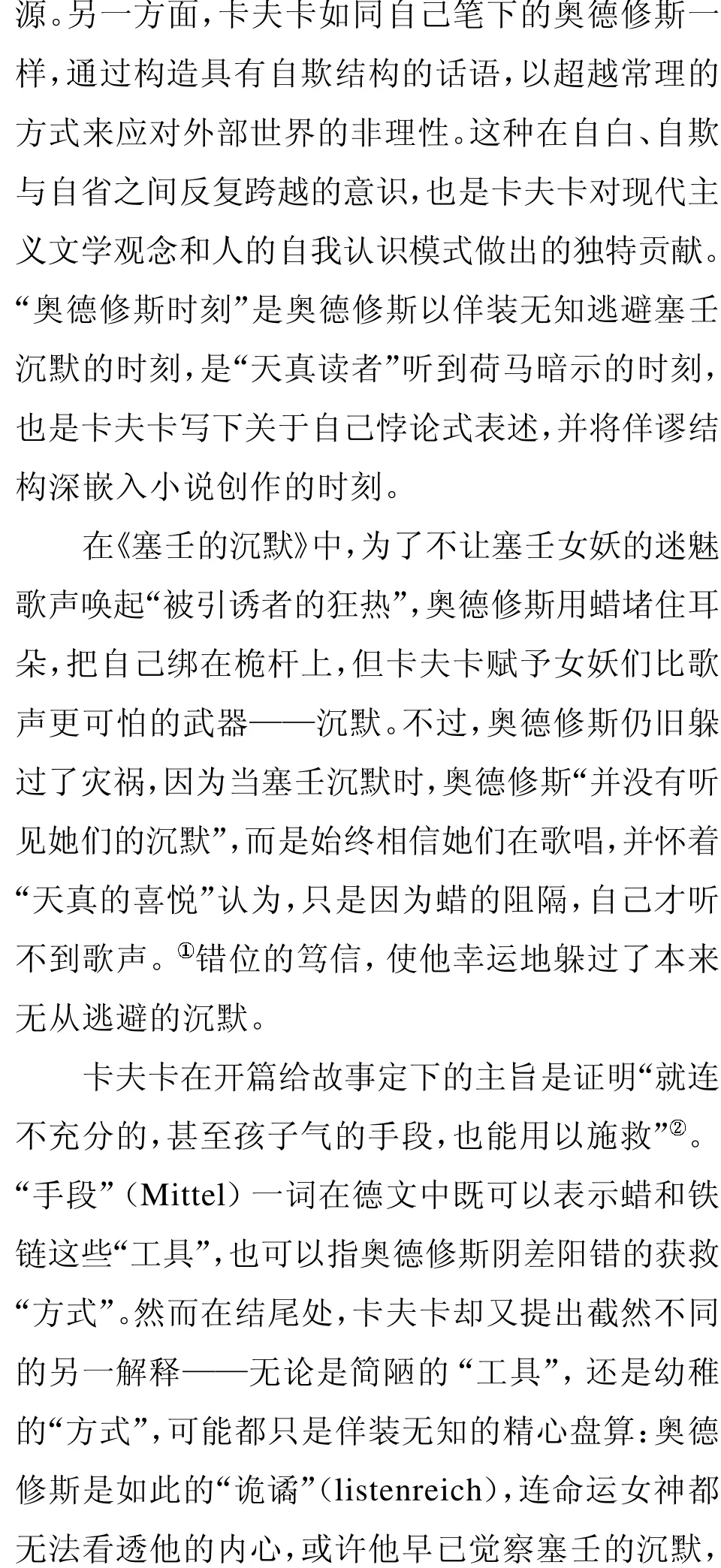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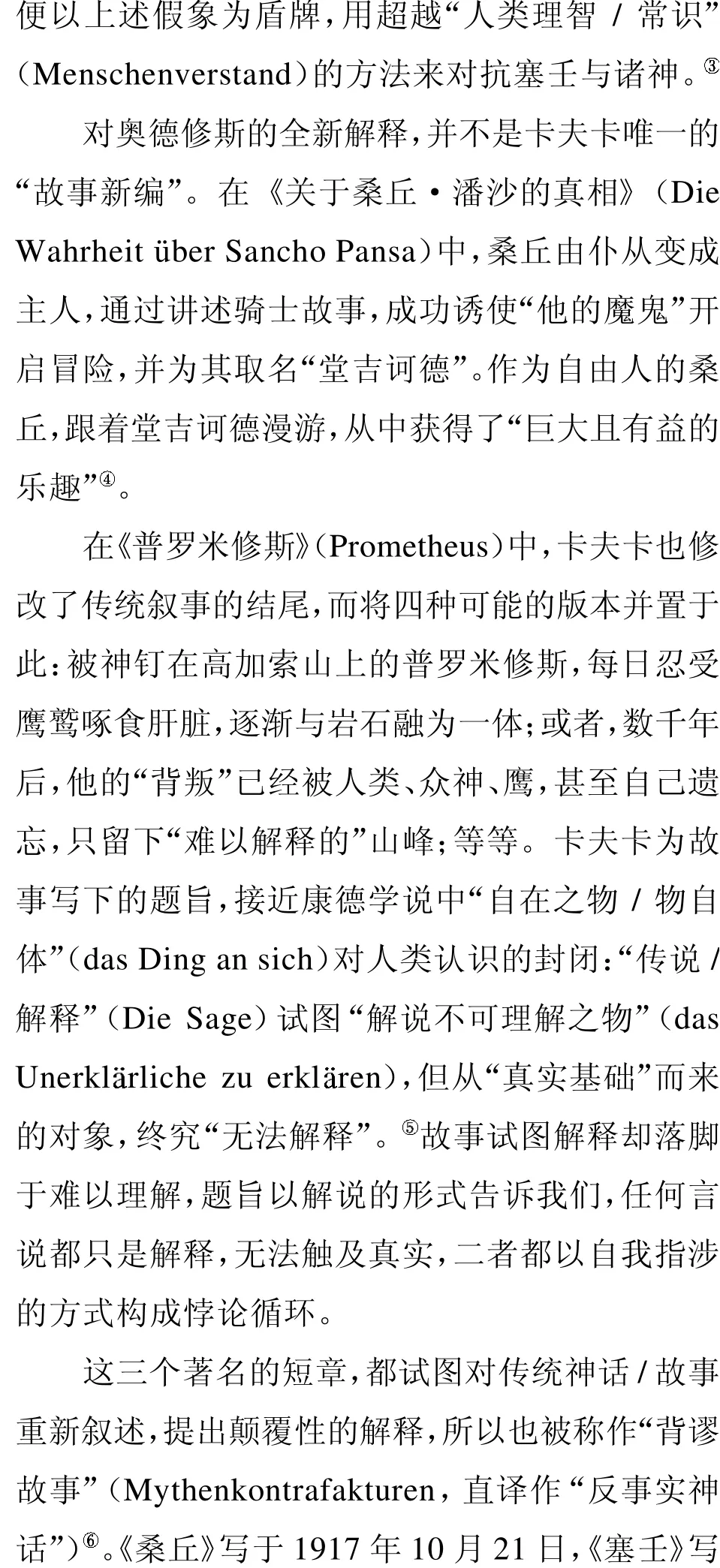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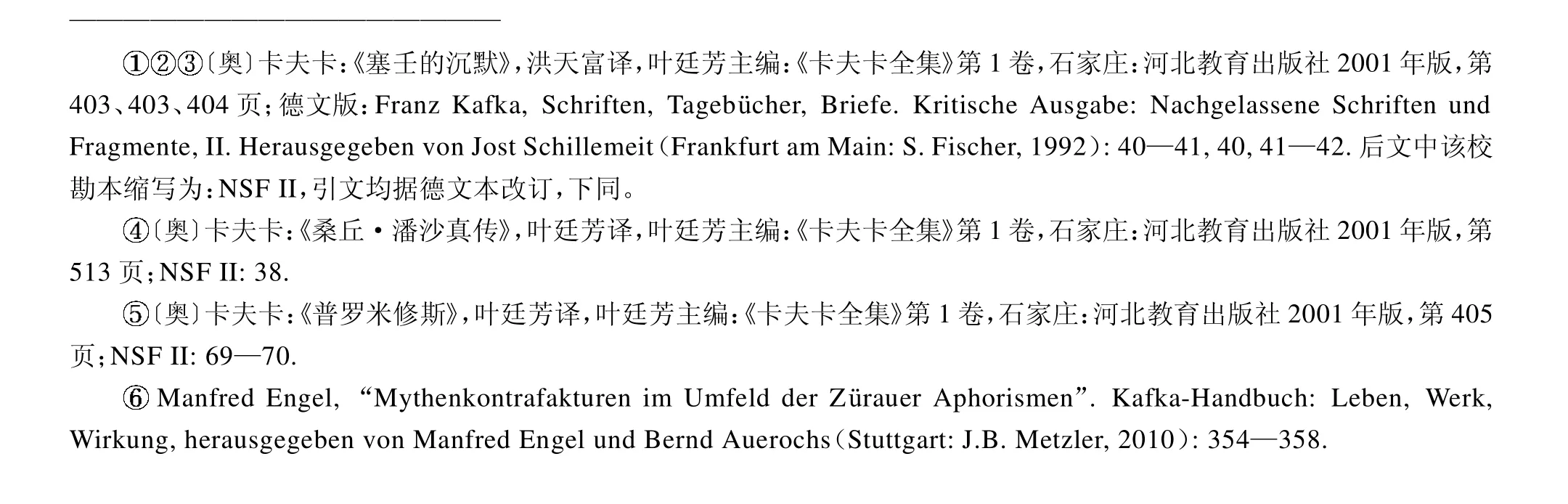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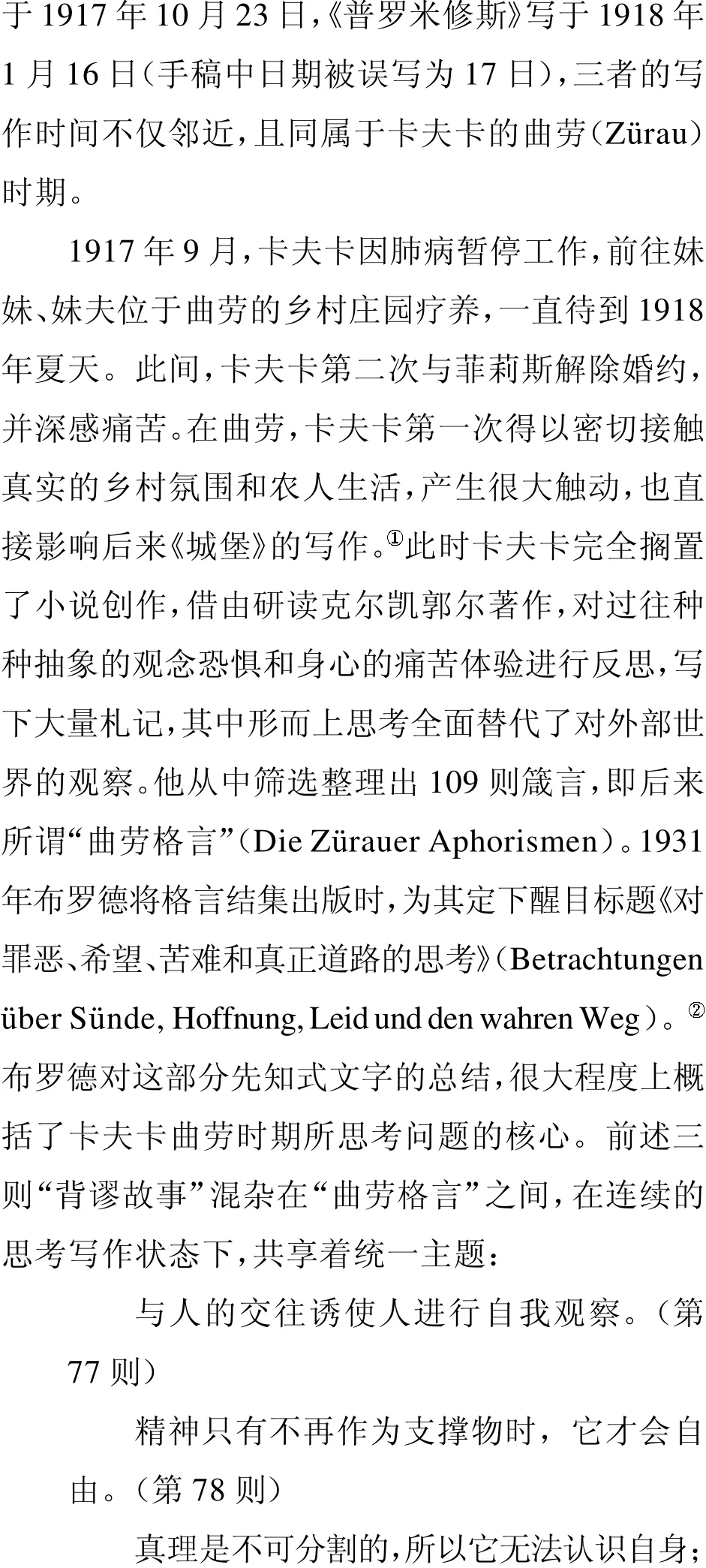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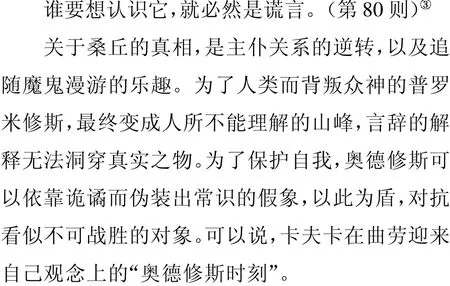
二、奧德修斯的“天真聽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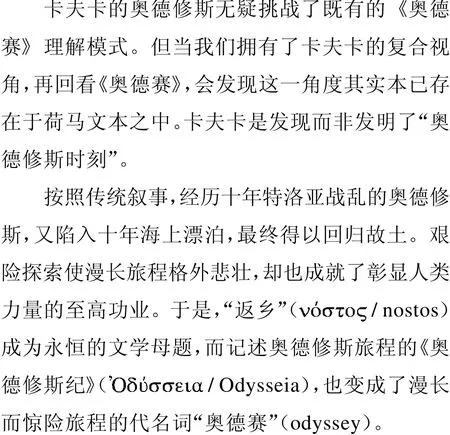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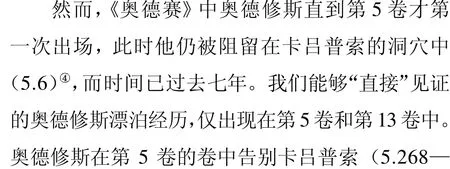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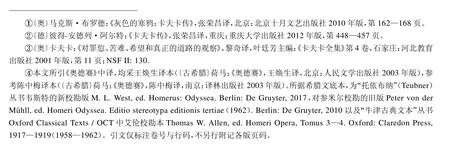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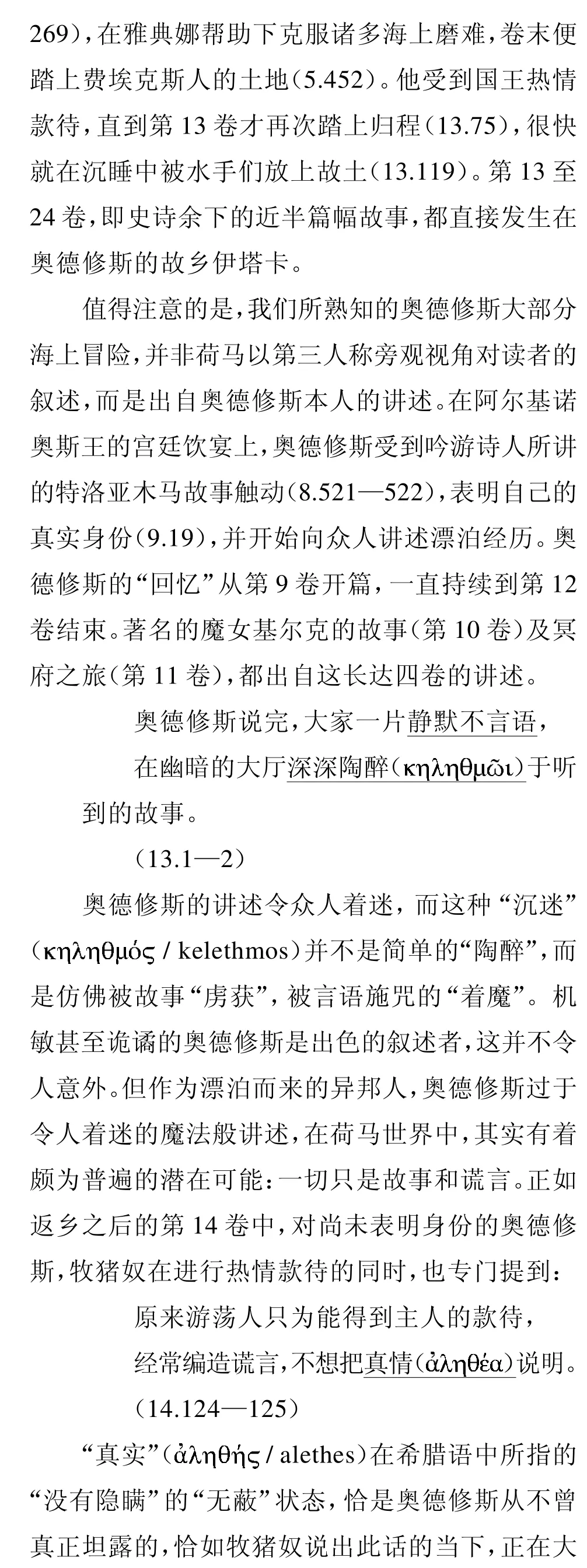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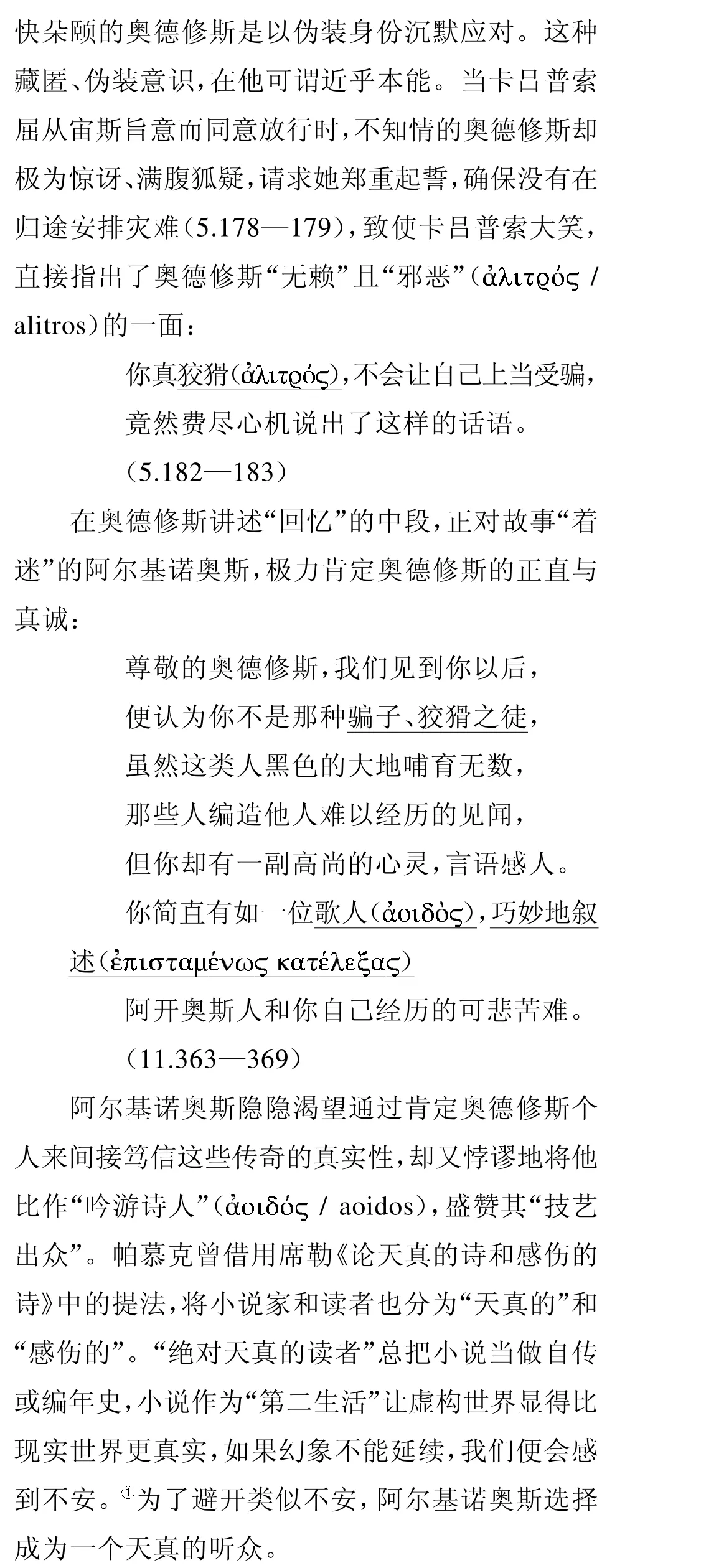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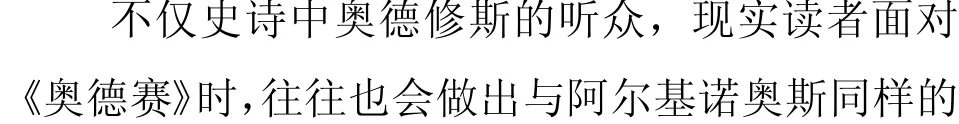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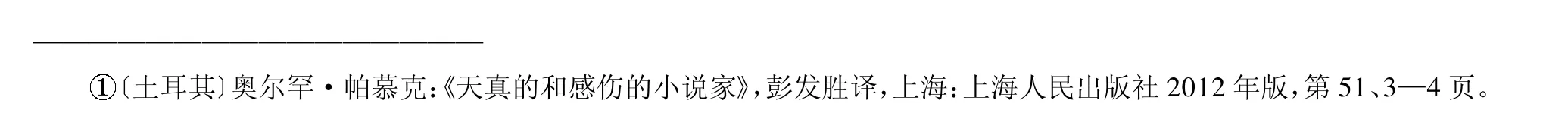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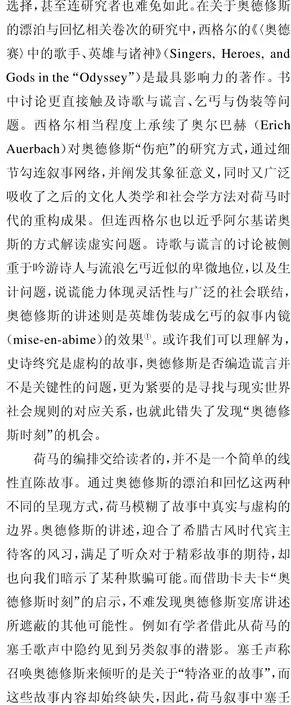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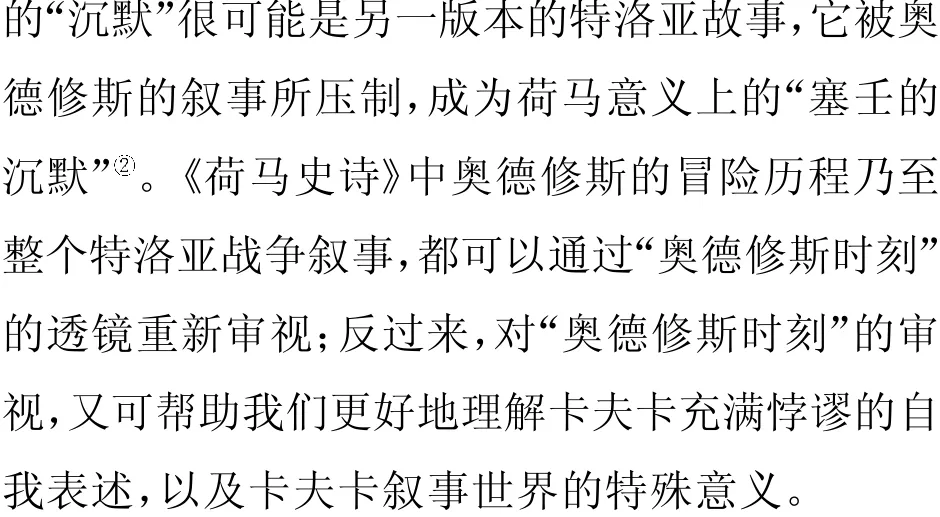
三、“自欺”、佯謬與“空無辯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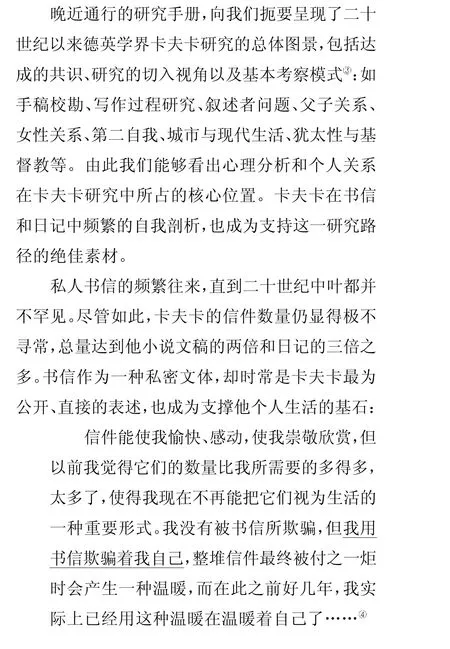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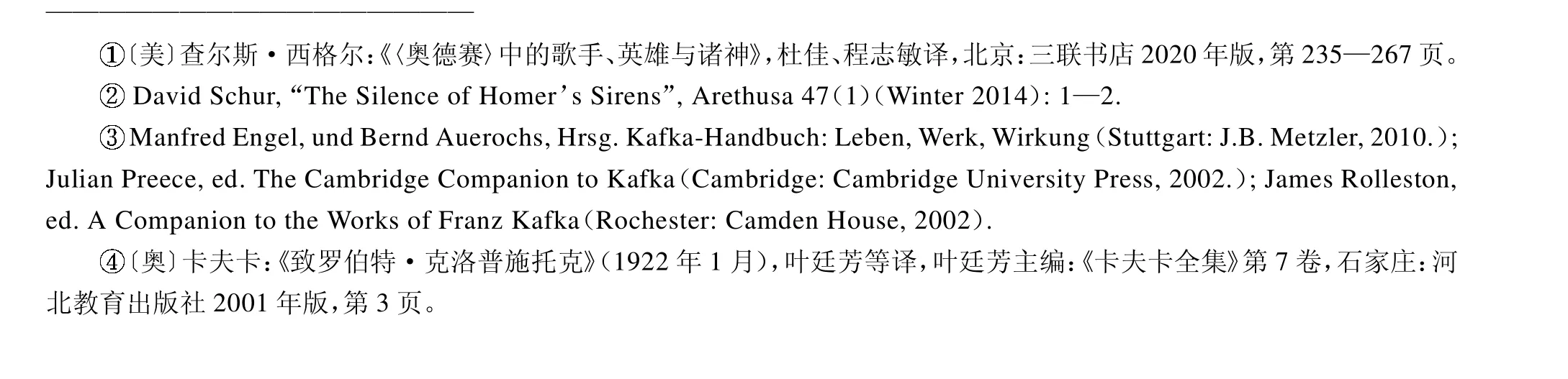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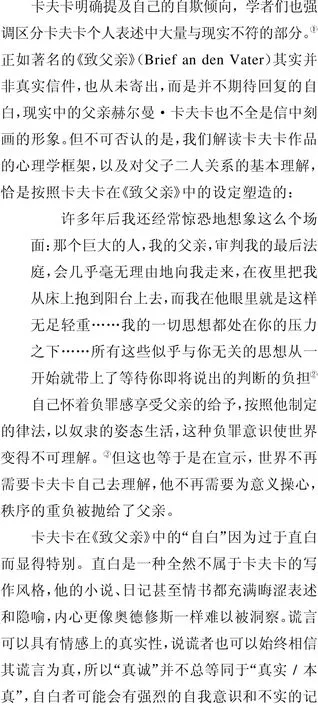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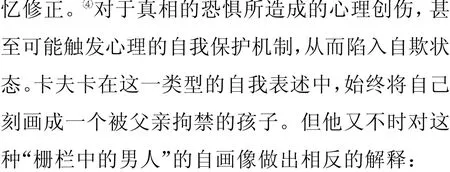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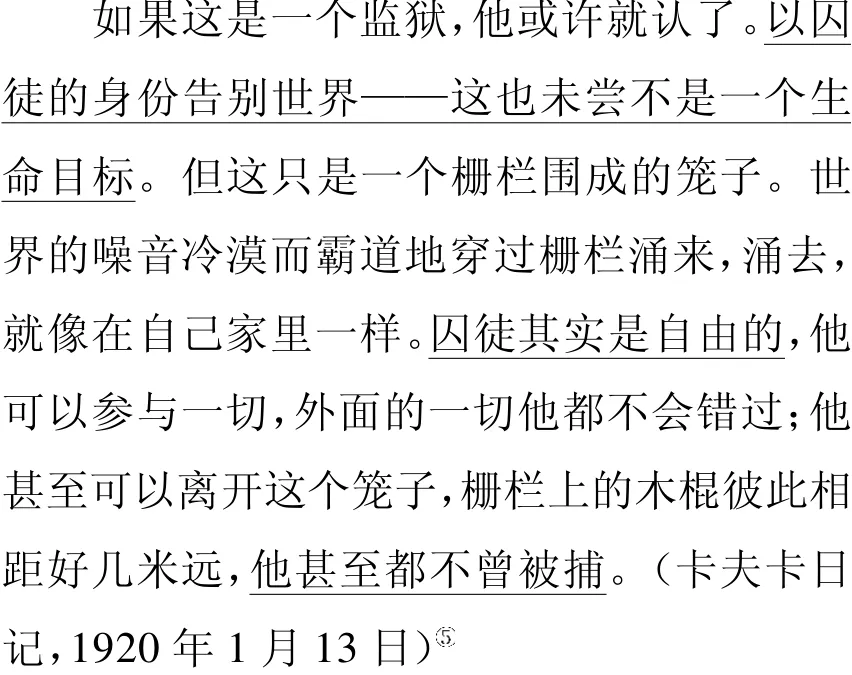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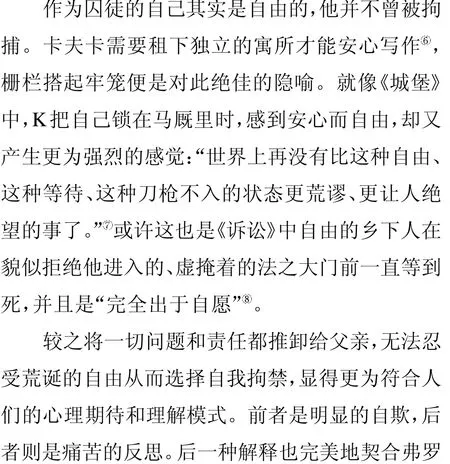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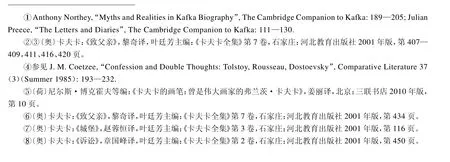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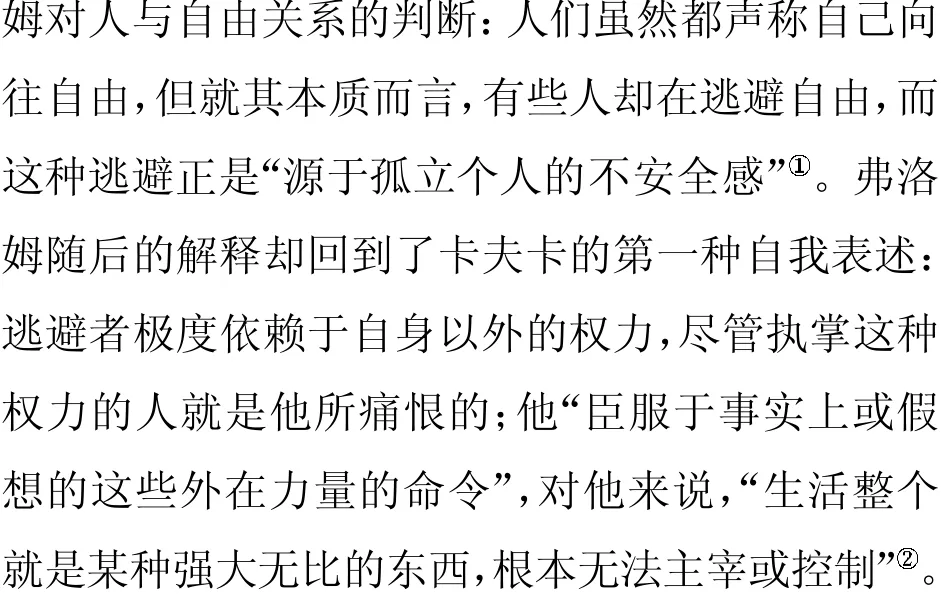

卡夫卡的兩種自我表述,原本可以組成心理學解釋上的邏輯閉環,但卡夫卡同時提供兩種解釋的行為,卻又突破了一般心理分析的預設框架。陷入自欺之人,很難自行破除假象,需要旁觀者來校正偏差。我們習慣于通過卡夫卡的書信日記來了解其虛構作品之外的真相,但其書信卻呈現出復雜的悖謬性:一方面,他虛構了《致父親》這樣的“自白”,另一方面,又明確指出是在用書信欺騙自己。更復雜之處在于,他還自嘲通過燃燒這些(自欺的)書信取暖,而這種以書信自欺、又以毀滅自欺來取暖的自我揭示,本身仍以書信方式予以呈現。卡夫卡同時扮演了自欺者和自省者兩個角色,并且這兩個角色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彼此糾纏,重疊復制,形成充滿辯證意味的佯謬。
然而,讀者通常對這種復雜性與辯證性卻有所忽略,對卡夫卡父子關系的認識仍舊依照卡夫卡過于直白的自我刻畫。因此卡夫卡的讀者也類似《奧德賽》中的天真聽眾,沉迷于奧德修斯的講述而意欲確證其真實性,而荷馬的聲音卻暗暗提醒我們可能一切只是謊言。我們從卡夫卡的“奧德修斯時刻”出發,借用《塞壬的沉默》中佯裝避禍的思考模型,便可發現,關于自欺和逃避自由之類“手段/工具”的表述,都內含著卡夫卡式的佯謬結構。若不能洞悉其微,那么,卡夫卡的真實世界便如同戴著多重假面的奧德修斯一樣,在其詭譎佯裝之下,從我們手中逃遁。
卡夫卡式的“自欺”和逃避自由的姿態,兼有《塞壬的沉默》中奧德修斯的二元性:其一,奧德修斯沒有窺透塞壬的奧秘,耳塞蠟丸抵御魅音,卻始終不知抗拒的只是“更加厲害”的沉默;其二,奧德修斯看透一切卻佯裝不知,將計就計,形成多重偽裝。對塞壬:裝作“聽見”沉默卻不受誘惑;對周圍眾人甚至天上諸神:裝作不知對手以沉默為利器而塞耳避聲;對自我:讓已知的塞壬沉默始終處于未知狀態,使之不至于因為沉默的透明性而喪失神秘。
兩種情形之間,卡夫卡似乎更注重后者,因為后者包含著對前者的洞察、反思和借用,后者是“奧德修斯時刻”的精髓。但這兩極只有同時并存才具備完整意義,或者說,后者只有讓外界看不出兩者區別才能真正奏效。不管奧德修斯無知還是佯裝無知,結果都體現為對塞壬的沉默無動于衷。而在奧德修斯眼中,塞壬也不例外。
塞壬對于奧德修斯究竟是知己知彼,還是知己不知彼,甚或知彼不知己,或是彼此兩茫然?她們和奧德修斯之間的博弈較量,究竟是相互誤解、相互欺瞞,還是相互理解、合作共謀?均無確切答案。唯一可知的是塞壬同奧德修斯兩相凝視,默然對峙而分離的場景。卡夫卡同時改寫了奧德修斯、塞壬以及兩者的關系。塞壬不再是奧德修斯自戀幻覺的主體投射,而是獨立存在;塞壬的欲望、知覺、謀劃均難以窺測。至于何以用沉默代替歌聲進行誘惑,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本來無一物,其妖魅歌聲只是虛構的傳說,因而必須保持沉默;抑或沉默是為奧德修斯量身定做,因為只有“沉默”,才能對充滿好奇心、探索欲的奧德修斯產生最大誘惑。奧德修斯與塞壬展開神秘的交流互動,而交流的基本語匯卻是“沉默”或“空無”。兩者之間的博弈,是一場充滿誘惑與反誘惑,充滿誤解、較量甚或合謀的“空無”辯證法。
卡夫卡作品中的空無,并非靜止的“無”,而是行進著的“無”。即使世界質本空無,自我充滿困惑,這一過程仍在繼續、仍須繼續。我們意識到目標的虛幻性,卻永遠走在不知所終的路上,永遠與“無”周旋。或者說,當目標失去本體意義,便以過程本身為目的,這是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現代人的存在境遇。
如前所述,在其“奧德修斯時刻”,卡夫卡還改寫了《堂吉訶德》。這些改寫的短文,預示了《城堡》中即將展開的世界。塞萬提斯的游俠騎士本已充滿了目標的虛幻性與自我操演性的張力。他是一部行走的書籍,一個游走的符號,一個空洞的能指。堂吉訶德的全部冒險,均來自對書本的模仿。然而他所模仿的騎士世界,曾經真實存在過,只不過這位“準游俠騎士”不幸置身于早已“脫魅”的日常現實。卡夫卡則更進一步,讓堂吉訶德理想主義的虛幻存在失去了宏偉不凡的淵源,讓一切均來自身邊這個不起眼的仆從桑丘的狡黠詭計。于此,桑丘不僅顛倒了主仆關系,變成了施動者,而且為堂吉訶德設計并維系了質本空無的人生目標。我們甚至有理由認為,卡夫卡的桑丘變成了設計者和誘惑者,來到《城堡》之中,分化成兩位莫名其妙的助手。《城堡》中的K,這位永遠弄不清地理環境的土地測量員,身份被證偽之后,是兩位助手的出現,維系了土地測量員的荒誕身份和源源不斷的無理由的后續活動。《城堡》以更復雜的形式、在更高意義上體現了卡夫卡“奧德修斯時刻”的洞察。卡夫卡并不關注奧德修斯是否抵達故鄉,正如他并不操心普羅米修斯是否獲救。《城堡》最后能否抵達,不得而知,K 關注的是打交道的人與物,世界便以這種方式存在。

如果說,城堡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目標,如果說,城堡的意義便是空無,如果說,奔向城堡的這位自封的“土地測量員”連自己身份和位置都無法弄清,卻仍然踏上通往城堡的永久徘徊之路,終其一生而不可抵達,這意味著什么?我們仿佛看到經過卡夫卡改寫而呈現給讀者的堂吉訶德:置身虛幻的世界,為虛幻的目標而奮爭,即使意識到所有這一切甚至源于身邊這個貌似笨拙的仆從的狡黠設計,卻依然拖著空洞的能指符號和疲憊的身軀繼續奔突;我們更看到卡夫卡重鑄的奧德修斯:發現世間最大奧秘不過是沉默和空無,卻在某種反思之域若無其事,仍將這一空無奧秘置于未知之境,繼續操演著同天地人神的虛與委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