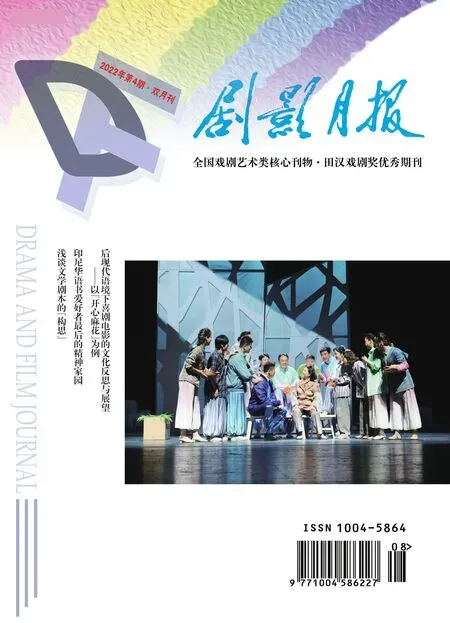論揚琴在錫劇演奏中的二度創作
■梅文解
幾十張曲譜,數十萬個數字音符,是一出戲音樂部分的總參和主體藝術組成部分。然而,在實際演奏中,因各種可能的因素限制,除了規定的戲劇情節有必要的配器外,大部分篇章中的唱腔、配樂僅是旋律表現而已。然而并不意味著這樣的旋律僅是樂器的照譜“死奏”,輔助錫劇表演的過程,配樂者應有二度創作的藝術發揮。作曲者創作的音樂其本身對于樂器表現出的藝術美既有闡釋也有期待。那種呆板的、不解而無情的演奏,既單調又無藝術感染力。在演奏中,看見一個音符就奏一個音符,沒有強弱、沒有技巧、沒有加花、沒有變化;在自己情感上無動于衷,“見其文而不見其心,見其面而未見其里”;毫無生氣的機械現形,對作品消極冷漠;枯燥而乏味,又毫無動人的氣韻。這是我們必須拋棄的奏法。每種樂器都有它自身的特點和演奏技巧,要將它們各自的特點融入伴奏,巧妙地進行二次創作。
二度創造的藝術升華不是肆意的,需要把握兩個基本原則:一是伴奏者要對劇本的主題、導演的構思,特別是唱腔、音樂等諸方面有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因為伴奏是為戲劇服務的。不應脫離服務本體的本身而進行所謂的“創造”。二是要以扎實的藝術功底充分發揮樂器的自身優勢。個人的音樂素養,如基本的樂理、作曲、和聲、復調等知識是創造的基本功。基本功愈好,二度創造的效果也愈加貼切。
戲曲伴奏中的二度創造是樂感和技巧的升華,是崇尚藝術追求的體現。出新出奇的二度創造,離不開伴奏者平時認真的觀察、研究、交流和積累,在具體劇情和演員的演唱情緒中,深入自身情感的解放,以經驗、技巧和樂感,賦予音符以生命,將伴奏和演唱情緒交相融合,使伴奏樂達到超越原譜的理想效果。以二度創造充分發掘觀眾藝術感受的新變化,才能圓滿完成演奏的使命。
揚琴原產東歐,音色介于鋼琴和古箏之間。經過廣東人改造,成了具有中國藝術特質的民族樂器。中國揚琴在錫劇音樂中,擔任著包括清板在內的所有音樂伴奏。揚琴琴體大,共鳴好,屬于擊奏弦鳴樂器。既有擊弦樂器的一般共性,又有弦鳴樂器的個性,演奏雙音及和音較為方便。它清脆悅耳,悠揚動聽,音量宏大,剛柔并濟,既純凈、明亮、圓潤、飽滿又極性,藝術表現力非常豐富,可以游刃有余地表現不同樂風。
筆者接觸錫劇已近四十余年,對錫劇的唱法、配樂、名角唱腔特色等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并多次同數位資深作曲唱腔設計、著名演員進行過深層次的探討。積累了很多的知識和經驗,并逐步形成了具有個人特色的伴演風格。
筆者以揚琴的配音伴奏和唱腔伴奏為例,錫劇《珍珠塔》中“贈塔”一折,陳彩娥手捧點心盒,懷著歉意和愛心,從上場門中緩緩走出,準備將點心送予方慶。這時長笛慢奏并帶著一絲惆悵,整個樂隊以長音和弦的方式,傳承至如今。然而,在筆者多次演奏后感悟,如此伴奏平常且單調,表達情緒上略微欠缺。經過反復思考和演練,筆者終于有了一種新的伴奏方式:用傳統的復調形式和現代鋼琴伴奏形式結合演奏此曲——是琶音、和弦輪音加復調式的伴奏方式,以表達彩娥愁思千萬,充滿矛盾,內疚不安的心態。然后,以拉長式地柔和的分解和弦伴奏,使原本憂愁的旋律充滿浪漫的溫馨感。揭示彩娥心中對親人、愛人的不舍愛意。如此多樣性的伴奏,既豐富了音樂的內涵和表達力,也使旋律更動聽,劇情更生動。再如本劇的第七場,愛慕虛榮的胡蓉以為自己要做狀元夫人了,心情異常激動、得意,如癡如醉地演唱了一曲《滿園春光》。這里本是和弦輪音,是唱詞“滿園春光花芬芳”中“滿園春光”的前奏。然而,單一個和弦輪音太過平淡,于是筆者采用一個五聲音階的大琶音來接唱,頓時令前奏有了寬廣明亮而又華麗的色彩,使唱詞有了一個極有音樂性的確切背景。而唱詞“花芬芳”的主旋律,筆者采用帶有裝飾音的輕盈而密集的全輪音技法伴奏,旋律速度略漸慢。這樣的伴奏方式使人更加感覺到鋪滿春光、簇簇盛放的花園是美景。當胡蓉唱至“我戴上珠冠、身披錦服、人看鳳凰”時,為了表達胡蓉的興奮之情、得意之態進入了巔峰,筆者采用了強力的音量對比和加花的手法,把唱腔旋律推向高潮!這一段戲進入一個精彩的高潮,為后來胡蓉神態反差的強烈對比奠定了基礎。
揚琴伴奏貫穿于全劇的二度創作,手法較多。比如運用半音階、變化音,反竹、刮奏等技巧,襯音、坐音等方式。在演奏中音量的強弱,速度快慢的變化等等都使錫劇的音樂更加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