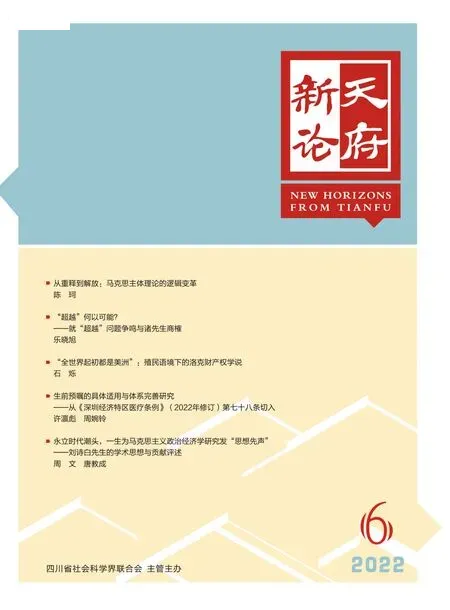以家為本,老而不休:農村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的家庭因素影響分析
慈勤英 程燕蓉
一、研究緣起和文獻綜述
(一)研究緣起
國家統計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60歲、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別為2.64億人、1.91億人,占比分別為18.7%和13.5%;其中,農村的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7.99個、6.61個百分點(1)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中國統計出版社,2021年。。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的趨勢較為明顯,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問題更加嚴峻。
老齡群體特別是農村老年人,既是需要社會保障、家庭關愛、子女照顧的養老群體,也是通過勞動供給、照料家務等人力資源開發方式,不斷創造著健康生產力、家庭功能生產力及勞動生產力的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2)邊恕:《老齡群體:不可忽視的社會生產力》,《理論與改革》2021年第5期。考慮到我國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數的55.83%,人均健康預期壽命為68.7歲,低齡、健康老年人口疊加其積累的專業技能、職業經驗和勞動愿望,是社會寶貴的人力資源。農村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宏觀層面的養老戰略選擇和制度建構,要著落在微觀層面家庭內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的資源開發和實踐。全面了解農村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狀況,助推消解老年人等于“無用”之人的年齡歧視,有助于國家養老戰略的適時跟進;關注家庭關系和家庭結構對老年人口勞動參與的影響和制約,有助于探究促進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家庭和諧之道以及建構養老的良性代際互動模式。
(二)文獻綜述
有學者提出,當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雖呈現明顯老化趨勢,但迫于家庭結構少子化等壓力,更多老年人退休后仍繼續留在勞動力市場。(3)蔣同明:《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及應對舉措》,《宏觀經濟研究》2019年第12期。農村養老保障水平偏低,秉持盡自己所能減輕家庭養老負擔的初心,農村老年人只要身體條件允許,仍會從事大量生產性勞動,即“無休止勞動”(4)譚娜、周先波:《中國農村老年人“無休止勞動”存在嗎?——基于年齡和健康對勞動供給時間影響的研究》,《經濟評論》2013年第2期。。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六普”)數據顯示,農村60~64歲、65~69歲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分別為68.74%、51.49%。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農村70~74歲和75歲及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仍分別有29.20%和11.90%。(5)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
人口結構、經濟轉型和老年人就業的相關法律等會影響我國老年人就業率。(6)鄭愛文、黃志斌:《基于個人和社會雙重視角的老年人再就業影響因素分析》,《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有學者認為,農村老年人是社會政策的主要受益者,(7)吳敏:《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意愿的經濟因素分析》,《人口與發展》2016年第2期。醫療保險為其提供了繼續從事勞動和工作的身體和勞動力保障,對勞動參與起到正向促進作用;也有學者指出,新農保養老金收入能明顯減少農村老年人的勞動供給,具有負向影響和時滯效應(8)李江一:《社會保障對城鎮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以原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為例》,《人口與經濟》2018年第2期。(9)黃宏偉、展進濤、陳超:《“新農保”養老金收入對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中國人口科學》2014年第2期。。
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受個體特征的影響,年紀輕、健康狀況好的農村老年人參與自家農業生產的比率和總的勞動參與比率均較高,勞動供給時間也較長(10)孫澤人、趙秋成、肇穎:《“新農保”是否真的減少了農村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基于CHARLS兩期截面數據的研究》,《商業研究》2020年第10期。。相較于勞動供給,低齡、健康的女性老年人為子女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隔代撫育(11)孫鵑娟、張航空:《中國老年人照顧孫子女的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人口與經濟》2013年第4期。。婚姻保護作用在老年期依舊發揮著作用,在婚老年人的安全感、歸屬感等主觀意識和身體健康等客觀條件保障和提高了其勞動參與的可能性(12)宋靚珺、呂明陽、湯衡:《基于分層線性模型的老年人“生產性參與”影響因素研究》,《人口與發展》2020年第6期。。
家庭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社會支持系統和福利載體。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中國家庭觀深刻影響著老年人的經濟行為和福利水平。家庭成員在面對生活困難時更傾向于在家庭內部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13)鄒紅、文莎、彭爭呈:《隔代照料與中老年人提前退休》,《人口學刊》2019年第4期。研究表明,在當前我國農村重視家庭、貢獻家庭的文化傳統下,農村老年人的勞動供給呈現以家庭為主要單位和場所、多重負擔的特征。(14)宋璐:《農村老年人生產性老齡化模式研究》,《人口與經濟》2021年第4期。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也是影響其勞動參與的因素之一。有研究發現,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參與家庭照料的概率是其他居住方式老年人的2.5倍。(15)劉燕、紀曉嵐:《老年人社會參與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基于311份個案訪談數據》,《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承擔著照顧子女家庭,特別是教養孫代的主要責任。(16)羅楚亮、袁璐璐:《代際居住方式選擇與農村老年貧困》,《勞動經濟研究》2021年第4期。有研究發現,與孫子女居住、有配偶、朋友支持程度高的老年人為高社會活動參與型和家庭照顧型的可能性更大。(17)謝立黎、汪斌:《積極老齡化視野下中國老年人社會參與模式及影響因素》,《人口研究》2019年第3期。另外,還有研究發現,代際關系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外在表現,給予子女的經濟支持、兒子數量的增加及性別結構比的提高會顯著促進老年人的勞動參與。(18)趙建國、王凈凈:《“逆向反哺”、子女結構與老年人口勞動參與》,《人口與發展》2021年第2期。還有研究認為,影響老年人勞動供給的核心要素是代際之間是否存在物質轉移。(19)李強:《中國外出農民工及其匯款之研究》,《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2期。子女的婚姻狀態和城市化需求通過代際關系影響老年父母的勞動參與和隔代撫養,甚至產生“房奴效應”。(20)彭爭呈、鄒紅:《兒子、房子與老子——未婚子女、房價與老年人勞動參與》,《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年第7期。此外,還有部分學者關注勞動力流動,特別是關注子女外出務工對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21)李琴、宋月萍:《勞動力流動對農村老年人農業勞動時間的影響以及地區差異》,《中國農村經濟》2009年第5期。(22)羅芳:《勞動力轉移對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參與概率和時間的影響——基于湖北省的經驗分析》,《江蘇農業科學》2011年第5期。(23)李琴、孫良媛:《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對農村老年人勞動供給的影響——基于“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學術研究》2011年第4期。
針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研究,學界主要聚焦農村老年人的農業或非農勞動供給,把老人承擔孫子女撫育歸為隔代照料的家務勞動,沒有納入勞動參與的范疇。家務勞動沒有得到社會承認,這是一個老問題了。但作為老年人晚年重要社會、家庭貢獻內容的孫輩、父母輩照料的家務勞動,照料對象指向老年人的孫代和父輩,其實承擔了本應由社會承擔的需要支付工資的“保姆”或“護工”的工作,應該是老年人勞動參與的重要部分。既有研究沒有把照料家務等同于老年人農業或非農勞動供給,放在大的勞動參與概念之下進行探討,對農村老年人勞動付出的特點和重要性是一種忽略和漠視。
同時,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三世同堂”基礎上的“四世同堂”不再是個案。“四世同堂”意味著在“上有老老”和“下有小小”的情況下,老人的年老的父母和孫子女在競爭和爭奪老年人照料的勞動投入。
故本文使用全國數據,將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兩個層面的勞動操作化為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考量指標,對參與勞動的農村老年人做全面的定量分析。在把照料家務納入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分析的基礎上,本文驗證和探索家庭因素對勞動參與的影響,嘗試回答以下兩個問題:其一,家庭子女數量的增加對農村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的影響。多子女的老人,有更多的子女可以提供養老服務,也意味著有更多需要幫忙照顧的孫子女。其二,子女的回饋對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子女對父母的代際經濟支持,既可以理解為對父母養育的回饋,也可能反映的是對父母勞動參與,尤其是對照顧孫子女勞務的回饋。通過以上研究,關注老年人口與其子女、孫子女三代人之間的代際互動。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1.農村家庭關系和老人勞動參與
代際關系是影響農村老年人晚年幸福感、生活質量和養老資源的重要因素。我國傳統代際關系強調父母承擔撫育子女責任,子女在父母年老時承擔贍養義務。當前,農村老年人的收入由63.7%的勞動收入、29.6%的子女經濟支持、3.1%的離退休金和其他收入構成,消費主要花在吃、穿、住和醫療上。(24)周祝平:《農村留守老人的收入狀況研究》,《人口學刊》2009年第5期。與城市老人相比,在低水平社會保障之下,農村老年人如果退出勞動,就需要以自己的儲蓄或子女的供養維持基本生活。大部分農村老年人從事勞動的原因并不是休閑娛樂或自我實現,而是為了維持基本生計。(25)聶建亮:《農村老年人的勞動、收入及其養老階段分化——對農村老年人“無休”的實證分析》,《學習與實踐》2017年第8期。當子女提供了充足的經濟支持時,老年人會減少參與農業和非農勞作,有利于促進老年人轉向照料孫代的家務,形成良性的隔代撫養和代際互動。
據此,提出假設1:子女對父母的代際經濟支持會降低農村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可能性或減少勞動時間;子女對父母的代際經濟支持會提高農村老年人的家務勞動的可能性或增加勞動時間。
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國代際關系呈現出了雙向互動的新特征。伴隨著以市場化為核心的現代性因素進入中國鄉村社會,子女在當今社會承擔著巨大的生存和生活壓力,所以農村家庭中父母的再生產目標開始由完成“傳宗接代”人生任務轉換為協助子代實現階層地位向上流動,即農村老年人不僅要幫助子代結婚、享受子女的反哺供養,而且要盡力滿足子代城市化、買房安居、孫代撫養和教育等發展性需求。農村家庭能動性適應家庭發展需求和提升家庭發展能力的目標,呈現出“一家三制” “彈性家庭” “功能性家庭”等新變化,更加強調實用主義,以經濟理性為基本原則,強調家庭網絡在資源互補、經濟互惠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的優勢,力爭通過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農”家庭生計模式形成“代際合力”,實現家庭的發展目標。(26)李永萍:《家庭發展能力:理解農民家庭轉型的一個視角》,《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27)劉超:《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家庭策略與發展型家庭秩序——基于“一家三制”的討論》,《寧夏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據此,提出假設2:農村老年人對子女經濟支持會顯著正向促進其勞動參與。
2.農村家庭結構和老人勞動參與
子女結構會對農村老年人的就業決策產生關鍵的影響。依據代際交換理論,子女數量對老年人代際贍養支持的影響可能存在“良性促進”作用。有研究認為,子女數量反映了代際支持資源的豐富程度,子女數量越多的老年人或許會獲得更多的支持。(28)王碩:《家庭結構對老年人代際支持的影響研究》,《西北人口》2016年第3期。有研究數據顯示,子代數量每增加一名,農村老年人獲得代際經濟支持的概率增加29.1%。(29)胡仕勇、李佳:《子代數量對農村老年人代際經濟支持的影響——以親子兩代分居家庭為研究對象》,《人口與經濟》2016年第5期。在養老資源充分滿足老人需求的情況下,農村老年人會相應地減少勞動參與、降低勞動強度。同時,農村老年人承擔孫代照料已是家庭應對教養孫代壓力的主要途徑,更是老人主要的晚年勞動參與方式。子女數量關系到農村老年人隔代撫養和照料孫代的數量和強度。
據此,提出假設3:健在子女數量越多,農村老年人非照料性勞動參與的可能性越低,勞動參與的時間也會減少;相對應,健在子女數量越多,農村老年人承擔照料孫代的可能性提高、照料強度增加。
另外,農村的社會風氣相對傳統和保守,宗法制的影響依舊深遠,甚至在部分經濟不發達地區,難以擺脫男性本位,傳統代際關系中更加強調“責任倫理”、血緣關系,因此孫輩照顧主要由祖父母承擔。當兒子數量增加時,相應孫代人數增多,祖父母照顧孫代的時間增多。
據此,提出假設4:健在兒子的數量對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數據來源和變量說明
1.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2018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30)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項目組:《2018年全國追蹤調查數據》,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 2020-09-24, https://charls.charlsdata.com/pages/Data/2018-charls-wave4/zh-cn.html,訪問日期: 2022-01-06。該數據庫采用了多階段抽樣,問卷內容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家庭結構和經濟支持、健康狀況、體格測量、醫療服務利用和醫療保險、工作、退休和養老金、收入、消費、資產以及社區基本情況等。根據需要,本文的研究對象為農村老年人,指年齡大于或等于60歲且戶口在農村的個體,對缺失值進行處理后,最終進入分析的有效樣本為4767人(31)首先是合并2018年CHARLS的部分數據庫(得到11505個樣本);其次,本文研究的是農村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行為,因此本文刪除了城市戶口且年齡在60歲以下的樣本(剩余5185個樣本);最后,本文刪除了在核心因變量、自變量和控制變量中存在缺失值的樣本,最后得到4767個觀測值。,其中60~69歲、70~79歲和80歲及以上個體分別為2791人、1506人、470人。
2.變量說明
本文的因變量為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分為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兩個方面。其中,農業和非農勞動包括農業自雇、受雇兩個二分變量,從是否參與和參與時間來衡量,受雇工作又具體劃分為農業受雇和非農工作;農村老年人承擔照料勞動,是指照料孫代。只要每周照料時間大于0,則記為“參與”,賦值為1;每周照料時間等于0,則記為“不參與”,賦值為0。因變量勞動參與,將參與農業自雇、農業受雇、非農工作和照料孫代任何一項賦值為1,都不參與賦值為0。
家庭影響因素由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和父母對子女的經濟支持、健在子女數量和健在兒子數量構成。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民族、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人口學特征變量,個人存款、個人債務、家庭土地資源等經濟變量,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等社會政策變量。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上賦值為1,小學以下賦值為0。“健康狀況”是受訪者的自評健康,分為“不健康”和“健康”兩類。個人存款是指是否有現金、存款等。個人負債分為“有”和“無”兩類,是指是否存在個人欠款、貸款或信用卡欠款。養老金和醫療保險是指是否參加、正在領取(預計將來可以領取)和正在繳納養老金或醫療保險的情況。具體影響因素的特征值見表1。

表1 樣本特征值描述
(三)研究方法
由于因變量老年人勞動參與分為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兩個方面,且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承擔照料勞動時間為受限連續因變量,所以本文分別使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檢驗各類影響因素對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
三、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現狀
(一)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總體情況
據CHARLS 2018數據分析,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勞動參與的人數為3395人,其中60~69歲參與人數占該年齡段樣本量的84.95%,即使到了身體健康狀態日愈下降的中齡和高齡階段,仍有60.36%和24.47%的老年人繼續參與勞動。此外,農業和非農勞動是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主要形式,占勞動參與的82.92%,農業和非農勞動在每個年齡段的參與率始終高于照料勞動。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兼顧是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另一種方式,占勞動參與的30.87%。如表2所示,整體來看,農村老年人只參與照料孫代勞動的占比為17.08%,從側面反映出農村老年人整體農業勞動負擔較重,且部分老年人在從事下地干活、養家糊口勞作的同時,還要承擔家務照料。

表2 農村老年人分年齡勞動參與的總體分布情況
(二)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具體情況
農村老年人農業和非農勞動集中體現在農業自雇、農業受雇和非農工作三個方面。參加農業自雇是指農村老年人為自家干農活、從事農業相關活動;農業受雇主要是為其他農戶或雇主干農活掙錢;非農工作涉及除去與務農有關的工作。樣本中,從參與勞動的類型來看,主要以農業勞動為主,占參與樣本總體的77.24%。以60~69歲老人為例,從具體勞動參與主要類型來看,以農業勞作為主,占比達76.5%;參與率排在前三的類型依次是:僅參與農業自雇、參與農業自雇和照料孫代、僅照顧孫代,分別占總參與人數的31.17%、25.14%和17.38%。在老人勞動參與廣度方面,發現60~69歲農村老年人勞作可選性較強,涉及類型較豐富;80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則以從事單一的農業自雇為主(見表3);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業自雇參與率逐漸增加,而非農工作的參與率卻在逐步下降。

表3 農村老年人分年齡勞動參與的具體分布情況
CHARLS 2018數據顯示,農村老年人承擔的照料家務對象主要集中在孫代,但也有1.11%的老人承擔照料父代的家務。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和速度加快,農村老年人將要面對的是新的“上有老老,下有小小”。此外,30.86%的農村老年人在承擔照料孫代家務時仍要參與農業和非農勞作。這表明,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以家為主,既要與子代共同維持家庭的整體生計需求,還要盡可能幫助子代照料和撫養孫代,勞動參與負擔重。
(三)農村老年人每周勞動參與時間的情況
以每周的勞動參與時間來衡量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強度。在參加農業自雇方面,人均每周勞作28.85小時。60~69歲老人每周的平均勞作時間為30.45小時,以每周工作五天計算,約等于每天工作6小時。即使在80歲及以上年齡組,每人每周的平均勞作時間仍有20.74小時。與農業自雇相比,受雇工作的每周平均時間遠遠高于農業自雇,差距達到15.59小時;不同年齡的農村老年人每周受雇參與勞動時間都在40小時左右。從每周五天工作制來看,受雇的老人都是每天8小時滿負荷工作(見表4)。就農村老年人每周承擔照料勞動的時間而言,照料孫代花費的平均時間分別高于農業自雇和受雇工作30.26小時和14.67小時。在年齡組差別方面,在照顧孫代方面,60~69歲老人每周平均承擔時間比 70~79 歲和80歲及以上的老人分別高出1.88小時、6.18小時。

表4 農村老年人分年齡每周勞動參與時間的情況 單位:小時/周
從參與強度來說,僅參與農業自雇的農村老年人每周參與平均時間為28.97小時,比僅每周參與受雇和照料孫代的平均時間分別少19.77小時、30.9小時。也就是說,老人參與農業自雇勞動強度相對較低,并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降低,但受雇和照料孫代的勞動強度均高于農業自雇。隨著勞動參與類型增多,老人每周平均勞動參與時間越來越長,勞動強度也隨之增加。
(四)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特征
在中國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的趨勢下,農村老年人仍繼續深度勞動參與。數據顯示,當前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體現了如下五個特征:第一,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以家為本、老而不休。整個勞動參與以家庭整體需求為主、以家庭為主要勞動場所,參與面廣。在60歲及以上的農村老年人中仍有71.22%進行勞動參與,59.05%的個體繼續參與農業自雇、農業受雇和非農工作,34.15%的老人需承擔照料孫代。第二,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靈活性較強,但仍以農業自雇為主。勞動參與類型在不同年齡段的變化體現了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選擇的靈活性,他們理性衡量自身身體狀況、知識資本和經濟狀況,結合已有的土地資源和周邊人力市場需求,在農閑、農忙間進行靈活的農業和非農勞動時間和強度的調整。第三,家務照料主要集中在照料孫代,且隔代照料孫代的時間長、勞動強度大。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自雇、受雇工作、照料孫代平均每周花費時間分別為28.85小時、44.44小時、59.11小時。尤其是照料孫代的時間高達59.11小時,按照每周七天計算,每天要工作8.44小時。第四,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比例在下降,但仍有部分中、高齡老年人繼續勞動參與。在農業和非農勞動參與中,七成左右的60~70歲農村老年人參與了農業自雇、農業受雇或非農工作,但部分70~79歲和8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仍繼續參加農業和非農勞動,沒有退出。第五,農村老年人互養和隔代撫養共存。隨著我國從輕度老齡化逐漸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農村老年人將要面對的是“上有老老,下有小小”的新情況,老年人承受著照料高齡父代和照料年幼孫代的雙重責任與壓力。
四、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家庭影響因素分析
(一)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家庭影響因素
1.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家庭影響因素回歸模型分析
表5中的模型1是以勞動參與為結果變量建立的回歸模型。結果表明,在家庭因素中,對子女提供經濟支持會顯著提高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可能性(驗證假設2);即與沒有向子女提供經濟支持相比,向子女提供經濟支持的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的可能性更大。

表5 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家庭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
模型中的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反映出農村不同類型老人群體的勞動參與狀況存在差異。年齡對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隨著老人年齡的增大,其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的可能性越低。良好的自評健康和穩定的婚姻是參與勞動的保障,農村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越好、有配偶支持,越有可能進行勞作。家庭土地資源對老人勞動參與有顯著促進作用,擁有越多家庭土地資源的農村老年人越傾向于選擇勞作。
2.農村老年人參加農業和非農勞動的家庭影響因素分析
表5中的模型2是以農業和非農勞動為結果變量建立的模型。結果顯示,在家庭因素中,對子女提供經濟支持會顯著提高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的可能性(驗證假設2);即與沒有向子女提供經濟支持相比,向子女提供經濟支持的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自雇、農業受雇和非農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健在子女數量對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健在的子女越多,老人參與農業自雇、農業受雇和非農工作的可能性越小(驗證假設3)。
同時,本文將農業和非農勞動參與分為農業自雇(模型3)和受雇工作(模型4)兩類,來揭示農業和非農勞動具體類型影響因素的差異。可以看出,在家庭因素中,農村老年人對子女的經濟支持對其參與受雇工作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與沒有對子女提供經濟支持者相比,要對子女進行經濟支持的老人參與受雇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部分驗證假設2)。模型5和模型6把受雇工作詳細分為農業受雇和非農工作兩個類型也證明了這個結果。但農村老年人對子女經濟支持對其參與農業自雇沒有顯著影響,可能因為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自雇的動力是復雜和多面的。除了家庭原因之外,傳統的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和農耕文化讓農村老年人有著深刻的土地情結,個體的衣、食、住、行深深地與土地鑲嵌在一起,土地凝結了老人對生活所有的經濟和情感依賴。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老人都會做些力所能及的農活,即農業自雇。另外,在子女結構上,健在兒子數對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自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生育兒子越多,老人參與農業自雇的可能性越大(部分驗證假設4)。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農村大量男性外出務工而忽略了對父母的支持,導致老人通過農業自雇這種傳統方式實現自力更生、自我養老。有學者的研究也發現,農村有兒子對其父母獲得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支持以及提升生活滿意度都沒有顯著影響,且隨著兒子數占比的提高,會顯著降低老年人獲得子女的各類支持。(32)張棟、鄭路、褚松澤:《養兒防老還是養女防老?——子女規模、性別結構對家庭代際贍養影響的實證分析》,《人口與發展》2021年第3期。在非農工作的家庭影響因素方面,子女的經濟支持和健在子女數都顯著降低了農村老年人參與非農工作的可能性(驗證假設1),但對農業自雇與農業受雇沒有顯著影響;同時,農村老年人對子女的經濟支持顯著促進其參與非農工作(驗證假設2)。究其原因,農村老年人在健在子女較多和子女給予充足經濟支持的情況下,減緩了迫于生計性的生產和生活壓力,農村老年人出于自身健康維護的需要,進行適度的農業勞作,而不去從事高強度、高要求的非農工作;但如果農村老年人需要給予子女經濟支持,會促使老人選擇高報酬的非農工作。
此外,在個人因素方面,年齡和自評健康對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有顯著影響。良好的自評健康是參與勞作的保障。年齡越大,自評健康程度越低,農村老年人參加農業自雇、農業受雇和非農工作的可能性越低。與女性相比,男性更傾向于選擇農業和非農勞動。隨著老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其進行非農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老人教育程度為小學以下更有可能參與農業自雇和農業受雇。受教育程度是反映個體知識資本的重要指標,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擁有的知識越多、技能越強,就業能力越強,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工作的機會也會越多。同時,對農村老年人來說,相對于非農工作涉及新技能的學習和新工具的應用等較高的工作要求,田間農業勞作門檻較低,并且可操作性強。農村老年人以小學教育程度為門檻,其農業和非農勞動產生了農業和非農分化。擁有家庭土地資源和配偶的農村老年人進行農業和非農勞動、農業自雇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土地資源對非農工作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家庭土地資源和婚姻對農村老年人起到“土地養老”和“婚姻紅利”的作用。在擁有土地資源的前提下,農村老年人更傾向于通過田間勞作實現自給自足;若沒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則通過非農工作實現經濟自由;在婚的老年人的安全感、歸屬感等主觀意識與身體健康等客觀條件保障和提高了其勞動參與的可能性。
社會政策因素中,醫療保險對農村老年人參與非農工作有負向顯著影響,即與參與醫療保險的農村老年人相比,未參加醫療保險的老人參與非農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但對農業自雇和農業受雇沒有影響。對于部分農村家庭而言,重特大疾病支出是家庭可能面臨的主要困難之一,參與醫療保險可以有效保障農村居民或其家庭成員在治療重特大疾病時的消費金額予以報銷,而未參與者就要通過高強度、高收入的非農工作加大抵御家庭大病風險的經濟保障力度。社會政策中的養老金對農業和非農勞動沒有顯著影響,主要是由于當前農村基本養老金政策是年滿60周歲、未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農村有戶籍的老年人均可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老人福利獲得的差異性較小,因此不存在影響。
3.農村老年人承擔照料勞動的家庭影響因素分析
照料勞動也是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重要組成部分。表5中的模型7分析了農村老年人是否承擔照料孫代的影響因素。可以看出,是否照料孫代不受家庭因素的顯著影響。究其原因,當前農村,隨著年輕勞動力日益流失,老人成為照顧孫代的主要承擔者,堅持的是“大家庭小個人”原則,本質上是以多代家庭為基本單位、以最大化家庭經濟收入為目的的勞動再分工的產物。(33)王也:《倫理為表,經濟為里:農村祖父母的隔代撫養驅動力》,《廣東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照料孫代是農村老年人著眼于整個家庭城鎮化、階層跨越等整體發展目標考量。且相較于子代,老人更受倫理價值的影響,當家庭經濟發展在倫理上獲得認同時,老人能夠體諒子女的生活和工作壓力,也更愿意通過自我奉獻提升家庭競爭力。有研究表明,子女是否在經濟上資助父母與父母是否幫助照顧孫代之間沒有顯著關系(34)孫鵑娟、張航空:《中國老年人照顧孫子女的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人口與經濟》2013年第4期。。
在控制因素方面,農村老年人是否照料孫代主要受年齡、性別和養老金的顯著影響,即年齡越小、女性、正在領取養老金的農村老年人更有可能去照料孫代。與男性相比,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生活模式的影響,女性在照料孫代中承擔著主要的家務勞動;在靠農業自雇實現自給自足的前提下,基本養老金為農村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讓老人幫助子女照料孫代。
(二)農村老年人每周勞動參與時間的家庭影響因素分析
1.農村老年人每周勞動參與時間的家庭影響因素
表6中的模型8是以每周勞動參與時間為結果變量建立的回歸模型。可以看出,在家庭因素中,子女經濟支持會顯著降低農村老年人每周勞動參與的時間(驗證假設1);即與沒有子女提供經濟支持相比,有子女提供經濟支持的農村老年人每周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的時間更少。

表6 農村老年人每周勞動參與時間的家庭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
在模型中的控制變量中,年齡對農村老年人每周勞動參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隨著老人年齡的增大,老年人每周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的時間更短。與無配偶相比,有配偶的農村老年人每周勞動參與的時間更長。
2.農村老年人每周參加農業和非農勞動時間的家庭影響因素分析
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由農業和非農勞動、照料勞動構成,其中農業和非農勞動又分為農業自雇和受雇。表6中的模型9、模型10、模型11分別分析了農業和非農勞動、農業自雇、受雇工作每周參與時間的影響因素情況。從家庭因素來看,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對老人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農業自雇強度有顯著的削弱作用(驗證假設1),即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使得父母每周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農業自雇的時間分別減少了10.53小時、2.58小時;但是,卻對受雇工作(農業受雇和非農工作)沒有顯著影響,原因可能是農村受雇勞作是“老人出力、雇主出錢”的雇傭勞動,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工作時間強度遠高于農業自雇,不受家庭因素的影響。
在個人因素上,年齡、受教育程度對農村老年人每周參與農業自雇、受雇工作有顯著的削弱作用;以小學為門檻,受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上水平的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自雇和受雇工作的每周時間分別減少了2.45小時、3.79小時。與受雇工作相比,男性、有配偶和個人負債的農村老年人每周參與農業自雇的時間更長;而老人自評健康對其每周參與受雇時間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身體健康的老人比不健康的老人每周受雇時間多4.64小時。社會政策中,醫療保險對農村老年人每周參與農業自雇的時間也有顯著降低作用。與沒有購買醫療保險的相比,購買了醫療保險的農村老年人每周參與農業自雇的時間少了6.01小時。原因在于,購買醫療保險已從側面說明這些農村老年人本身對身體健康狀況十分關注,努力通過適度勞作保持身體健康,適當減少農業自雇的勞動時間。
3.農村老年人每周參加照料孫代的時間的家庭影響因素分析
以每周承擔照料孫代的時間來反映農村老年人承擔家務勞動的強度。表6中的模型12分析了農村老年人每周承擔照料孫代的時間的影響因素。健在子女數量顯著影響到農村老年人對年幼孫代的家務照料時間,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加,農村老年人照顧孫代的時間也在增加(驗證假設3)。在健在子女數中,健在兒子數對農村老年人每周承擔照料孫代的時間也有顯著影響,每增加一個健在兒子,老人每周照料時間多3.51小時(驗證假設4)。
在控制因素中,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個人負債對農村老年人每周承擔照料孫代的時間有顯著影響。年齡越大的農村老年人,每周承擔家務照料孫代的時間越短;受教育程度在小學及其以上水平者,每周承擔照料孫代的時間比受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下水平者長5.32小時。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表明,當前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以家為本,老而不休。其勞動參與以家庭整體需求為主、以家庭為主要勞動場所,參與面廣;隨著年齡的增長,勞動參與比例下降,但仍有部分中、高齡老年人繼續勞作,且勞動類型選擇靈活性較強;照料勞動主要指向高強度的孫代照料,面臨“上有老老、下有小小”的老人互養和隔代撫養共存現狀。
家庭關系中農村老年人對子女的經濟支持顯著提高了其勞動參與的可能性,而子女對農村老年人的經濟支持顯著負向影響其參與非農工作;與沒有子女經濟支持者相比,有子女經濟支持的老人每周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農業自雇的時間分別減少了10.53小時、2.98小時。在家庭結構方面,健在子女數量顯著負向影響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與照料勞動。健在兒子數對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自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生育兒子越多,老人參與農業自雇的可能性越大。整體而言,老人勞動參與很大原因是為了對子女提供經濟支持;以家庭子女為核心,老人與其孫代、子代、父代四代人之間通過勞動參與實現了財富和勞務的跨代流動傳遞。
同時,農村老年人的勞動參與也是其“教育紅利” “健康紅利”和“婚姻紅利”在老年階段的延續。以小學教育程度為門檻,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類型產生了農業和非農工作類型和勞作強度的分化;隨著農村老年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參與非農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農村老年人教育程度為小學以下者更有可能參與農業自雇和農業受雇;受教育程度在小學以上水平的農村老年人參與農業自雇和受雇工作的每周時間分別減少了2.45小時、3.79小時。健康狀況是老人進行勞作的前提和基礎,老人基于自身身體狀態研判是否參與勞作。婚姻狀況對老年人的勞動參與有保護作用,有配偶的農村老年人比無配偶的農村老年人每周勞動參與時間更長,每周農業自雇參與時間多2.64小時。此外,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彰顯了兩性勞動參與的差異和性別分工。在勞動參與、農業和非農勞動中,男性比女性更傾向于進行勞動參與;但在照料孫代上,女性老人更占優勢。這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的傳統社會性別結構具有穩定特征,男性主導地位、“男主外、女主內”的文化信念和社會實踐還沒有實質改變。
“老而不休”具有“主體性”和“弱勢性”雙重屬性。在農村社會和家庭變遷背景下,農村老年人通過主動勞動參與進行“自我身體健康維護”與“自我養老積累”,主體性文化在不斷尋求個體價值與家庭價值平衡中得以孕育與發展,反映出老人在家庭轉變中能動性的自我成長。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可以是一個“雙贏”的選擇,其一贏在老人健康、有配偶、有文化,其二贏在老人持續為家庭、為社會做貢獻。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弱勢性”體現在:傳統觀念中,老年人應該在家養老的時間無限往后推遲,“老而不休”甚或“老而難休”。基于利他主義、實現家庭價值的和主動的勞動參與值得鼓勵;但部分農村老年人為維持生計,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重負下,仍需在高齡階段繼續長時間勞作,以緩解經濟壓力及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這種被迫的“被啃老”式勞動參與則應引起社會警醒。
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實踐也表明,需要社會和家庭完全贍養的主要是7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為社會養老負擔的匡算提供了依據,有助于宏觀養老政策調整的“有的放矢”。
在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下,要重點重視構建支持和保護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的政策和制度。保護和促進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應建設和完善老年人勞動參與的權益保障配套法規,來依法保障老年人在生產勞動過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另外,照顧孫子女和父母的照料勞動,也應得到社會承認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