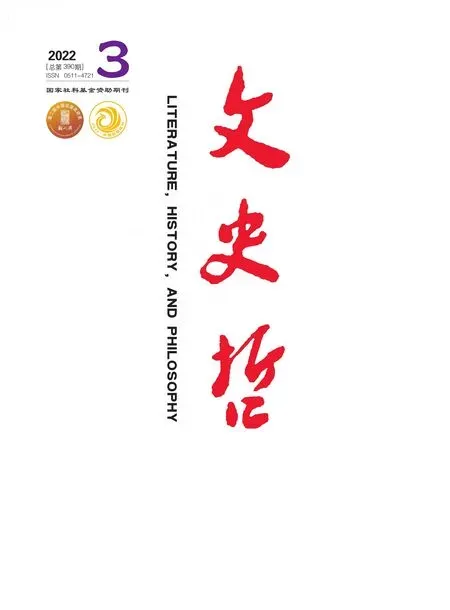現代互文化中的中國之哲學研究
萬俊人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4)
能否且如何建立具有獨立品位的中國學術研究范式?這一問題之所以再一次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前置性問題,我想至少與兩個因素有關:其一可稱之為文化學術史的因素,其二則是中國社會與中國學術的當代處境。前者實際上可以追索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國門被迫洞開后,激進的“拿來主義”與消極的文化保守主義之爭隨之而起,中國學術究竟向何處去成為一個必須直面的大問題:是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全盤拷貝西方現代知識體系?還是僅僅以“西學為用”的工具主義方式,求得以“中學為體”的文化守成或自我續存之目的?同這種兩極極端迥然有別的是,20世紀20-40年代看似邊緣實則堅韌的開放積極的文化守成主義一脈,比如說,著名的清華“學衡派”所取的文化與學術之“中道”方式,作為其代表性人物的陳寅恪先生在為王國維先生撰寫的碑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命題的前半句是就學者之學術研究立場來說的,實際也關乎中國學術的立場和姿態,這就是獨立自主與學術自律;后半句是就中國學術的現代方式而言的,實際關乎中國現代學術的基本立場和方法,這就是開放地面對并學習援用現代世界、特別是現代西方學界的“自由思想”之現代學術方式和科學理性主義立場。事實上,陳先生本人的研究乃至當時整個清華國學院和人文學院導師群體的研究,大都具有這種“融通古今”“無分中西”的自由思想之學術風格,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的國學研究,到朱自清、聞一多的文學語言學研究,蔣廷黼、雷海宗的史學研究,馮友蘭、金岳霖、張岱年的哲學研究等等,莫不如是。也唯其如此,他們才創造了堪稱20世紀中國學術典范的學術成果。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再次發起有關中國“學術自律”的討論,表明現代中國學術自立意識的持續與強化,洎今重提這一問題實在不過是其來有自,于斯尤盛而已。
或問:為何此一問題意識于斯尤盛?這便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因素,即當代中國社會所處的時代境況再一次激發了中國學術的自律意識,并且使其進至這樣一個關口:無論中國社會文明的當代處境還是中國學術的當代處境,都需要一次全局性的身份重置(status re-set),包括學術身份、方式和方法、話語表達等方面。確切地說,經由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轉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全面小康階段,并邁向全面現代化的新開端,其中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從簡單學習西方現代化經驗轉向學習與自主創新相向并進的新發展方式,文明發展的單向“拿來主義”既不可取,也不再可能。與之類似,當今中國學術的發展同樣也面臨著文化“拿來主義”既不可取也不再可能的新局,這其中當然不只是一個廣義的“知識產權”問題,更是一個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民族國家之文化自主(權)與現代性文化知識創新的責任承諾。因此,如何突破“古今中西”的百年糾結,以期真正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型轉化”與“創造性發展”?真真確確地呈現為中國現代性學術的優先課題。
中國現代性的學術課題如此龐大而復雜,作為單刀直入式的一篇主題筆談,實難洞徹其萬一。故此,我僅從哲學的視角,從“現代互文化”的維度,試探這一課題的某些題義,以期拋礫石而引玉璞。
一、題義:現代互文化中的哲學倫理學視角
“現代互文化”(the modern contextualization)亦可譯為“現代語境化”,廣義指現代世界視域中多元文明暨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狹義上則主要指現代世界體系中跨際——即地區、國家、民族、社群之間——的思想與學術的話語交流互動,其核心要義有二:一是現代時間維度,亦即把所謂“互文化”限定在現代世界;二是“互文化”的動態關注,也就是說,我們將要討論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互文”或“語境”問題,而是“互文”的動態過程。我深信,不僅僅是在已然較為充分的經濟全球化之當今世界,而且面對西方現代化的先行經驗,任何關于中國現代性的討論都不可能離開“現代互文化”的歷史維度而獲得某種真實的意義。也就是說,在經濟全球化已然充分展且歷時開長達五百余年、國際通訊交流幾無技術障礙,并且最重要的是日趨開放且開放趨勢不可逆轉的“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Immanuel Wallerstein語)之時空架構中,脫離“現代互文化”話語方式,任何關于某一地區、某一國家、某一民族,乃至某一社群的文明/文化討論,最多都只能獲得“地方性知識”甚或“個人知識”(“a local knowledge or personal knowledge”,Michael Polanyi語)的有限意義,并且,在“非現代互文化”(non-contextualization)情形下,任何“地方性知識”或“個人知識”的討論都難以充分普遍有效。然而問題在于,作為一個廣泛且日益深刻地嵌入“現代世界體系”之中的大國,無論當代中國社會實踐還是當代中國文化學術,都不可能、也不應該囿于民族國家的“地方性知識”范疇而無以超越,失去同世界多元文明/文化,尤其是作為現代先進的西方文明/文化展開平等對話,從而通過相互交流與學習而融入現代互文化過程之中的歷史性機遇,盡管對我們來說,這一機遇同時也意味著前所未有的文化困惑與學術挑戰。
與此同時,“現代互文化”主張的提出,也恰恰是基于這樣一種確信:多元文明/文化同樣是一個前提性的話語現實或現代文明/文化事實,面對這一前提性事實,我們同樣可以作出這樣一種判斷:忽略或者輕視文明/文化多元論的前提性事實,任何有關“現代世界體系”或者“現代性”(modernity)背景下的思想和學術討論,都難以獲得其真實合理性,也難免落入空洞抽象的教條主義,或者落入自以為是且實際上僅僅是某種特定形式的獨斷論,甚或演變為某種文化優越論或文化霸權主義。也就是說,“現代互文化”不僅是現代思想和學術研究的一種在先的“現代世界體系”或現代世界知識的開放性論理(邏輯)預制,同時也是一種在先的多元或多樣性“地方性知識”的前提性預制。
上述雙重預制是幾乎所有關乎現代學術研究和思想探討都不得不面對的理論前提。面對一直處于發展不平衡不平等的現代世界體系,如何尋求多元文明/文化之間的公平相待和平等對話,亦即如何尋求一種公平平等的“現代互文”交流方式,同樣也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代性課題。這其中,不僅有尚處在前現代或現代化過程中的后發國家的文化自主(權)和文化自信問題,也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包容和文化“他信”(trust the others)問題。
開放性的論理預制源于現代世界的開放性事實。相對說來,人們對于人類文明的客觀事實不難達成某些甚至是較高程度的理論共識,諸如:科技理性、市場經濟、經典藝術;而有關文化多元的地方性知識交流則容易產生觀念差異,難以達成哪怕是某種較低程度的理論共識,因為理論的邏輯推理很難彌合文化邏輯偏好所產生的價值分歧。究其根源,蓋因事實性的邏輯推理與多元文化的價值訴求之間具有難以逾越——遑論消弭——的鴻溝。不難發現,“現代互文化”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或者說主要不在于有關現代世界體系和多元文明的普遍客觀主義的事實確認,而在于,或者說主要在于有關現代世界體系或現代性本身的文化價值偏好與文化意義理解,在于多元文明/文化主體——地區、國家、民族、社群等等——自身的文明/的特殊主義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訴求。更簡要地說,在于“現代互文化”中的事實認知與價值判斷之間難以契合的分歧,在學術和思想理論上同樣如此。
這的確是一個難以消解的難題。對于一些高度專業化的人文社會科學來說,這一難題或許可以借助專業技術和學術限定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譬如,類似德國“年鑒學派”那樣的實證史學、在考古學中已然相當普遍的碳的同位素年代測定技術、人類社會學中的田野調查、數量經濟學、統計學、大數據分析、“數字人文”等等。但是,對于另一些哪怕是具有相當專業化特性的人文社會科學而言,問題遠非如此,比如,在馬克斯·韋伯式的社會學理論中,在有關人種、民族、宗教、禮制的人類學、民族學和宗教學研究中,韋伯所說的“價值中立”就很難達成。易言之,面對這一疑難,我們可能需要且不得不通過跨學科或多學科交叉的學術論理方式,來嘗試打通“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隔閡。就此而論,以非專業理論化或運思論理之“業余風格”(amateur)見長的哲學,確乎需要承諾更多的學術工作。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在解決這一疑難上的作用,而僅僅是說,哲學——或許還有廣義語言學——在此一論題上具有較大的回旋余地,因之應承擔更多的學術責任。
然則,實際上事實與價值的兩分性問題自古以來一直都是中外哲學倫理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對此,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大致以兩種進路切入這一課題:一種可以概括為經驗-邏輯論進路,西方古典哲學中的經驗主義和現代哲學中的邏輯實證主義堪為代表;另一種則是所謂超驗論或本體論暨存在論進路,古典哲學中的形而上學和現代哲學中的現象學-存在主義堪為典范。以經驗-邏輯論的方式論之,事實與價值分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范疇,若要打通兩者之間的分隔,必須借助可普遍化的經驗實證或邏輯的推理證明,才可能解答所謂“休謨難題”,即如何合乎邏輯(理性)地從“是然”(to be)中推導出“應然”(ought to be)。而對于超驗論或本體論暨存在論的進路來說,人們關于“存在”(being)本體或“存在之存在”(beingbeings)的形而上學意義與價值意義的理解,本質上是可以相互聯通的,或者說,是具有內在價值(意義)關聯的,因之,所謂事實與價值的兩分只不過是意義理解的分別,而非意義本身的分離。事實上,“存在”本身即蘊涵可能的價值(意義)理解,使“是然”(to be)獲得“應然”所必須的價值意義。英文表述可見:“to be”既可能為“to be bad, or to be worse and worse, or even to be worst”,也可能為“to be good,or to be better and better, or even to be best”,這其中既包括內在目的性價值(意義),也包括外在工具性價值(意義)。
現在的問題是,即使我們假定上述兩種哲學進路或方式都能最終解答事實與價值/意義之間的兩分性問題,又如何將之應用于或者擴展到不同文化之間的思想和學術的交互理解之中呢?如何表述并解答這一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們將要討論的現代互文化中的中國之哲學倫理學研究范式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在直入本文主題之前,先探討并聚焦現代互文化之哲學主題的基本緣由所在。
二、題問:“歷史經驗”與“互文方式”
我們可以通過中西哲學轉型的歷史經驗,來獲取對上述疑難的部分解答,進而尋求現代互文化視域中中國之哲學研究的現代范式,為建構當代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貢獻一份哲學的專業方案,盡管她可能仍然只是——事實上也只能是——一份開放式或嘗試性的方案草圖。
哲學(Philosophy,即“愛智慧”)被公認是古希臘文明的兩大發明之一,古希臘文明的另一大發明是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a Games,即“奧林匹克運動場的體能競技游戲”)。古希臘人的哲學之愛源于對人所處世界和宇宙萬物變化的“驚異”,因而其哲思最先起于宇宙論,歷經形上存在本體論,最終回歸反思人之自我及其生活實踐的倫理學和“城邦學”(今譯“政治學”)。隨著古希臘文明從“內部極盛”走向“外部極盛”,古希臘哲學已經難堪希臘化羅馬帝國之文化大用,職是之故,基督教乘“虛”而入,成為羅馬帝國之文化思想體系的主脈或帝國政治意識形態之維。歷史地看,作為基督教之原始母體的猶太教,自古猶太人被驅逐出古埃及之日起,便成了一種漂游不定的或者無確定地方性標識的民族文化。可是,這種非地方性的文化是如何轉化為羅馬帝國的主導型文化,繼而擴張為一種“普世主義”(ecumenicalism)文化的?又是如何切入或者融合于古希臘哲學的呢?就本文主題而言,關注這一點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與學術之“互文性”鏡鑒意義。
如果說,之所以能夠從羅馬帝國的文化邊緣走向其意識形態中心,基督教主要還是借助于帝國政治的擢升和推廣才得以邁出第一步的話,那么,透過西方中世紀的千年文明與文化遞嬗歷程,特別是經過教父哲學時期奧古斯丁對柏拉圖哲學的宗教哲學挪用和神學化時期托馬斯·阿奎那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神學重構,便不難發現古希臘哲學與基督教宗教神學之間的文化互動,也正是通過這一長逾千年的“互文化”(contextualized)方式,西方哲學完成了從形上本體論向宗教神學本體論的范式轉化。
進至近代前夕,借助于“地理新發現”、科技發明和由此帶來的全球殖民化市場擴張,以及更重要的是,古希臘羅馬世俗文學藝術的重新發現,亦即“文藝復興”所帶來的思想文化啟蒙,首先是西歐,繼而是幾乎整個歐洲的現代社會轉型,最終形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理性啟蒙運動共同建構的西方現代性。也正是在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中,哲學最先通過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家的人道主義呼吁,繼而通過英國哲學家培根的《新工具》和《崇學論》,法國數學家哲學家笛卡爾的《方法論》和《形而上學的沉思》,以及隨后英、法、德諸國近代哲學的共同努力,哲學實現了擺脫宗教神學、回歸知識理性的知識論或認識論轉型。如果說,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命題是西方近代哲學第一知識宣言,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命題是西方近代哲學自我認知的先聲,那么,康德和黑格爾所代表的德國理性主義哲學便是西方古典哲學最后的理論總結。
西方哲學的近代轉型是現代知識體系的轉型,標志著理性主義科學觀和人文觀的現代確立,堪稱西方現代性得以最終確立的重大理論成果,其意義確實是空前的、劃時代的。然而,西方哲學的現代性轉型并不是終極的,借用當代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話來說,她仍然是一項“尚未完成的現代性謀劃”。事實上,到20世紀前后,就先后出現過唯意志論、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等多重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哲學逆轉。二戰后,西方哲學經過理性與非理性/超理性的反復博弈,哲學又開始醞釀一場自我更新和轉換的“范式革命”(Thomas Kuhn語),即:從知識(認識)論導向逐漸轉向方法論導向,因而出現了更多的哲學流派和更多“做哲學”(doing philosophy)的方式,除了人們所熟悉的英美分析哲學和歐陸實踐哲學兩大風格之外,還相繼出現諸如解釋學(闡釋學)、文化哲學、哲學人類學,甚至“他者哲學”等風格各異的新型哲學流派。這其中,文化解釋學和“他者哲學”因其鮮明的“互文性”特征尤其引人矚目,也獲得了較強的跨文化拓展能量。
從古希臘的形上本體論(for why)到中世紀的神學哲學(for God’s being),再到近代理性認識論(for what),進至現當代的多元方法論(for “how”),西方哲學一路走來,不斷轉換其哲學主題、思想目標和理論方法。顯然,這一進程不單是轉換哲學(研究)范式的持續努力,而且也是哲學思想內涵和理論方法的持續豐富,更是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之持續更新的自我鏡像。它給我們留下的有益啟示至少有如下幾點:其一,哲學的理論范式和“做哲學”的學術方式總是與時俱進的;其二,如同所有人文社會科學一樣,哲學范式的轉換既與特定的文化傳統和歷史經驗密切相關,更與特定的社會實踐變革密切相關;其三,哲學范式的轉變既是特定社會歷史進步轉化的思想先導,也是其特定社會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其四,哲學范式的生成和轉換必定同特定的社會文明和文化傳統有著某種內在的精神聯系,換言之,哲學及其理論與學術研究范式從根本上說乃是特定文明/文化和特定民族精神、社會心理的精神調適。
上述啟示幾乎同樣適用于中國哲學及其歷史演進情形。應當首先申明,筆者不太認可這些年來國內哲學界聚訟不已的所謂“中國哲學之合法性”討論,甚至也不太認可這場討論的某些學術方式。我的理由是:(1)這種討論本身多少陷入某種虛擬的唯名論與實在論之爭而無法自拔。拘泥于“哲學”概念而荒疏于其實質內涵——即“愛智”的普遍意義,斷言中國沒有“哲學”不僅武斷,而且并不符合實際。“愛智”之為人類思維的智慧游戲并非古希臘人獨有,若以概念之名斷定哲學所有權之實,那么,除了古希臘人之外,孰敢宣稱擁有哲學?文明和文化的發明(權)并不意味著實質意義上的專有權,即便是科技知識產權也并不意味著壟斷或專有,本質上是可以共享的,也是可以共同創生的,一如某種科學技術知識,發明有先后,擁有不可永久專權。最多也只能說“某時某地尚無某事”,而不能說“某某永遠沒有或者永遠不能有某事”。因此(2)中國有無哲學的討論或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之說既無可證成之依據,也顯得較為狹隘。人類文明雖然存在著不同區域、民族、國家、社群的文明/文化創造成果的多樣性差異,但根本說來是可以也應該相互學習借鑒的,任何人都不應以優先發明或發現為由而拒絕人類文明和文化的共享,更不應拒絕相互學習、借鑒、改進的權利。誠如人們不能正當合理地說古印度人創造了佛教就不允許佛教傳入東亞和世界一樣,更不能因此否認禪宗作為中國創造的一種新型佛教而具有佛教之一般特性和文化之合法正當性。(3)此類討論或多或少受到諸如黑格爾等西方近現代哲學家的既定論斷的影響,并非都是基于“知識社會學”的考量而提出的,因而多少屬于“舊事重提”,并無新意。(4)任何學科都是人類“知識體系”的組成部分,學科的知識能力和發展有先(進)與(落)后、快與慢之分,人類知識的學習、傳播和運用卻不能劃分為可與否,在現代開放社會的條件下更是如此,這也正是“現代互文化”之所以必要的根本理由。這一問題并非本文主題,但卻與之相關。
我想說的是,中國哲學其實也存在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持續轉換。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自無須贅言,僅以儒家為例,從孔孟儒學到宋明理學再到今日儒學的多期遞嬗便是顯證。孔子之后,儒分為八,思孟一脈與荀學一脈便有內在美德論與外向禮學之分別;同樣,在宋明儒學發展階段,也有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分殊;現代儒學更是眾說紛紜,學派林立,難以歸宗于一。從先秦“原儒”(the Original Confucianism)到宋明“新儒”(the Neo-Confucianism)再到現代所謂“新新儒”(the New Neo-Confucianism),中國儒家始終在持續更新中生長綿延,思想的主題內容、思想資源、理論方法、話語方式等要素的更新轉換和互文重構充盈其間。如果說,儒禪互文構成了宋明新儒互文化轉換的基本特征,那么,中西互文則構成了現當代中國儒學之互文化轉換的基本面貌。作為一種具有鮮明道德倫理指向的實踐哲學,盡管整個中國儒學的歷時性范式轉換并不像西方哲學演進那樣激烈和徹底,出現從哲學轉向神學,又從神學轉向科學(理性主義知識論)的“革命性”轉換,但在其實踐哲學的理論形態、論理方法和思想內涵等基本面向上,更新轉換的基本特征卻是犖確可見的,而且始終保持著開放互文的文化姿態和思想立場。這也正是作為中國文化與價值精神之主脈的儒學,能夠歷數千年歲月更替而屹立不倒、經萬重沖擊沉浮而經久不衰的根本緣由之所在,一如古老的中華文明和文化能夠五千年一脈相承,縱使屢次經風浴火,仍能鳳凰涅槃。
中西哲學文化流演的歷史經驗,給我們留下許多有益的“現代互文化”的提示,也可以將之看作是現代互文化之基本規則的雛形。試撮其要概述如次——
(1)主動嵌入多元文化的互文化進程。借助波蘭尼的“嵌入”概念,我想表達的基本意思是:直觀地看,“現代互文化”展示的是一種動態的現代諸文化文本共存互文情景,主動“嵌入”其中是加入同其他文化的對話互動之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嵌入”是為了與其他文化展開對話交流。近代以來,哲學經由日本翻譯,得以正式的學科身份進入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國之哲學研究從此開始進入同西方哲學、印度哲學等異域哲學的交流互動,取得相當成功的經驗。比如,金岳霖、馮友蘭、張岱年諸先生接受并援引現代西方邏輯實證主義方法,梳理和建構中國哲學(史),便是成功一例。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胡適先生也曾試圖借用歐美經驗主義——確切地說是美國實用主義——的方法,率先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可惜只成半部,留下半部未竟之憾。
(2)持以開放平等的學術姿態參與互文交流。開放既是一種學術姿態,也是一種理論方法,亦即通過開放各種問題域,獲取域外哲學的理論信息,同時激發中國之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在這一過程中,確立學術主體意識并建立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同情之理解”(陳寅恪先生語)誠然必要,樹立學術開放意識并平等地看待“他者”哲學同樣重要,某種意義上說,在現代互文化過程中,開放而平等的學術意識對于后來者甚至更為重要。就此而論,港臺新儒學(如牟宗三、唐君毅諸先生)所做的學術貢獻和理論成果都是引人注目的。約20年前,華裔美籍學者王蓉蓉教授發起的中美哲學家倫理學家對話,更是中美當代哲人第一次直接的哲學倫理學主題對話,也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影響。
(3)對話不僅是雙向對話(dia-logue),而且應當是多向的或者全方位對話(omni-logue)。這一點是基于當代和未來全球化背景下人類共同體應當采取的現代互文化方式而提出的。現代世界體系歷經了從單極帝國稱霸到兩極集團對峙,再向多極世界的艱難演變,也正面臨著某種重回單極帝國霸權的危險。這是我們現時代的實際處境,也是我們現時代的思想與學術處境,多向的或全方位的對話正是突破或超越這種雙重處境所急需的民主學術姿態。
(4)對話的目的在于平等交流、相互學習、相互理解、尋求共識,而非話語權力爭奪,更不是攝取話語霸權。對于那些學術民粹主義者和意識形態的霸權主義者,這一點尤其需要反復申言和強調。
(5)尊重互文的基本規則,堅持互文化過程中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以盡可能實現最大公約數的正義共識。這是現代互文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目標。
(6)保護和尊重不同話語、不同文本、不同話語之各自不同的語法規則系統的獨立自主和自由,同時提倡和激勵不同話語、不同文本、不同語言系統之間的互譯、互鑒、互學和互助。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概述絕非中西哲學之互文化歷史經驗和互文方式的全部,更不是現代互文化的既定規則體系,而只是筆者個人的初步探究體會,或者,最多可望作為一種現代互文化的初步的“個人知識”,只可供有關主題討論參考。
三、題外:文化多元論的兩種理解
無論是探討如何建立具有中國學術品位的中國學術研究范式,還是本篇所取之“現代互文化”視角的初步探討,其實都涉及當今聚訟諸多的“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和“多元文化論”(multipleculturalism)問題,因為如何看待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文明/文化多樣性,以及如何料理多元文明/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不僅直接關乎“現代互文化”是否可能,而且關乎如何建立具有中國學術品位的學術研究范式的方法論原則。
對于多元文化或文化多元的事實存在,當今國際學術界并無異議,但卻或明或隱地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較為消極的理解,即:把文化多樣性差異看作是建構現代人類共同體,并形成可普遍化之現代價值共識難以逾越的障礙,因之堅持某種固化形式的特殊主義或狹隘地方主義。這其中又表現出各種不盡相同的學術態度:或者隱藏著某種現代文明/文化優越論或差異等級化的文化歧視,以先進與落后或者強與弱來刻畫并定性多元文明/文化之間的差異、張力和限度;或者因擔心甚至恐懼西方普世主義的擴張同化壓力而拒斥開放,拒斥現代互文化;抑或堅持文化傳統、歷史語境和社群之獨特個性而懷疑達成任何形式的跨際——即:不同地區、國家、民族和社群——共識的可能性,更有甚者,這一懷疑甚至被引申到對整個西方現代性或所謂“普遍理性主義”之“道德謀劃”已然失敗的判決,譬如,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倫理學家麥金泰爾。
另一種是較為積極的理解,即:不僅把文化多元差異的事實看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正常面貌,而且將其視之為改進和完善人類現代性發展方式的文化資源和動力,相信具有不同特質和品性的多元文明/文化不單可以相互學習、取長補短,還可能為人類社會的現代性追求,作出各自不同卻又有益于現代性改進的文化貢獻。正因為如此,“現代互文化”不僅必要,而且意義重大,一個健全的可持續的“現代世界體系”應當是且只能是能夠兼容多元文化優勢的開放的文明/文化的平等對話體系,在此意義上,“現代互文化”確乎是一種較為積極合理的理解文化多元論的學術方式。
當然,即使遵循“現代互文化”的學術方式,也還需要面對和料理諸多學理技術難題,比如,如何看待與解決多種語言之間的語義差異?進而,如何處理不同語言系統之間的互譯問題?如何解決或消解話語權利的爭執和話語霸權問題?最棘手的是,如何避免文化學術的互文過程受到政黨政治和資本集團利益等非文化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如此等等。所有這些不僅關乎學理技術,還關乎學術道體或學術根本。而實際上,這類具體問題及其解決常常比一般理論問題更難更復雜,因之需要更多的耐心與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