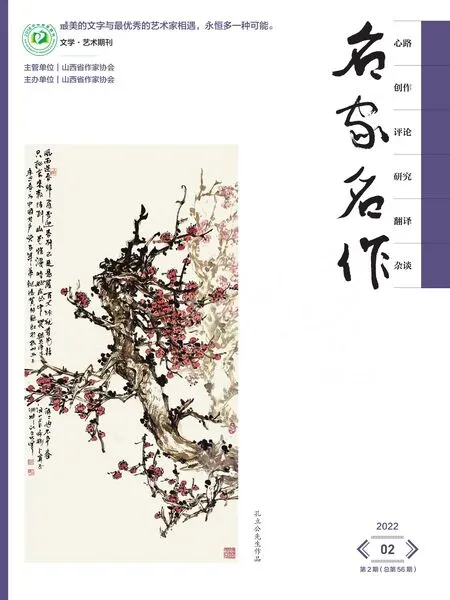論《詩經·君子偕老》中的諷刺藝術
秦永芝
《尚書·堯典》中記舜云:“詩言志,歌永言。”《毛詩序》亦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可見古人作詩是為表達人之“志”。結合《詩經》創作之背景,其“志”與政治聯系密切,每首詩都反映著詩人對社會政治生活的看法與評價。詩言志的主觀需要結合古人含蓄蘊藉的詩學觀,催生了如《君子偕老》一類的諷刺詩,顯現出獨特的藝術風格及深遠的文學影響。
一、《詩經》——諷刺藝術的開端
《詩經》乃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人們關注著普通民眾和社會現狀,創作了大量映照現實之作以抒情言志。鄭玄《詩譜序》言周懿王執政后,國勢漸衰,乃至“周室大壞……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此即《漢書·禮樂志》所言:“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西周后期,周道始崩,怨刺之詩形于詠歌,《詩經》中便出現大量諷喻現實的作品,詩人們或出于對腐敗朝政的不滿,或悲于自身生活的不幸,作詩以譏刺統治者不符禮儀之行,或諷喻國君,抑或警示世人。《詩經》中的諷刺詩多集中于《國風》中的周朝民歌。詩人們直面現實,又因明哲保身的需要,運用諸如比喻、對比、反語等藝術手法,營造出委婉含蓄的諷刺效果。《毛詩序》指出這類諷刺詩的諷刺特色為“主文而譎諫”,因此,諷刺詩在表達時具有更獨特的藝術風格與表現手法。這些諷刺詩使《詩經》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由此成為我國現實主義的源頭,其現實主義內涵為后世諷刺文學開啟了寫實傳統,諷刺詩所用的藝術手法亦為后世詩人所繼承。
二、《君子偕老》中的諷刺主題
《君子偕老》是《國風》衛國鄘地的一首民歌,全詩茲錄于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發如云,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纟希 ,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毛詩序》言:“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古今各家多從《毛詩序》之說,以為是刺宣姜之作。宣姜淫亂之行,史料中記載如是。《左傳》桓公十六年:“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伋子。”《左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史記·衛康叔世家》中亦有相關記載。由史料所載,宣姜乃齊女,本應嫁于衛宣公之子太子伋,卻因姿色過人而為宣公所霸占,若說此時宣姜是不得已而嫁之,之后與公子朔謀害太子伋,則是宣姜之過也,后侍公子頑則亦于禮不合也。由是,《君子偕老》當有刺宣姜之意無疑,但結合《詩經》中《新臺》《墻有茨》《桑中》《鶉之奔奔》諸篇可知,除刺宣姜淫亂之外,亦當有譏刺衛君好色不好德之意。
衛國自康叔立國,歷武公修德,二者皆為治國之君,給衛國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但自衛宣公以來,宣姜與公子朔(后繼位為衛惠公)謀位而害太子伋,引發左右公子的怨恨。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衛國由此展開長達數十年的諸子之爭,國運日漸衰落。錢澄之言:“明衛之所以為鄘,由宣姜淫亂,人倫道絕,以致衛化為狄而遷于鄘,姜其禍之首也。”但他忽略了衛國公室動蕩的源頭乃衛宣公失德之行(前烝父妻夷姜,后奪子妻宣姜,聽信宣姜與公子朔讒言殺太子伋),而僅將其歸于宣姜一人之過,有失公允矣。孔穎達《詩譜序》言:“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墋黷,亦怨刺形于詠歌。”人民心中有怨,發而為詩,遂以《君子偕老》刺宣姜之失德及衛君之昏庸,又囿于惡劣的政治生存環境,諷刺方式委婉含蓄,頗具特色。
三、《君子偕老》的諷刺特點與文學影響
《君子偕老》一詩,最突出的諷刺特點乃欲刺先揚。《君子偕老》全詩三章,除首章“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之如何?”三句,余篇皆大力鋪陳宣姜服飾之盛、儀容之美,讓人恍覺“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地也?”,儀態端莊若仙子下凡,不了解衛國此段歷史的讀者初看此詩,定認為其為描寫某一賢夫人之作,而難解其深意。通讀全篇,其實“子之不淑”四字已顯露了詩人本義,毛《傳》、鄭《箋》、孔《疏》及后世諸儒,皆謂“不淑”為“不善”,言宣姜之背禮。可見,《君子偕老》一詩,通篇大肆宣揚宣姜之美,給人以美好的假象,繼而以一二譏諷之語揭示諷刺主旨,所揚與所刺形成強烈反差,使人對宣姜與衛君之淫亂事產生極大反感,從而達到諷刺效果。
《君子偕老》一詩的另一諷刺藝術,是以隱晦語言營造出委婉含蓄的諷刺效果。詩貴含蓄,《詩經》中的諷刺詩尤其凸顯這一特點,《邶風·靜女》陳靜女之美,實則刺衛君欲易今夫人;《齊風·猗嗟》塑造出一英俊非凡、射技高超的男性形象,實則是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行亂倫之事,《詩經》中諸如此類詩篇者甚多。《君子偕老》亦是此種諷刺藝術的代表,詩中反復詠嘆宣姜外表之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描繪其服飾之盛;“鬒發如云,不屑髢也”言其秀發濃密;“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摹其膚色白皙。詩人精心雕刻宣姜之容貌,目的在于突出其內在的“不淑”,痛斥其淫亂,亦蘊含著對昏庸統治階級的不滿。只字不提歷史事實,諷刺委婉含蓄,這貼近孔子所言“溫柔敦厚”的詩教觀,朱熹亦評其“辭益婉而意愈深矣”。
運用反語,是《君子偕老》一詩最具特色的諷刺藝術。該詩詩題為“君子偕老”,毛《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禮記·郊特牲》:“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古人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前述已明,宣姜一女侍多夫,王先謙亦云宣姜“乃與公俱陷大惡”,《君子偕老》一詩實為諷刺宣姜的淫亂與衛君的失德,則明宣姜萬不能與君偕老,君子偕老乃反語也。詩中,作者用大量筆墨渲染宣姜的服飾與儀容,具“小君”風度,但用“子之不淑,云之如何?”二句點出其品性之不端,可見其內德與外貌之不相稱,詩中所用之美詞皆為譏刺之反語也。由此看來,詩中描繪愈是濃墨重彩,愈讓人惡心統治階級之無德與無道,贊美之詞包含著強烈的諷刺意義。
《君子偕老》的文學影響首先體現在對后世詩人詩作的直接影響。《君子偕老》所用諷刺手法,杜甫《麗人行》一詩便有所繼承。杜甫《麗人行》一詩,用大段篇幅描寫楊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用細膩的筆觸描繪出游春仕女的體態之美和服飾之盛及宴會的豪華,僅在最后一句以勸說口吻委婉點出楊國忠的驕橫:“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諷刺方法與《君子偕老》一詩有異曲同工之妙:語言鋪排華美,諷刺之事不直露而諷刺之意更深矣。《君子偕老》一詩描寫女主人公容貌時,詩歌所用雖為反語,但遣詞造句齊整巧妙,意象精妙絕倫,讓人恍覺仙女下凡,連姚際恒亦不禁感嘆:“此篇遂為《神女》《感甄》之濫觴。‘山、河’‘天、地’,廣攬遐觀,驚心動魄;傳神寫意,有非言辭可釋之妙。”可見《君子偕老》一詩所用辭藻之盛、意象之妙,開啟了詩歌史上“神女”題材書寫的新領域。
四、結語
《君子偕老》一詩,運用欲刺先揚、反語等諷刺手法,著力描繪了一個衛國夫人的端莊形象,但她卻德行有失,品行與華服不稱,而導致其失德的根源乃上層統治者的裹挾玩弄,故詩歌的華美辭藻下其實暗含著對宣姜失德的諷刺及對無道統治階級的披露。該詩描摹衛夫人之筆法,下啟宋玉《神女賦》、曹植《洛神賦》,對后世詩賦中“神女”題材的書寫起了一定的典范作用;詩歌中委婉含蓄的藝術表達,亦對我國溫柔敦厚的詩教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