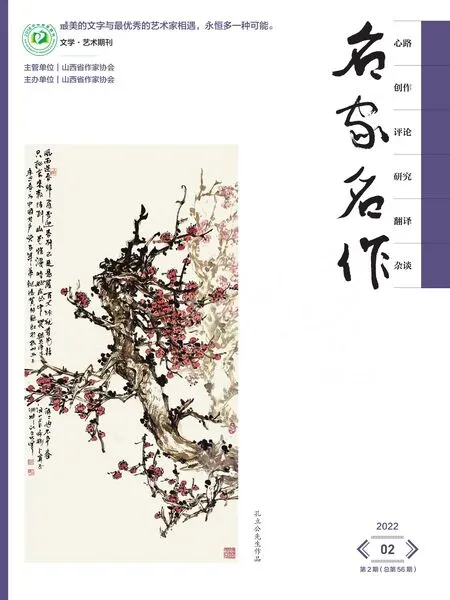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乞丐新娘》中露絲的身份困境與抗爭
沙 寧
一、引言
加拿大短篇小說家艾麗絲·門羅是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其作品幾乎都選取女性做主人公,尤其是那些來自生活底層的女性,因為在她們身上折射出自己過去的影子。《乞丐新娘》就是一部這樣的自傳體小說,它呈現了女主人公露絲基于多種不調和的文化勢力影響下的身份困惑,進而鋪開了加拿大復雜的社會歷史景觀。《加拿大小說雜志》的一篇專訪,指出門羅的故事“蘊有含蓄的社會評論……存在某種階級體系”。門羅對此回應說,離婚后回到家鄉,她立刻意識到了階級差別,并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乞丐新娘》中,門羅對于這種因懸殊的家庭背景而導致的巨大文化差異做了深刻的挖掘。露絲和帕特里克的愛情故事就是門羅和第一任丈夫吉姆關系的翻版,兩人分分合合,婚姻最終走向盡頭。
“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必定帶著階級的烙印。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站在本階級的立場去分析、評價生活。因此,不管是題材的選擇,還是人物的描寫,都反映了作家的階級意識和階級傾向性。”門羅出身寒微,通過婚姻躋身中產階級,她的作品多展現底層女性對貧窮的恐懼和對舒適生活的向往,而在一個充斥著等級差異和貧富差異的社會,這些女性的成長之路必然充滿坎坷。在門羅平靜的筆下,暗流涌動,對社會階層劃分帶來的種種身份困境進行了鞭辟入里地剖析和鞭撻。
二、《乞丐新娘》中露絲的身份困境與抗爭
(一)獎學金女孩
《乞丐新娘》收錄在1978年出版的《你以為你是誰?》短篇小說集中。1972年,阿特伍德在《生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中指出,加拿大文學的主題是“生存”。露絲和門羅一樣,都是“獎學金女孩”。門羅出生在安大略省溫厄姆鎮的下城區,那里是“貧窮”與“落后”的代名詞。高中時期成績優異,但是貧困的家庭無法為門羅提供經濟幫助,她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1949年秋天,門羅進入能提供不錯獎學金待遇的西安大略大學。加拿大那個時期的大部分“獎學金女孩”,都來自下層勞動階級的家庭。“‘獎學金女孩’的標簽對于露絲來說,首先就意味著她在經濟上的脆弱性和依賴性”,也暗示了一種文化背景的劣勢。
露絲和帕特里克也和門羅與吉姆一樣,相識于圖書館。帕特里克的家庭在不列顛哥倫比亞擁有連鎖百貨商場,而露絲出身于貧窮的勞動階層,就像早年的門羅一樣,操著明顯的小鎮口音,常為自己的出身困擾,表面自信而內心敏感,性格矛盾。雖然這種階層與文化上的差異自門羅和吉姆相識之初就一直存在,但矛盾確實因為門羅在經濟上的日漸獨立而加劇了。露絲最終也從家庭主婦走上了經濟獨立,成為家喻戶曉的媒體名流。在加拿大的歷史上,“獎學金女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后涌入勞動市場,以填補男勞動力的短缺。隨著女性解放的進程不可逆轉,戰后職業女性的人數不斷增長。“事實上,正是這一群‘獎學金女孩’,構成了‘加拿大女權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的生力軍。”
(二)乞丐女
“乞丐女”是世界名畫《科法圖國王和乞丐女》中的要飯女。這位非洲國王對乞丐女一見鐘情,使她一步登天成為皇后。門羅以此為藍本,創作了一個個現代版的“乞丐女”形象。就像門羅本人一樣,這些來自社會底層的女性,因為某種偶然的機緣嫁入豪門。但是,門羅并不是在展現婚姻救贖貧家女的童話,而是展現深刻的階層問題,《乞丐新娘》在展現階級沖突方面尤為突出。當露絲向帕特里克坦言他們來自不同的世界,表現出不安:“我那邊的人是窮人,你會覺得我住的地方是垃圾堆。”帕特里克卻說:“很高興,你是個窮人。你這么漂亮。你就是乞丐新娘。”帕特里克雖然對露絲癡迷和心懷敬意,但是也含糊地承認這是她的運氣。
對該畫作一無所知的露絲,特意去圖書館查閱資料,“她看到乞丐新娘那欲說還休的順從,那種無助和感激。這就是帕特里克心目中的露絲嗎?這就是她會成為的人嗎?”即便如此,她也不能拒絕他,因為她無法忽視的是那一堆愛,還有來自她那個階層的人的羨慕的眼光。露絲要經常說服自己,這個男人帥氣,是研究生,有學問。對帕特里克勉為其難的接納,其實就是對一個更高階層符號的向往。帕特里克最終也只是淪為一個閃亮的象征符號,這段愛情是她夢想的東西,卻不是她想要的東西。國王和乞丐女的傳說正是帕特里克和露絲之間關系的投射,在乞丐新娘皆大歡喜的結局背后,掩藏著階級和身份多重復雜的社會現象。
在一個基于財富標準界定階級性的社會,“乞丐女”就是一個被凝視的客體,這是經濟上羸弱而個性獨立的露絲不情愿接受的角色分配。于是,帕特里克對露絲的癡迷成就了她的掌控力,她戲弄他、傷害他,讓他心醉又讓他心碎,僅僅是為了想試驗自己對其生殺予奪的權力。而露絲已經逐漸習慣去分享帕特里克所擁有的階層光環給她帶來的炫耀資本,她發現失去了帕特里克的愛,自己并沒有多少機會和選擇的權力。經歷一番周折以后,露絲主動和好,并走入婚姻殿堂。門羅表達了露絲對自由的向往和對現實的妥協,這種矛盾在加拿大社會底層的女孩身上對立又融合地呈現。在門羅的小說中,起初滿懷抗爭精神的女性往往會最終妥協于現實的無奈,因為對她們而言,“幾乎沒有什么可期待和追求的,根深蒂固的悲觀是他們最后的智慧”。
(三)底層階級女孩
20世紀70年代,與丈夫分居隨后離婚的門羅開始對這種階級差異進行深刻反思,創作了一系列的身處富人階層的丈夫和未婚夫的形象,就像《乞丐新娘》中的帕特里克對露絲的家人和朋友表現出來的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即便是努力遷就和容忍階級差異,也不時會流露出一副屈尊服就的態度。在與帕特里克的交往中,露絲時常為自己所在的階層辯護,為特權階層對底層民眾的不理解和不尊重而深感憎惡。
處于兩個不同階層的情侶別別扭扭地糾纏在一起,一切都叫人難堪,充滿了不祥之感。露絲和帕特里克這兩個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年輕人走到一起,十年后婚姻解體。
十年婚姻,帕特里克和露絲發生爭執、和好又分手的場景一遍一遍重復,直到露絲找到第一份工作才正式分開。離婚九年之后,露絲成為家喻戶曉的新聞界名流。有一次深夜在多倫多機場,露絲偶遇帕特里克,“她一下子就認出了他。她又有了那種同樣的感覺:這是她注定要在一起的那個人……”而他對她做了一個表情,是真切的痛恨,是兇狠的警告。“但是她并沒有真正理解……為什么有人會這么恨她呢?哦,帕特里克會的。”階層門第的差異帶來的隔閡和傷口,永難彌合。對于來自社會底層的露絲,從“獎學金女孩”的身份定位向“乞丐女”轉變過程中,她不斷承受著心理矛盾與妥協。當露絲舍棄小鎮方言時,就意味著與自己的出身和階層決裂,但想盡力融入社會上層階級最終失敗,自己成了文化層面和階級層面的“蝙蝠”。門羅出身寒微,通過婚姻躋身中產階級。她的作品多展現底層女性對貧窮的恐懼,對舒適生活的向往。而在一個充斥著等級差異和貧富差異的社會,這些女性的成長之路必然坎坷,門羅對社會階層劃分帶來的種種身份困境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鞭撻。
“約翰娜·希金斯在分析《乞丐新娘》中的階層問題時,指出露絲的階層和其性格之間的關系,認為露絲的生活是 ‘一個試圖尋找歸屬、建立溝通和彌合差異的漫長歷程’”。露絲為情感掙扎,被生活改變,卻依然堅持對自我的追尋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門羅筆下的底層女性,偏離了傳統的“乞丐新娘”和“灰姑娘”的婚姻救贖模式,批判了階級意識中普遍存在的男權中心思想,凸顯了門羅作品中的身份和階層屬性。小說中的露絲,也和門羅本人一樣,最終走出了不幸婚姻的陰霾,成了職業作家,回到了家鄉,從而完成了對個人身份的重構。
三、結語
門羅在《乞丐新娘》中的寫作呈現了在加拿大社會現實中貧富差異和階級差異的關切。將讀者引入文本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對話中,剖析女主人公多重身份困境和抗爭,深刻思考加拿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