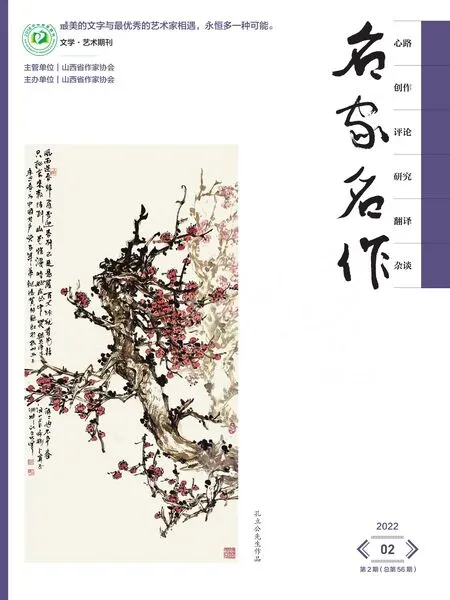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蠅王》成長主題下的悲觀意識書寫
褚金莉子
“成長”主題作為西方敘事文學的一個傳統,在文學創作中經久不衰,其作為人類經驗的豐富集合,成為文學家藝術創作的寶庫。此外,戈爾丁于198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大受關注,因作品充滿黑暗色彩,批評界給戈爾丁冠上了“悲觀主義者”的名號,但作家本人拒絕認領此稱謂,他將自己稱為“對人類微笑的人”,戈爾丁作品的情感傾向成了批評界莫衷一是的懸案。本文將分析《蠅王》的成長主題,探討戈爾丁辯證的悲觀意識。
一、悲觀意識的形成原因
(一)歷史語境
《蠅王》陰郁消極的底色與時代密切相關。戈爾丁正式創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兩次世界大戰,納粹的極權主義,大規模的人種滅絕以及科學理性主義的破產,給西方人造成了普遍的精神創傷,傳統價值體系中關于是非、善惡、正邪的基本要素變得模糊不清,因此戰爭結束后彌漫在西方知識分子心中的是濃重的悲觀氣氛,蜂涌的后現代“非理性”思潮取代了窮途末路的理性信仰,構成了戈爾丁悲觀意識的客觀基礎。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戈爾丁在英國海軍服役,親眼目睹人類在戰爭中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后,戈爾丁改變了從前的樂觀主義,他相信邪惡來自人的內心深處,而不僅是社會的壓力。如果說戰前的他是一個擁護傳統人文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那戰爭的結果則使戈爾丁及同齡的一代歐洲人對現實的想法被徹底改變,人通過切實可行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使人類發展到一個完美階段的想法是簡單幼稚的,這種信仰已經一去不復返,戈爾丁更加成熟地思考起人的境遇和存在本質。
(二)個人經歷
除戰爭催生的悲觀情緒之外,年輕時的任教經歷也使他對人性幽微有了不一樣的洞察。通過長時間近距離地觀察,他發現與印象中的“純潔無瑕”不同,兒童身上具有驚人的邪惡,高年級學生對不服從他們的低年級學生經常拳打腳踢、恃強凌弱并且樂在其中,撒謊、打架等不文明行為更是時常發生。戈爾丁意識到如果沒有教師和學校制度的約束,孩子會做出更多野蠻行為,由此更進一步認識到,邪惡也是人與生俱來的,失去文明限制后,邪惡會不斷膨脹,最終造成巨大破壞。他認真思考起人類悲劇的本源,最后得出結論:人具有邪惡的本性,而作家的責任是追溯其病態,在尋求一種藝術形式將其闡釋后,他決定用小男孩荒島成長這個常見的敘事模式來表現自己的思考結果。
二、《蠅王》成長主題的呈現
(一)《蠅王》的成長主題書寫
“成長”敘事在結構上經常呈現出一定的模式化傾向,如青少年經歷考驗后頓悟,最后得以認識人生和自我,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個失去天真的過程。成長小說多具有此模式,或在此基礎上變異。該模式在《蠅王》主人公拉爾夫身上體現得最明確。拉爾夫最初來到島上時感到一陣快意,因為逃離了家庭,此時他天真懵懂,充滿幻想,但很快便迎來了生存“考驗”。沒有成年人的指導和保護,飲食起居和求救成為一個巨大問題。拉爾夫自覺擔任領導者的角色,企圖在孩子中建立文明秩序,然而自己號召的所有行動均告失敗,其秩序又遭到以杰克為代表的集團的沖擊,這是拉爾夫在現實中首次遭受挫折。隨后其思想發生轉變的一個關鍵情節是西蒙之死,在肉的誘惑下,拉爾夫參加了杰克一伙人的篝火宴會,吃完肉之后由于對雷電的恐懼和施暴欲的鼓動,孩子們激動地跳起舞來,拉爾夫也加入了狂舞,在暴雨夜里他們沒有認出從森林里走出的西蒙,反而把他當作一直以來害怕的“怪物”,混亂中將他打死。事后拉爾夫沒有勇氣承認自己成為幫兇的事實,這是其思想產生混亂的開始,死亡和人性的黑暗有力地打擊了拉爾夫尚顯稚嫩的自我,與他純潔的心理預期產生了激烈碰撞。混亂、暴力和難以抑制的食肉欲將拉爾夫裹挾而去,這時的拉爾夫被困惑震撼了,他不得不重新審視自我,直面現實。
拉爾夫的“頓悟”則源于自己被追殺,最后失去了所有盟友的拉爾夫在荒島上被追趕得四處逃竄,在逃跑過程中他遇到了具象化的“蠅王”——被獻祭的豬頭,腐爛的、散發惡臭的豬頭被孤零零地串在兩頭削尖的木棍上,冰冷地凝視拉爾夫,拉爾夫憤怒地捶向它,豬頭仍一動不動地瞪著他,拉爾夫終于明白自己是個被遺棄的人,是一個被同伴追殺且無路可走的人,他意識到人性之惡就像地上的豬頭一樣,永遠消滅不了,面對人類發出永恒的嘲笑。最后遇到海軍軍官,即將獲救的拉爾夫發出孩子的哭聲,荒島短暫的生活像一個黑色的荒誕不經的夢,可是西蒙、豬仔和其他孩子不會再醒來,成長帶來的巨大創傷永遠留在拉爾夫的內心深處。
(二)對傳統成長主題的顛覆
《蠅王》對傳統成長主題的顛覆體現在其對理性主義內涵的消解。傳統西方成長小說注重成長的塑造作用,通常表現為“最黑的夜,最亮的光”這種模式,人物由搖擺走向堅定、從混亂走向明確,最后品格完善,彰顯人文精神,可以說成長書寫最終將導向這種結局。杰克的刻畫顛覆了傳統,通過對比,可以看到拉爾夫的成長經歷了明顯的“頓悟”,小說結尾他面對燃燒的島嶼失聲痛哭,安全穩固的童年時代在了解世界和人性的癲狂后結束,自我得到更新,可以說這是其成長的結果。然而回到文明世界的拉爾夫又將如何是小說的開放性結局,而且小說情節里尸體從天而降的不祥,也不同于虛擬世界的機械降神,在現實中是真實發生的,因此回去的拉爾夫面對的只能是一個更殘酷、更無情的世界,他的淚水只是文學家借虛擬人物的雙目流露出的無能為力的悲痛,這是《蠅王》悲觀主義的一面。
杰克形象更鮮明地流露出作家的失望,他代表了人類理性的喪失和失控的暴力,在小說中杰克的性格變化表現為不斷地墮落,拉爾夫的成長尚可以看見“頓悟”和覺醒后的痛苦,杰克的成長則不存在轉變,他和自己帶領的唱詩班成員最初還能和其他孩子和平共處,后來因沒有規則和秩序的束縛,便整日沉迷于血腥的打獵和殺戮,將文明拋到了腦后。小說極其細致地描寫了杰克一伙宰殺野豬的過程,其殘酷手段襯托出人性的兇狠,這是杰克喪失理性的開始。“涂面具”是杰克性格轉化的又一個關鍵點,戈爾丁寫“他發出一種‘嗜血的狼嗓’的笑聲,躲在面具后擺脫了羞恥感和自我意識”。
三、成長主題書寫的意義
戈爾丁雖然描繪了一個黑色和絕望的世界,但沒有放棄希望,西蒙是《蠅王》黑暗世界里的光明,是善與愛的化身,西蒙之愛等于神之愛,是戈爾丁小說的寬恕一切的希望。西蒙的善良發自內心,他支持拉爾夫的統治,維護海螺的權威,在豬仔遭到嘲笑時為他辯護。此外,西蒙性格無私,在其他孩子都膽怯時,爬上孤巖摘最高處的野果分給他們,在豬仔沒有肉時,把自己的分享給他吃。另外,戈爾丁還將耶穌的受難特征加諸他,賦予西蒙以救贖意義。戈爾丁稱他在《蠅王》中放入了一個像基督那樣的人物,他講話結巴,孤零零的;熱愛人類,是個喜歡幻想的人。如《新約》中神將自己的獨生子賜予世人,也印證了西蒙形象的神性特質,使他在小說中象征拯救,如同為背負凡人之罪被釘上十字架的耶穌,承擔起自我犧牲的命運。雖然西蒙的成長因為死亡終止了,但其成長也經歷過轉折,當西蒙的癲癇病發作時曾在頭腦中與蠅王對話,蠅王引誘西蒙和其他孩子一起丟棄人性、墮落為獸,他稱自己掉入巨大的、漆黑的嘴巴里,墜入黑洞。一方面是因為物理上的發熱而昏迷,另一方面是一種被罪惡吞噬的隱喻,但是西蒙沒有就此沉淪,反而在醒來之后帶著“怪物”之謎的謎底返回孩子中,想打消他們的恐懼,不料孩子竟在狂亂的錯覺中將他當成怪物殺死。西蒙經歷邪惡的誘惑而沒有屈服,是《蠅王》成長書寫中唯一一個保持住堅定人性的人,他寄托了戈爾丁對人類未來的希望,表達了戈爾丁的道德追求。
四、結語
戈爾丁在《蠅王》中抽離一切社會和文明因素,讓兒童經歷失敗的成長,使作品充滿黑暗色彩,因此不少評論家稱其為一個對人類及其未來不信任的“悲觀主義者”。但戈爾丁曾在訪談中明確表示,雖然自己不知道具體用什么方法來實現,但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由此可見戈爾丁對人性的悲劇敘事絕不是為了激起悲觀情緒,相反則是想起到療救作用,希望通過揭露人對自身罪惡的無知,積極探索出重建人性的道路。對于人類,他或許是憎恨的,但卻不愛看他們墮落,這樣來評價戈爾丁的情感立場或許更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