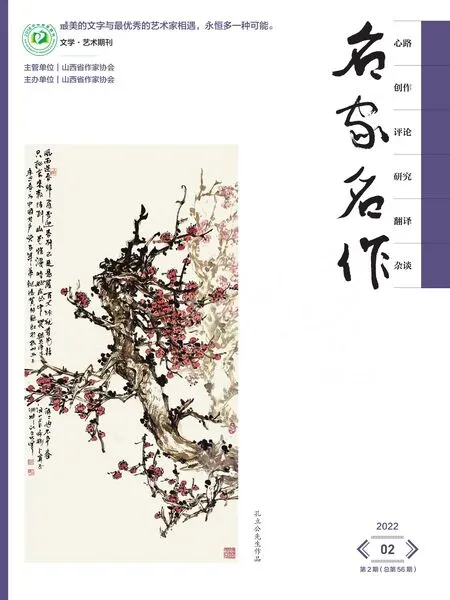原生家庭陰影下的精神創傷
——解讀《可愛的骨頭》中的哈維
王思懿
一、引言
《可愛的骨頭》是美國當代女作家艾麗斯·西伯德的小說處女作,小說于2002年出版后便立刻引起巨大反響,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近30周,連續在榜70余周,獲得了“美國年度最佳小說獎”和“英國年度好書大獎”等榮譽。書評界對該小說也是贊嘆不斷,《紐約客》評論該書為“驚人的成就”。目前該小說有英、法、日、中等版本且風靡各國,銷量已突破1000萬冊。艾麗斯·西伯德也被美國媒體稱贊為“最具潛力作家”。
小說講述了活潑可愛的14歲少女蘇茜遭鄰居哈維奸殺肢解后,靈魂升入天堂,在天堂觀看了家人、同學好友、警察甚至兇手十年來的生活與變化,目睹了親人面對突發慘劇所經歷的崩潰絕望、逃避分離和和解的過程。國內對于這本小說的研究并不多,且都聚焦在蘇茜一家人身上,而對于喬治·哈維這一角色未予以足夠重視,僅將他看作是殺害蘇茜的兇手,并沒有對他進行深入研究。而事實上,作為小說中唯一的反面人物,哈維同樣有著重大的文本意義。他不僅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本文則將關注點聚焦在哈維身上,探究其扭曲人格形成的原因,從而對其有更全面的認知。
二、原生家庭的陰影帶來的精神創傷
創傷理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精神病臨床領域向歷史、哲學、文學批評等人文領域擴展,將它與文學研究結合已成為文學批評的流行趨勢。創傷一詞源自希臘語,本意是外力給人身體造成的物理性損傷。后指某種外部力量造成的身體或心理損傷。通常,人們將這種外部力量稱之為“生活事件”。通過對哈維童年成長經歷斷斷續續的描述,我們可了解到哈維的原生家庭是極其不幸的。家庭系統理論認為,家庭是一個有機的情緒整體,其中每位成員的行為都會影響系統中的其他成員,個人的行為與情感必須放在家庭的語境中方能解讀。原生家庭不幸是后來哈維心理扭曲,成為殺人魔的重要誘因之一。
哈維的父親在小說中并沒有被大量提到,但從寥寥數語中,一個粗暴蠻橫的典型父權形象躍然紙上。父親經常喝得酩酊大醉,沒有固定的工作,有時“在沙漠里工作,用碎玻璃和舊木頭蓋些簡陋的小屋子”,有時“在德州的一個地方打零工,靠雙手拆木板”。整個家也是隨著父親的工作變動,他們沒有固定的住處,“從小到大,他搬了太多次家,他以為女孩和他一樣居無定所”。父親在家里有絕對的地位,對待母親和哈維很不客氣,就像哈維經常想起父親斥責母親:“你比我們兒子好不到哪里去。”對于他們母子而言,從老哈維身邊偷溜出來,開車到隔壁鎮上買食物雜貨便是解脫;此外,哈維很少能得到父親的關注,哈維初次對女孩施暴后,在自己手背上劃了一道口子,他想如果父親問起身上的血跡,就可以以割傷手作為借口,“但他爸爸什么都沒問,也沒有人找他興師問罪”。哈維長期生活在這種缺乏父愛,而且遭受來自父親的冷暴力和精神欺凌的家庭里,可以說是在經歷一種“細水長流”的災難。
對于童年的哈維而言,母親是他唯一的依靠。但神經錯亂的母親并未履行一個合格母親的職責,反而加劇了哈維的心理扭曲。哈維母親也沒有固定收入,僅靠帶著小哈維撿破爛來掙錢。后來母親開始偷商店里的東西,起初沒有被逮到的時候是她最幸福的歲月;當他們母子第一次被逮到時,店員小姐看在8歲小哈維的面子上,很客氣地放過了他們。但此后,哈維就產生了很大的陰影,他“一想到被人識破,他的胃部就像碗里被攪拌的雞蛋一樣翻騰,非常不舒服”。后來,母親開始利用他人的同情帶著小哈維偷竊,她會把贓物交給他,讓他藏在衣服里;事后,母親會坐在車里神經錯亂般地大笑,雙手猛力敲打方向盤,狂贊哈維是她的小同謀。哈維在那時已經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感覺到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錯的,但是為了能完成母親的交代,他選擇順從。因為“在母親的笑聲中,他心中確實了無牽掛,內心充滿溫暖,感到非常自由自在”。更有甚者,母親把發財的機會投向墓地,他成年后還記得母親對他的教導:你不要光看死人和墳墓,眼界放寬一些,有時候從他們身邊拿走些可愛的小東西也沒什么大不了。這句話對哈維的影響很大,以至于他總喜歡從受害女性身上取下來一些小物件作為紀念品,他覺得這樣能感覺到母親的溫暖。母親給哈維灌輸的扭曲的價值觀,直接影響了他心理的正常發展,為后來他的悲劇人生埋下了伏筆。
創傷理論始于20世紀90年代,這一術語由美國學者凱茜·卡魯斯在其著作《沉默的經驗》(Unclaimed Experience)中首先提出。她將創傷定義為“對某一突發性或災難性事件的一次極不尋常的經歷”。細讀《可愛的骨頭》,哈維的童年所遭遇的兩件突發事件給他留下了極大的陰影。一次是母親開車撞人事件:哈維和母親像往常一樣睡在卡車里,半夜時,有三個醉酒的男人猛敲車頂并且虎視眈眈地盯著他母親,哈維縮在毛毯下瑟瑟發抖。母親讓哈維扭動車鑰匙,發動引擎,哈維雖然不知道母親要做什么,但因為她的迫切,哈維照做了。后來母親突然加速,“卡車猛然撞向站在幾英尺之外的男人,哈維蜷伏在車里,清楚地感覺到車子的沖擊力。男人被撞得飛到車頂,母親很快再度倒車,把男人甩在地上。在那個時刻,他清楚地領悟到該怎么生活:不是身為女人和小孩生活,女人和小孩總是處在最差的情況中。”這次恐怖的經歷使哈維明白:婦女和小孩處在社會的底層,他們很少有選擇且最容易受到攻擊。這也是后來哈維總是找兒童婦女下手的原因。
另一件事則是母親的離開。作者通過蘇茜的全知視角,再現了當時的情景:最后一次見到他母親時,老哈維夫妻二人在去往新墨西哥州郊外的途中發生了爭執,父親把母親拉出車外,母親這時拋下了與她“同一條戰線上的”哈維,選擇了逃跑,小哈維看著母親瘦弱遠去的背影,緊握著母親從脖子上扯下的琥珀,聽著父親對他說她走了,永遠不會回來了,“像石頭一樣呆坐在后座,他睜大眼睛,心里沒有一絲害怕的感覺,周圍的事情如慢動作一般發生”。母親可以說是哈維黯淡童年的唯一光源,是唯一能獲得愛的地方。相依為命的母親選擇拋下他獨自離開,哈維深感背叛,完整的家也不復存在,這種缺失給哈維帶來巨大的陰影。對于年幼的兒童來說,與父母分裂或喪失父母意味著依戀關系的破壞,而依戀關系對年幼兒童具有生存意義。分離一直被看作是童年時期重要的創傷事件。小說中雖然沒有對青少年時期的哈維進行敘述,但是通過周圍鄰居對成年哈維的描述:不太正常,是個怪人,可以發現哈維在這樣的生活背景下,已經將自己完全封閉,行為和性格都發生極大改變。母親一身潔白素凈,在公路旁的田野上奔跑的場景總會出現在他的夢中,這是創傷后應激障礙的典型特征:在侵入記憶(閃回)、睡夢中反復再現創傷場面,受害者感到恐懼無助等,這些癥狀在哈維身上都有體現,無時無刻不纏繞著他的心靈,造成心理創傷。
如果說上述提到的哈維父母所營造的家庭環境對哈維來說是“細水流長”式的災難,那么母親撞人和離開這兩件突發事件可以說對哈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傷。冷漠粗暴的父親、神經錯亂的母親以及破碎的家庭對哈維的情感經驗學習產生了惡劣影響,持續阻礙了其人格形成和正常情感模式及人際關系的建立,最終誘發了他的人生悲劇。
三、精神創傷引發的人生悲劇
正如上文提到,哈維的精神創傷追根溯源來自他的原生家庭。根據Bowen家庭系統理論,個人過去在原生家庭中與父母的關系模式,將持續影響其未來的重要人際關系。凱西·卡魯斯在她的創傷理論中也提到,人們對創傷事件的反應具有延遲性,災難將會在人們的內心留下創傷,但心理創傷不會出現在災難發生時,而是在災難發生后的某段時間。災難會在受害者的心里留下陰影和傷害,影響未來的生活。對于受創者而言,甚至連生存本身都有可能變成一場危機。親情的缺失仿佛在哈維和外部世界間設置了屏障,使成年后的哈維無法與他人交流,他變得敏感孤立。在鄰居眼中,他是“怪人”,從不參加小區里的任何活動。除了日常采買,幾乎不出家門,“他最常待在一樓后面的房間里,不是在廚房糊玩具屋,就是在客廳聽收音機。色欲浮上心頭時,他就畫些地洞、帳篷之類的建筑物”。哈維以建造玩具屋為生,并且小說中有哈維在寒冷的戶外,近似瘋狂地搭建“新娘帳篷”的片段,這都是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童年生活給哈維心理留下的陰影。他對房子有著超乎常人的依戀,其實是內心對于安全感、對于家庭的瘋狂渴望。小時候親眼目睹母親撞死人后,哈維對待殺人有著異常的興奮,他每次作案前都會進行周密的計劃,比如他會費盡周折挖地窖去引誘蘇茜;作案后為洗清嫌疑,他會定好幾個鬧鐘提醒自己何時拉開、關閉窗簾,何時熄燈;面對警察的盤問,能冷靜地說出“我很抱歉”;必須親自仔細編排每樣東西,才覺得安心,“他作案越來越得心應手,每次都出新招,連他自己都想不到,每次犯案都像送給自己一個令人驚喜的禮物”。這種變態心理常常吞噬哈維的理智。
弗洛伊德指出,有創傷經歷的患者傾向于不斷重溫痛苦的情緒。比如,會在夢中不斷反復夢見經歷過的創傷性事件。目睹母親的離開可以說是哈維一生的夢魘。當母親被惡棍侮辱和被父親趕走時,小哈維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自己的命運。長大后的哈維試圖通過殺戮來彌補過去的軟弱來證明自己的控制力。只有暴力和權威才能給他安全感,才能緩解以往創傷帶給他的恐懼和焦慮感。母親的離去讓哈維失去了唯一的愛,他則想通過控制受害者來彌補他的缺失。這也是哈維每次選擇弱小的女童下手的原因之一,也是在殺死蘇茜前,逼她說出“我愛你”的理由。
哈維不僅敏感,缺乏安全感和愛,同時也是個矛盾體,具有雙重人格。艾麗斯·西伯德在刻畫哈維變態殺人魔形象時,也在細微之處體現了他“人”的一面。例如,有一陣子附近街區頻傳寵物丟失的消息,所有人都認為一定和社區里的小霸王喬有關,但真兇實際是哈維。他將石灰撒在動物的尸體上,通過看動物白骨來遏制自己的獸欲,讀到這里,我們難免會更加認證哈維的扭曲變態,但作者便在下面借蘇茜的口吻提道:“每次一有沖動,他都試圖控制自己。他殺害小動物,為的就是犧牲一些比較沒有價值的生命,借此阻止自己出手殘害孩童”。只有數著這些白骨,他才能遏制這些沖動。哈維那殘存的人性也反映在他的夢中。他曾三個月一直夢到來勢洶洶的洪水將房屋一瞬間吞噬;“但他最常夢見的是沃洛格達的‘圣主變容大教堂’。謀殺我的那天晚上,這座他最喜歡的教堂就出現在夢中。隨后他夜復一夜地夢見那座教堂,直到夢境中再次出現那些女人和小孩”。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第三章中以“夢是欲望的滿足者”為標題,指出“夢完全是一種心理現象,是一種欲望的滿足”。哈維近三個月夢到房屋被吞噬,這其實是一個重復創傷性夢境,哈維經歷了一個無家可歸的童年,他極度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洪水把房屋吞噬表現了他內心無盡的恐懼,他害怕自己被抓而再度喪失庇護所。此外,他最常夢到的是“圣主變容大教堂”,這個教堂是俄羅斯基濟島上最大的建筑。教堂一般是人要懺悔或尋求救贖的地方。這個教堂最常出現在哈維的夢中,說明哈維在潛意識里是想要坦白罪過,求主饒恕的。或許哈維并非完全泯滅人性,他潛意識里知道自己的罪過,但無法控制自己魔鬼般的欲望。他將自己孤立在社會中,無法也不愿向他人尋求幫助,只能讓無盡的欲望將他一步步推向深淵。
四、結語
哈維是《可愛的骨頭》中唯一的反面人物,同樣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悲劇式人物。艾麗斯·西伯德在這個人物的設置上,體現了她特有的人文關懷。他可以說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物,因為蘇茜一家的不幸都是因他而起。但是縱觀哈維的成長歷程,他也是不幸原生家庭的受害者,一生都在缺少愛與關心的環境中孤獨生活。其他人物幾乎都從創傷中復原,唯有哈維越陷越深。艾麗斯·西伯德沒有將小說結尾設置成哈維被繩之以法的大快人心的結局,而是以跌進溪谷意外死亡而結束,體現了寬恕的主題思想,也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道德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