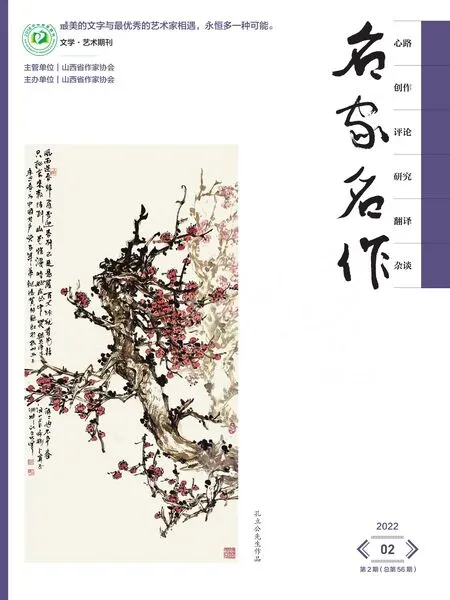淺析辛稼軒詞中的“劍”意象
朱袁婷
縱觀辛棄疾的詩詞,“劍”成為詞人聯系現實和人生理想的紐帶,做到了真正的“人劍合一”。“劍”作為詩人情感的載體,承載著的不僅有夢中的劍影,更有拳拳愛國之心。詞人筆下賦予劍再多的內涵,都抵不過劍刃流光戰場風沙翻過的剎那,心血之句,寄托了詞人多少淚與恨的渴望——國與家!
一、“劍”意象的內涵及分類
在辛棄疾的詞中,“劍”的意象多次出現,據鄙見,按照它的客觀存在性姑且將之分為實與虛兩類。
劍作為一種實指之物,在詞中的實際指向是現實的真物。詞人在真實的劍中融入情感與理性,作為一種意象在詞中傳達其獨特的記憶和經歷。青年時參與耿京起義,創飛虎軍,想來必有寶劍系腰。劍作為實際物品最基本的功用是正當防衛,辛棄疾將拔劍出鞘那剎的感受熔鑄到“劍”意象之中并通過劍本身帶有的藝術性寫入詞中。辛棄疾一生都渴望光復故土,洗去被金軍侵略的恥辱。“漢中開漢業,問此地,是耶非。想劍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戰東歸。” (《木蘭花慢·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 此詞描寫的是辛棄疾在追憶劉邦當年從漢中率軍出發,直指關中,把踞守關中的秦的三將章邯、司馬欣和董翳相繼擊潰的往事,同時也在回憶自己劍下的風刃,在驚羨三將的同時,也在無奈如今的朝堂一派文恬武嬉,國勢衰微,萎靡不振。知敵軍入侵之時,辛棄疾被國家流放,滿腔的熱血按捺不住手中之劍,化筆為劍墨灑詞場。懷古與傷今渾然一體,此處的“劍”是三將手中一揮指三軍的權威熱血之劍,是辛棄疾在回憶曾經血戰沙場時振臂一呼的劍,更象征著詞人心中被激起的平生報國之志。
劍亦為虛指之劍,即辛棄疾心中之劍。劍中蘊含的熱血和風雨只有親歷感受才能寫出情韻,才會產生國破與復國之間的情感落差和張力。手中空握殺敵之劍,卻離戰場越來越遠,只能與山水對飲,獨自舞劍,這是詞人南渡之后的現實。“笑吾廬、門掩草、徑封苔。未應兩手無用,要把蟹螯杯。說劍論詩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水調歌頭·白日射金闕》)此詞上闋在用周邦彥典故安慰友人,有才干的人終究會發跡,下闋便以說劍論詩,慨言武備文事。辛棄疾的《美芹十論》中曾提及自己對說論的看法“文韜武略都是無用的‘余事’”。無用的說理,只有在無事閑談中才會經常出現強作豁達。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壓抑感、壯懷激烈而無人理解的孤獨感和年華虛度的失落感交織于胸,怎能不讓詞人狂歌醉舞,哀從中來?寄予詞以“說劍”而非“用劍”,媚化本質的剛性,抹逝其功用,讓它和詞人都終身不見沙場征戰,即使是在詞中也是奢望,在悲劇性的層面上將詞和詞人的情感上升到感慨人生無常的境界。“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詞中回顧了當年在山東和耿京一起領導義軍抗擊金兵的情形,詞中壯烈和悲涼、理想和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就這樣快要溢出的滿腔熱血,也只能在詞中借夢中之劍聊以抒懷。“夢連環,歌彈鋏,賦登樓。黃雞白酒,君去村社一番秋。長劍倚天誰問,夷甫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此事君自了,千古一扁舟。”(《水調歌頭·送楊民瞻》)“歌彈鋏”三字笑中藏淚,本來應該用來戰場殺敵為國的長劍,卻被用來彈擊和歌、吟唱風月。
二、“劍”意象的獨特意義
劍于稼軒是何意義?是什么樣的執著讓夢中的世界都充滿了刀光劍影,甚至寧愿長睡不起?
辛棄疾的性格、氣質顯然屬于“陽剛”的典型,擁有天賦異稟的陽剛之氣。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 (陳亮《辛稼軒畫像贊》) “精神此老健于虎,紅頰白須雙眼青。”(劉過《呈稼軒詩》)叛變分子義端被辛棄疾追獲時,曾向辛棄疾求饒說:“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更有黃幹《勉齋集》中稱贊辛棄疾:“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真一世之雄也。”可是天命也真是殘忍,給予才能卻無法施展,徒讓氣與魄漸行分離……曹丕在《典論·論文》中云:“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暫且不談清濁陰陽,氣于文章之形早在魏晉南北朝甚至更早便有明確說明。后劉勰《文心雕龍》中也提及:“才有庸俊,氣有剛柔。”“風趣剛柔,寧或改其趣。”辛老擁有無數文人羨慕的先天浩然正氣,其在化氣運劍時,不僅帶動了后代武將,更是運起后代豪放詩人的心中熱血。
劉克莊先生在他的《后村詩話》中評價辛老的作品:“大聲鏜鎝,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秾麗綿密處,亦不在小晏、秦郎下。”不僅風格多樣,而且能夠調動各種藝術手法抒發他胸中的真氣、奇氣,完美做到了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 “其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干青云之概。”
辛棄疾的思想受多方面的影響:老莊之道,儒家參透,佛理玄思,這些豐富而各異的思想對辛老而言,無非是疏導其出仕與入仕的手段。有人可能否認后期辛棄疾歸隱后對朝廷的留念,我想引用魯迅先生在《草七》中所說的:“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詞人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同是豪放派的蘇軾,雖然詞風有相似之處,但二位的思想卻不相同。蘇軾的詞更見放曠飄逸,是能夠超脫的。而辛棄疾要想忘世卻不能忘世,欲求超脫而難以超脫。
三、藝術特色的渲染效果
辛棄疾使用的“劍”意象,突破性的想象與創造和他天生對藝術的把握有關。“劍”意象的使用大大提升了辛棄疾詞中的審美、實用和創新的價值。
辛棄疾詞中“劍”意象的使用突破傳統意象,擴大了詞的審美范疇,為其藝術成就更添一筆。宋前的花間詞的題材在詞人中頗為流行,傷春悲秋、兒女情長、閨房繡戶、秦樓楚館等女性化的意象幾乎成為詞人的集體無意識選擇,這是詞自晚唐五代以來的基本格局。雖然在張先、柳永處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卻沒有成為體系,同時沒有實際開闊的經歷支撐,僅僅是骨架鮮明,沒有久經沙場的血肉填充。而辛棄疾是經歷過戰場的詩人,那份豪情和壯志不自覺地融入他的氣質中無法消抹,這樣自然而然地體現在詩詞的意象上。在辛棄疾的詞中,馬、劍和戰場等意象的使用與先前的花間詞風形成鮮明對比,為后代的審美和題材開拓做出重要貢獻。
在跳脫審美范式的同時,“劍”意象的使用為其豪放大氣的詞增加一抹亮色,成為后世學習的典范,具有啟發和思考的意義。但由于辛棄疾本人特殊的藝術與情感天賦,后人學起來并不是非常容易。再加上同時摒棄后人的形式主義之風,使得后世崇拜敬仰之下只能望其項背。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寫道:“后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并無其情。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后人萬不能及。”這放在如今同樣發人深思。真正純熟的天才,往往擁有個性,不會被眾生消解,反而可以在時代的變遷下愈淘愈新。
辛棄疾的婉約風格并不像一般的婉約派詞人那么柔婉和局限,沒有自怨自艾、顧影自憐的閨中哀怨,而是含蓄深沉地表達壯志難酬的抑郁之情,因此是婉約中透豪放,豪放中有婉約,在豪放中蘊含著婉約的情思。疊字是婉約詞人特別愛使用的語言技巧,辛棄疾同樣在他的詞中多次使用疊詞。在辛棄疾的詞作中,“年年”是運用最為頻繁的疊字。此外,諸如《踏莎行》:“吾道悠悠,憂心悄悄。最無聊處秋光到。西風林外有啼鴉,斜陽山下多衰草。長憶商山,當年四老。塵埃也走咸陽道。為誰書便幡然,至今此意無人曉。”更有如“溪上青青草”“易水蕭蕭西風冷”“爭先見面重重”“更草草離筵”“煙雨濛濛”等等,這不僅在音律上增加了辛棄疾詞中婉約的情調,更在句式上給他的詞帶來一個突破,詞性張力盡顯。
四、結語
王國維先生曾在《宋元戲曲考戲》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稼軒縱是未能平生舞劍沙場,卻是于失意處造就了文學藝術的新“劍”術。即使劍與人被夢想流放,仍在胸中開出文學之花。先生之劍,可謂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