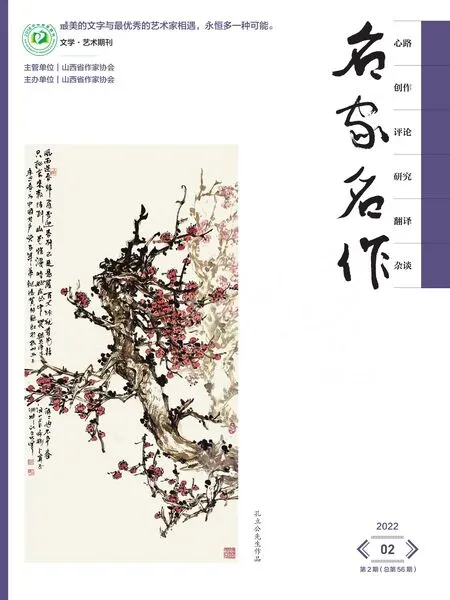當代陜西外國文學研究的傳承與創新
——以代表性學者為例
劉一靜 惠 欣 王思雨
外國文學研究是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邁入快速發展階段,怎樣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史新模式成為學界關注的主要問題。新時期以來,陜西外國文學研究與學科建設逐漸取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學術資源更加豐厚,理論視野更為寬廣,研究方法也愈加多樣。陜西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們在對傳統的文學研究范式進行傳承的同時,也緊跟時代步伐,關注學界前沿問題,以創新精神走出了風景各異的學術研究道路。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成果豐厚的今天,也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如何進一步建設好外國文學研究這一學科,如何進行外國文學研究的傳承與創新,值得當代陜西外國文學研究者傾力思考。
一、煥發生機的外國文學研究
1978年12月,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成立,標志著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工作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1980年11月,陜西省外國文學學會正式成立,匯聚了一批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在陜專家學者,陜西外國文學研究自此也正式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老一輩陜西學者緊扣時代脈搏,重新把握文學與政治的正確關系,將文學研究歷史觀點和美學觀點相統一,采用多樣化方法展開文學研究。
馬家駿教授聚焦蘇俄文學,出版了相關專著,并參與編撰了一系列外國文學教材,發表了多篇關于有關外國文學教學經驗的文章。雷成德教授深耕蘇俄文學,積極開展譯介學研究,創作了一批超越文本和翻譯技巧且具有一定理論深度的蘇俄文學理論譯本。陜西省外國文學學會第一任會長周駿章關注英法德文學,發表了一系列富有介紹性和針對性的評述文章。張成柱將自身對法國當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評介同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緊密結合,為當時的文學譯介提供了有效指導。曹汾密切關注日本文學領域,并對唐代中日文學藝術交流方面的問題展開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該時期,陜西省外國文學研究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蘇俄文學研究在彼時陜西省的外國文學研究中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馬家駿、雷成德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極為注重蘇俄文學譯介,對大量蘇俄文學作品展開詳細介紹,強調文學研究的現實功用色彩。雷成德譯介了一系列蘇俄文學作品及理論研究書籍,促進了蘇俄文學研究的繁榮。20世紀80年代初,馬家駿先生意識到國內推出新的普希金代表作《奧涅金》譯本指日可待,便著手重新推敲當時最受歡迎的查良錚版《奧涅金》譯本中的相關細節,并就該譯本中同作者本意存在出入或意圖不符之處的相關內容展開探討,以推動蘇俄文學研究領域內譯介學的發展。
第二,陜西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們積極擴展外國文學研究的范圍,把握文學史上多個重要流派,關注傳統文學以外的重要作家及其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優秀作品,在學術著作方面取得了初步進展后,進而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效突破了既往外國文學研究的一系列禁區。他們依托陜西省外國文學學會這一平臺,加強自身與其他在陜外國文學研究者之間的交流與對話,使陜西省外國文學研究向著全方位、全領域的方向快步前進,并取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
第三,陜西學者在發揮外國文學研究積極性的同時,不忘協同合作積極開展外國文學研究的教材編著工作,這為陜西高校外國文學相關課程的開設提供了寶貴的教材資料。雷成德的《外國文學作品欣賞》、周駿章的《外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讀》、馬家駿的《外國文學作品選講》、石昭賢與馬家駿合著的《歐美現代派文學三十講》等書籍,均作為彼時外國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相關專業教師及學生可以廣泛閱讀。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歷史性變化,不僅彰顯了新時代下科研建設工作迸發出的巨大活力,更證明了改革開放以來陜西省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
二、逐步擴展與深化的國別文學研究
20世紀90年代,中國逐步融入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中,在文化領域也廣泛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這一時期的陜西省外國文學研究者們雖然將研究視角聚焦于具體作家研究與民族國別文學現象之上,但也有意識地開始把對具體作家研究和民族國別文學的研究放置于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視野下來比較和考察。他們逐漸調整研究方法,采取世界性眼光來審視和研究當時的文學現象。
學者韋建國連續多年致力于蘇俄文學研究,考察分析蘇聯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梳理蘇俄象征主義詩歌的發展脈絡。學者梅曉云投身于印度文學研究領域,探討印度古代文化中“陰性原則”展現方式的演變,分析中、印文學中獨特的愛情悲劇。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學者戶思社長期耕耘于法國文學翻譯與研究領域,運用互文性理論撰寫有關杜拉斯的研究專著,并譯介了諸多法國經典文學作品。留德歸來的學者聶軍潛心從事德語文學研究,積極譯介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美學的相關核心理論,選取彼得·漢德克、伯恩哈特等奧地利作家及其作品展開研究,豐富了德語文學的研究對象。
該時期,陜西省外國文學研究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陜西省外國文學研究在國別文學領域取得了豐碩而多元的成果,研究方法上顯示出了鮮明的開拓意識和創新精神。一方面,學者們積極擴展研究范圍,對后殖民作家、存在主義作家、奧地利文學、法國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等進行介紹與研究,創作了大量專著、譯著及期刊文章,為陜西外國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另一方面,運用比較詩學、形式主義等前沿的研究方法與理論進行外國文學研究,推動陜西外國文學研究不斷創新。
第二,陜西省外國文學研究學者們在這一時期廣泛開展外國文學史重構、名作家重評、名著重讀的研究活動,針對各個國家的經典文學作品及其作家進行述評和研究的文章和專著大量增長。例如,學者楊昌龍系統論述巴爾扎克創作,獨立寫出三十多萬字的《巴爾扎克創作論》,并對薩特、加繆等存在主義作家進行了研究論述。學者薛迪之對莎士比亞戲劇具有獨到見解,多年來致力于系統評述莎翁戲劇,著有專著《莎劇論綱》。陳孝英發表多篇文章分析中西方喜劇的差異,梳理中西方喜劇的發展脈絡,闡釋喜劇的基本審美特性。
第三,陜西外國文學研究的隊伍逐步壯大,研究者構成更加多元,研究成果愈發豐碩。例如,馬家駿在俄羅斯文學史、美學史、西洋戲劇史等方面進行研究整理,并出版多部相關專著。仵從巨發表多篇論文,對馮尼格、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進行了深入研究。韋建國、梅曉云、王文、孟長勇等一批學養深厚、基礎扎實的學者在這一時期開始成為陜西外國文學研究的生力軍。此外,戶思社、聶軍等一批素養極佳的年輕學者,在接受系統的文學教育且具有足夠學術積累之后從國外學成回來,憑借優越的外語優勢,取得了豐碩的國別文學研究成果。
三、比較文學視野下的跨學科研究
19世紀以來,諸多學者都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試圖重新建構中華文化傳統。王國維、錢鐘書、朱光潛等學者都曾經進行跨學科研究,成為中國早期比較文學研究的先驅。進入21世紀,比較文學迅速發展,出現了諸多新穎獨特的研究視角與對象,在不同學科的交叉地帶又生發出形形色色的“新學科”。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葉舒憲將文學與人類學結合,積極倡導和實踐文學人類學研究,開拓了一片廣闊的學術天地,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1997年,由葉舒憲先生作為發起人之一的“中華文學人類學會”成立。隨后,由他主編的《文學人類學論叢》也相繼問世,文學人類學研究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同道。陜西師范大學的李永平教授、西安外國語大學的蘇永前教授相繼發表諸多論文,在文學人類學研究領域做出了獨有的學術貢獻。這些學者的比較文學研究不僅有著跨文化的視野,而且始終是在跨學科甚至超學科的學術立場上來發現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
該時期,陜西省外國文學研究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跨學科性。文學人類學的“破學科”觀念與“文學人類學”學科的建立為比較文學的發展拓展了空間。葉舒憲先生從人類學的視野進行文學研究,其多部著作以民俗學、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等知識為研究基礎,運用“三重證據法”對中國上古文化進行重新解讀與闡釋。文化概念作為文學人類學這一學科德基礎與核心,“對原有的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都有巨大牽引力和穿透力。文化概念提供的宏觀整合性視野是文、史、哲、政、經、法等所有學科都沒有也都需要的,因而自然發生了超越學科界限的新知識整合與重建過程。此一過程至今遠未結束, 這就給各個學科帶來變革機遇”。正是借助文學人類學研究理論與方法,一些中國遠古文化的相關問題被得以重新發現,并在跨學科分析中得到解決,從而拓寬了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領域。
第二,跨文化性。葉舒憲先生的研究體現了一種自覺的跨文化對話特征,其研究目的之一在于將世界與中國的學術進行溝通,增加各民族之間的了解與互動,由文化互動而產生新的民族認知。葉舒憲曾選取巴比倫的《吉爾加美什》史詩與中國的羿神話做個案分析和跨文化比較,將散漫凌亂的羿神話連綴起來,發現了它與巴比倫史詩在表層敘述上共同具有的九大母題和亞母題。如戶曉輝所說,這些研究體現的是比較文學作為一種自覺的跨文化對話所具有的學問與實踐的雙重特性,其最根本的任務就在于溝通中西學術,以創造性地實現跨文化的文學意義形式的轉化。文學人類學研究致力于打破單一的文化語境,以“世界眼光”對中華文學與文化進行重新闡釋,體現了中國比較文學的跨文化視野。中西互通的跨文化深層研究,使得文學研究者能夠打破國別限制,真正將文學研究回歸到全體人類而非僅僅個體民族的層次,從而在人類文學發展經驗的互通中尋求生活經驗與情感體驗的共鳴。
四、立足當下的文化外譯工作
在當今的多元文化語境下,中華文化需要“走出去”,而譯介中華文學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徑。陜西文學具有濃郁的鄉土特色,其地域語言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為譯者帶來相當艱巨的挑戰。在全球化格局中,王宏印、胡宗峰、張生庭等陜西學者肩負傳播民族文化的使命,不斷探索嘗試新模式,致力于推動陜西作家作品在異域的有效傳播,促進陜西文學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王宏印教授的諸多譯介學論著,融入了文學、哲學、藝術、心理學等多方面的知識,走出一條獨樹一幟的學術之路。近年來,胡宗峰相繼譯介賈平凹的《黑氏》《廢都》《土門》《白夜》等多部作品,致力于將陜西作家的作品介紹到國外。針對陜西文學在德語國家譯介不足的情況,學者張世勝從創作方言、語言特色、文化意象等方面分析了原因,并提出相應的改善舉措,致力于推動陜西文學走出去。
該時期,陜西省外國文學研究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具有鮮明的陜西地域特色,十分重視對極具陜西地域特色的作家作品進行譯介。出于濃厚的興趣,王宏印教授長期致力于對陜北民歌的翻譯與研究,并且常常去陜北進行采風。他所翻譯的陜北民歌十分貼合其原初特色,這離不開獨特的陜北地域文化與深厚的地域情感。賈平凹先生曾在《秦腔》后記中談道:“我的故鄉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風街;棣花街是月,清風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風街是鏡里花……我決心以這本書為故鄉樹起一座碑子。”也正是出于相同的家鄉記憶,陜西譯者對陜西作家作品的翻譯也才具有了更加深厚的情感共鳴,對語言文字的把握也才會具有獨有的見解與處理,從而選取最為適當的翻譯策略,傳播陜西獨特的風俗文化。
第二,陜西譯者譯介陜西作家作品,能夠較好地把握與處理文學作品中的方言、風俗等內容,更好地傳達出地域文化特色。對陜西譯者而言,如何對小說文本中的方言進行恰當有效而富有魅力的翻譯,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胡宗峰教授曾以翻譯賈平凹《廢都》的經驗談到陜西譯者翻譯陜西作家作品的語言優勢:“比如,陜北人把老人不叫 ‘老漢’或‘老頭’,而是叫‘蒼老’。如果孩子假裝著哭不叫‘裝哭’,而是叫‘佯哭’。類似的例子在陜西話中比比皆是,如果要是別省的人來翻譯,有時候就會搞不清楚。”文學研究如何傳承、發展、創新是一個重大課題。在不同時期,文學研究總是在變化,總在不斷地傳承與創新。在文學理論不斷多樣化的今天,作為陜西外國文學研究者,更應當多加思考文學研究的傳承與創新問題。在批評性揚棄的基礎上,放開眼光,對中外各種文學研究的方式方法、理論范式進行有所取舍的傳承,并在傳承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發展與文學發展,創造出新的文學批評范式,運用新的媒介、途徑和載體,促進文學研究的創新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