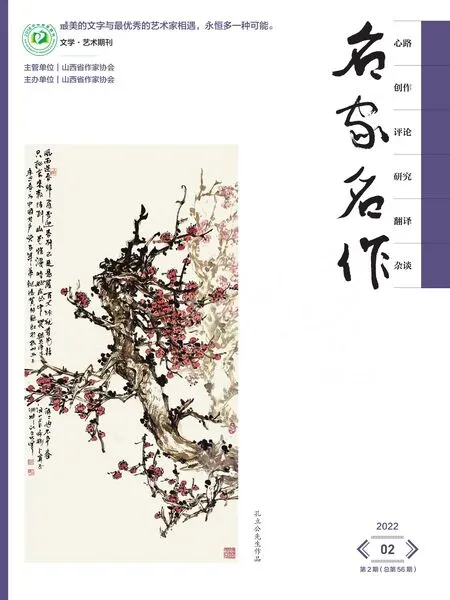試論在華俄僑作家的東北書寫
肖霽同
20世紀初,以哈爾濱為中心聚集了大批的俄羅斯僑民,因中國的生活環境、生存境遇與俄羅斯相似,這些僑民很快地適應了東北的生活,將其視為第二故鄉。東北也成了他們生活的綠洲、創作的自由天地。
一、中國東北俄僑文學的出現
俄羅斯是文學大國,俄羅斯民族是愛讀書、愛寫作的民族。俄羅斯僑民同樣保留了這一優良的傳統,無論是知識分子、軍人、工人、農民,只要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都會化身“繆斯”借文學作品表達他們作為漂泊者的辛酸以及發現第二故鄉的喜悅。
(一)漂泊者的無奈與辛酸
幾次移民潮中的俄僑大多為貴族、軍人和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來到中國以后,雖說生活沒有以前富裕,但是也足以溫飽,生活無憂。然而,在靈魂深處,總不能免除失去故園、漂泊流亡者的無奈與辛酸。葉甫蓋尼·雅什諾夫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來到哈爾濱,作為僑民詩人他經常借詩歌表達個人難以把握命運的悲哀。在《漂泊的繆斯》中他寫道:“我的影子把兩條長腿/拋向相鄰的深溝。/口袋里只有潮濕的護照,/還有一個舊錢包……/為迷路的伊萬哭泣吧,/母親,為我祈禱!”女詩人葉列娜·涅杰利斯卡婭同樣借詩歌表達了對幸福的渴望:“永遠的驚慌不安中,我們所有人是何其孤單。”“我們需要的是愛,是好運,是夜晚火的溫暖。”因此,愛讀書、喜歡文學的俄羅斯人用自己的筆來表達對世事無常、歲月蹉跎的無奈,既是一種精神的慰藉,又是一種謀生的手段。
(二)發現第二故鄉
中國東北,在地理位置上與俄羅斯相鄰,有類似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緯度較高,冬季寒冷,處于邊疆地區,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小。而俄羅斯尤其是遠東地區,同樣處于文化、地理的邊緣地帶,受西方大陸文化影響較小,邊境較為開放,與中國的文化交融、交流歷史較早。這吸引大批俄僑暫居到與俄羅斯相近的哈爾濱等地,而東北文化具有的包容性、開放性、民族兼容性更加促進了俄羅斯文化與東北文化的快速融合。于是,哈爾濱成為中國較早開放的一批城市之一,也成為俄僑作家“詩意的”棲居之所。許多詩人借詩歌表達他們對中國的喜愛。“你們多遼闊、寧靜、舒適!讓我們棲留,對你們感激。”雖然客居他鄉,“一切多么不像俄羅斯啊,但一切又好得多么奇妙!”尤其是給第二代、第三代俄僑的人生留下豐富的記憶:“在這里,我的生活剛露晨曦,/在這里,我長大到成熟年紀。/在這里,我懂得了歡樂,也懂得了最辛酸苦凄。/我會永生永世記憶,/晚霞的照耀和啟迪,/有那夜間風的微微吹拂/和渾濁松花江寬闊的水域。”這里的生活使俄僑及其后代形成一種中國情結,以至于回國和再次遠赴他鄉后依然深深懷念。
二、俄僑作家的東北書寫
在華俄僑文學從產生背景、創作題材、創作風格等方面來看都鮮明地烙上了中國印記,他們既寫中國的市民生活、農民生活,又寫森林河流等自然風光,抒情、敘事中飽含著對這片土地的熱愛。
(一)東北意象書寫:興安嶺密林、松花江、哈爾濱
俄羅斯是一個與大自然關系密切的民族,歌頌大自然也是俄羅斯文學家永恒的題材內容之一。在許多作品中,俄羅斯文學家都向讀者傳達著由大自然的一切所啟迪的美與哲理。中國東北森林覆蓋面較大,河流湖泊眾多,東北人漁獵放牧的生活以及熱情豪放的性格更是激起俄僑作家的創作欲望。他們紛紛將創作的視野與題材鎖定在能夠代表東北特色又與俄羅斯記憶疊合的興安嶺密林、松花江、哈爾濱等意象上。
尼古拉·巴依科夫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俄僑作家。他曾走遍黑龍江、吉林的深山老林,在東北的密林里生活、研究動植物、狩獵近20年,可以說對東北廣袤無垠的原始森林了如指掌。他的小說以東北密林、動植物為創作對象,寫了虎、鹿、熊、山鷹、野雞、蜜蜂、螢火蟲、稠李樹、蘋果樹、榛子樹等動物、昆蟲、植物上百種,并最終凝聚成“密林”和“虎王”兩大意象。他在《虎》(又譯作《虎王》《大王》《偉大的王》)中用寥寥數語便勾勒出生機勃勃的東北原始森林景象:“早春,密林生生的恢復起來,黃灰色的地面,由于嫩嫩的茂葉和翡翠的幼枝,已帶了綠色。沿著澗川和山的斜面,開了櫻桃和蘋果的花。青竹蘭那白色小鈴形的花,在樹林那陰暗的茂葉里,也已經開始稀疏地現了出來。水晶般清澄的山的空氣,充滿了花的香氣和大地的氣息。”尼古拉·巴依科夫描寫東北森林動植物的作品曾風靡世界,受到評論界高度評價,“被各國文學評論家譽為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生態小說家之一”,是“生態文學大師”。尤其是他留下了大量關于密林里虎的作品,猶以寫牝虎的最多。在巴依科夫的筆下,作為森林之王的牝虎常常是偉大而堅強的化身,被作家賦予了神靈和人性之光。《牝虎》(又名《母親》)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中像牝虎似的女主人公娜絲達霞獨居森林,與野獸為鄰。丈夫谷利哥里被牝虎吃掉,娜絲達霞獨自一人撫養幼兒,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虎崽,顯示了母性的光輝。這使我們想起許多俄羅斯文學作品,如高爾基的《母親》、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個》等作品中塑造的勇敢超人的女性形象。巴依科夫將這篇小說命名為《牝虎》,實際上是一語雙關,不僅描寫了牝虎作為森林之王的強悍,而且歌頌了其母性的偉大,同時又贊美了娜絲達霞高尚的精神和人性的光輝。當牝虎遇到獵人圍攻時本可以獨自逃開,但是在母愛的驅使下,她準備保護孩子“直到血底最后的一滴”。在精疲力竭之后,獵人眼前出現了一幅令人震撼而又直刺靈魂的畫面:“她這時正舔著一只老虎并用足掌撫摸著他。”正是這幅觸動心靈的畫面讓獵人放下了槍,“這并不是對一個野獸,而是對一個母親,因為她表現了那樣高度的自己犧牲和情愛”。作品中作者賦予牝虎偉大的人性和母性,而“殺掉牝虎——一個母親是一種犯罪甚而罪惡”。作者在文中自省:“我常是反對殺掉所有野獸和鳥類底牝者,這不是由于道德的觀念,也是基于實際的見地,因為牝者底保存是正當而合理的狩獵底必要的條件。”這正是獵虎給作者帶來的啟示,也是作者生態觀的體現。
松花江是中國著名的河流之一,流經吉林、黑龍江兩省,也是黑龍江在中國境內的最大支流,流域面積近56萬平方千米。松花江不僅是中國作家書寫的對象,也成為俄僑作家偏愛與鐘情的書寫對象。因為俄羅斯有許多世界聞名的河流湖泊,而暫居在哈爾濱的俄僑就將對家鄉的思念寄托在松花江上,從而寫出了不少優秀的詩歌作品。例如:“夜晚在江面灑下閃爍的銀光……/浸在江水里的蕃紅花,/觸摸人的軀體,軀體柔軟,/風像掙脫了鎖鏈,大聲吼叫,/江上的夜空變得白茫茫一片。”再如:“江中的波浪跑得很慢,/岸邊的沙被悄悄洗涮。/岸上到處是陽光一片,/岸上到處是春意一片。”松花江的波浪、松花江的夜色成為慰藉作家心靈的一劑良藥,面對滔滔江水,吹著和煦的晚風,詩人獲得了心靈的寧靜。
除了自然山水以外,哈爾濱這個俄僑生活的重要棲居地也成為作家寫作的對象。歷史上,哈爾濱曾生活過數十萬的俄國僑民。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們的參與使哈爾濱迅速完成了由小漁村到國際化城市的轉型。許多詩人在詩歌里記錄下了他們參與建設哈爾濱的歷程。阿爾謝尼·涅斯梅洛夫就是其中一位,他在《舊墓——致哈爾濱的建設者們》中寫道:“他們曾舉起丁字鎬和鐵錘,有為的一生曾美好無比——它證明俄羅斯人到處強有力,不管把他們派到哪里。”在另一篇《建筑者》中又記錄了年華已逝的城市建筑者們。可見,哈爾濱被譽為“東方莫斯科”“俄羅斯城市”是不無道理的,這座城市在文學教育、文化底蘊、宗教信仰、建筑風格等方面有今天的面貌,無疑是受到了俄羅斯文化的影響和熏陶。從今天留下來的文化遺產來看,哈爾濱在建筑風格、城市規劃上依稀可見俄羅斯風格及俄羅斯文化的滲透。例如,圣·索菲亞大教堂、“洋蔥頭”俄式建筑、紅腸、面包在如今的哈爾濱街頭隨處可見。除了阿爾謝尼·涅斯梅洛夫這樣的哈爾濱的建設者們用文學記錄了他們的工作和心路歷程以外,還有很多作家記錄了他們的哈爾濱印象、感覺。例如,在葉列娜·伏拉吉的印象里,哈爾濱“街上是香噴噴的空氣,/大煎餅使勁揮放香味,/故鄉哈爾濱,中國城市,/使勁揮放春天的氣息”。在阿列克桑德拉·巴爾考的眼里,春天的哈爾濱,“滿街刮大風”“五色旗在半空中被撕得稀破”“汽車使勁地鳴笛”“大齋禮拜令人心碎的鐘聲”,也有美麗柳枝上掛滿的迷人的花絮和“節日市場上殷勤的嘈雜聲”。不管怎樣,在相同的背景下每個人都在這座城市演繹著無法重復的歷史。
(二)書寫東北愛情故事
愛情是沒有國界的,愛情也是文學作品永恒不變的話題。愛情中的癡迷、熱烈、幸福、孤獨、迷茫、幻滅和殘酷,都令人深深感動。俄僑作家跟所有人類一樣首先把神圣的愛情當作精神支柱,或表達對本民族愛人的懷戀,或表達對中國女孩的愛慕,或抒發愛情生活中的復雜情感,或借愛情的抒發表達對祖國的思念。就像阿列克謝·阿恰伊爾的詩作《我用雙手撫摸……》,寫出了對愛情的奇妙感覺:“我用雙手撫摸你的頭發,/你的發綹似有陽光閃爍……/我的視線剛觸到你的目光,/就在注視我的柔波中沉沒。”表達了青年男女戀愛中的微妙情緒變化及對愛情的堅貞。基里爾·巴圖林在《寧波姑娘》中憶起與有著“黑黑的辮子,黑黑的、調皮的眼睛”的中國姑娘的愛情故事,表達了“對她們我永遠不忘情”。當然也有表達愛情中的無奈與殘酷的。奧利加·捷利托夫特在《你走進屋來……》《愛》等詩作中抒發了對美好愛情的渴望以及戀愛過程中的孤獨、憂傷、痛苦的情緒變化。由于當時俄僑特殊的生活經歷,“閃電”式的愛情時常發生,令年輕的俄僑們很難把握,娜塔莉婭·列茲尼科娃在《不要再海誓山盟了……》揭露了愛情過程中的欺騙和謊言,對愛情的穩定性提出了質疑,抒發了對純潔、忠貞愛情的渴望。總之,俄羅斯僑民的愛情是跌宕起伏的,他們的愛情生活都讓人感動和深思。
(三)展現東北城鄉生活
俄僑作家長期與東北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東北的一些城鄉生活、民風、民俗、鄉土文化是他們每天會接觸到的,但這并不妨礙其以異域的獨特視角去審視這里的生活和人。他們感興趣的一切都成為書寫對象,變成文學作品里的特殊意象。如自然、地理意象:興安嶺、草原、森林、松花江、暴雪、怒風、陰雨天、炊煙、白色的小樹林、池塘、畦田、中國的農村、城市、春天的哈爾濱、銀色的大連、長春、火車站、公園、教堂、水果店、小酒館等;時間意象:晚霞、黃昏、日落、黎明、清晨、冬夜、夏天、熱辣辣的秋天等;動植物意象:金蓮花、松樹、稠李、櫻桃、丁香、魚尾菊、獨鶴、貓頭鷹等;獨異人意象:老撞鐘人、女基督徒、吉卜賽女郎、紅胡子、老毛子、盲人、算命先生、日本姑娘、東北妞兒等;民俗意象:辣煙、燈盞、煎餅、占卜、藍色的節日、陰歷新年等。例如,尼古拉·斯維特洛夫的《中國的新年》描寫了印象中的中國新年景象:“大鼓小鼓拼命地敲打,/開懷暢飲,特別熱鬧。”“胡琴、喇叭還有鑼聲,/有板有眼地響個不停,/蹦蹦跳跳的民間舞蹈,/讓人陶醉,神魂顛倒。/空中好像是雷聲隆隆,/萬千鞭炮在一起轟鳴。”阿列克桑德拉·巴爾考的《按中國日歷》《陰歷新年》也寫出了中國的時令節氣和年俗。再如,格奧爾吉·薩托夫斯基的《木匠干活兒輕松快樂》描寫了做木匠活的場景:“大胡子蓬松像霜打的亞麻,/師傅穿白襯衫頭頂著涼棚,/戴樹皮護膝,纏著包腳布,/精神專注雕刻帶花的窗欞。”當然也寫到了拋下妻子和母親走出村外闖蕩的紅胡子、“抽鴉片煙的人”以及“中國的景色極其單調”“身穿長袍的和尚和老者”,他們在不語中激烈地爭吵。更寫到了民間的疾苦:“黝黑的憔悴的男孩子,/睡在難民病女人膝上。/沿著石灰漿、廢物、垃圾,/褐色的葉子瑟瑟作響。”體現出了閃耀在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人道主義光芒。
三、結語
在華俄僑作家的創作是多元的,他們的文學創作內容豐富、題材多樣,集詩歌、散文、小說等多個形式,成為俄羅斯僑民的精神食糧。其中國東北書寫,豐富了東北地域文學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文本,特別是巴依科夫的中國東北密林書寫,為我們保留了東北原始森林的文學影像。總之,在華俄僑作家在中國東北的生活與文化交流軌跡,為新時代中俄文化交流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