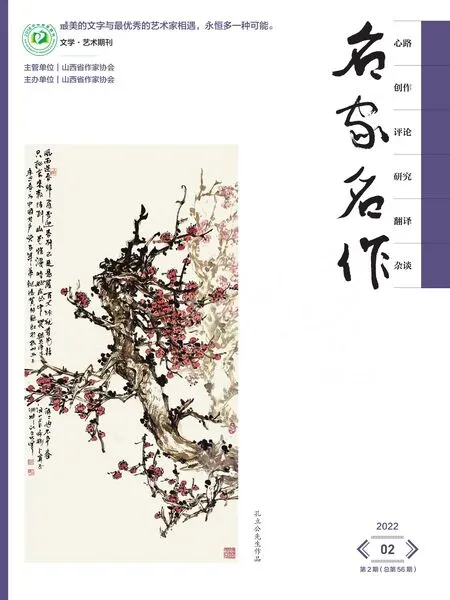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理想國(guó)》溯源
何芙蓉
柏拉圖的思想意蘊(yùn)無窮,是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學(xué)的源頭之一。其代表作《理想國(guó)》,是他最經(jīng)典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既是西方文明開端的經(jīng)典之作,又涉及柏拉圖思想體系的各個(gè)方面,更是以理想之人和理想國(guó)家的建構(gòu)影響至今。
一、《理想國(guó)》的整體架構(gòu)
《理想國(guó)》全書內(nèi)容龐雜、主題多元,涉及經(jīng)濟(jì)、政治、宗教、體育和藝術(shù)在內(nèi)的古希臘公共生活的全部?jī)?nèi)容,全書是一個(gè)多條經(jīng)緯線交織、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復(fù)雜結(jié)構(gòu)。《理想國(guó)》的終極目標(biāo)就是要建立一個(gè)正義、和諧的理想社會(huì),因此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正義”這條主線。后人將《理想國(guó)》分為十卷,按順序來看,全書由有關(guān)正義與心靈間的關(guān)系開始討論,柏拉圖開篇便提出了“何為正義”的論題,繼而談到了公民受教育的途徑、理想城邦何以實(shí)現(xiàn)、“衛(wèi)國(guó)者”與“哲人王”如何塑造等問題,在政治體制、城邦權(quán)力、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變革思想,進(jìn)而指向公民心靈的歸宿,最后將這些問題匯總并展現(xiàn)出一幅所謂“理想城邦”的美好圖景。
二、對(duì)話體的方式
在閱讀《理想國(guó)》中的對(duì)話時(shí),往往不能立刻明了柏拉圖想要表明的觀點(diǎn),因?yàn)槠渲胁o嚴(yán)整的理論體系,而僅僅有以蘇格拉底為主角的、與一個(gè)個(gè)鮮活的人的口頭對(duì)話。
柏拉圖的《理想國(guó)》與其他的哲學(xué)著作有很大不同的一個(gè)重要的點(diǎn)在于,它并不是從自己的觀點(diǎn)出發(fā)進(jìn)行長(zhǎng)篇的概念論證和抽象的哲學(xué)思辨,其語篇結(jié)構(gòu)主要是以對(duì)話為主。柏拉圖所寫的每一組對(duì)話幾乎都是以蘇格拉底作為主要發(fā)言者,他用一種特殊的互相詢問的對(duì)話方式向普遍觀點(diǎn)發(fā)起挑戰(zhàn)。《理想國(guó)》中的蘇格拉底從不以老師自居,也不愿意讓別人成為自己的信徒,向他人灌輸自己的邏輯思路。而是將對(duì)話既作為探討真理的方法,又作為對(duì)話者之間思想交流的交際活動(dòng)。蘇格拉底和他的對(duì)話者在對(duì)真理的探問中結(jié)成了以愛智為核心的友愛共同體。理論的提出和建構(gòu),在對(duì)話者的多方互動(dòng)、共同探究的動(dòng)態(tài)過程中得以實(shí)現(xiàn)。
《理想國(guó)》采用的對(duì)話體方式深深地受到了柏拉圖老師蘇格拉底“助產(chǎn)術(shù)”的影響。蘇格拉底的“助產(chǎn)術(shù)”,集中表現(xiàn)在他經(jīng)常采用的“詰問式”中。詰問中,蘇格拉底自己并不給予正面的、積極的回答,因?yàn)樗姓J(rèn)自己無知。整個(gè)過程通過一問一答,反復(fù)詰難,一方不斷揭露另一方的矛盾。他從對(duì)方認(rèn)可的觀念出發(fā),通過自己不斷的質(zhì)疑和提問,歸納出關(guān)于討論對(duì)象的一般定義。蘇格拉底終其一生都在日常生活中進(jìn)行著對(duì)話性的教育實(shí)踐,用以培育人們的愛智精神。《理想國(guó)》中的柏拉圖和他的對(duì)話者,也是在對(duì)真理的探問中結(jié)成了以正義為核心的友愛共同體,對(duì)智慧和真理的追求貫穿對(duì)話始終。
三、觀點(diǎn)闡發(fā)的一般步驟
(一)拋出一個(gè)問題,引導(dǎo)對(duì)方說出自己的觀點(diǎn)
《理想國(guó)》中對(duì)話的雙方都扮演的是正義城邦的締造者,沒有誰比誰更權(quán)威之說。蘇格拉底首先是尊重對(duì)方的觀點(diǎn),謙虛地請(qǐng)教并樂于聽取對(duì)方的觀點(diǎn),引導(dǎo)對(duì)方說出自己的理論。然后他從身邊的小事出發(fā),讓對(duì)方覺得這樣的哲學(xué)問題與個(gè)人利益息息相關(guān),討論有必要進(jìn)行下去。同時(shí),他也不斷地以積極話語暗示所討論的哲學(xué)問題的重要性,保證對(duì)話的連續(xù)性與討論的積極性。
在蘇格拉底與玻勒馬霍斯討論關(guān)于正義的問題時(shí),玻勒馬霍斯由于觀點(diǎn)不和對(duì)其大發(fā)雷霆,想要暫停兩人的對(duì)話。蘇格拉底只是說:“要是我們的目的是尋找金子,我們就絕不會(huì)只顧相互吹捧反倒錯(cuò)過找金子的機(jī)會(huì)了。現(xiàn)在我們要尋找的正義,比金子的價(jià)值更高。”蘇格拉底不斷地暗示著對(duì)話內(nèi)容比生活中的瑣碎小事重要百倍,這不僅關(guān)乎對(duì)話雙方,也涉及城邦所有的人,乃至世界上所有活著的人。這一方式,促使接下來關(guān)于正義討論的繼續(xù)進(jìn)行。
當(dāng)然,追問本身就是哲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多思考、多提問,這是哲人的基本素養(yǎng)。在《理想國(guó)》中蘇格拉底說:“除了接受無知懲罰外還能有什么別的嗎?而受無知之罰顯然就是我向有智慧的人學(xué)習(xí)。”這一回答,既以虛心的態(tài)度引導(dǎo)玻勒馬霍斯繼續(xù)闡明他的觀點(diǎn),也向我們又一次展現(xiàn)了他不為任何個(gè)人利益,將對(duì)知識(shí)的熱愛與追求作為唯一的目的和動(dòng)力,從而不斷追問。
(二)通過對(duì)話和發(fā)問,揭露對(duì)方的矛盾,使對(duì)方放棄自身原有的觀點(diǎn),承認(rèn)自己的錯(cuò)誤
這一階段的目的是推翻對(duì)方錯(cuò)誤的觀點(diǎn)。但書中的蘇格拉底并不急于反駁對(duì)方,而是順著對(duì)方的觀點(diǎn)反問他,從而使對(duì)方一步步地自己發(fā)現(xiàn)矛盾所在,承認(rèn)自己的錯(cuò)誤。
柏拉圖作為哲人的生活方式——即使面對(duì)的是有名望的人,要質(zhì)疑的是權(quán)威的理論,也要不斷追問,不滿足于已有的答案。如關(guān)于正義的討論中,克法洛斯認(rèn)為,正義就是“有話實(shí)說,有債照還”。接著,柏拉圖對(duì)克法洛斯的觀點(diǎn)進(jìn)行了反駁。他認(rèn)為,這種正義只是日常生活中某一情形下的行為,而不是正義的定義,因?yàn)槿绻颜x理解為“有話實(shí)說,有債照還”,會(huì)造成“有時(shí)是正義的,有時(shí)是‘不正義的’的后果”。也就是說,這類行為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正義的。“譬如說,你的朋友在頭腦清楚的時(shí)候,曾經(jīng)把武器交給你,假如他后來瘋了,再跟你要回去……如果竟還給了他,那倒是不正義的。”正義的定義就遇到了還債的時(shí)機(jī)和還債對(duì)象的難題。如果債主是敵人,那會(huì)造成對(duì)敵人的幫助,還債也是非正義的。因?yàn)椤皵橙藢?duì)敵人所欠無非是惡”。因此,“有話實(shí)說,有債照還”這個(gè)原則的范圍太過于狹窄,代表的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不符合對(duì)正義的定義。
(三)依循對(duì)話者的現(xiàn)實(shí)處境引導(dǎo)人走向靈魂的美善,得到普遍性、一般性的認(rèn)識(shí),從而獲得真理
最后一階段是讓對(duì)方憑借已有的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回答,輔之以必要的解釋,使對(duì)方理解蘇格拉底的角度,逐漸接受、肯定蘇格拉底的觀點(diǎn),獲得某種真理。這一階段以蘇格拉底和阿得曼托斯討論“神是否是一切事物的原因”為例。蘇格拉底提問:“神不肯定是善的嗎?故事不應(yīng)該永遠(yuǎn)把他們描寫成善的嗎?”阿得曼托斯:“當(dāng)然應(yīng)該。”蘇格拉底:“其次,沒有任何善的東西是有害的,是吧?”阿得曼托斯:“我想是的。”蘇格拉底:“無害的東西會(huì)干壞事嗎?”阿得曼托斯:“啊,不會(huì)的。”蘇格拉底:“不干壞事的東西會(huì)作惡?jiǎn)幔俊卑⒌寐兴梗骸敖^對(duì)不會(huì)。”蘇格拉底:“不作惡的東西會(huì)成為任何惡的原因嗎?”阿得曼托斯:“那怎么會(huì)呢?”蘇格拉底:“好,那么善的東西是有益的?”“是的。”“因此是好事的原因嗎?”“是的。”蘇格拉底:“因此,善者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原因,不是壞的事物的原因。”阿得曼托斯:“完全是這樣。”這是一段典型的柏拉圖式問答。對(duì)話者從生活的道理出發(fā),沒有深?yuàn)W的哲學(xué)理論,只憑借已有的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提問和回答,從而一步步地引導(dǎo)對(duì)方進(jìn)入自己的邏輯思路,即柏拉圖“有意要讓人經(jīng)過精神的操練”,最后以正確的途徑來理解自己、認(rèn)識(shí)世界。柏拉圖的對(duì)話主要展現(xiàn)一種旨在培育心靈的教育,而不是為了傳遞外在于生命的客觀知識(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