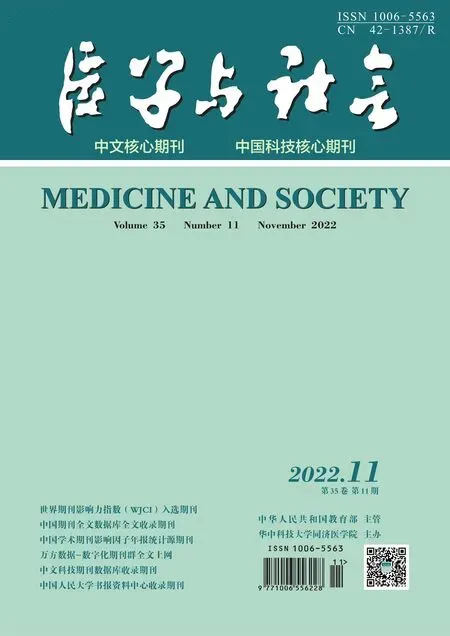希望水平與疾病應對方式在乳腺癌患者社會支持和生命質量間的鏈式中介作用
木巴拉克·依克拉木,曹 艷,2,張翠萍
1新疆醫科大學護理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11;2新疆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日間病房,新疆烏魯木齊,830011;3新疆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護理部,新疆烏魯木齊,830011
乳腺癌是目前全世界女性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1]。據2019年美國癌癥統計數據報告,女性乳腺癌患者年新發病例高達26.8萬,占所有女性癌癥發病率的30%[2]。伴隨現代醫療技術的加速發展,乳腺癌患者平均5年生存率已達到73%[3],越來越多的臨床工作者將關注視角由提高乳腺癌患者生存率轉向提升其生命質量。
社會支持是指當個體面對應激性事件造成的壓力時,從親友或社會中所獲得的物質或精神上的援助支持[4],研究表明[5],社會支持對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起正向預測作用。家屬、朋友等給予的關懷,以及來自組織、醫護人員的關愛是幫助患者緩解壓力、重塑希望、維持身心健康的關鍵[6]。“希望”是指個體應對疾病時產生的有效信念和策略[7]。研究顯示[8],社會支持與希望水平亦呈顯著正相關。對于乳腺癌患者來說,罹患癌癥是威脅其希望水平的內部資源,而來源于外界的社會支持彌補了其內在資源的缺失[9],并對提升其生命質量起到正向促進作用[10]。因此,社會支持可能通過希望水平的中介效應間接影響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
疾病應對方式是指個體在應對疾病壓力時所產生的認知信念及行為傾向[11]。研究顯示,在影響個體疾病應對方式的眾多因素當中,社會支持最為關鍵[12]。個體獲得的社會支持水平越高,疾病適應能力就越強,越傾向于采取積極的疾病應對策略,從而促進健康行為的產生,最終提升個體生命質量[13]。此外,研究顯示[14],希望水平能夠顯著預測乳腺癌患者疾病應對方式。希望是壓力應對的主要環節,在調節情緒和心理適應機制中起到關鍵作用[15]。Snyder等提出的“希望理論”和Folkman等提出的“應對過程理論”認為[16-17],“希望”是促進個體積極應對壓力與挑戰的關鍵因素,高希望水平的個體具備更強的路徑思維和動力思維,更傾向于將壓力、困難視為挑戰,主動采取正向應對策略處理問題,從而達到更好的適應結局(生命質量)。因此,本研究假設社會支持可能通過希望水平與疾病應對方式的鏈式中介作用對個體生命質量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社會支持、希望水平和疾病應對方式等均為影響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缺乏對各變量間影響機制的研究。本研究基于Snyder等提出的“希望理論”和Folkman等提出的“應對過程理論”,應用結構方程模型構建并探究希望水平和疾病應對方式在乳腺癌患者社會支持和生命質量間存在的效應關系,并揭示變量間的作用路徑。為臨床工作中制定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提升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0年5月-2021年1月新疆某三級甲等腫瘤專科醫院日間病房290例乳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經病理學診斷確診為乳腺癌的患者;②接受術后化療的患者;③年齡≥18周歲;④認知功能正常,意識清晰,溝通與交流無障礙。
排除標準:①合并其他惡性腫瘤或嚴重軀體疾病的患者;②哺乳或妊娠期婦女。本研究已經過本院倫理委員會審核(倫理審批號K-2019063),患者均知情同意參與本研究。根據結構方程模型樣本量計算方法[18],樣本量與觀察變量的比例為10∶1至15∶1。本研究共計15個觀察變量(社會支持3個維度、希望水平3個維度、疾病應對方式3個維度、生命質量6個維度),因此樣本量應為150-225例,考慮到20%的樣本缺失率,至少需要樣本量180-270例。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采用研究者自行設計的一般資料調查問卷,包括患者的年齡、婚姻狀況、經濟收入、TNM分期等。
1.2.2 Herth希望指數量表(Herth hope index,HHI)。該量表中文版由趙海平等修訂[19],共計12個條目,包括積極態度(4個條目)、積極行動(4個條目)、親密關系(4個條目)3個維度。采用Likert 4級計分法,每個條目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賦予1-4分,共計12-48分。總得分越高,則提示個體希望水平越高。該量表在國內重測信度為0.92,Cronbach's alpha為0.850。該研究中此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為0.847。
1.2.3 醫學應對方式問卷(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中文版由沈曉紅等修訂[20],用來評估患者在應對疾病過程采取的認知-行為策略。該問卷共計20個條目,包括面對(8個條目)、回避(7個條目)和屈服(5個條目)3個維度。采用Likert 4級計分法,面對維度總分計8-32分,回避維度總分計7-28分,屈服維度總分計5-20分,某一維度分值越高,面對、回避和屈服3個維度的Cronbach's alpha分別為0.754、0.734、0.792。
1.2.4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SSRS)。該量表由肖水源等編制[21],共計10個條目,包括主觀支持(4個條目)、客觀支持(3個條目)、社會支持利用度(3個條目)3個維度,其中第1-4,8-10條均采用4級評分法,選項“1、2、3、4”依次計為“1、2、3、4”分;第5條分“A、B、C、D、E”5項,每項從“無”到“全力支持”依次計為0-4分;第6、7條,如有幾項來源計幾分,如無任何來源則計0分,總分共計12-66分,得分越高提示個體社會支持度越高。該量表在國內的重測信度為0.92,Cronbach's alpha在0.89-0.94。該研究中此量表Cronbach's alpha為0.882。
1.2.5 癌癥患者生命質量核心量表(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QLQ-C30)。該量表由歐洲癌癥研究與治療組織研制[22]。包括30個條目,15個領域,其中包含5個功能領域(軀體功能、認知功能、情緒功能、角色功能及社會功能)、9個癥狀領域(惡心嘔吐、便秘、疼痛、失眠、腹瀉、食欲減退、疲乏、呼吸困難及經濟困難)、1個生命質量領域。總分范圍0-100分,得分越高,提示個體生命質量越高。根據本研究實際情況,選取5個功能量表和1個生命質量領域作為主要調查工具。
1.3 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由2名經專業培訓的調查員向研究對象詳細講解此次研究的目的、內容及問卷填寫時應注意的事項。在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后發放問卷,患者填寫完由調查員當場收回并核查,剔除無效問卷。本研究共計發放問卷290份,回收有效問卷274份,有效回收率為94.48%。
1.4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共274例完成研究,均為女性,患者年齡≤30歲18例(6.57%),31-45歲89例(32.48%),46-60歲131例(47.81%),>60歲36例(13.14%)。婚姻狀況:已婚235例(85.77%),未婚8例(2.92%),離婚/喪偶31例(11.31%)。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112例(40.88%),3000-5000元95例(34.67%),>5000元67例(24.45%)。TNM分期:Ⅰ期94例(34.31%),Ⅱ期133例(48.54%),Ⅲ期39例(14.23%),Ⅳ期8例(2.92%)。
2.2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素因子分析,對希望水平、疾病應對方式、社會支持和生命質量4個變量共72個條目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轉的因素分析得出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有13個,第一個因子的方差解釋率為18.52%,小于臨界值40%,說明該研究中沒有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乳腺癌患者在各變量得分上的差異比較
運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法研究不同人口學變量在社會支持、希望水平、疾病應對方式及生命質量得分中是否存在差異,結果表明:處于不同年齡階段下的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及疾病應對方式得分存在顯著差異;處于不同經濟收入水平的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得分存在顯著差異;處于不同婚姻狀態下的乳腺癌患者社會支持得分存在顯著差異;處于不同腫瘤分期的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得分亦存在顯著差異。見表1。
2.4 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疾病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生命質量的相關性分析
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與希望水平、面對應對方式、生命質量呈顯著正相關(P<0.01),與屈服應對方式呈顯著負相關(P<0.01);希望水平與面對應對方式、生命質量呈顯著正相關(P<0.01),與屈服應對方式呈顯著負相關(P<0.01);面對應對方式與生命質量呈顯著正相關(P<0.01);屈服應對方式與生命質量呈顯著負相關(P<0.01)。見表2。
2.5 希望水平和疾病應對方式在乳腺癌患者社會支持與生命質量間的鏈式中介模型分析
采用Hayes(2013)編制的SPSS進行統計分析,根據相關文獻[23],在控制了可能對結果產生影響的人口學變量(年齡、婚姻、經濟收入)和臨床特征(腫瘤分期)等變量后,使用Process中的Model 6檢驗希望水平和疾病應對方式在社會支持和生命質量間的鏈式中介效應。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檢驗法(設置重復抽樣5000次),計算95%的置信區間。考慮到中介模型的基礎是變量間存在較為穩定的相關關系,因此模型中并未納入回避應對方式。

表1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乳腺癌患者在各變量得分上的差異檢驗

表2 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疾病應對方式、社會支持及生命質量的相關性分析
鏈式中介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生命質量影響的總效應顯著(β=0.540,P<0.01)。納入中介變量后,社會支持不僅能正向預測希望水平(β=0.528,P<0.01),而且能夠正向預測面對應對方式(β=0.215,P<0.01);此外,社會支持對生命質量的直接效應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β=0.199,P<0.01)。同樣,希望水平不僅能正向預測面對應對方式(β=0.392,P<0.01),而且能夠正向預測生命質量(β=0.279,P<0.01),此外還能反向預測屈服應對方式(β=-0.284,P<0.01);此外,面對應對方式能夠正向預測生命質量(β=0.463,P<0.01)。見表3。
中介效應分析顯示:經Bootstrap法檢驗希望水平和面對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其95%的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提示希望水平和面對應對方式在社會支持與生命質量間的鏈式中介效應成立,中介效應值為0.342,占總效應的63.33%。該中介作用共包含3條路徑:①間接效應1(0.147):社會支持→希望水平→生命質量。②間接效應2(0.099):社會支持→面對應對方式→生命質量。③間接效應3(0.096):社會支持→希望水平→面對應對方式→生命質量。間接效應1、間接效應2、間接效應3分別占總效應的百分比為27.22%、18.33%、17.78%。見表4,圖1。

表3 鏈式中介模型分析

表4 中介效應檢驗

圖1 鏈式中介作用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乳腺癌患者社會支持與面對應對方式、希望水平和生命質量間均呈顯著正相關,與屈服應對方式呈顯著負相關,這與以往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24-25]。
3.1 希望水平在乳腺癌患者社會支持與生命質量間起獨立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希望水平在社會支持與生命質量間起完全中介作用,且占總效應的27.22%,表明社會支持能夠通過希望水平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生命質量是評價腫瘤療效的關鍵指標[26]。本研究中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整體處于偏低水平(56.27±15.84)分,低于國外學者Park等的研究結果[27]。究其原因,乳腺癌患者在疾病進展及治療過程中往往需要承受疲乏、睡眠障礙、焦慮、抑郁等諸多軀體和心理癥狀,這些癥狀常同時發生,彼此關聯,形成不同的癥狀群并產生協同效應,從而嚴重降低個體生命質量[28]。社會支持為患者提供了一種緩沖壓力的方式,有助于緩解乳腺癌患者在疾病治療過程中所產生的負性情緒,激發個體產生克服當前困境、戰勝病魔、重塑健康的希望,增強自身對疾病的控制感,從而報告更高的生命質量[24]。
3.2 面對應對方式在乳腺癌患者社會支持與生命質量間起獨立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面對應對方式在社會支持與生命質量間起完全中介作用,且占總效應的18.33%,表明社會支持能夠通過面對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間接影響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應對方式指個體對自身及周圍環境變化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調節策略[29]。社會支持作為患者尋求健康支持最有力的外部資源,對個體疾病應對方式的選擇具有重要影響[30]。本研究表明,社會支持水平能夠正向預測面對應對方式,與國內學者姚敏等的研究結果一致[31],即乳腺癌患者在應對術后軀體形象改變及化療不良反應等應激事件刺激時,獲得的社會支持水平越高,越傾向于主動采取保護性的應對策略,積極地配合醫護人員的各項診療工作,維持自身機體、心理、社會健康處于較高水平。相反,若消極的采取屈服應對策略,將加劇應激事件造成的心理壓力,甚至加速病情進展,嚴重降低患者生命質量。
3.3 希望水平和面對應對方式在乳腺癌患者社會支持與生命質量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還發現,在納入希望水平與面對應對方式兩個中介變量后,社會支持對生命質量直接效應的顯著性明顯降低,說明社會支持能夠通過影響希望水平和面對應對方式兩個中介變量,對乳腺癌患者生命質量產生影響。基本驗證了“希望理論”和“應對過程理論”模型[16-17],即乳腺癌患者的社會支持度越高,越能夠針對應激源采取積極的認知評價和行為調節策略,激發患者產生緩解和抵抗壓力的內在動力和信念(動力思維),主動尋求更多方法(路徑思維)來應對疾病治療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有助于患者心理狀態、社會功能及生命質量的提升。乳腺癌患者在面對術后創傷及長期化療階段獲得來自父母、配偶及親友等給予的社會支持越充足,抗癌信念則越強,表現為主動地采取面對應對方式積極對抗疾病,從而提升自身生命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