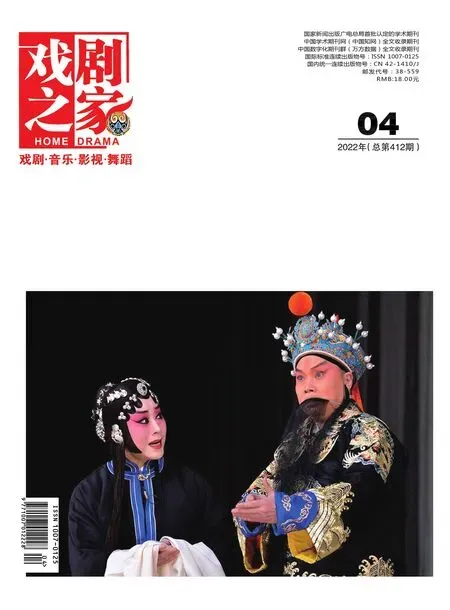場面調度對人物關系塑造的研究
——以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為例
曹 芳
(南京傳媒學院 文化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72)
一部電影就是劇中人物關系形成、發(fā)展和轉變的過程,電影的敘事技巧都是建立在成功的人物關系之上的,通過主要人物與其他人物建立起的關系來揭示人物真相,讓觀眾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命運,從各個角度來把握人物與眾不同的性格和豐富的內心世界。所以,一部電影中,人物關系的塑造對于故事的展開和推進至關重要。
在電影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導演通過場面調度將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具象化,最終呈現(xiàn)在電影銀幕之上。根據(jù)劇本的主題、故事情節(jié)、人物性格等,導演將人與物依照三維空間的觀念進行安排,通過對演員的站位姿態(tài)、手勢動作、行動路線等表演活動進行藝術處理,對攝像機方位、視角和運鏡方式進行綜合考量,將現(xiàn)實世界轉變?yōu)槎S空間的影像。電影中對場面調度的運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綜合了攝影、燈光、演員等諸多元素,既關注單個鏡頭及多個鏡頭的連接,又注重影片的內在連續(xù)性。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是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的巔峰巨作,講述了二戰(zhàn)期間一名叫辛德勒的納粹商人,借助二戰(zhàn)的機會,利用廉價的猶太人做工大發(fā)戰(zhàn)爭橫財,但在親眼目睹納粹對猶太人的血腥屠殺后,原有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一路坍塌,他開始了人生中充滿艱辛與血淚的心靈救贖之路,一改原本迷戀浮華生活的作風,不惜耗盡全部身家,全力營救1100 多名猶太工人的故事。
導演斯皮爾伯格通過嫻熟的場面調度,在流暢的運動鏡頭中調度演員,對演員在景框內進行區(qū)域位置的安排、處理演員的空間距離、攝像機方位以及角色空間占比,成功塑造了眾多豐富立體的人物群像以及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從貪婪好色的德國商人辛德勒,意志堅定的猶太裔會計師伊扎克·斯特恩到殺人如麻的阿蒙·戈特等,這些人物之間的關系緊密交織、不斷發(fā)展、轉變,重現(xiàn)了二戰(zhàn)期間飽受苦難的猶太民族的血淚情仇,其思想的嚴肅性和非凡的藝術表現(xiàn)都達到了無法超越的高度。
一、景框內區(qū)域位置與人物權力關系
景框內的空間,即是電影的世界,不同區(qū)域位置具有不同的象征意義,代表著導演對電影世界中的人或物的不同態(tài)度和評價。景框區(qū)域位置通常分為中央、上、下、邊緣四部分,每部分都具有不同的隱喻與象征。
(一)景框區(qū)域位置之上、下區(qū)域
景框的上方區(qū)域通常象征著權力、權威和精神信仰,處于這個區(qū)域的人或物,對景框內其他區(qū)域具有絕對的控制力。下方區(qū)域則代表著服從、無力、軟弱,該區(qū)域的人或物在整體氣勢會弱于其他區(qū)域,處于被支配的地位。
在辛德勒與會計斯特恩初次見面的這場戲中,斯皮爾伯格通過調度兩位演員在景框區(qū)域內位置完成這場戲中人物關系的塑造,交代了辛德勒和斯特恩之間的權力關系。
辛德勒與斯特恩進入房間,此時的辛德勒是一個善于利用各種關系攫取最大利潤的投機商,是納粹中堅分子,他感謝殘酷的戰(zhàn)爭,因為戰(zhàn)爭可以令他暴富,讓他具有德國人的優(yōu)越感,所以隨著劇情推進,導演調度斯特恩坐到一把椅子上,安排在景框的下方區(qū)域,而辛德勒則坐在了桌子上,位于景框上方區(qū)域。通過對兩人行動的處理完成兩人在景框內的區(qū)域位置安排,二人之間的強弱主導關系一目了然,身為德國人的辛德勒要比猶太會計斯特恩更有權力和優(yōu)越感。
已與納粹軍界打通關系的辛德勒請斯特恩幫忙向猶太人借貸,收購瀕臨破產的一家工廠,并轉產為生產軍用搪瓷產品。辛德勒雖是德國納粹黨員身份,但自己沒有錢,需要借助斯特恩籌集資金,兩人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導演斯皮爾伯格調度辛德勒至對面座位上,此時辛德勒不再處于景框上區(qū)域位置,而是和斯特恩處于同一高度上,從而在銀幕上完成了此時這一人物關系轉變。
(二)景框區(qū)域位置之中心與邊緣區(qū)域
景框中央?yún)^(qū)域的人或物是畫面的焦點,被安排在中央?yún)^(qū)域的人通常對景框內其他區(qū)域的人或物具有絕對的主導性。而景框內左邊緣或右邊緣區(qū)域因距離景框中央太遠,偏離視覺焦點,導演通常會將失勢、不重要、被忽視的人或物調度至這一區(qū)域。
會計斯特恩因忘帶工卡被誤抓送上火車,辛德勒得知后匆忙奔赴車站營救。此時的辛德勒人物弧光尚未展露,具有強烈的民族優(yōu)越感。于他而言,斯特恩只是他攫取猶太利潤的工具。在這次營救的過程中他霸氣十足,導演將此時的辛德勒安排在景框的區(qū)域中心。救下斯特恩后,攝像機正面跟隨拍攝辛德勒,辛德勒始終位于畫框的中央,昂首闊步,形象高大,而斯特恩和其他德國士官始終在辛德勒側后方顯得低矮。導演有意識地把斯特恩和德國士官“擠壓”在了畫框左下角,通過強化辛德勒與其他人物的位置關系突出辛德勒的主導地位,使得辛德勒與德國士官、斯特恩之間的關系一目了然。
二、空間距離與人物心理關系
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將人類之間距離的關系分為四種:親密距離、個人距離、社會距離、公眾距離,每人都根據(jù)親密關系保持相應的空間距離。電影中,這種距離關系也被用于描述人與人之間的心理關系。
在阿蒙與辛德勒對話的這場戲中,斯皮爾伯格就是通過兩人之間的空間距離,將兩人之間不斷變化的關系直觀地呈現(xiàn)在熒幕上。
辛德勒在山上看到納粹分子屠殺猶太人,被深深震撼到。回到工廠又發(fā)現(xiàn)工人全部被帶到納粹軍官阿蒙·戈斯的勞動營里。辛德勒十分氣憤,決定去找阿蒙理論。這場戲一開始兩人就處于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tài),導演將兩人站位調度至景框的左右邊緣處。
隨著對話的推進,阿蒙想要打破當前僵持的狀態(tài),他讓自己的猶太女傭海倫過來倒酒,海倫此時調度入畫給阿蒙和辛德勒倒酒。這一動作調度自然而然的引出阿蒙和辛德勒前傾的動作,兩人從座位上前傾端起酒杯隨后又回到原來位置,他們之間的距離發(fā)生改變,兩人之間的對立關系開始松動。
隨著對話繼續(xù)深入,兩人關系轉暖。阿蒙主動示好,稱贊辛德勒是懂得知恩圖報、有抱負的人,此時阿蒙上半身開始前傾。辛德勒對此心領神會,知道阿蒙想要索要好處費,兩人之間是可以合作。這時,辛德勒身體也開始前傾并拿起酒給阿蒙倒酒,阿蒙和辛德勒之間的空間距離縮短,兩人由的對立關系轉變?yōu)槔骊P系。
三、攝影機方位與人物內在關系的揭示
攝影機與演員有五種基本方位,正面、四分之一側面、側面、四分之三側面以及背面。從心理學層面看,每種方位都代表了不同的隱喻。
會計斯特恩通過辛德勒開設的工廠,以招工的名義將教授、科學家、工程師、牧師等猶太人換成技工的身份,為他們獲得生存的藍卡,外界盛傳辛德勒的工廠是猶太人的安全避難所。一名叫里賈納·帕爾曼的猶太女子因此前去求助辛德勒,請求辛德勒救出她的父母。辛德勒知曉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后大發(fā)雷霆,怒氣沖沖的去找會計斯特恩。
辛德勒奪門而入,指責會計斯特恩不應該私下通過工廠招工去營救年邁體弱的猶太人,這種做法會給辛德勒及其工廠招來橫禍。這是辛德勒內心真實的想法,所以指責斯特恩的過程中,辛德勒一直是正面面對鏡頭。此時斯特恩想辯解但又猶豫,不敢向辛德勒流露內心真實想法,所以斯特恩一直處于正側面方位,無法感知他內心真實的想法和感受。
直到辛德勒勸慰斯特恩應該體諒阿蒙工作的不易,內心的憤怒讓斯特恩不再沉默,他脫口而出:阿蒙還喜歡殺人。這是這場戲中,斯特恩第一次向辛德勒袒露心聲,第一次和辛德勒正面交鋒,也讓兩人不同的價值觀做了一次碰撞,此時斯特恩由側面轉為正面面對鏡頭。
當斯特恩講出阿蒙在集中營的暴行后,辛德勒內心無法直面這個殘酷的事實,他拒絕和斯特恩達成共識,也不想讓斯特恩感受到他內心的掙扎。辛德勒的站位不再是正面或者側面方位,而是調度至背面的方位,試圖隱藏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和感受。
良知最終讓辛德勒接納了斯特恩的做法。辛德勒開始理解猶太人內心的恐懼。他取下手表遞給斯特恩,讓他去隔離區(qū)把帕爾曼的父母帶出來。此時辛德勒由抗拒轉為接納斯特恩的做法,在方位調度上,辛德勒由背對斯特恩轉身調度至面對斯特恩,完成了兩人關系的轉變。
四、區(qū)域空間與人物權力主導關系
心理學和人類學研究表明,人的空間觀念與權力階層有關。人是有領域性的,一個人的主導性越強,擁有的空間也就越多,在特定的區(qū)域中,一個人的重要性和他所占的空間大小成正比。藝術源于生活,電影空間配置的原則也如此,角色的銀幕空間可以表達角色的心理和社會關系。主角通常擁有較大的空間,當主角對場面失去控制、喪失主導性時,空間會被壓縮。當銀幕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fā)生改變時,角色占有的銀幕空間也會隨之調整。
在辛德勒與斯特恩第一次談判中,盡管辛德勒手中既沒有資金又沒有人員,但因為他是德國人,是納粹黨員,所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在談判過程中一直占據(jù)主導地位,斯特恩和辛德勒兩人之間的這種權力關系,導演通過調度兩人在銀幕區(qū)域空間的占比來完成這一關系的塑造。斯特恩占據(jù)畫面小于二分之一的區(qū)域,反打鏡頭中,辛德勒幾乎占據(jù)整個畫面。斯特恩與辛德勒的雙人鏡頭中,辛德勒更是占據(jù)了絕對空間,從而強化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兩人的權力主導關系。
《辛德勒的名單》中,斯皮爾伯格正是通過這些嫻熟的場面調度技巧把人與人之間的隔離與仇恨、靠近和責任一一予以呈現(xiàn),也正是這些鮮活的銀幕形象、不斷變化發(fā)展的人物關系讓《辛德勒的名單》在二十年里成為經受住歷史考驗的作品,經典之至,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