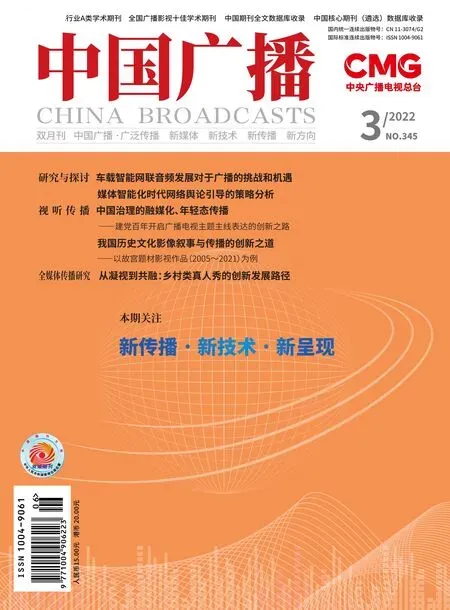視聽作品版權保護之探討
☉李艷芬
2021年6月,新修訂的《著作權法》開始實施。修訂后的《著作權法》第一章第二條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作品,無論是否發表,均享有著作權。第二章第一節第九條規定:“著作權人對自己的作品享有發表權、署名權、復制權、發行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17 項權利。”與修訂前相比,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增加了網絡等新型傳播平臺應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的內容,還提高了法定賠償數額、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等條款,以增加侵權違法成本、遏制盜版等侵權行為。同時規定,“單純事實消息”雖不涉及著作權保護,但明確要求傳播報道他人采編內容應當注明來源。
盡管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已經對當前諸多著作權可能面臨的糾紛進行了列舉,但在現實生活中仍然有部分作品無法界定其著作權,如通過技術手段模擬某些已故名人的聲音作品、大量因權利分散導致無法確權的音畫作品等,這是著作權實踐中存在的現實問題。
本文主要討論的是由作者獨立創作和帶有個人特色的視聽作品的著作權保護問題:如馬三立的單口相聲、劉蘭芳演播的評書、廣電主持人固定播出的談話類節目等。
一、視聽作品在網絡上海量呈現
互聯網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激發了視音頻工作者的創作熱情,海量存儲和多元需求也為創作者提供了創新空間。相較于視頻、制圖、文字等創作載體,音頻或許是最能獨立表達個人思想的媒介產品之一,因為投入成本小、操作簡單,錄制視音頻成了遠程教學的最先嘗試者。特別是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線上教學,世界各地都開啟了網課,應該說網課模式的普遍推行,就是技術革命帶來的成果之一。
一批學者、大咖都紛紛推出自己的視音頻賬號,在網絡上推銷傳播自己的思想理念。例如羅輯思維、樊登讀書、凱叔講故事等等,專門以“聽”作為傳播方式的移動客戶端、網站層出不窮,比如喜馬拉雅、蜻蜓等。這些網絡電臺和手機客戶端的推出,打破了廣播依靠技術傳輸覆蓋有限性的短板和劣勢,實現了公眾實時收聽異地電臺節目的愿望,這不能不說是科學技術帶給傳統媒體的顛覆性革命。
二、視聽作品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
《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人享有多項財產性權利,廣播權就是其一。新修訂的《著作權法》第二章第十條第十一項規定:“廣播權即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公開傳播或者轉播作品,以及通過擴音器或者其他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類似工具向公眾傳播廣播作品的權利”。按規定需要向作者支付音樂著作權使用費。關于此規定的解讀,媒體和行業協會始終存在分歧,媒體認為我國的專業音樂人或者作家創作的作品絕大多數屬于職務行為。媒體支付廣播權使用費應不歸屬于某個協會。雖然認識有差異,但從2010年開始,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簡稱音著協)與全國數百家電臺、電視臺達成音樂作品版權使用許可授權,結算方式已普遍得到推行。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2年春節聯歡晚會播出前夕,各地方電視臺就收到“非授權,地方電視臺以及各網絡平臺不得以拆條、轉播的方式進行播出”的通知。2022年北京冬奧會,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也通過授權方式,對冬奧賽事轉播等實行知識產權保護。2021年10月,北京廣播電視臺在業界發出《保護聲音作品著作權倡議》,倡議各類市場主體應充分尊重聲音作品創作者的智慧與付出,嚴格遵守聲音作品的著作權規則,遵循“先授權后使用,先授權后傳播”的財產權流轉原則,規范對聲音作品的各種使用行為。這種保護知識產權不被侵犯的意識,讓媒體人看到了維護知識產權的前景和現實價值,值得點贊。
2022年北京冬奧會轉播為保護知識產權提供了借鑒。據國家知識產權局介紹,打擊短視頻平臺公眾賬號未經授權提供冬奧賽事節目盜播鏈接、集中批量在網絡平臺上傳播冬奧賽事節目的行為,是冬奧會期間版權保護的重點工作,“授權”成為打擊盜版的關鍵詞。據統計,3363 個賬號因傳播涉冬奧侵權內容被處置,39個境外非法網站被關閉。可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人乃至全社會的關注和重視。
三、視聽作品版權保護存在的幾個問題
相較于自媒體,大部分傳統媒體版權保護意識略顯欠缺、措施滯后,后知后覺往往造成屢屢被侵權且維權艱難。比如,很難看到或聽到其他網站對羅輯思維平臺內容的分享。商業平臺的盈利模式輕而易舉解決了版權保護和知識付費的難題,這既是自媒體營銷的獨有方式,也是版權保護的一種策略。
2020年4月2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侵害知識產權及不正當競爭案件確定損害賠償的指導意見及法定賠償的裁判標準》正式發布,對賠償標準做出具體規定:網絡主播未經許可在網絡直播中播放或演唱涉案音樂作品,根據主播人員的知名度、直播間在線觀看人數、直播間點贊及打賞量、平臺知名度等因素,酌情確定賠償數額。根據此規定,有律師經過核算,一首歌曲如果被侵權,一般賠償不少于600 元,而原詞、曲著作權人賠償占比為40%、60%;如果原告為錄音制作者,每首音樂作品的賠償數額一般不少于2000 元;原告為表演者,每首音樂作品的賠償數額一般不少于400 元。即若各權利人同時主張權利,侵權人將面臨每首音樂作品至少3000 元的賠償。為此,網絡直播平臺紛紛推出使用音樂版權的結算辦法。2021年3月,快手公司對外公布了音樂版權結算政策,通過支付手段解決平臺詞曲版權的合法性問題,增加詞曲權利人的收益。騰訊公司則將目光投向了技術服務層面,推出了首款適用于網絡直播場景的正版音樂授權服務系統“音速達引擎”。通過技術手段,授權費用實時分賬,保障了上游版權方的權益。
傳統媒體受媒體屬性與從業者的職務行為影響,版權保護意識仍有待加強。相當多的作品,由于分工專業精細、參與人眾多,導致一部作品權利過于分散,在版權法律認定上,出現繁瑣復雜、難以確權的現實問題。在操作層面,筆者認為存在廣播電視節目是否應免費上網、廣電節目版權如何界定、視聽作品侵權行為的界定和舉證難等問題,提出并希望得到業內相關人士的探討。
問題一:
是否應免費為網絡提供廣播電視節目?網絡作為技術工具和載體,通過網絡傳播廣播電視節目已廣泛得到運用。傳播方式的改變為廣播電視節目擴大影響提供了全新的播出平臺;但是許多廣播電視節目并未申請版權保護,面臨勞動成果被網絡無償使用的風險。以廣播節目為例,此前一些省市電臺紛紛與喜馬拉雅、蜻蜓等平臺合作,通過移動互聯實現了異地傳播,但在利益分割方面商業網站及平臺和廣電媒體并未探索出有效的模式和途徑。初期,網站為了獨家壟斷,甚至不允許電臺與其他網站分享節目;后期,商業網站借助各省市電臺提供的海量節目以及節目點擊量加載廣告實現了運營變現,但提供內容生產的電臺節目生產機構和人員并沒有獲得多少效益。隨著融媒體技術的推進,一些廣播電視臺相繼推出自主研發的移動端或者網站,上傳本臺的廣播電視節目,極大豐富了網絡節目源。但廣播電視從業者卻并未因此而受益,反而淪為無報酬的網絡“打工人”。許多廣電節目也因未進行版權保護等相應維權措施,面臨盜版侵權的法律風險。
問題二:
廣播電視節目版權未完全清晰。新修訂《著作權法》第四章第二節第四十五條規定:“將錄音制品用于有線或者無線公開傳播,或者通過傳送聲音的技術設備向公眾公開播送的,應當向錄音制作者支付報酬。”但在現實中以音頻內容為主的廣播節目并無明確作品對應類別。這就導致司法實踐中音頻內容常常被認定為“錄音制品”,作品和制品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法律意義卻相去甚遠,導致以音頻為載體的廣播節目在一定程度上無法以作品形式加以保護。如一檔談話類節目,從策劃、欄目名稱確立,到欄目構架的搭建、子欄目的擬定,最后到片頭片花的錄制、互動環節的設計,所有這些僅僅是欄目的前期準備,需要創作團隊協同合作發揮集體智慧。等前期準備完成節目正式播出后,真正決定節目是否打響叫座,還取決于主持人的主持水平、駕馭話題能力和聽眾的反饋,更取決于媒體持續的投入、不斷的改進和長久的積累。假設這檔節目經營打造了數年終于成長為一檔品牌欄目,那么,這檔欄目的節目版權在法律界定層面往往存在意見分歧。據北京廣播電視臺副總編輯李秀磊介紹,該臺目前存儲的廣播節目約有25 萬小時,但具有獨立版權的音頻節目僅有3 萬小時。很多貌似屬于電臺獨家原創的廣播節目,因為多種原因而并不擁有獨立版權,權利分散、權利歸屬不明確都阻礙了電臺音頻產業的發展。
問題三:
侵權行為界定難度大。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將兜底條款修改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這種表述在司法實踐中讓司法機關對新作品的認定多了法律依據,但對侵權認定則更加謹慎,因為法律鼓勵并保護創新的態度和理念,對新作品予以支持。一部作品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需要具備三個條件,即獨創性、合法性和可復制性,其中,獨創性是被放在首位進行強調的。獨創性又稱原創性,是指作品由作者獨立創作的,是作者獨立思考和勞動的產物。例如評書表演藝術家單田芳去世多年,他的很多評書演播作品仍在保護期內。某網站通過機器人聲音模仿的技術手段,成功克隆單田芳聲音,并與其家人達成協議,取得授權。在此情況下,擁有單田芳原版評書獨家播出權的媒體就面臨維權難的現狀,其中對于網絡播出權是否等同廣播權、模擬聲音是否屬于技術創新、法律是應該保護創新行為還是應該歸為侵權行為等幾個核心問題,在實踐中都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和爭議。北京互聯網法院綜合審判一庭副庭長顏君認為:“實踐中,如何去區分表演者權和原權利之間的權利界限,假設朗讀者或者表演者對音頻內容有很高的貢獻度,其貢獻能不能作為一個獨創性的表達,必須要認真分析。”
問題四:
音頻作品被侵權,舉證難是困擾維權的最大障礙。版權司法糾紛中,音頻作品侵權后,給原告造成實際損失的舉證是困擾維權的最大障礙。對于文化精神類產品,實際損失是一個很難量化的指標。雖然目前司法實踐中,法院采取歌曲侵權每首賠償2000 元的標準,但是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音頻作品侵權后,要舉證造成的實際損失,難度要遠遠大于舉證其侵權行為。司法指導案例武漢斗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與音著協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就是實例之一。
案件起因是音著協多次將武漢斗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斗魚公司)以侵權為名告上法庭。其中一起案例顯示,2017年7月11日,在斗魚公司直播平臺上,主播“馮提莫”在相關直播過程中,播放了涉案歌曲《好運來》,直播時長約2 分55 秒。根據判賠要點,法院認為:斗魚公司侵害了音著協就涉案歌曲《好運來》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為此,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斗魚公司賠償原告音著協經濟損失2000 元及合理支出2000 元。除此之外,音著協多次起訴斗魚公司,但基本判決都維持每首歌曲賠償2000 元的標準。雖然勝訴,但是音著協并未舉證證明其遭受的實際損失和斗魚公司的獲益,這也成為被告不斷上訴的直接理由。
四、結語
盡管視聽作品版權保護中存在某些亟待解決的爭議焦點,一部法律也不可能解決現實生活中所有問題,但是隨著自媒體的蓬勃興起,視聽作品需求量呈現出井噴狀態,各類通過聲畫元素來傳遞思想內容的視聽作品也會層出不窮。相信通過文化產品的繁榮、人們版權意識的增強以及法律法規的健全,版權糾紛中出現的各種紛爭會迎刃而解,維護版權保護的法治意識也會越來越深入人心。
注釋
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0〕19號),360 個人圖書館,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1222/16/70808058_1009856126.shtml.
②《中宣部版權管理局:3363 個賬號傳播涉冬奧侵權內容被處置》,光明網,https://m.gmw.cn/baijia/2022-02/14/1302803758.html.
③侯偉:《“聲音作品”喊響著作權保護強音》,《中國知識產權報》,2021年11月2日。
④《直播中未獲授權能不能播放或演唱他人歌曲?或侵權》,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2020年4月25日。
⑤《主播侵權翻唱如何裁定?音著協狀告斗魚勝訴每首歌獲賠2000 元》,澎湃新聞,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7140760,2020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