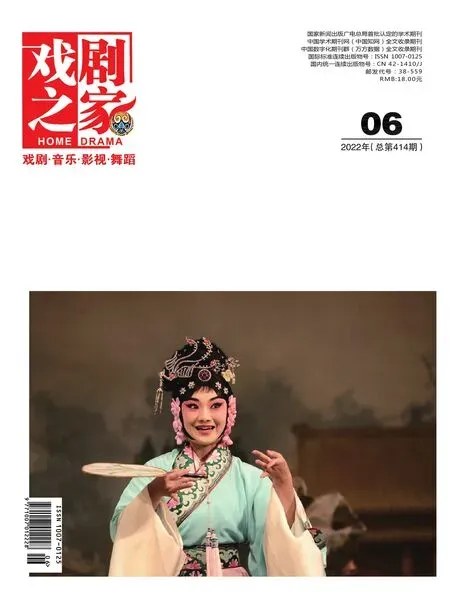《變臉》:巴蜀文化背景下的兒童戲劇與教育
邱齡浩
(遼寧大學 藝術學院,遼寧 沈陽 110000)
在中國傳統戲劇中,臉譜常用于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與思想感情。“變臉”作為川劇的表演特技之一,通過臉譜的轉變,來表現人物內心情感的變化,常常用于塑造人物。川劇《變臉》以“變臉”為名,一方面意在表現小女孩狗娃和變臉藝人水上漂之間,圍繞變臉這門技藝所展開的故事,另一方面意在表現社會各階層中那些會“變臉”的人,也通過人物的“變臉”來展現舊社會的黑暗并加以諷刺。
整部戲劇帶有濃厚的川蜀地區地域色彩與戲劇語言特色,作為一部兒童戲劇,川劇《變臉》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其文學劇本中的第二場,也被收錄于人教版九年級語文教材之中。
一、川蜀地域文化氛圍
兒童戲劇《變臉》圍繞川劇表演的“變臉”特技,依托小女孩狗娃的人生遭遇,向觀眾展現了川蜀地區的傳統文化與地域特色。
(一)戲劇場景與戲劇語言設置
在戲劇場景設置上,在戲劇的開場,導演設置了纖夫拉船的場景,以在舞臺上展現川蜀地區的勞動人民拉纖的生活場景,營造帶有濃烈的川蜀地域色彩的人文環境,并結合川蜀人民安逸的生活習慣,以及對于茶館的喜好,在戲劇中搭建了“茶館”“戲臺子”這樣的場景。
在戲劇語言設置上,劇作家充分運用了四川方言,通過極富地域性的唱詞,帶觀眾走進一個獨具四川特色的市集。如:
“跑灘要跑!叫賣要叫!鬧臺要鬧!高腔要高!……請嘗川味紅海椒!”以此引出了水上漂的川劇變臉絕技,也為這部戲劇作品注入了更多的生活氣息,更體現了四川人民豪爽的性格與灑脫的氣質。例如水上漂與梁素蘭在茶館喝茶時,用方言與唱詞輪番進行交流,以及水上漂一直掛在嘴邊的那句“有茶壺嘴嘴兒沒得”,這些戲劇語言帶有四川話獨有的語音語調,顯得十分生活化,更貼近觀眾的生活,也使得整部戲劇都帶有強烈的川蜀地域特色。
(二)“幫腔”的設置
川劇大師張德成說:“要懂得川劇,必須先懂得高腔,要研究川劇,首先應該研究高腔。”而幫腔則是川劇高腔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在中國傳統戲曲中類似于“旁白”的存在。
在戲劇語言中,旁白作為人物語言的一種,是角色暫離對話場景,轉而對觀眾或自己說的話。旁白通過聲音來交代劇情,幫腔常常用來推動戲劇發展,解讀人物內心,幫助人物說出他們不能說的話。
戲劇《變臉》對于幫腔的運用,也充分體現了“旁白”縮短情節的功能性與烘托氣氛的抒情性。
幫腔在戲劇開場的唱詞:
“道琴一響話滄桑,返璞歸真唱善良,請君試問川江浪,人情與之誰久長?”提到了“川江”,在開場即讓觀眾明白,這是一個發生在巴蜀地區川江周邊的故事。同時在唱詞中也點明了主題,即“人情”。在開頭即對觀眾提出問題,引發觀眾對于人性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的思考,讓其隨著戲劇情節的發展自己對這個問題進行解讀。
在《變臉》中,幫腔還對人物動作進行了解讀,例如,狗娃在水上漂睡著之后,拿出了臉譜,想要自己琢磨,幫腔即說道:
“娃娃好奇探秘密。”
唱出了人物的內心想法,也推動了劇情發展,縮短了情節,加快了戲劇沖突的發生。
《變臉》中,對于幫腔的運用最特別的一點在于,水上漂想要拋棄狗娃時,幫腔從臺前走到幕后,為狗娃說情。
“啊!幫腔幫她說句話,幕后走到臺前來!滿場觀眾也悲哀,要求老漢留女孩!”
其中幫腔以旁觀者的身份,向觀眾表明了立場,同時,幫腔的唱詞與行動也反映創作者的主觀情感,并且引導觀眾的心理情緒變化,增加了舞臺上演員與觀眾的互動,令觀眾參與到表演之中。
幫腔的出現與行動,也使得戲劇《變臉》打破了寫實主義所強調的觀演關系中的“第四堵墻”,達到了布萊希特表演體系所強調的“間離效果”,使戲劇成為可以直接對話的寫意性、開放性戲劇。打破了觀眾的沉浸幻覺,讓觀眾更加理性客觀地看待表演,對表演中發生的事進行思考。
二、兒童戲劇藝術特征
筆者認為,只要其出發點是為兒童服務,那么一切反映兒童生活并為兒童所接受和欣賞的戲劇都可稱為“兒童戲劇”。川劇《變臉》反映了小女孩狗娃的童年生活,故事內容十分淺顯易懂,能為少年兒童所接受,因此可以被稱為“兒童戲劇”。
(一)兒童戲劇特征
兒童戲劇與其他戲劇相比,其特殊性表現在接受群體上,即為3-12 歲的兒童群體。因此兒童戲劇的創作,要考慮兒童群體的心理接受能力與審美需求。其藝術特征主要表現為“兒童性”。
《變臉》的兒童性體現在通過川蜀方言戲劇語言的運用以及具有川蜀地域特色的場景鋪設,使得戲劇情節淺顯易懂,戲劇表現形式更加活潑鮮明,以及讓戲劇所體現的情感十分淳樸真摯,觀眾容易產生情感共鳴。
在情感上,《變臉》主要圍繞狗娃與水上漂這對爺孫之間的真摯的情感展開敘述。結合當今社會,兒童多為祖父祖母帶著長大的,往往祖孫之間有著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川劇《變臉》也能讓許多少年兒童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從而達到一定的演出效果。
美國著名的戲劇學者格林·威爾遜曾經說過:“幻想和游戲的一種正規化形式,就是戲劇。”在兒童戲劇中,為了貼合少年兒童的審美趣味,常常采用游戲的表演方式,也通過游戲來增加與觀眾的互動。例如在兒童戲劇《馬蘭花》的表演中,逃跑的貓會藏在觀眾席中,少年兒童觀眾會幫助演員來抓捕逃跑的貓,從而達成互動。在《變臉》中,運用“張打鐵,李打鐵,打把剪刀送姐姐”這樣類似于“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戲形式,加之富有四川地區傳統意味的游戲唱詞,展現了狗娃與水上漂這對爺孫日常親密的行為,與水上漂對于狗娃這個“孫子”的喜愛。
而在兒童戲劇中伴隨著游戲,也常常有著夸張的戲劇動作,例如唱詞到“小小船兒漂荷葉”這一句時,狗娃的動作更貼近兒童的日常生活,也使得狗娃稚嫩、充滿童趣的形象呈現于觀眾眼前。還有在捉迷藏時,狗娃躲在水上漂后面,兩人夸張的動作展現了兒童在游戲時開心的神態,也將水上漂對于狗娃的寵愛展現出來。
(二)兒童戲劇的教育功能
隨著國家教育政策的不斷優化,“大語文”的教學趨勢不斷深入,在我國,一部分具有先進的教學理念的幼兒園已引進了“教育戲劇”這一課程,將幼兒喜愛的故事繪本改編為戲劇的形式,讓幼兒參與表演,并在表演中學習知識,增長個人見識。在小學與中學的語文教材中也收錄了許多的戲劇劇本,例如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等。總體呈現出“戲劇進校園”這一趨勢,也體現出現今時代越來越重視幼兒的戲劇教育。《變臉》文學劇本中的第二場也被收錄于人教版九年級語文教材。
在《變臉》中,兒童戲劇的教育作用體現在戲劇中對于傳統文化與技藝的傳承。為了避免變臉技藝的失傳,水上漂努力尋找著自己的下一個傳人,狗娃對于變臉感興趣,想要學習這個技法,也體現了對于四川地區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精神。這其中的傳承精神極富教育意義,同時有利于提升少年兒童對于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視。
兒童戲劇也是培養兒童精神品質與生活習慣的重要手段之一。《變臉》中,通過對川江邊上拉纖的纖夫、集市上兢兢業業賣貨的勞動人民、賣藝為生的水上漂還有在社會底層生活的狗娃的描摹,體現了四川人民勤勞勇敢、吃苦耐勞的品質,與他們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變臉》中狗娃作為乖巧可愛、知恩圖報的藝術典型,可以讓兒童進行摹仿,并在摹仿中學習人物身上的可貴精神品質。
余秋雨在《世界戲劇學》中指出“戲劇是學習語言最好的方式和手段。孩子們在真實的語言交流場景中以戲劇角色的身份去聽和說,這尤其符合兒童學習發展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戲劇教育在兒童教育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兒童語言發展具有差異性,體現在語言獲得的早晚與語言發展水平的高低上。不同民族、地域的語言有著個性差異。戲劇《變臉》中,趣味性的戲劇語言、豐富的四川地區方言的運用,使兒童在對戲劇中的人物行動進行摹仿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接受了語言的教育。
《變臉》通過帶有地域色彩的戲劇場景與戲劇語言設置,依托變臉藝人水上漂與狗娃之間動人的情感,為我們展現了民國時期川蜀地區的社會現狀。通過戲劇語言與幫腔的設置,引發了觀眾對于“重男輕女”思想的理性思考,達到了布萊希特表演體系所強調的“間離效果”。
這部戲劇塑造了狗娃知恩圖報的人物形象,對少年兒童觀眾起到了教育作用的同時,也通過“游戲情節”的設置與夸張的戲劇動作,增強了作為兒童戲劇的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