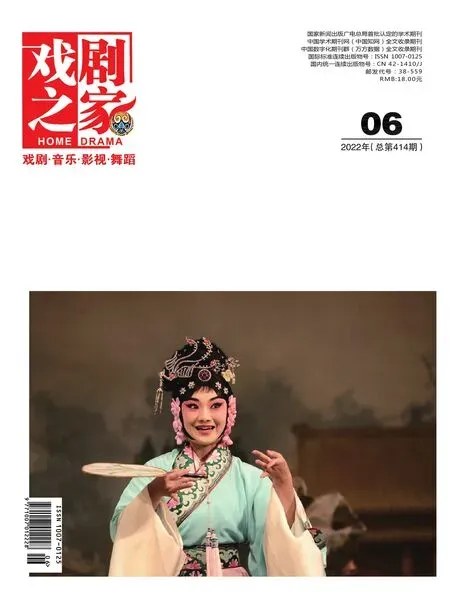淺析《一個人的朝圣》中的自我救贖與再成長
田 悅,喬沛然
(1.沈陽理工大學 遼寧 沈陽 110159;2.東北大學 遼寧 沈陽 110004)
《一個人的朝圣》是英國BBC 資深劇作家蕾秋·喬伊斯于2012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同年入圍布克文學獎及英聯邦書獎,并被譽為2013 年歐洲首席暢銷小說。其英文名稱為“The Unlikely Pilgrimage of Harold Fry”——“哈羅德·弗萊不可能的朝圣”。而小說的結局卻是一個歷時87 天,從英格蘭最西南徒步627 英里到英格蘭最東北的朝圣之旅。65 歲的哈羅德完成了看望患病老友最后一面的歷程。女作家喬伊斯運用樸實的語言、細膩的描寫、鏡像拉伸的手法令主人公哈羅德回憶起自己的一生,解放了自己過去二十多年來努力回避的記憶,通過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激發了哈羅德對生命的熱愛與渴望;旅行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使哈羅德認清了生活的本質,特別是在幾位女性的幫助下,哈羅德重溫生活的美好,慢慢完成了心靈的自我救贖。
一、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責任
自我意識是人對自身機體、思維、情感、意志等方面的認知,其中自我評價、自我體驗、自我調控是其重要內容。從心理學角度來講,自我意識與人的周圍環境密切相關,并且兒童時期的自我評價能力是自我意識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一個人的朝圣》中的主人公哈羅德從年少時期就經歷了母親的離家出走、父親的冷漠遺棄,他自己生活在陰暗與恐懼中無法釋懷,從小身心就帶上了被遺棄的烙印,沒有人喜歡。自己從兒童時期就得不到別人的關注,也無法了解人在不同時期應該承擔哪些責任。“小小年紀就學會了安身立命之道——保持低調,做個隱形人。”沒有個性,沒有特征,沒有同齡人正常的意識覺醒和感悟,即便哈羅德成人后,他按部就班地找工作—娶妻生子—贍養家庭—退休,但有時他發現“早年的沉默一直跟著他,進了他們的房子,藏身在地毯下、窗簾后、墻紙內。歷史就是歷史,你無法逃離你的出身,就算你戴上領帶你也不會改變。”“沉默”的哈羅德由于缺失父母的關愛而停止了自我的成長,無法理解責任之重。在他的兒子戴維兒時的一次溺水事件里,哈羅德沒有及時下水相救卻在岸邊停下來弄他的鞋帶。無情?冷漠?反正結果是救生員救起了戴維,從而導致了父子間的深度隔閡,因為這種遺棄感遷移到兒子戴維心里。戴維長大后,雖然讀完了劍橋大學,但一直以喝酒、吸毒等消極的反抗方式對抗著自己“沉默”的父親,以致后來抑郁癥發作而自縊身亡。哈羅德的沉默、平庸、麻木、機械仿佛是這個故事中父子關系的宿命。究其根本原因,哈羅德沒有自我意識,不知道如何表達自我,不知道如何與人溝通交流,更何況是如何承擔一個好父親的責任!害怕、擔心、無助一直圍繞著他。但從他收到好友奎妮的來信,并且堅持看望友人的歷程中,他逐漸打開了心扉,逐漸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不斷得到很多人的幫助與鼓勵,也學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思考了很多可以化解矛盾以及勇于承擔父親責任的方式。這種內在的勇氣和力量,來自對生命的尊重與責任,也是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哈羅德的妻子莫琳在朝圣前是一個自私的人。她自私到過度寵愛兒子戴維,無條件地贊同兒子的任何行為,從而維護他們母子的“親密”,而家里只要出現不和諧的聲音,她會隨時隨地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哈羅德的行為,二十多年的談話總是以“我不這么認為”而結束。直至戴維離世,莫琳認為作為父親的哈羅德難辭其咎。莫琳的自私、冷漠,嚴重地傷害了她與哈羅德之間的關系,導致家庭問題激化,生活壓抑,痛苦不堪。但正是這場突如其來的朝圣之旅,不僅改變了哈羅德,也促進了莫琳自我意識的覺醒,她開始思考自己對婚姻、對丈夫、對兒子的責任。伴隨著哈羅德的旅行,莫琳也開始反思自己語言行為的不當;學會理解哈羅德的身世背景造成的性格缺陷;學會從哈羅德的角度考慮問題而對婚姻的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
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贏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生態主義的發展衍生了生態哲學、生態神學、生態文學、生態藝術等領域,促成了生態文化的產生。生態文化從精神層面上促進環境與教育、科技,生態與哲學、神學、文學、藝術的交融,其中,生態文學是生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文學的特殊性在于迫使人類從人與自然的對抗—征服—報復的惡性循環中走出來,重新擺正人與自然的關系訴求,以文學形式表達出來。生態文學側重激發人與自然關系的內在情感反應,或對人類與自然的困境加以審美的解答,并探索人與自然發展的新倫理。女性作家喬伊斯將生態文學的主題巧妙地運用在《一個人的朝圣》中的自然描寫段落中,安排哈羅德在一個人的朝圣之旅中與大自然親密接觸,感受大自然的愛與力量,接受大自然的陽光與陰暗,溫暖與寒意,舒適與挑戰。眾所周知,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不僅為人類提供豐富的物質資源,也為人類提供豐富的精神歸屬。人的自我意識在對大自然的順應與抗爭中得到展現與覺醒。哈羅德的人生創傷導致他一直生活在自我否定、自我療傷的循環里。為了給友人帶來求生希望的一次徒步之旅將這位自我封閉、沉默的老人帶入了活力盎然的大自然中——沿途的植物、花卉、曠野、高峰、森林、河流、谷地、淺灘以及難以名狀的事物,都像是生命的種子在發芽,重新激活了哈羅德的生命!他竟然買了一本《野生植物百科辭典》,認出了數不勝數的植物。作家筆下“一云云黃色連翹,一道道紫色庭霽,都叫人驚詫不已。嫩綠的楊柳風中微擺,流光溢彩……聰明豐富的新生命一下子把哈羅德弄得眼花繚亂。”大自然用它溫柔的色彩,使哈羅德重拾對自然的陶醉與激情,令他回憶起曾經的美好歲月。一輩子生活在家—車上—酒廠三點一線的“沉默”的哈羅德終于可以走出曾經的桎梏,自我意識在接近大自然的進程中得以舒展。不再擔心自然界的危險與冷酷,能夠安心適應野外的生活,對哈羅德來說意義非凡!
三、女性之光的鼓舞與影響
女性作家借助女性的力量為主人公哈羅德的朝圣之旅添磚加瓦,引領照明。在哈羅德的成長過程中,他那個冷酷無情、自私狹隘,毫無責任感的母親在他兒時沒有給他帶來女性的光輝,而在他成人之后的再成長的道路上,卻體會到了女性的善良、豁達、愛心、召喚。哈羅德在釀酒廠工作了40 多年,一直默默無聞,沒幾個朋友。工友奎妮是一個樸實、善良、替他頂過罪的姑娘。作家安排這樣一個女性的臨終告別信,直擊他的內心,因為他覺得寫幾句安慰的話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實心意。但當時他仍有點茫然,不知所措。緊接著在經過加油站的時候,加油站的女孩兒說:“人的大腦里有太多的東西,我不明白。但是人都有信念,只要你相信她能好就可以了。”這一句鼓舞的話語猶如一束光照亮哈羅德的內心,他毅然決定徒步去探望他的好友,并且堅信只要他走一天,奎妮就會多活一天。接下來遇見的餐廳女服務員也對哈羅德說,“我一直很想試一試,但是從來沒有成功地開始過。人的一生需要瘋狂一下,要不日子就沒有盼頭了!”確實,從平庸到拖延,人就是這樣拖拖拉拉一輩子。旅程中的艱難使哈羅德的雙腳潰爛,但是他得到了一個來自斯洛伐克的女醫生瑪蒂娜的幫助。盡管她的生活也是那么困頓、拘謹,但女性的親和、涵養以及細致的救助和安慰,使得哈羅德的精神萌發了新生的力量。尤其在旅程的后半段,哈羅德也崩潰過,他也想就這樣放棄,回家。他在給莫琳的電話中說,“我是不可能做到了,我不想繼續走了。”那個曾經對他很漠然的妻子,由于內心的自我救贖和覺醒竟對哈羅德大喊“繼續走,別停下來,還有十六英里就到貝里克了,你可以的!走下去……”在自己失意和沮喪時,能得到妻子的支持和鼓勵,還有什么比這更寶貴,更動聽的言辭呢?而此刻的莫琳也非常渴望哈羅德能馬上回到家!然而她也知道,如果在目標很近的情況下讓他放棄,他的余生都會后悔!愛他(她)就要彼此了解,希望他(她)余生沒有遺憾。最終莫琳陪同哈羅德探望奎妮,完成朝圣之旅。兩人也從此解開了心結,彼此接納,心靈得到了救贖。在小說結尾處,兩人手牽著手,沿著海岸,伴著浪花,笑意盈盈。
四、結語
人的一生注定要經過無數個十字路口,有時會彷徨,有時會無奈,有時會沮喪,甚至遺憾!不論是人際交往,還是日常處事、婚姻生活等,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麻煩,遭遇變故。學會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內心裝滿愛與信念;面對現實,積極把握,什么樣的人生都會有最完美的結局。無論自我救贖與再成長的感悟來得多么晚,但對于個人的意義與價值都會不同凡響,令人贊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