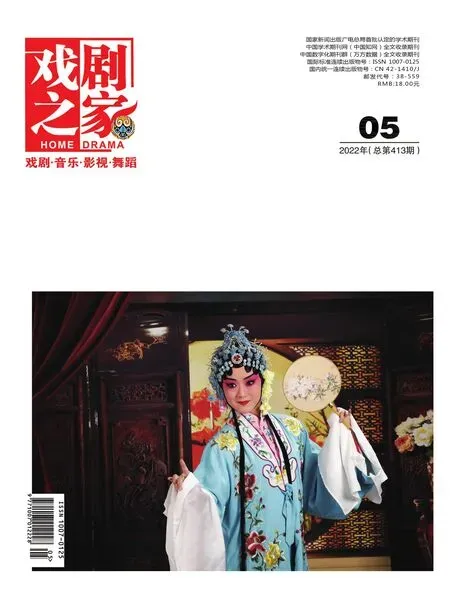淺談中國民族室內樂的發展史
陸 洋
(黑龍江藝術職業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中國民族室內樂與民族交響樂隊相比規模較小,曲目結構短小,體裁較為豐富,創作空間廣闊,在音樂領域有一定分量。西洋室內樂在教堂音樂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成型,通常由2-4 種或更多器樂合奏音樂作品,各樂器單獨負責一個聲部,可演奏弦樂三重奏、小提琴二重奏、鋼琴四重奏等音樂作品,其定義中無獨奏、獨唱有關內容,并不包括合唱、管弦樂合奏等類型的樂曲。西方室內樂可追溯至16 世紀初期,我國室內樂歷史要早于此,只是未能用名詞予以概括。然而,在音樂史研究中卻存在中國民族室內樂研究頻率低、內容不系統等問題,這有礙中國民族室內樂的發展。基于此,為使新時代中國民族室內樂能被更多人接納,探析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史顯得尤為重要。
一、溯源中國民族室內樂
室內樂創作追求精致且較為復雜,復調音樂在創作中較為常用,音樂情感具有細膩性與含蓄性,作曲者思維縝密并能駕馭編曲技巧,演奏者表現力較強,同時能互相配合。中國民間民族音樂與中國民族室內樂存在區別,后者結構嚴謹并較為復雜,通常不即興演奏,作曲家獨立完成樂曲創作任務,演奏者專業水平較高,前者則對曲式結構并無過高的要求,多為即興創作,是集思廣益下的藝術結晶,對演奏者專業技能水平亦不做過多要求。通過資料分析可知泉州南音、廣東音樂、江南絲竹、山西八大套等地域性音樂類別歸入民間民族重奏音樂之列,并不屬于中國民族室內樂。
民族器樂自夏商時期開始發展,周代器樂種類增多,根據樂器材質及工藝用八音分類,此時還出現了七聲音階與十二律。通過對《詩經·周南》等詩歌及歷史文獻進行分析可知,民族樂器自周代逐漸成型并在室內演奏,重奏亦是民族樂器演奏形式之一,期間配器有組織性,演奏所需資料更多。《中國音樂簡史》指出,宮廷音樂源于周代,主要分為兩種:不設樂懸房中樂和大型房中樂。燕樂屬于宮廷樂舞一種,在伺宴時由后宮嬪妃演唱,用瑟、琴等撥彈類樂器伴奏。《中國音樂詞典》對“房中樂”有解釋,可將其視為中國民族室內樂的雛形。秦創建“樂府”,秦滅后“樂府”在漢代繼續發展,漢武帝時期擴建,并培養諸多音樂家,從民間網羅音樂藝人,滿足宮廷娛樂需求。“樂府”為民間音樂發展做出極大貢獻,在搜集民間音樂作品同時分類整編、創作、演唱、演奏。宋代“樂府歌詞”被郭茂倩分成了12 類,“相和歌”為第5 類,據《晉書·樂志》記載其由琵琶、琴、笛等樂器演奏,同期出土文物有“瑟”“竽”,印證了當時“相和歌”的演奏方式。《中國音樂詞典》指出,絲竹泛指管弦樂器或音樂。中國民族室內樂通過絲竹組合的方式不斷發展并誕生了新的器樂合奏形式。
唐玄宗時期依據宮廷音樂表演形式分成“立部伎”和“坐部伎”兩類,后者在室內表演,人數從幾人到十幾人不等,創作許多新作品,龜茲、西涼及其他的少數民族樂器在伴奏中起到重要作用,前者與后者的區別在于,前者強調展現個人技巧,樂曲表現細膩優雅,通常4 人一組,這可視為舞臺演奏模式的發展基礎。南宋時期教坊樂隊規模縮小,箏等樂器加入其中,形成了趨近于民族管弦樂演奏編制的四類聲部,其間小型樂器合奏在民間廣受歡迎,如小器樂合奏、清樂、細樂等,笛與鼓、葫蘆笙與秋琴、阮咸與雙韻及其他的器樂配合形式較為常見,有時加入水盞、札子等樂器。明清時期音樂文化不斷發展,絲竹樂、鼓吹樂等合奏形式較多。鴉片戰爭后中國音樂步入近代發展時期,民族器樂合奏形式有所創新,民族音樂創作活力逐步超過民間民俗音樂。八國聯軍入侵后,西方音樂涌入中國,對“廣東音樂”“江南絲竹”等音樂形式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至此,中國民族室內樂演奏形式更加多樣且穩固,從“房中樂”“絲竹”到“坐部伎”,再到小型樂器新型合奏模式,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有以下特點:一是本民族器樂廣泛應用,在器樂創新的同時擴編室內樂隊;二是始終在堂上或室內演奏,空間有特定性,演奏人數幾人到十幾人不等;三是演奏作品均為原創,同時以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為底蘊;四是在注重個人演奏技藝的同時更關注合奏效果,這使得中國民族室內樂演奏日益規范。
二、中國民族室內樂的發展
20 世紀初西方音樂及樂曲創編技法進入中國,推動合奏曲發展。以《變體新水令》為例,最初樂譜上僅有旋律譜,在借鑒西方音樂創作經驗后逐段標注主奏樂器,楊蔭瀏1943 年從《劉天華先生紀念刊》中得到原譜并標明器樂提示,使合奏總譜更加完善。上世紀50 年代我國民族器樂處于萌芽期,民間藝人組成藝術團體,通過專業培訓成為演奏員。受傳統音樂文化傳承方式影響,因僅記錄骨干音,加之作品處理源于口傳心授,所以曲目理解要依靠演奏者自行體悟,這使得傳統樂器演奏存在即興、結構冗長等特點。建國后,國家加大民間、民族、民俗音樂史料的規整力度,陸續編輯并出版樂譜,這使得傳統樂曲得以有固定的形式流傳推廣。陸華柏先生于1953 年依據劉天華二胡曲目創編三重奏《光明行》《空山鳥語》等作品,將鋼琴、三弦、二胡視為合奏主體,同期雷雨創作古箏、高胡三重奏作品《春天來了》《豐收舞曲》(張世瑞)為琵琶、二胡二重奏,《南泥灣》(趙德震、馬可)為古箏、二胡二重奏,這說明中國民族室內樂在建國后得以蓬勃發展。
20 世紀60 年代,民族樂器發展前景廣闊,曾經的西洋樂隊演奏者許多主動改學了民族器樂。受“文革”影響,中國民族室內樂乃至整個民族音樂發展遭遇“寒冬”,傳統樂器被看作是舊社會遺存的一部分,得不到人們的認可,許多民族樂器演奏者改學西洋樂器,使中國音樂史上民族器樂歷史存在一段空白期。雖然“文革”時期對“傳統”的東西較為敏感,但這亦成為器樂及音樂作品創新的動力之一,促使民族器樂與西方音樂交融碰撞,借鑒歐洲室內樂演奏方式及創作技法,同時將西方作曲、重奏等知識引入課堂,為“絲弦五重奏”新型合奏形式的誕生給予支持。胡登跳先生借鑒西方作曲技法,如復調、曲式結構等,用古琴、揚琴、中阮、琵琶、二胡創作絲弦五重奏作品,如《躍龍》《歡樂的夜晚》等,時至今日許多作品依舊深受人們喜愛。
20 世紀80 年代,《天籟》(何訓田)首演引起極大的爭議,同期劉德海(中國音樂學院民樂系教授)組建“女子彈樂五重奏”。“華夏室內樂團”于1986 年成立,民族音樂在現代音樂史中不斷發展。“長風國樂團”由鄭曉慧女士于1984年創立,還舉辦了民族室內樂比賽,為優秀民族室內樂作品的誕生提供沃土。上世紀90 年代,《秋問》音樂會成功舉辦,創作者瞿小松指出,應“倡古之古,新之新對”,強調凸顯音樂的人文關懷屬性,使人們能重視音樂的歷史價值及現實意義。民族室內樂及樂團的發展是推動相關歷史進步的重要條件,如“華韻九芳”“卿梅靜月”“幽蘭三重奏”等樂團在全國掀起了解、演奏、研究與創作中國民族室內樂的熱潮。西安、上海、北京等地的音樂學院開設民族室內樂有關課程,這使得中國民族室內樂走上了規范化及專業化的發展之路。
21 世紀民樂受到追捧及廣泛關注,中國民族室內樂走上國際舞臺。2003 年“暢想絲竹室內樂團”(臺灣省)向黃振南、孫沛立等音樂家委約民族室內音樂會作品,該樂團舉辦的音樂會極為成功,使中國民族室內樂知名度與美譽度有所提高。同時,民族室內樂賽事亦是助推此類音樂發展的動力,如“TMSK 劉天華獎中國民族室內樂作品比賽”等,使人們能用更為專業的角度看待中國民族室內樂。
三、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路徑
(一)重視歷史,保障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一脈相承
中國民族室內樂與西方室內樂存在差異,以中國歷史文化、人文底蘊、自然環境、政治經濟等因素為支點不斷發展。雖然新時代國際文化交融碰撞,但中國民族室內樂依舊需保留獨特風采,這就需要重視歷史,理順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思路,在溯源的同時可關注器樂、聲樂、獨奏、重奏、編制等方面的問題,使歷史性研究更為細致針對,為以史為鑒發展新時代的中國民族室內樂奠定基礎。
(二)加強創新,助推中國民族室內樂與時俱進
音樂是充實國民精神世界的重要藝術形式,為使中國民族室內樂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愛,需基于新時代主流審美觀及價值觀謀求發展之路,加強創新、勇于嘗試、累積經驗,例如可在中國民族室內樂中引入電子樂元素,為其編曲、器樂重奏等方面的創新拓寬思路,使中國民族室內樂更具生機活力。
(三)培育人才,為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提供必要條件
通過對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歷史進行分析可知,教育力量的引入是助推相關歷史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指引中國民族室內樂走上正軌。無論是建國初期針對民間藝人的規范化培訓,還是音樂高校有關教材的開發與利用,均為專業人才認識、賞析、演奏、研究中國民族室內樂并傳承傳統音樂文化疏通了渠道。基于此,新時代需發揮專業院校的育才作用,強化中國民族室內樂教育指導師資力量,加強相關教育改革,豐富教法、科學評價、資源整合、理念升級,繼而培養出更多敢創新、重傳承、技術強、素養高的優秀人才,為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提供人才保障。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中國民族室內樂是我國音樂藝術范疇重要的一部分,對相關歷史進行研究可為中國民族室內樂發展給予經驗支持,在此基礎上能指引新時代中國民族室內樂的發展方向,保留本國音樂韻味,同時立足新時代創新爭優并培育更多人才,使中國民族室內樂能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