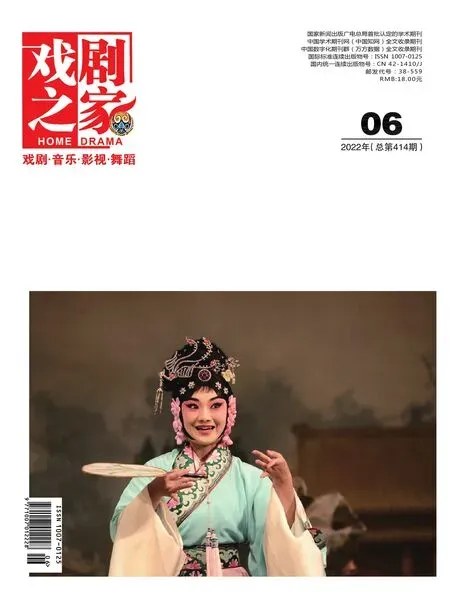一個姐姐的自我和解
——從精神分析視角看《我的姐姐》
鐘煒靜
(中山大學 廣東 廣州 510275)
一、《我的姐姐》中的安然形象
雖然電影的命名是從弟弟的視角出發,但是鏡頭更多地跟隨姐姐安然,通過聚焦安然的自我在本我、超我以及現實的拉扯中搖擺前進的過程來推動劇情的發展。因此,這部影片的主角毫無疑問是姐姐安然。
安然的童年是灰暗的,相較于備受寵愛的弟弟,她只因性別為女便遭到父母的粗暴對待。她在少女成長的關鍵時期被父母要求假裝殘疾,正是愛美的年紀卻連裙子也只能偷偷地穿……十年過去,脫離原生家庭的機會終于到來了,她卻因高考志愿被父母偷偷篡改而無法逃離。于是當被父母告知“家中的一切都屬于你”的弟弟安子恒聽到姐姐安然的經歷的時候,他天真地問:“為什么我們爸爸好像不是一個人?”
雖然姐弟的父母都是同一人,但父母面對不同性別孩子的雙重面孔卻讓安然痛苦不已。從小便缺少父母的寵愛,使安然對于家庭和親情充滿了向往。于是,盡管安然明知獨自北上讀研是最好的選擇,但在家庭和血緣的聲聲呼喚中,最終選擇了順應母性的本能,試圖兼顧弟弟的成長與自己夢想的實現。
二、本我的原始沖動
“本我”來自于人格最深層,它遵循享樂原則,無關理性,只求本能的滿足。
安然第一次見到弟弟安子恒是在他們父母的葬禮上。相較于姐姐的沉默隱忍,年幼的弟弟面對至親的死亡顯得十分懵懂。接著鏡頭一轉,當親戚們忙著處理父母遺留下來的學區房的時候,安然經年累月的對于原生家庭的不滿突然爆發了。飽受“重男輕女”思想觀念摧殘的安然對父母的差別對待深有怨言,然而父母去世之后,她仍然處于“姐姐”身份的桎梏下。面對這些眼前要求自己撫養弟弟成人的親戚,她反復地在親戚面前重復著:“我要學區房,我要去北京,我要離開這里”,最終她的怒氣達到頂峰,她甚至與大伯父爆發了肢體沖突。
然而,仔細分析安然的沖動行為便會發現,安然看似脾氣很差,沖動易怒,但她的怒氣其實精確地對準了她的父母以及她的親弟弟安子恒。相較于她面對親戚的惱怒,對父母埋怨的態度,她對于弟弟的情感表達顯然要更為外放。安然在影片的一開始仿佛將她的弟弟視作敵人,急于擺脫他,譬如將弟弟喜愛的玩具盡數丟棄、動輒推搡弟弟、執著地為弟弟尋找一個領養家庭……影片開始不久,姐弟之間已經爆發了好幾次沖突。
弟弟安子恒是在安然上大學之后才出生的,他理應與安然沒有太多的直接矛盾。但在弟弟出生前的十幾年,備受父母打壓的安然針對那還未來到這個世上的弟弟的愛與恨的情感已經萌芽了。而且由于這個尚未出生的弟弟,她人格中渴愛的本能無法被父母滿足,于是,成年后,當“弟弟”這個實體真正靠近她的時候,安然累積的情感有了發泄的對象。由此可以看出,安然采取的這些行動背后最本質的還是對于自己幼時無法得到足夠的愛的補償,以及對重男輕女的父母的報復。
安然不時的情感爆發以及面對安子恒時的沖動作為其實都是非理性的,而且并不符合中國忍讓內斂的民族性格以及重視血緣的倫理道德。她的所作所為都在順應本能最原始的沖動,沒有考慮結果,她只求壓制弟弟的反抗行為以及在壓制成果顯現的同時取得直接快感。
倘若追溯至安然深藏的被壓抑的無意識,可以發現她行為的動因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她童年的遭遇。在她年紀尚小的時候,她的父母便對她十分嚴厲,要求假裝殘疾騙過計生人員。她也曾試圖反抗父母在家中設立的權威,譬如在計生人員家訪的時候穿上裙子——但那天她卻因此受到了父親前所未有的憤怒責罵與毆打。此外,根據弟弟的存在可以推斷,恐怕安然自那以后便老老實實地假裝殘疾,服從于父親的權威之下,直到她的父母獲得了生育二胎的資格。隨著年紀漸長,這段經歷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記憶里,而且在她沒有意識到的內心深處,她幼時渴望反抗父親權威、取代父親建立新的家庭規則的愿望成為她的潛意識的一部分。可以說這個與童年經歷緊密相關的“俄狄浦斯情結”仍然對她造成影響:從前她的父親壓抑她的愿望,要求她順從,將她的一切都贈給弟弟,那么現在的她希望奪回她應得的一切,壓制弟弟的反抗行為,使弟弟服從于姐姐的權威,就像幼時她服從于父親的權威那樣。她在父母在世時被壓抑下來的對于弟弟的嫉恨在本我的作用下得到了宣泄,有意無意的,她對于弟弟的嚴厲管教與從前的父親有許多相似之處。
安然的“本我”促使她忽略社會主流的道德規范,遵循本能對弟弟釋放出她被壓抑多年的對于家庭的不滿。
三、超我的強大束縛
雖然安然期望能夠擺脫父母留下來的親情羈絆,但她注定無法隨心所欲。
“超我”作為道德化的自我,遵循著道德原則,它的形成與后天的教育和社會環境相關。在安然的成長過程當中,父母的要求以及社會規則已經內化為她的一部分,而這些都在她的“超我”的建立過程中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安然家庭中“重男輕女”的氛圍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這是整個社會、整個家族幾代人傳承下來的固有思想觀念,他們早已經習以為常。“重男輕女”這個思想,在人類社會中已經流傳了上千年,在潛移默化當中對社會成員施加著影響。譬如安然在醫院中負責的那個患有孕期子癇的產婦,即使已經有了兩個女兒卻依然選擇拼上性命去賭一個兒子。當孕婦被送上救護車的時候,她的婆婆和丈夫卻都懷著“盡力賭一個兒子”的迫切心態而對安然的哭喊和勸說無動于衷。由此可以窺見“重男輕女”思想的社會影響有多么廣泛。
安然一家也同樣受到這個思想的影響。在安然幾次提出要脫離弟弟的束縛、去北京讀研實現自己成為醫生的理想的時候,同為女性的姑媽的反應反而最為激烈。姑媽苦口婆心地教育安然“長姐如母”,她認為姐姐為弟弟無償奉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實際上,她也確實將這一觀念落實在了行動當中。考上西師大的姑媽為了考上中專的安然父親放棄了繼續念書,她為了弟弟簽字放棄了學位房的繼承權,當年為了照顧初生的安然,她甚至放棄了在俄羅斯做生意的機會回國開了個小店。姑媽看似作為一個完美的“姐姐”既無私又偉大,但當她撫摸著俄羅斯套娃的時候,她那落寞的目光以及喃喃的幾句俄語,已經展露出她內心不愿承認的遺憾和無奈。其實她對于自己的人生選擇并非那么滿意,但自奶奶那里灌輸的思想,使她屈從于既定的命運。于是,姐姐這個身份對姑媽而言是一個在來到世界的第一天便已經準備好的模板,她認定“我是姐姐,從生下來那天就是,一直都是”,既然身為長姐,她的出生意味著父母必定會再要一個男孩,而她也一定會需要承擔姐姐照顧弟弟的責任。
即使清醒獨立如安然,她也仍然受到這些道德準則的影響,在行為之后進入“姐姐”的身份。譬如當弟弟受傷后撒嬌要她背回家的時候,她雖然猶豫但也照做了;當弟弟要求她幫忙系鞋帶的時候,她也蹲下去照辦了;當弟弟想吃肉包子的時候,憤怒歸憤怒,但她還是去便利店買給他了,甚至最后她為了弟弟學會了自制肉包子。而當弟弟幾次有機會被領養家庭接受的時候,安然的超我屢次出現,通過無意識的罪惡感對她進行支配。于是她數次落淚,糾結反復,頗有不舍之意。安然期望擺脫既有生活的決心無人能夠否認,她也清楚地知道承擔教育撫養安子恒的責任和她去北京追夢的計劃是沖突的,但每當她選擇順從內心的尋夢的沖動之時,遵循著道德原則的超我便出來對她的行為做出批判與譴責,使她對于弟弟的態度忽軟忽硬。
超我與本我雖然都離意識很遠,但是對于自我的影響很大。因此,無論安然的理性所處的立場和觀念如何,它們都對她的目標實現過程造成偏移。
四、自我的平衡實現
“自我”是人格結構的中心。人的意識隸屬于自我,自我也控制著能動性,它遵循現實原則,與遵循享樂原則的本我相矛盾,但它也習慣于把本我的意志轉變為行為。同時,超我以道德的形式或無意識的形式支配自我。②可以說,自我作為意識與外在世界接觸的代表,調和著來自社會、本我和超我的不同意志。
隨著與弟弟相處時間的變長,安然對于弟弟的態度漸漸軟化,主動承擔了對弟弟的教育責任。而在安然的教導下,弟弟也由一開始的驕縱任性慢慢變得聽話懂事。隨著情感交流的增加,他們在彼此心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但安然仍然對自己被父母篡改的志愿耿耿于懷。于是安然仍然鍥而不舍地為弟弟尋找領養家庭,并在弟弟故意鬧出事故拒絕去領養家庭之后再次回到了之前對弟弟冷漠嚴厲的狀態。然而,安然的自我能夠調節自身以及所處的環境,在現實原則下滿足本我的要求。于是當弟弟端著泡好的姜茶到她床邊之后,雖然她被懂事的弟弟所感動,沒有拒絕弟弟主動的肢體親近,但面對弟弟的撒嬌,她仍舊表達了她去北京讀醫學碩士的決心。這時,安然仍居于矛盾狀態,面對親情和理想,她無法做出最終的決定,她的自我依然沒能平衡本我與超我。
對于安然來說,除了弟弟安子恒,她那因車禍去世的父母也是她的心結所在。安然對于父母的感情相當復雜,他們對她動輒打罵,對弟弟嚴重偏心,還私自更改她的高考志愿使她與觸手可及的理想失之交臂……面對父母的所作所為,自從她的自我意識覺醒以后,她對于父母是有恨的。而當她聽到表姐說那天早上自己的父母本想打電話給她,但是因心肌梗塞造成汽車失控而意外身亡的時候,盡管她依然無法輕易原諒父母,但對鮮少與自己交流的父母突然有了幾分愧疚。而當她在與弟弟相處的過程中,在親情的影響下,她回憶起了從前夏天與父母一同玩水、母親幫年幼的她洗頭的溫馨片段。自我受到本能的影響,存在著可以被置換的能量,因此當現實發生變化以及安然經歷增加,當其對于父母和弟弟的劇烈對抗被克服之后,她以前所恨的對象成為她所愛的對象。在數次的愛與恨的轉化之后,安然對于親情和倫理道德的認可度飛速上升。于是,她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父母的墓前,在淚水中說出了內心真實的想法:“我努力生活,只是希望有一天能得到你們的愛和認可”,并撕碎了為弟弟誕生提供條件的“殘疾人證明書”。安然在墓前的內心獨白以及撕碎那張殘疾人證明的舉動,象征著安然最終選擇與家庭和灰暗的過去和解,相比起對家庭的恨,愛占了上風。于是當血脈相連的弟弟為了安然的前途主動前往不允許安然和弟弟再次見面的領養家庭的時候,安然丟下了存有二十萬的銀行卡,拉著弟弟跑出了領養家庭。
《我的姐姐》是一個開放性結局,影片的最后一個鏡頭停在了安然和弟弟一同踢完球后緊緊擁抱的身影。回想影片的開頭,安然反復強調她為弟弟尋找領養家庭是為了給他一個更好的家。依照計劃,安然晚上將要乘坐飛機前往北京,但在如此接近夢想的時刻,安然卻無法放下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親弟弟。奇怪的是,倘若弟弟安子恒能夠順利被領養家庭收養,那么這對于安然的追夢計劃以及安子恒的成長都是有利的。當年幼的弟弟都傾向于選擇離開姐姐被領養家庭收養的選項時,安然反而成為姐弟中不理智的那個。究竟是弟弟無法離開姐姐,還是姐姐無法離開弟弟?或許,還是安然內心深處渴望完整家庭和親情的本能作祟。即使是一個年幼、需要她照顧的弟弟,她仍然期望能夠從他的身上得到來自以血緣為紐帶的原生家庭的一部分親情補償。但她也依然無法放棄自己的理想,于是她也沒有放棄乘上飛往北京的飛機。
在結合多種因素之后,安然的“自我”在遵循社會道德準則的“超我”以及遵循享樂主義的“本我”中間選擇了一個微妙的平衡點。
事實上,在父母去世、與弟弟安子恒同住以前,安然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處在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她對于父母懷有恨意,對于與男友一同去北京讀醫學碩士的理想非常堅定。雖然它們三者的力量時有變動,且偶爾會有摩擦,但安然還是能夠心無旁騖地依照自己的未來規劃行動。然而家中突發的意外使她不得不將弟弟也納入她的生活當中,而弟弟的存在打破了安然在之前十幾年保持的人格結構的平衡,使她不得不對自身的人格結構重新進行調整,直到在自我的調控下達到新的平衡。
五、總結
《我的姐姐》的選題十分新穎與大膽,這或許是中國首部以“中國姐姐”這一沉默而龐大的群體為切入點的大眾商業電影。不過,它的劇情走向和故事結局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重男輕女”思想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也仍然盛行。對于許多女性來說,“姐姐”這個身份是對于她們的規訓,迫使她們放棄自我價值的實現,不得不將自己的人生拴在弟弟的身上。鑒于題材的特殊性,在觀看電影以前,那些在現實社會飽受封建思想摧殘的觀眾期待影片的女主角安然能夠脫離“姐姐”的身份,實現現實中“姐姐們”無法實現的理想。然而,安然卻由一開始充滿攻擊性與個性的女孩,最終變成了愿意親自承擔撫養弟弟的重任的溫柔姐姐。當她將要啟程去北京圓夢的那日,她轉而將賣房得來的二十萬贈與弟弟的領養家庭,拉著弟弟憤而離開領養家庭。在安然放下二十萬的那一刻,弟弟的重要性甚至一瞬間超過了她為之奮斗了數年的夢想。來自原生家庭的傳統觀念以及社會固有的道德準則在潛移默化中終究還是進入了她無法逃避的潛藏的無意識,并對她造成了影響,結果導致由她的意識所掌控的自我最終實現了對于“姐姐”的身份認同。
導演為了兼顧親情與理想兩大主題的圓滿安排了模糊的開放性結尾,電影的結尾好似童話故事般不真實,姐弟二人緊緊相擁,而他們的未來仿佛充滿了無限可能。但從理性的角度分析,安然的選擇可謂全然不顧后果:一個窮學生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要兼顧學業和撫養年幼的弟弟實在是不太現實。但影片終究只是影片,它與現實社會終究還是有差別的。弟弟安子恒的扮演者機靈可愛,最終成長為能夠體恤姐姐的“小天使”。然而現實中的“弟弟”絕大部分都不會這么討喜,他們可能終其一生都會將“姐姐”的付出視作理所當然,成為好吃懶做的“吸血鬼”。雖然說《我的姐姐》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關懷電影是不完美的,但作為影片之外的觀眾不必對角色有那么高的共情感。能夠通過觀看這部電影,了解到“中國姐姐”這一群體的苦楚,便能使那些社會中已經習以為常以至于視而不見的落后觀念有了改變的可能。從這個角度而言,《我的姐姐》這部影片作為一個帶領觀眾走近“中國姐姐們”內心的引路人已然成功實現了它的目的。
注釋:
①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128.
②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137.
③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