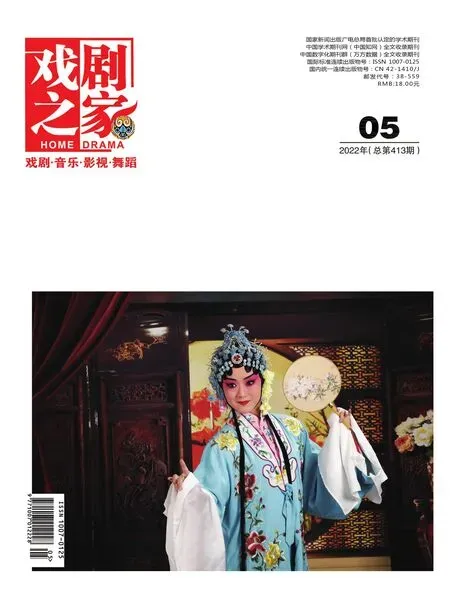蒙古貞長調民歌和短調民歌的聯系與異同
于新潔
(內蒙古藝術學院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8)
民歌承載著民族精神,也是民族文化重要的構成要素。蒙古族民歌作為蒙古族乃至中國北方諸多游牧民族音樂文化的代表,同樣具有這樣的特征。現在生活在遼寧阜新地區的蒙古族,他們的祖先無論是世代居住于此的部落,還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由其他地區遷居至此的諸如蒙古貞、兀良哈、土默特等部落,起初都過著游牧生活。在游牧的歷程中,民歌始終伴隨著蒙古族人民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成為他們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養分。游牧時代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都決定了長調民歌在蒙古貞地區的流傳。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周邊農耕文化不斷滲透和影響,這一地區蒙古族群眾逐步棄游牧而逐農耕。這一變化反映在音樂領域,就表現為長調民歌的式微與短調民歌的逐漸興起。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長調這種音樂形態造就的文化基因已經在蒙古貞地區徹底消亡,相反,直到現在,它對目前我們看到的蒙古貞短調民歌依然產生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一、蒙古貞農耕生產方式的形成
蒙古貞原本是蒙古族的一個部落的名稱,在歷史的長河中,幾經變遷,部落的含義逐漸淡化,慢慢就成為一個地域的稱謂。地理意義上的蒙古貞,位于現在遼寧省西北部的阜新地區,這里起初是別里古臺(成吉思汗同父異母弟弟)的封地。14 世紀后期,木華黎后裔、北元丞相納哈出歸順明朝,其屬下的一部分軍民就在這一地區駐留。16 世紀末,居住在朵顏山的蒙古族部落兀良哈部在游牧過程中遷移到這里。1632 年,居住在河套地區的蒙古貞部落和土默特部落也遷移至這個地區。1637年即清崇德2 年,歸順清政府的達爾汗鎮國公善巴建立土默特左、右翼旗。其中,蒙古貞部落的民眾在土默特左翼旗居民中占絕大多數,因此,民間就把該旗稱為蒙古貞旗。這樣,蒙古貞就從部落名稱演變為地名。
(一)盟旗制度的建立
蒙古族是馬背民族,也是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早期的游牧方式是集體游牧,氏族是游牧的單位。后來,家族代替了氏族,成了游牧的基本單位,游牧方式也演變為個體游牧。有清以來,朝廷在蒙古族聚居地區實行盟旗制度,利用宗教控制普通群眾,而對王公貴族則采用封官進爵和聯姻等各種手段進行拉攏。當時,清政府禁止蒙古族人民跨越旗界自主游牧、狩獵和遷徙。這樣,以旗為單位,蒙古各部就變成一個個相對封閉的獨立體,不僅限制了黎民百姓的人身自由,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游牧民族的生產生活習慣。
(二)漢族移民的遷入
清順治十年(1653 年),政府頒布并實施了《遼東招民開墾條例》,于是,大量漢族群眾遷往關外墾荒種田。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山東等距遼東較近地區的漢族群眾,就有數十萬人往來于關內關外,或經商或種田。雖然這些人多數還只是候鳥式地遷徙——每年的春天去往關外,冬天則回到家鄉,并不“移家占籍”,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移民,但是,其中也有不少逐步在遼東定居并不斷與當地的蒙古族融合,他們把內地的農耕技術帶入了蒙古族聚居區,并將草原開墾為農田。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步在當地滲透,在他們的影響下,部分蒙古族牧民也開始轉向農耕。到了道光年間,農耕文化的影響和滲透不僅使半農半牧逐漸成為蒙古貞部的基本生產方式,而且使得當地蒙古族的飲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方式和內容也都逐漸漢化,幾乎“與內地民人無異”,發生了質的變化。在生產方式變革的大背景下,蒙古貞地區的音樂形態也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變化。
二、蒙古貞民歌的嬗變軌跡
古今中外,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都必然會推動民眾生活方式的變化,進而引發社會意識形態包括音樂形態的變化。蒙古貞地區的人們在從游牧向半農半牧過渡的過程中,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不斷撞擊、融合,推動著其音樂形態也由長調民歌向半長調民歌過渡,再由半長調民歌向短調民歌變異。比對分析長調民歌與短調民歌的音樂形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兩種不同類型的民歌;而探究半長調民歌的出現及其向短調民歌的轉變,也正好可以將蒙古貞民歌音樂形態的嬗變軌跡清晰地呈現出來。
(一)長調民歌與短調民歌的聯系與不同
蒙古族民歌中,長調和短調分別是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的產物,長調與游牧的生產生活方式相稱,而短調則與定居耕作的農耕文化相稱。由于長調民歌與短調民歌產生的環境存在較大的差異,所以,這兩種民歌的音樂形態,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迄今為止仍然流行于內蒙古錫林郭勒地區的民歌《小黃馬》,是一首典型的長調民歌。長調節奏自由,音域寬廣,音程跳躍,運用拖腔和諾古拉裝飾音是其最顯著的特點。
長期流行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的蒙古貞民歌《海麗海丹》,則是一首典型的短調民歌。短調的節奏相對規范整齊,音域相對較窄,每句的末尾基本都會用到一個長音。音程平緩,多數為六度、七度、八度,超過八度的大跳很少出現,不使用“諾古拉”裝飾音。
由此可見,長調與短調,雖然都屬于蒙古族民歌,但從節奏到音域、音程,都可以看出明顯的不同。
(二)半長調民歌:一種過渡階段的音樂形態
由于長調和短調兩種民歌在音樂形態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我們可以根據這種差異輕而易舉地辨別一首蒙古族民歌的類型。但是,在現存的蒙古貞民歌中,有一種兼具長短調民歌風格特征的“半長調民歌”,這是一種出現在過渡階段的音樂形態。在蒙古貞地區,流傳下來的長調民歌,大部分其實都是這種“半長調民歌”。
這首蒙古貞民歌的起音是比較自由的拖腔,中間部分節奏規范整齊,句子的尾音是一個長音。可以看出,這首歌曲的音樂形態中,既存在長調自由拖腔的特點,又出現了短調節奏規范整齊的風格。
半長調民歌的過渡性還體現在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上,即在不同的歌曲中,分別代表長短調特點的節拍,其排列規律并不固定,體現長調風格的自由節拍和體現短調風格的規整節拍可以出現在歌曲的任何一個部分。
這首歌曲中,突出體現長調音樂特點的自由拖腔頻繁地出現在每小節的中間部位,而具有明顯的短調音樂特征的相對規范整齊的節奏則分布在旋律的其他部分,這是一首典型的半長調民歌。
三、蒙古貞長短調民歌音樂特征嬗變分析
蒙古貞長調民歌向短調民歌的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對這些特征進行系統分析,有助于我們把握這一嬗變的進程,進而為我們理解蒙古貞短調民歌音樂形態的變遷提供學理支撐。
(一)逐漸短調化
同一首民歌,在牧區,其音樂形態往往表現為長調,而流傳到半農半牧或農耕地區后,其音樂形態就會發生變化,常常表現為半長調或短調。這種現象充分說明,很多半長調民歌是長調民歌在其傳播環境發生變化時逐漸演變形成的。
《小情人》是一首長調民歌,在內蒙古牧區流傳很廣。而當這首民歌出現在內蒙古東部的半農半牧地區時,音樂特征就不再完全是長調,而是變成了一首半長調民歌。
對比這兩首歌曲,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以長調形式呈現的《小情人》,節奏自由,音域跨度很大,拖腔較多,“諾古拉”裝飾音反復出現,尤其在拖腔中運用得十分頻繁;而以半長調形式呈現的《小情人》,只有個別節奏比較自由,多數節奏規整鮮明,基本不用拖腔,音域在十度之內,跨度較小,“諾古拉”裝飾音很少出現,是典型的長短調民歌風格特征融合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這首歌曲,還以短調民歌的形態出現在了內蒙古的巴林地區。
短調民歌《小情人》節奏十分明顯而且規整,歌詞與音符一一對應,幾乎是一字一音,并且只有句末存在拖腔,音域跨度較窄,整首歌曲中幾乎沒有出現“諾古拉”裝飾音和襯詞。
通過以上幾首民歌的對比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隨著蒙古貞地區蒙古族群眾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生存環境的變化,蒙古族民歌的音樂形態也逐步發生了質的變化。長調民歌綿延的拖腔、寬廣的音域、華麗的裝飾音、繁復的曲調、跳躍的音程都逐漸減少或消失,歌曲的節奏逐漸規整,節拍逐漸固定。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蒙古貞地區與游牧文化相適應的傳統長調民歌逐漸被植根于農耕文化的短調民歌所代替。
(二)部分衍生性嬗變
在蒙古貞地區的長調民歌向短調民歌演變的過程中,王府文書、胡爾沁、喇嘛等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人,也都參與其中。可以說,蒙古族短調民歌的創作,多數是以長調為基礎,但都對長調的音樂特征進行了部分或者全部的創新與加工。因此,我們看到,現存的短調民歌中,有些民歌的曲調仍與傳統的長調民歌相似,而有些則已經完全有別于作為其創作基礎的長調民歌。
《贊馬》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長調歌曲,《駿馬贊》由《贊馬》衍生而成,在保留原來曲調的基礎之上,節奏變得規整,具有鮮明的短調特征。
流傳于蒙古貞地區的敘事體民歌《韓淑英》屬于短調民歌。據記載,這首歌的創作者是特古斯胡爾沁,創作時間大約在20 世紀30 年代。
對比長調民歌《贊馬》和短調民歌《韓淑英》,我們可以發現,它們的前半部分,有著極其相似的旋律,而二者的后半部分,旋律已經沒有任何關聯性,完全是兩首不同的歌曲。然而,經過認真對比不難發現,特古斯胡爾沁具有較深的民族音樂修養,他在創作《韓淑英》這首歌之前,肯定非常熟悉長調民歌《贊馬》。因此,他把《贊馬》的前半部分旋律運用到了他的作品中。這樣,長調民歌《贊馬》,就成了短調民歌《韓淑英》的音樂素材。這種現象說明,有一些長調民歌,仍然存在于其衍生出來的短調民歌中,并隨之流傳至今。
(三)民族音樂性格的保留
在長調民歌向短調民歌演變的過程中,音樂形態最明顯的變化就是自由的節奏節拍變成了有規律的節奏節拍,可以說,節奏節拍的逐漸規范整齊是其最重要的特點。而長調民歌在裝飾音、襯詞、調式、音程結構等方面的一些特點,也依然在短調民歌中延續著其生命。
1.音階與調式的聯系和異同
從音階與調式的角度分析蒙古族長調民歌與蒙古貞短調民歌的聯系和異同,我們可以看到長短調民歌之間更多的繼承性、滲透性。
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是蒙古族長調民歌的音階基礎。而在目前我們能夠找到的220 首蒙古貞短調民歌中,屬于五聲音階的有170 首,屬于六聲音階的有41 首,屬于七聲音階的則僅有8 首。其與長調民歌的聯系由此可見一斑。
蒙古族長調民歌的調式也與中國傳統的五聲調式一脈相承,其中運用最廣泛的是羽調式。上述220 首蒙古貞短調民歌中,使用羽音的短調民歌有84 首,使用徵音的短調民歌有64 首,而使用商音、宮音、角音結束的短調民歌,則分別只有35 首、23 首和14 首。可見,羽調式也是蒙古貞短調民歌中最常見的調式。
2.音程結構的聯系和異同
蒙古族長調民歌節奏明顯、旋律悠揚、氣韻舒展,旋律結構中頻繁出現六度、七度、八度音程,此外,九度、十度、十一度等各種夸張的大跳也時有呈現。長調民歌在音程方面的這些特點,較好地體現了蒙古族豪放熱情的民族性格,并與其長期游牧生活所處的自然環境相適應。短調民歌的旋律中,八度以上的大跳很少出現,但是還沒有完全消失,在一些短調民歌中,八度以上的大跳依然被保留了下來。
3.裝飾音與襯詞的聯系和異同
“諾古拉”是長調民歌最重要的標志。除“諾古拉”外,長調民歌還經常巧妙地在樂句的開頭、中間和結束音上運用其他各種裝飾音,滑音、顫音、波音、甩音、倚音等獨具特色的裝飾音在長調旋律中的大量運用,進一步凸顯了長調的民族風格。長調民歌旋律悠揚但歌詞很少,演唱中大量使用啊、嗬、喲、嗬咿等襯詞。蒙古貞短調民歌中,棄用了長調最重要的裝飾音“諾古拉”,滑音、波音、甩音等裝飾音雖仍在使用,但頻率也大為減少,由各種語氣助詞構成的襯詞則被保留了下來。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長調民歌與短調民歌聯系密切又各具特色,相互之間具有繼承性、滲透性。蒙古貞短調民歌與傳統的長調民歌相比較,其音樂形態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但是,無論外在形象還是內在血脈,都還或多或少地保留著長調民歌的“基因”。
綜上所述,無論長調民歌還是短調民歌,都是在不同的生產生活環境中產生和發展的,都深深地留存著民族性格的烙印。其中,長調民歌是蒙古民族將自己擅長的游牧生產勞動高度音樂化的產物,是馬背民族為歌頌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而創造的藝術,是唱給大自然的贊歌,也是人的心靈與神圣的大自然的對話。短調民歌是農耕文明在人的思想與情感中激起的浪花,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更注重人與人之間心靈的交流。盡管蒙古貞地區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經歷了棄游牧逐農耕的變遷,音樂形態也經歷了由長調到半長調再到短調的變化,但是,在草原漫長的游牧生活中長期積淀而成的蒙古民族傳統的音樂性格卻始終在蒙古貞民歌中存在著。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依然能夠在蒙古貞短調民歌中看到蒙古族音樂性格基因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