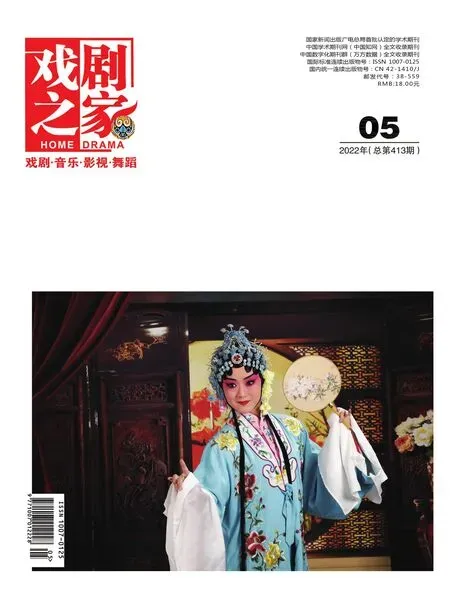以熱奈特敘事理論分析電影《孤味》
楊博雯
(南京藝術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13)
電影《孤味》是許承杰導演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雖然是其處女作,但是導演細膩內斂的手法將一個平淡的故事講述得溫情而有深度。電影以和解為主題,講述了一個家庭中的故事以及親情的羈絆,導演在作品中嫻熟地運用敘事技巧表達主人公從心有執念到放下和解的心路歷程。
法國著名敘事學家熱奈特在對電影敘事學的研究中,提出了敘事時間、敘事語態和敘事聚焦等概念。
一、敘事的時間性:《孤味》中的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
影視作品中的時間關系是構成故事完整敘事的重要元素之一,法國學者熱奈特將敘事分成兩種時序——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故事時間是指故事發生的自然時間狀態,而敘事時間是指故事在影視作品中由編劇或者導演重新排列組合后所呈現出來的時間狀態,這是一種通過對原故事的加工改造后提供給觀眾的文本秩序。
首先,是電影敘事的時序。現在越來越多的電影不再是單一的直線式敘事,很多電影的看點以及亮點都在于不是按照一個故事所要發生的自然順序進行展開,通過讓故事發生的自然順序與被敘述的順序的不一致,電影中產生錯置順序,從而導致了倒敘、預敘、插敘等敘述次序的出現。電影《孤味》以母親林秀英在七十歲壽宴這天接到了離家出走多年的丈夫逝世消息后為他舉辦葬禮的故事為線索,通過時間的推移和故事的發展揭開了這個家庭中眾人不敢面對的創傷,同時講述了母親從心有執念到放手成全的心態轉變。電影一共分為兩條敘事線,主線是以準備葬禮為主的正敘時間線,還有一條副線是以母親林秀英回憶感情為主的時間線,副線通過四次插敘的方式補全了主線中沒有介紹到的故事內容、回答了之前片中埋下的伏筆,影片也通過這四處的插敘介紹了在影片開頭就逝世、全片中沒怎么出現過的父親角色是怎樣的,同時也補充了林媽媽年輕時的形象。
其次,是電影敘事的持續性。電影作為一種時間的藝術,很難在大銀幕中將故事時間完整地呈現出來,在電影發展的一百多年歷史中,經過了無數導演的不斷探索,最終發現電影在90 分鐘到120 分鐘的時長可以保證一部電影的敘事以及電影院的排片,對觀眾來說其體驗也可以達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熱奈特在《論敘事文話語》中提到了電影敘事時長主要分為概要、省略、停頓、場景四種。在電影《孤味》中并沒有用冗長的篇幅去介紹母親林秀英和去世的丈夫陳伯昌兩人曾經感情有多么深厚,而是采用了概要的方式,在四段插敘中用最后一段插敘的僅一分鐘時長描述了之前一家五口共度中秋的幸福時光。但是從母親一直保存著父親曾經的衣物和情書可以看出,即使父親離家多年,母親對父親的感情依舊很深;從林秀英和蔡小姐的交流中,我們也能從側面得知父親為保護母親所做的一切,父親雖離家多年,但他對妻子以及家庭仍舊有著深深的愛和掛念。概要是指一種使得敘事時間比故事時間更短的手法,通過概要的敘事方式可以壓縮描述事件過程的文本時間,來達到加快敘事速度的效果。熱奈特將TR 表示為敘事時間,將TH 表示為故事時間,概要的公式表現為:TR <TH,即敘事時間小于故事時間。在電影《孤味》中沒有把敘事時間著重放在母親林秀英和父親陳伯昌曾經美好的感情上,而是通過概要的敘事方式壓縮了對其事件的描述篇幅。
第三,是電影敘事的頻率。頻率即故事中事件發生的次數和電影敘述中該事件發生次數之間兩者的關系。熱奈特將其主要分為單一描述和重復性描述,根據單一還是重復,熱奈特將其主要劃分為了以下幾類:單一敘述,即講述一次發生過一次的事;特殊的單一敘述,即講述N 次發生過N 次的事;重復敘述,即講述N 次發生過一次的事;反復敘述,即用一次講述發生N 次的事。在電影《孤味》中,對父親陳伯昌偷拿了妻子林秀英父親的印章到銀行貸款做生意結果生意失敗,阿公將診所賣掉換錢打擊太大病倒這一事件進行了反復敘述。第一次敘述出現在影片的第一次插敘中,以父親陳伯昌的角度描述;第二次敘述出現在舅舅來殯儀館言語惹怒阿瑜的情節中,以舅舅的角度描述;第三次敘述出現在佳佳和蔡小姐對話,以佳佳無知的角度看待;第四次敘述出現在林媽媽和女兒們圍坐起爭執的情節中,通過阿瑜的講述,是以阿瑜的視角看待;第五次敘述是在寺廟里,林秀英和蔡小姐的交談中,通過蔡小姐的講述提及,以蔡小姐的角度看待;第六次是在母親林秀英給女兒們分金子的情節中,母親講述了這件事情的真實情況,以母親的角度看待這件事。重復敘述的策略讓所有的人物都卷入了電影的矛盾和沖突之中,既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又揭示了每個人物對這個事件的看法,同時也塑造了每個人物的性格。而且在片中重復敘述的這個事件,由于每個人物對事件了解得不充分,以及不同的身份和視角,也制造出了片中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同時,這個事件作為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一環,不僅通過每個人物對事件的描述可以交代補充完整故事,也解釋了父親陳伯昌當年為何執意想和母親離婚,以及離家出走的原因,這是電影故事發生的背景。
二、敘事語態:《孤味》中的分層敘事
“敘述層”這個概念是熱奈特對于電影文本敘事結構進行的一個層次上的劃分,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將電影中的敘事結構整理得更加清晰明了。在熱奈特的《敘事話語和新敘事話語》一書中寫道,“敘事講述的任何事件都處于一個故事層,下面緊接著產生該敘述行為所在的層”。在電影《孤味》中,母親林秀英七十歲壽宴當天丈夫陳伯昌去世,之后為其守喪、舉辦葬禮的故事情節為第一敘事內容,稱之為故事層或故事內事件,而林秀英和陳伯昌之間的感情故事以及由陳伯昌偷阿公印章做生意失敗進而使得阿公受打擊病倒的故事情節則被稱為第二敘事層和元故事事件。第二敘事層作為第一敘事層的補充,并不會干預到第一敘事層,只是起到了補充解釋、交代故事完整性的作用。
“元故事”敘事是一種“故事中的故事”,其本身具有一種復雜性,如果其處在多個敘述主體的故事中將會更加難以分辨,而可以分辨其是否作為整個故事情節中元故事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作為第二敘事層與第一敘事層之間的一種依附關系,即元故事敘事是在第一敘事層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第一敘事層和第二敘事層之間一定存在的某種關系,熱奈特將其分為了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第一敘事層與第二敘事層之間所存在的一種因果關系,第一敘事層賦予了第二敘事層解釋的功能;第二種是一種純粹的主題關系,第一敘事層和第二敘事層之間存在著一種對比關系或者類比關系;第三種是第一敘事層和第二敘事層之間并不存在著某種非常明確的關系,在第一敘事層中起作用的是不受第二敘事層內容牽制的敘述行為本身。回顧電影《孤味》的第一敘事層和第二敘事層,可以發現第二敘事層與第一敘事層之間是一種非常明顯的因果關系。在第一敘事層中,陳伯昌離家多年毫無音訊,在妻子林秀英七十大壽這一天回到家鄉病逝,但壽宴并沒有因此停止,看似并不在意丈夫逝世的林秀英實際上心系丈夫的事宜,在壽宴結束后趕去醫院打聽消息,并在丈夫離家的數十年中依舊珍藏著丈夫的衣物和情書。且從壽宴上舅舅的態度可以得知因為陳伯昌的緣故,家族中有一些隔閡和不愿提及的故事。
在第二層敘事層中,交代了當年是林媽媽偷了印章,而陳伯昌為了保護妻子才將罪行包攬下來,而這個秘密除了陳伯昌和林秀英沒有任何人知道,這也解釋了第一敘事層中,為何林秀英對丈夫一直念念不忘,以及陳伯昌當年不得不放棄家庭離家出走的原因。
三、敘事聚焦:《孤味》中的不同敘事聚焦視角
在對于故事敘述空間的分析論述中,熱奈特采用了一個較為抽象的名詞:“聚焦”,而敘事聚焦又分為內在敘事聚焦(內聚焦)、外在敘事聚焦(外聚焦)和零聚焦敘事。所謂內在敘事聚焦就是電影的敘事可以從一個人物轉換到另一個人物、也可以是不同人物對同一個事件的幾種不同看法。對于和父親陳伯昌有關的事件,比如陳伯昌借錢做生意失敗、林秀英去旅店捉奸父親等事件,林媽媽和大女兒、二女兒就屬于內聚焦,她們是這些事件的親歷者、見證者。內在敘事聚焦的優勢在于可以比較充分地敞開人物內心世界,淋漓盡致地表現人物激烈的內心沖突和思緒,可以對人物和事件有著屬于自己的認知范圍和認知視角。而其局限性也非常明顯,內在敘事聚焦有著嚴格的視角限制,它必須固定在人物的視野范圍之內,不能脫離其自身范圍,也無法深入剖析他人思想。因此林秀英和大女兒、二女兒都對陳伯昌有著不同角度的認知,她們每個人對其了解都不全面,三人心中陳伯昌的形象不同,從而造就了兩個女兒不同的性格。而很多的電影導演也正是充分發揮運用內在敘事聚焦所具有的這種限定性功能,在影視作品中有意造成觀眾觀看影片時的死角或空白,以獲得某種意蘊或者是引起觀眾的好奇心。在《孤味》中,導演就運用這種方式讓觀眾對陳伯昌的事件有了疑問和好奇,這些事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所謂外在敘事聚焦就是聚焦者不參與故事,完全置身于故事之外。外在敘事聚焦為觀眾提供了與故事保持距離的觀察態度,《孤味》中的小女兒佳佳對這些事件就屬于外在敘事聚焦,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她還沒有出生或剛出生不久,因此她對父親陳伯昌的相關事宜和家族中的恩怨情仇并不知曉。在她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的角色基本上處于缺失的狀態,她對自己的父親完全不了解,僅有的印象就是父親從臺北給她帶的糖果。外在敘事聚焦的特點是,其視角是一種較為客觀、有限的視角,這種視角絕大程度上依賴他人的視角,處于情境中的這種聚焦視角只能通過他人的敘述慢慢地了解事情的過程和真相。《孤味》中的林秀英和兩個姐姐為了保護佳佳對家庭和父親的美好幻想,不忍心告訴她父親的另一面和一些她無法理解的事情,因此造就了她不同于兩個姐姐的對父親的認知以及她貫穿全片的“圣母”審視感。
而在對父親陳伯昌這個人的了解中,林媽媽和三個女兒共同形成了內在敘事聚焦中的多重式內聚焦。所謂的多重式內聚焦是指在同一時間中,根據不同人物的敘述,讓不同的人物從各自所站立的不同角度觀察同一個事件或者同一個人物,以產生互相補充或相互沖突的敘述。無論是對陳伯昌了解最深的林媽媽還是對父親了解甚少甚至對父親過去完全不了解的小女兒佳佳,她們都對父親陳伯昌有著不同于別人的屬于自己的認知。林媽媽所了解的丈夫陳伯昌是和其他所有人了解得都不一樣的,當所有人都將阿公病逝怪罪在陳伯昌身上時,只有林秀英自己清楚事情的真相,而陳伯昌為了保護妻子將罪行包攬下來,得知丈夫為了自己將這個秘密保守了一生的林媽媽不禁痛哭流涕。大女兒阿青對于父親的認知更多的是他的多情和自由,所以在阿青的身上也折射出了父親的影子。她叛逆,勇敢的追求愛和自由,但又活得很透徹、清醒。二女兒阿瑜對于父親的印象在于她只要在學校獲獎,父親一定會去看她的頒獎典禮,為了可以讓父親回來,天真的她拼命努力學習拿獎,而當她以優異的成績從醫學院畢業也見不到父親的時候,她才清醒地意識到父親真的從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正因如此她內心極度的敏感和不安,對于愛情充滿了不信任、在婚姻中存有一種很強的不安全感。小女兒佳佳對父親的了解在于,正是由于她對父親以前的一無所知,以至于她對父親似乎只有依戀沒有一絲的怨恨,她會在長大之后偷偷跑去臺北找父親,背著母親與父親的女友蔡小姐保持聯系,通過蔡小姐的描述了解自己所不熟悉的父親。這種“多重內聚焦”使得觀眾可以從多種不同角度聚焦的視角中,了解并思考人物以及事件的豐富性和歧義性,就如同面對畢加索的畫一樣,人們的眼睛不再只是享受單一的畫面,而是折疊式的空間。正是幾個女兒和林媽媽的多個視角共同拼湊在一起,才向觀眾展現了一個在電影中沒怎么出現過的陳伯昌更為全面生動的形象。
四、結語
經典敘事學理論對于電影的分析不應該僅僅是浮于表面的形式分析,還應該深入探究分析其敘事方法的運用對影片形成了怎樣的敘事效果以及為了達成怎樣的敘事目的。電影《孤味》采用了插敘、概要、反復敘述等敘事技巧將林秀英家庭中的故事展現出來,通過對敘事語態的分析,研究了影片中的第一敘事層故事和第二敘事層故事,再通過不同敘事聚焦視角完成了對事件和人物的認知和情感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