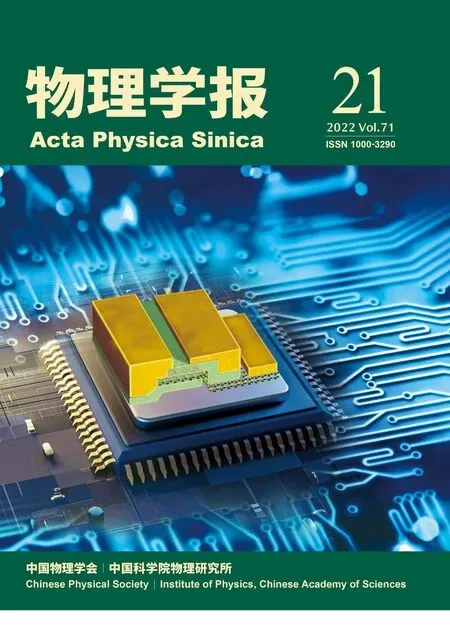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層結構靶優化伽馬射線的產生*
熊俊 安紅海 王琛? 張振馳 矯金龍 雷安樂 王瑞榮 胡廣月 王偉 孫今人
1)(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激光等離子體研究所,上海 201899)
2)(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核科學技術學院,合肥 230026)
3)(浙江大學物理學系,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杭州 310027)
在神光-Ⅱ升級及皮秒拍瓦激光裝置上,開展了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層結構靶優化伽馬射線產生的實驗研究.一束納秒長脈沖激光預先燒蝕第一層碳氫薄膜靶,產生等離子體,經一定時間的自由膨脹后,形成較大尺度的低密度等離子體.第二束皮秒短脈沖激光與低密度等離子體相互作用,通過光場直接加速等非線性加速機制,將電子加速到相對論量級.相對論電子束經過傳輸后在第二層金轉換靶上通過軔致輻射的方式產生伽馬射線.該方案能夠有效提升超強超短脈沖激光加速產生的相對論電子束流品質,獲得能量更高、發散度更小的相對論電子束,進而有可能獲得品質更高的伽馬射線輸出.
1 引言
伽馬射線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諸如閃光照相[1,2]、復雜結構的無損探傷[3]、產生用于對原子核物理及等離子體物理的微觀過程進行時間分辨的動力學研究的正電子源[4,5]、作為核光子學研究的驅動源來誘導放射性材料發生嬗變[6,7]以及制備醫用同位素材料[8]等.
目前而言,在諸多的超快伽馬射線產生方案中,利用高能電子在靶基底內的軔致輻射產生伽馬射線的效率最高,其截止能量為高能電子束的峰值.對于能量不是特別高的非相對論高能電子來說,產生的伽馬射線輻射方向主要與高能電子運動方向垂直,即在側向;而對于能量非常高的相對論電子來說,產生的伽馬射線輻射總是沿著高能電子的初始運動方向.兩相比較,相對論電子驅動的伽馬射線方向性好,具有更高的能量,對于應用來說,更具有優勢.因此,高能高通量的相對論電子束流成為產生高品質伽馬射線的關鍵因素之一.超強超短脈沖激光的發展為激光驅動伽馬射線源的發展帶來了契機.超強超短脈沖激光可在極短的時間內將大量的能量集中在極小的空間尺度上,創造出高溫高密度的等離子體環境.在這種溫稠密等離子體中,激光場通過多種非線性加速機制在極短的時間(幾十飛秒到幾個皮秒)和距離(百微米)內加速到相對論條件,獲得高通量的相對論電子束流,其后再通過與轉換靶材料相互作用產生超快伽馬射線束.
神光-Ⅱ皮秒拍瓦激光裝置可產生數百焦耳的皮秒激光輸出,同時神光-Ⅱ升級裝置還能夠同時輸出多路納秒長脈沖激光,這為開展長短脈沖聯合驅動相對論電子束和伽馬射線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本文開展了相應的實驗研究,通過利用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層結構靶的構型,來提高相對論電子束的品質,進而優化獲得了更強的伽馬射線脈沖輸出.這一結果為后續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啟發.
2 相對論電子束的產生
超短超強皮秒激光作用到靶面之前,自發輻射的脈沖前沿[9](ASE)預先燒蝕靶面產生密度梯度陡峭的預等離子體,超熱電子的加速機制主要是在臨界密度面附近產生有質動力加速[10,11].而如果在主脈沖作用前,存在更大尺度的低密度等離子體層,皮秒短脈沖激光在低于臨界密度面的區域范圍內,可能會通過光場直接加速機制[12](DLA)、自調制尾波場加速(SMLWF)[13]等非線性加速機制將電子加速到更高能量狀態,最終獲得能量更大、束流通量更強的高能電子束流.
納秒激光輻照薄膜靶產生的等離子體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自由膨脹后,產生較大尺度的低密度等離子體,基于此,開展了初步的實驗.實驗利用高功率激光物理聯合實驗室的神光-Ⅱ升級裝置及皮秒拍瓦裝置進行,方案如圖1 所示.在圖1(a)中,單束皮秒激光輻照平面薄膜靶產生相對論電子束;而在圖1(b)中,采用了長短雙脈沖激光聯合驅動的方式.首先使用一束脈沖較長的納秒激光輻照平面薄膜靶,將靶完全燒蝕,經一定延時后,會形成較大尺度的低密度等離子體,其后脈沖較短的皮秒激光注入,與產生的較大尺度的低密度等離子體發生作用,加速產生相對論電子.對于這兩種實驗方式,除了納秒激光的差異,其他完全相同.靶均為2 μm 厚度的C8H8平面薄膜靶.皮秒激光的條件是脈沖寬度約1 ps,能量約150 J,基頻(波長1.053 μm),焦斑尺寸約Φ30 μm,與靶面法向成21°角注入,功率密度約6×1019W/cm2.納秒激光的條件是脈沖寬度約1 ns,能量約600 J,三倍頻(波長0.351 μm),與靶面法線方向呈約45°角注入,采用連續位相板(CPP)束勻滑方式聚焦,在靶面位置形成尺寸約Φ450 μm 的均勻焦斑.皮秒與納秒激光之間的延時約1 ns.采用2 套完全相同的電子磁譜儀EMS1 和EMS2 分別對產生的相對論電子進行探測,其中磁場均為3000 G(1 G=10-4T),測量范圍0.2-260 MeV.EMS1 放置在皮秒激光的前進方向上,即與靶面法向成21°;而EMS2 則放置在靶面法向的另一側,與靶面法向成約50°角的方向,用來測量側向的電子發射.EMS1 和EMS2到靶距離均約為500 mm,基本一致.

圖1 針對出射電子束測量的實驗方案示意圖(a)單皮秒激光驅動平面薄膜靶方式;(b)納秒、皮秒長短脈沖聯合驅動平面薄膜靶方式Fig.1.Experimental schem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outgoing electron beams:(a)A film target driven by a single ps laser;(b)a film target jointly driven by long ps and short ns pulse lasers.
圖2 給出了由EMS1 測量得到的單發次激光入射方向的電子能譜圖像(dN/(dEdΩ)是單位能量單位立體角內的電子數目),左側為低能端,右側為高能端.圖3 則是根據EMS1 與EMS2 記錄圖像處理之后的電子能譜分布曲線.從圖3 可以明顯看出,在激光入射方向上(由EMS1 測量),ns+ps的長短脈沖聯合驅動條件下,高能段的相對論電子數目及所占份額明顯高于單ps 脈沖驅動條件,且其能譜更“硬”,電子的最高能量也明顯更高.而在側向(由EMS2 測量),總的電子能量和數量明顯低于激光入射方向,同時兩種不同情況對應的電子能譜差異也比較小,表明電子主要的發射方向以激光入射方向為主的.

圖2 由EMS1 測量得到的單發次激光入射方向的電子能譜圖像(a)單皮秒激光驅動平面靶;(b)納秒、皮秒長短脈沖聯合驅動平面靶Fig.2.Electron energy spectrum image of the laser incident direction measured by EMS1:(a)A film target driven by a single ps laser;(b)a film target driven by ns and ps lasers.

圖3 由EMS1 與EMS2 記錄圖像處理之后的電子能譜分布曲線Fig.3.Electronic spectrum distribution curves recorded by EMS1 and EMS2.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長短脈沖聯合驅動條件下,電子能譜存在多個“峰”,而單脈沖激光驅動條件下僅有一個較為明顯的峰,這似乎表明雙脈沖驅動情況下,可能存在多種加速機制,而單脈沖條件下則以臨界密度面附近的有質動力加速為主.多種加速機制共同作用,提高了相對論電子的能量和數量.
3 低密度等離子體增強相對論電子
為更好理解上述實驗結果,利用PIC 粒子模擬程序(EPOCH)[14],進行了簡單的數值模擬.模擬中選取激光波長1 μm,脈寬1 ps,焦斑10 μm(FWHM),對應靶面功率密度1019W/cm2.靶材料為C8H8,靶成分比C:H 為1∶1.分別針對兩種實驗情況選擇對應的模型進行模擬: 一是固體靶模型,對應單皮秒激光驅動平面薄膜靶方式,固體靶密度設置為20nc,此處nc為等離子體的臨界電子密度,對于波長為1.053 μm 的基頻皮秒激光來說,nc=1×1021cm3.激光以與法線方向30°角斜入射輻照在靶面上.考慮到實際皮秒激光存在的前沿的影響,在固體靶前設置密度標長4 μm 的陡峭分布的預等離子體.二是低密度等離子體模型,對應納秒皮秒長短脈沖激光聯合驅動平面薄膜靶方式,為簡化起見,等離子體設為均勻等離子體,電子密度設置為0.1nc,皮秒激光正入射到等離子體上.
模擬結果如圖4 和圖5 所示,其中圖4 是針對帶陡峭分布預等離子體層固體靶進行數值模擬的結果,圖5 是針對低密度均勻等離子體進行數值模擬的結果.圖4 和圖5 兩子圖分別為對應條件下的激光場分布、電子密度分布.

圖5 針對低密度均勻等離子體進行數值模擬的結果(a)激光場分布;(b)電子密度分布Fig.5.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for low-density uniform plasma:(a)Laser field distribution;(b)electron density distribution.
對于帶陡峭分布預等離子體層的固體靶情況,皮秒線偏振入射激光與密度陡變的固體靶截面相互作用時,電子加速的主要方式是有質動力加熱和真空加熱機制[15],發生在臨界密度面附近,電子能譜呈麥克斯韋分布.當激光與等離子體作用時,輻射壓使離子正向加速,將臨界密度面向更高密度區推進,使原來密度分布進一步陡化.如圖4(b)所示,等離子體內的電子被激光場排開,形成一個向內凹陷的空洞,使得臨界密度面向內彎曲.由于有質動力加速產生的超熱電子的運動方向以垂直臨界密度面為主,臨界密度面的這種彎曲將會使得高能電子的發散角顯著地增大.

圖4 針對帶陡峭分布預等離子體層固體靶進行數值模擬的結果(a)激光場分布;(b)電子密度分布Fig.4.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a solid target with a steeply distributed pre-plasma:(a)Laser field distribution;(b)electron density distribution.
而對于電子密度為0.1nc的低密度的均勻等離子體來說,情況則完全不同.相對論級別的皮秒激光在低密度等離子體中傳輸時出現明顯的成絲不穩定性(filamentation instability)[16],進而誘發自聚焦效應,激光強度有所增強.在百微米尺度范圍內,激光依然保持前向傳輸.從圖5(b)可以看出,相對論激光通過有質動力將電子排開,在次臨界密度等離子體中形成多條“等離子體通道”[17-20].形成的通道可有效地增大激光與電子之間的能量轉換,將電子加速到數十MeV.在Li 等[21]、Arefiev等[22,23]的PIC 模擬工作中也證實了這種通道結構的形成對超熱電子的影響.
圖6 給出了針對兩種靶結構模擬的前向相對論電子發射能譜,可以明顯看出,對低密度均勻等離子體條件來說,盡管在低能電子數量方面比帶陡峭分布預等離子體層的固體靶條件要少一些,但在更高能的相對論電子,不但數量大大超出,并且截止能量更高,即電子能譜更“硬”.同時模擬結果也顯示,低密度均勻等離子體條件下所產生的相對論電子方向更為集中,發散角更小.這表明,通過創造低密度等離子體的環境,有助于顯著提升相對論電子的能量、降低發散角,這些性能的改進對于提高伽馬射線的品質非常有利.盡管前述實驗中采用的是納秒激光驅動燒蝕形成的低密度等離子體,與數值模擬中采用低密度均勻等離子體存在較大的差異,但基本原理是相同的,而實驗結果也的確表明了這一點.

圖6 兩種情況對應的前向電子能譜模擬結果Fig.6.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forward electron spectrum corresponding to the two cases.
4 皮秒激光驅動產生伽馬射線
根據上述低密度等離子體可能獲得更強的相對論電子這一想法,基于高功率激光物理聯合實驗室的神光-Ⅱ升級裝置及皮秒拍瓦裝置,設計了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層結構靶產生伽馬射線的實驗方案,如圖7(a)所示.靶是雙層結構,第一層為厚度2 μm 的C8H8平面薄膜靶,第二層是一塊厚度約2 mm 的Au 厚靶,兩層表面間隔650 μm,如圖8 所示.首先,一束1 ns,600 J 的脈沖較長的三倍頻激光以Φ450 μm 的CPP 焦斑直接輻照C8H8平面薄膜靶,將其完全燒蝕,經過一定延時后,形成密度梯度相對平緩的低密度等離子體;另一束1 ps,150 J 的基頻短脈沖皮秒激光以Φ30 μm 的焦斑沿21°角注入,焦面位于C8H8平面薄膜靶位置.入射的皮秒激光與大尺度低密度等離子體發生作用,加速產生相對論電子;相對論電子束流經過傳輸后進入Au 厚靶中,與Au 轉換靶作用,通過軔致輻射產生伽馬射線.采用2 套完全相同的伽馬射線堆棧譜儀(γ-1,γ-2)對產生的伽馬射線進行探測,測量的能段范圍為20 keV-2 MeV.其中γ-1放置在皮秒激光的前進方向上,即與靶面法向成21°;而γ-2 放置在靶面的切線方向,用來測量側向的伽馬射線發射.γ-1 和γ-2 前端到靶的距離均為700 mm,基本一致.

圖8 雙靶結構示意圖(a)及實物照片(b)Fig.8.Schematic diagram of dual target structure(a)and actual photo(b).
作為對比,還進行了另外兩種方案的實驗,分別如圖7(b)和圖7(c)所示.圖7(b)方案與圖7(a)的差別僅是去掉了納秒激光,只采用單束皮秒激光驅動;而圖7(c)的方案,則采用單束皮秒激光驅動單塊Au 厚靶的方式,與圖7(b)相比,又去掉了第一層厚度2 μm 的C8H8平面薄膜靶,同時皮秒激光的焦點位置移動到單塊Au 厚靶的靶面上.其他條件,如靶參數、激光參數、診斷方式等完全一樣.

圖7 三種產生伽馬射線的實驗方案示意圖(a)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靶;(b)單脈沖驅動雙靶;(c)單脈沖驅動單靶Fig.7.Experimental schemes for generating gamma rays:(a)Dual targets driven by ns and ps lasers;(b)dual targets driven by a ps laser;(c)a target driven by a ps laser.
圖9 給出了上述3 種實驗方案下,利用伽馬射線堆棧譜儀測量得到的單發次實驗的伽馬射線能譜分布,其中a為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靶產生的輻射能譜強度,b為單脈沖驅動雙靶的輻射能譜強度,c為單脈沖驅動單靶的輻射能譜強度;-1 后綴表示是γ-1 譜儀即激光入射方向的測量結果,-2 后綴表示是γ-2 譜儀即靶面切線方向的測量結果.皮秒激光的注入時刻是納秒激光脈沖的下降沿中點時刻.由圖9 可以明顯地看出,通常情況,在激光方向上γ-1 測得的伽馬射線強度要明顯高于靶面切線方向γ-2 的結果,即相對論電子引起的伽馬射線占主導地位.對于能量高于0.5 MeV 的區域,利用方案(a)獲得的伽馬射線輻射強度要明顯高于(b)和(c)兩種方案,而(b)和(c)兩種方案獲得的輻射強度則比較接近.在方案(a)中,納秒激光脈沖預先燒蝕C8H8薄膜靶,形成大尺度的低密度等離子體狀態.而在方案(b)中,盡管靶前也與一層C8H8薄膜靶,但皮秒激光作用時間短,難以形成大尺度低密度的等離子體.皮秒激光注入,在大尺度的低密度等離子體中可能通過多種非線性加速機制將電子加速到相對論水平,獲得能量更高、流強更大的相對論電子束,進而與Au 固體靶作用,產生更強的伽馬射線輻射.表1 給出了3 種方案幾個能量點的伽馬射線輻射強度,可以看出,相比于傳統的單路皮秒激光直接驅動Au 厚靶的方案(c),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層結構靶的方案(a)在0.5 MeV,1.0 MeV,1.5 MeV 和2.0 MeV 四個能點,伽馬射線的輻射強度分別增大了39%,96%,100%和100%;而采用單皮秒脈沖雙層結構靶的方案(b),則增長有限,僅增大了-3.7%,20%,21%和22%.這一結果充分表明了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層結構靶構型在提高相對論電子數目和伽馬射線強度方面的顯著效果.

表1 不同能量處3 種方案獲得的伽馬射線強度Table 1. Gamma ray intensity obtained by the three schemes at different energies.

圖9 三種條件對應的單發次實驗伽馬射線的能譜分布,其中a-1,b-1,c-1 對應γ-1 測量的數據,a-2,b-2,c-2 對應γ-2測量的數據Fig.9.Spectrum distribution of gamma ray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conditions.a-1,b-1,and c-1 correspond to the data from γ-1,and a-2,b-2,and c-2 correspond to the data from γ-2.
5 伽馬射線的角分布
從上述實驗可以看出,在激光方向上的伽馬射線強度要明顯高于靶面切線方向.針對伽馬射線的角分布,針對上述方案(a)和(c)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實驗方案如圖10 所示.在已有的2 套伽馬射線堆棧譜儀(γ-1 和γ-2)之外,另外增加了兩套伽馬射線堆棧譜儀(γ-3 和γ-4)分別放置在相應的方位角上進行伽馬射線的診斷.以靶背法向為角度零點,4 臺伽馬射線堆棧譜儀的方位角如下:γ-1 對應21°,γ-2 對應90°,γ-3 對應0°,γ-4 對應60°.4 套伽馬射線堆棧譜儀參數和配置完全相同,前端到靶的距離均約為700 mm,基本一致.

圖10 伽馬射線角分布的測量方案示意圖Fig.10.Experimental schemes for measur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amma-ray.
圖11 為方案(a)和(c)對應的伽馬射線能譜分布.從圖11 可以看出,與方案(c)單束皮秒激光驅動單塊Au 厚靶方式相比,方案(a)對應的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靶方式下,4 個方位伽馬堆棧譜儀測量得到的曲線更加分離.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隨著伽馬射線能量的增大,21°即激光前進方向的伽馬射線強度逐漸超過了0°靶背法線方向.這些現象表明,與方案(c)相比,方案(a)產生的伽馬射線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為此,針對特定能量的伽馬射線,如2 MeV,繪制了伽馬射線與探測角度的關系曲線,如圖12 所示.很明顯,在方案(c)單束皮秒激光驅動單塊Au 厚靶方案時,伽馬射線輻射強區是靶面法線方向,不同方位角上的輻射強度差異程度較小,接近各向同性.而在方案(a)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靶方式下,在21°的激光方向上,伽馬射線出現了明顯的峰,表明在該方向相對論電子占據明顯的優勢.正是由于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靶方案中存在的低密度等離子體,增強了相對論電子,并使其更加集中在激光方向上,才產生了上述相應的效果.

圖11 不同方向測量得到的伽馬射線能譜分布(a)長短脈沖聯合驅動雙靶;(b)單脈沖驅動單靶Fig.11.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gamma-ray energy spectra:(a)Dual targets driven by ns and ps lasers;(b)a target driven by a ps laser.

圖12 方案(a)與方案(c)的伽馬射線能譜空間分布對比Fig.12.Comparis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gamma-ray energy spectra between scheme-(a)and scheme-(c).
6 低密度等離子體狀態的影響
上述實驗基本證實了低密度等離子體的存在會改善相對論電子束的品質,進而提高伽馬射線的輸出.而不同的低密度等離子體的狀態,也可能對伽馬射線的輸出產生影響.通過改變納秒-皮秒長短脈沖之間的時間間隔,可以有效改變皮秒激光到達時刻的低密度等離子體的狀態,從而獲得相應的規律.
實驗方案依然如圖7(a)所示,改變納秒與皮秒激光的時間間隔,所得結果如圖13 所示,4 條曲線分別對應單ps 激光(無納秒激光)、納秒激光提前0 ns,1 ns,1.5 ns 的條件,其中納秒激光提前0 ns 指皮秒激光注入時刻在納秒激光下降沿中點時刻,即圖9 中的a-1 對應的條件,而單ps 激光條件則對應圖9 中的b-1 曲線.可以看出,對于能量高于0.5 MeV 能段范圍的高能伽馬射線,納秒脈沖提前1 ns 時刻的效果最好,0 ns 時刻次之,而時間間隔在1.5 ns 時,高能伽馬輻射強度又明顯下降,甚至低于單脈沖條件.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隨著納秒激光與皮秒激光之間的時間間隔改變,納秒激光輻照C8H8薄膜產生的等離子體電子密度和密度標長都會不同,影響著相對論電子的產生,進而導致伽馬射線強度的不同.納秒與皮秒長短脈沖激光之間的時間間隔越大,即納秒激光越早,那么在皮秒激光到達時,等離子體膨脹的時間也越長,對應區域更大,電子密度更低.

圖13 不同時間間隔條件下對應的伽馬射線的能譜分布Fig.13.Spectrum distribution of gamma rays under different time interval.
當長短脈沖激光時間間隔為0 ns 時,納秒激光剛剛結束,等離子體的膨脹還很不充分,等離子體的密度分布陡峭,一部分皮秒激光能量會在臨界密度面處反射,導致對皮秒激光的能量吸收并不充分,影響相對論電子的產生;當時間間隔達到1 ns 時,等離子體狀態比較合適,皮秒激光會在等離子體形成自聚焦的等離子體通道,從而高效沉積能量,打破有質動力加速的能量極限,獲得能量更高的相對論電子;而當時間間隔更長,如1.5 ns 以上,等離子體已經充分膨脹,電子密度過于稀薄,大部分皮秒激光將會穿過了低密度等離子體,影響在低密度等離子體中的能量沉積,無法產生更多的相對論電子.但由于皮秒激光聚焦位置的不同,此時的條件與單皮秒激光是有區別的.在單皮秒激光驅動Au 單靶的情況下,皮秒激光的聚焦位置在Au 靶靶面,而在長短脈沖激光聯合驅動雙靶的情況下,皮秒激光的聚焦位置是在前面的C8H8薄膜靶上,兩者相差650 μm.這就使得穿越低密度等離子體后的皮秒激光輻照在后面的Au 靶上的功率密度大大較低,從而造成了產生的伽馬射線反而比單皮秒激光方案更低的結果.
7 結論
超強激光驅動下的伽馬射線源具有裝置小型化、短脈寬、高分辨率等特點,在材料瞬時動力學診斷,核光子學中誘導放射性材料嬗變以及制備醫用同位素材料方面有著重要的應用前景.而目前制約激光驅動伽馬射線源應用的主要瓶頸在于實驗中產生伽馬射線源強度遠低于傳統的伽馬源,尚不能滿足傳統應用的需求.針對這一需求,本文提出通過改變靶前等離子體狀態,進而調控超短激光驅動伽馬射線源的技術方案.
通過對傳統超短超強激光驅動伽馬射線源實驗的認識和分析,目前在激光驅動伽馬射線源研究中,伽馬射線源主要來自于相對論電子在固體靶中傳輸過程中產生的軔致輻射.提升激光驅動伽馬射線源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提升相對論電子的品質.數值模擬結果顯示,超短超強激光與大尺度低密度等離子體作用,與傳統的超短激光直接與固體靶作用方案相比,可望獲得能量更高、發散度更小的高品質相對論電子束.基于這一結果,本文設計了長短雙脈沖驅動雙層靶的方案.長脈沖激光驅動第1層靶產生大尺度的低密度等離子體,超短脈沖激光與低密度等離子體作用產生高品質的相對論電子束,其與第2 層靶作用產生伽馬射線源.實驗結果證明,這一方案是合理的.在適當的參數條件下,雙脈沖雙層靶的方案能夠有效的提高伽馬射線的強度和流強.
這些結果表明,盡管在當前的超短超強激光器件條件下,所獲得伽馬射線源尚不足以開展應用實驗,但此方案為提升超短激光驅動伽馬射線源轉換效率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條可行的技術途徑.隨著超短超強激光器件輸出能量的進一步增大,在此方案基礎上,通過對驅動條件、等離子體狀態等參數進行深入的優化,可望逐步獲得滿足相應應用需求的超強伽馬射線源.
感謝神光-Ⅱ升級裝置運行人員的大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