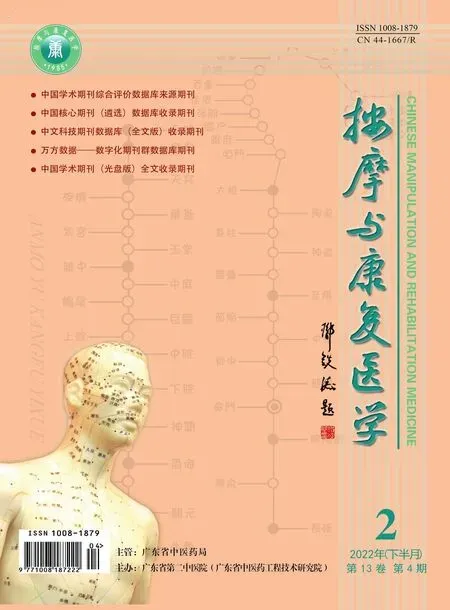針刺治療周圍性面神經麻痹后遺癥的研究進展
李德純,林萬慶,2
(1.福建中醫藥大學,福建福州 350108;2.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福建福州 350004)
面癱是以口眼?斜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疾病,中醫稱“口僻”、“口眼歪斜”、“吊線風”,關于面癱的研究,歷代醫家多有涉及,如“邪緩正急,相互牽引”、“風邪初入反緩,正氣反急,牽引口眼?僻”(《醫學入門》),“口眼喎斜,血液衰涸,不能榮潤筋脈”(《類證治裁》)等。主要因人體正氣不足,以致脈絡空虛,風寒或風熱之邪乘虛客于面部經絡,使面部經筋功能失調阻痹氣血,經脈失去濡養而發病[1]。
現代醫學稱此病為周圍性面神經麻痹或貝爾氏麻痹(Bell's palsy)。此病可發生在一年中的各個季節,任何年齡無論男女均有可能發生。此病發病前無明顯征兆,以突然一側面部癱瘓為主要癥狀,可見患側前額紋消失、閉眼不全、無法皺眉、鼻唇溝變淺、鼓腮漏氣、口角下垂歪向健側及流涎和塞食等情況。一般在發病起7日內為急性期,發病后1至2周為靜止期,2周至1個月為恢復期。若發病超過3個月,未經任何治療,或治療后未痊愈,則易產生面肌痙攣、面肌癱瘓、聯帶運動及鱷魚淚等面癱后遺癥[2-3]。
1 發病原因
1.1 中醫觀點
《諸病源候論》曰:“風邪入于足陽明、手太陽之筋,遇寒則筋急引頰,故使口?僻,言語不正,而目不能平視”。風邪侵襲面部,氣血阻滯,經脈筋肉失約,導致眼、口不能閉合。六淫以風邪為首,風為百病之長。風中經絡,常夾帶熱、痰、寒邪等為患,一旦久病致瘀,瘀血阻滯經脈,則易發本病。本病急性期主要表現為風寒客絡,經筋失用或風邪襲絡之象;恢復期則以瘀血阻絡,痰濁壅阻,筋脈失司或經脈阻滯,失其濡養;后遺癥期則為氣血不足,血不榮筋,筋痿不舉。中醫認為,面癱的發生主要以正虛為本,與風寒濕邪侵襲密切相關[3-4]。
1.2 西醫觀點
面癱相當于西醫學的特發性面神經麻痹(idiopathic facial palsy),亦稱面神經炎(facial neuritis),指因莖乳突孔內面神經的一種急性非特異性炎癥所致的周圍性面癱。面神經炎主要為貝爾氏麻痹和膝狀神經節綜合征(Ramsay Hunt綜合征)兩種類型。貝爾氏麻痹的病因尚未明確,目前認為是由一種嗜神經病毒引起。面神經中第七對腦神經主要是負責臉部表情、淚腺與唾液腺分泌及舌部的味覺,若其受傷或因感染而損傷,便會造成神經功能的障礙[5-6]。
2 面癱后遺癥
面癱后遺癥包括面肌痙攣、面肌癱瘓、聯帶運動及鱷魚淚等,是指患者患病超過3個月未痊愈,以面部表情肌群運動功能障礙為主要特征的一種疾病。面癱后遺癥多由面癱失治、誤治、久治不愈所導致。若恢復不完全,在面癱后遺癥后期可能會引起很多并發癥,因此,須盡早治療以提高痊愈率[7]。
3 以針刺為主治療面癱后遺癥研究進展
現代醫學認為周圍性面神經麻痹具有一定的自愈性,但部分類型的面神經麻痹患者不能自愈且預后較差。目前研究表明,僅約70%患者可自愈,臨床主要的治療措施包括:藥物治療、針刺治療等,急性期以激素、抗病毒藥物、營養神經藥物、維生素等為主[8-9]。面癱后遺癥的治療較為棘手,目前臨床最常見的療法仍是針刺法,如透刺法、健側刺法、遠近端配穴法等,針刺聯合其他療法的治療手段也被廣泛運用。現代研究表明,穴位與周圍神經有著密切的關系,通過針刺治療,直接或間接刺激傳入神經纖維及其感受器,調節交感與副交感神經所支配的肌肉,促進局部血液循環,改善局部供氧需求,加速神經水腫的吸收并提高神經的興奮性,改善神經抑制狀態,促進病損神經的修復[10]。針刺治療面癱后遺癥的方法眾多,但皆療效顯著,與其他療法相比具有一定的優勢。
3.1 針刺
池志勇[3]以針刺為主治療頑固性面癱50例,早期(急性期)以行疏風通絡為法,針健側為主。取穴迎香、地倉、陽白、四白和合谷。在中后恢復期,取地倉透頰車、攢竹透睛明和陽白透魚腰,以透刺為主。每日1次,10次為1療程,治療結果:有43例痊愈,6例好轉,總有效率98%。運用針刺健側的方法,來緩解初期因肌肉緊張而痙攣的患側,使患側肌肉得到舒緩而利于后續治療,經刺激量大的透刺針法來治療后期則可達到較高的治愈率。黎明等[11]治療頑固性面癱患者使用頭體針并用,取雙側合谷、太沖、足三里和三陰交以及健側下關采取瀉法,剩余穴位采用補法,并用局部透穴電針療法:太陽透下關、陽白透魚腰、地倉透頰車、牽正透地倉和承漿透地倉。治療結果:針灸組33例痊愈,51例顯效,15例有效,總有效率99%。采用遠近端配穴為治療面癱常用的療法,近端取面部穴用透刺法,可刺激神經功能和促進血液循環,改善面肌功能,而遠端取太沖、合谷,是由于經脈通于面部可疏通淤滯的氣血,促進代謝,幫助恢復面肌正常功能。倪麗偉等[12]對面癱后遺癥的面部癱瘓肌群進行經筋透刺和排刺,如陽白四透,陽白穴以四枚針分別向上星、頭維、絲竹空、攢竹方向透刺,選人中、承漿、頰車分別透向地倉,頰車與地倉互透,太陽透地倉,太陽向下穿顴弓透向地倉。施捻轉平補平瀉,治療頑固性面癱共43例,總有效率97%。透穴刺的特點是針刺少,而刺激穴位多,一方面能減輕針刺的痛苦,另一方面可以激發多個穴位的協同作用[13];一針兩穴點線連結,和多點連線的效果產生大的刺激量,對于難治的面癱后遺癥及面肌痙攣有著顯著療效。
3.2 針灸結合
潘愛鳳[14]用普通針刺結合麥粒灸治療周圍性面癱后遺癥。針刺主穴:陽白、地倉、迎香、下關、頰車、顴髎、攢竹、合谷(健側)。針刺結束后立即行臉部麥粒灸治療,隔日治療,3次為1個療程,總共4個療程,總有效率為100%。劉曉瑜等[15]采用百會溫灸結合透穴針刺,療程均為30天,觀察House Brackmann(H-B)面神經功能分級和臨床癥狀改善情況。結果:觀察組在臨床癥狀改善上均優于對照組,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灸法具有溫經通絡、活血利竅,促進氣血運行,對于改善面肌功能增加血液循環代謝,舒緩肌肉收縮或痙攣具有一定的功效,加上針刺療法可提高整體有效治療率。
3.3 針刺結合針刀
張利多等[16]運用針刺結合針刀的方式治療面肌痙攣。先以針灸針取地倉向頰車透刺,同時在風池、翳風、天容等穴進行針灸治療,每日一次。針刀取患側翳風穴向莖突方向行針,取翳風和天容穴向第二頸椎橫突方向行針,均刺至骨面通透剝離。隔日治療,10日1療程,共2療程,總有效率90%。鄭智等[17]以針刺聯合針刀為治療組,電針治療為對照組,對比兩種方法治療面癱的療效,治療結果顯示:前者痊愈率為90%,后者為65%,針刺結合針刀治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針刀療法通過直接松解切割粘連組織,能改善神經血管的壓迫和周圍血液循環,使口角麻木及周邊肌肉運動障礙很快得到改善,治療效果突出[18]。要注意的是,面部神經血管分布復雜,針刀操作具有風險性,需要充分的解剖學經驗,若松解不當容易造成損傷。
3.4 針刺結合拔罐
張敏燕和丁德光[19]運用透刺結合拔罐療法治療頑固性面癱:面針包括頭維透絲竹空、陽白透魚腰、太陽透下關、迎香透顴髎、地倉透頰車,體針包括雙側足三里、太溪、合谷與太沖。取針后,根據患者發病部位的輕重選擇相應的穴位進行拔罐治療,總有效率為96%。曾蕾[20]等采用針刺結合刺絡拔罐治療難治性面癱,對照組采用常規針刺治療,觀察組采用針刺聯合刺絡拔罐治療,通過面神經麻痹功能量表評價兩組患者靜態觀(額紋、眼眉)及動態觀(抬額、閉眼)。結果顯示:治療后對照組總有效率67%,明顯低于觀察組91%。拔罐療法有疏通經絡、祛除病邪等作用,能夠促進機體的血液循環,提高機體神經的興奮性,改善機體局部的營養與代謝,從而加速面神經管水腫的吸收,恢復面部的神經與肌肉的功能狀態[21]。在操作方面,面部拔罐容易留下罐印,不可過久過重,對患者外觀造成影響。
綜上,針對面癱后遺癥的治療,針刺仍是目前療效較好,費用較低、安全性高、不良反應小,受大眾肯定的治療方法。從古代醫家提出的理論與治法,到現代不斷更新的技術與方法,都能讓面癱患者得到滿意的療效。但在目前的臨床研究上仍然有待討論的問題,如面癱在各時期治療該采取的何種手段,各醫家仍有不同見解。有些臨床醫師認為急性期不宜用強刺激手法,淺刺治療即可。鄭魁山[22]認為“病在表,淺而疾之”是治療此病的原則,面癱會有后遺癥多是在早期時深刺重刺患側導致,在發病3天內應禁針患側。劉錦[23]認為急性期如果手法不當,過早使用電針等強刺激,可使局部神經肌肉的興奮性增高而出現面肌痙攣,使面神經髓鞘纖維再生障礙,妨礙面神經功能的恢復。而李振[24]則認為,周圍性面癱的最佳治療時間就是急性期,此時應給予合適的干預治療。鄭暉等[25]對針灸治療周圍性面癱的刺灸方法進行了循證評價,結果表明,針灸早期介入有助于縮短療程,提高療效,推薦使用電針或毫針刺結合灸法進行治療。臨床發現,針刺結合其它療法如針刀、艾灸、埋線、藥罐、穴位敷貼、推拿等,整體療效更好。因此,開創新的治療方法也是增進臨床療效重要的一環。
患者的治療態度也影響著療效。患者如在治療過程中自覺療效進展緩慢,認為無法治愈,中途放棄治療;或是恢復情況尚可,停止治療,這都是危險的。面癱后遺癥在后期若未痊愈,會引起諸多并發癥。也有部分患者求治心切,采用非正規的民間療法治療,導致病情加重,或耽誤最佳醫治時間。
另有研究發現,面癱常對患者心理層面產生消極影響。罹患此病,患者常有自卑或自閉心態,進而出現自我隔離、不愿與人交談或交往現象。部分患者常因心情低落,對待事物冷漠或毫無興趣,甚至感到人生沒有希望。長久的負面心態也會影響患者身體,出現陰陽失調、精神萎靡、失眠、憂郁、代謝障礙、臟腑功能衰弱等。醫者不可忽視患者的心理問題,應當適時的提醒與引導患者保持愉快心情,并接受病情事實,聽從醫師指導,適時參加戶外運動,提升免疫力,注意健康飲食,補充B族維生素及鈣等營養素。唯有患者和醫師合作,才能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