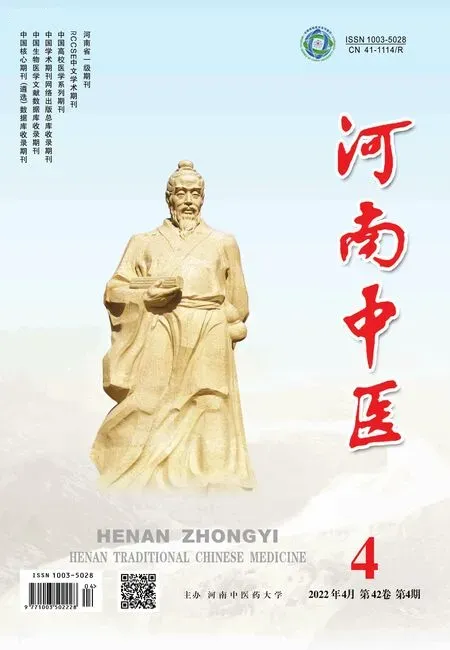張子和攻法淺析*
黃偉智,羅寶珍
福建中醫藥大學,福建 福州 350122
張子和(1156—1228年),名從正,字子和,號戴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學術思想和臨證經驗見于《儒門事親》。該書前三卷包括30篇醫論,其攻邪理論和汗、吐、下三法均在其中,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載139個病證,162例醫案。現有研究多從理論上分析張子和學術思想,較少關注其用攻法治療疾病。筆者將理論與醫案相結合,淺析其攻法如下。
1 攻邪主張
宋金元時期,香藥大量輸入,醫生或患者濫用香燥、溫補之藥,導致疾病加重甚至死亡,如“痿”案中張子和欲用攻法,患者為他醫所惑,用溫補藥致死。張子和言:“誤人而不見其跡,渠亦自不省其過,雖終老而不悔。”[1]溫補法只有在“脈脫下虛,無邪無積”[2]時才可使用。
張子和認為:“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2]邪氣入侵人體,導致疾病發生,影響病程與病情。“輕則傳久而自盡,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2]而“人身不過表里,氣血不過虛實”[2],疾病的常態為表實里虛,或里實表虛,有一實必有一虛。“良工治病,先治其實,后治其虛。”[2]《儒門事親》“黃疸”案中一男子四肢不舉,面黃無力,似無實邪的虛證,張子和也用吐下之法,效果顯著。《黃帝內經》中使用刺灸法的原則是:欲用針灸調血氣,必先散其寒凝,去其血絡,否則針灸的遠達效應無從發揮[3]。正如張子和所言:“針之理,即所謂藥之理。”[2]。治病應先祛邪。《儒門事親》“膏淋”案中女子,諸醫用盡補法治其膏淋,卻依舊面色晦暗,效果不顯,張子和使用吐瀉法,次日便臉色紅潤,正氣恢復。
2 攻邪法
人與天地相統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天之六氣,地之六氣,人之六味應相互協調。張子和認為:“天邪發病,多在乎上,地邪發病,多在乎下,人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為發病之三也,處之者三,出之者亦三。”[2]汗、吐、下三法可盡治其病。
2.1 汗法張子和認為,凡是解表的方法均為汗法。《儒門事親·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言:“諸風寒之邪,結搏于皮膚之間,藏于經絡之內,或發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腫癢拘攣,可汗而出之。”[2]此為一般意義上的表證,可用汗法。醫案中除少數如“感風寒”“風水”“中暑”等表證使用汗法,其他大部分醫案均無明顯的表邪及表證,如“飧泄”“不寐”“鬼交不孕”等亦使用汗法。可見,張子和認為表者乃皮毛、肌膚、腠理、經隧、脈絡、六腑、苗竅之總稱,歸于廣義“玄府”。無論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凡病機屬于“玄府”閉塞所致者,皆可先辨而后“汗”之。汗法目的在于“開玄府而逐邪氣”[2]。
張子和主張發汗應先“辨陰陽,別表里,定虛實”[2],“發汗欲使周身,然不欲如水淋漓。”[2]“發汗中病則止,不必盡劑。要在劑當,不欲過也。”[2]臨證不局限于理論上的發汗量。“面腫風”案僅取“微汗”疏陽明經風邪;“飧泄”案則“汗出如洗”,使風、濕隨汗而出;“因寒腰強不能屈伸”案,用九曲玲瓏灶連汗七天,直至“腹中鳴”,散太陽寒凝。張子和在靈活運用汗法的同時不忘汗法禁忌:“表虛亡陽,發汗則死”[2],“諸亡血之證者,不可發汗”[2],“病有熱者勿蒸,蒸則損人目也”[2]等。
張子和指出:“世俗止知唯溫熱者為汗藥,豈知寒涼亦能汗也”[2],提出辛涼發汗之法,補充了《傷寒論》汗法的不足。他將發表藥物按溫、涼劃分,方便臨床用于寒、熱不同的表證。而在醫案中,張子和只用過通圣散、雙解散、益元散、胃風湯、麻黃劑,最常用通圣散。相較于藥物發汗,張子和用外治發汗更多,包括:灸、蒸、熏、渫、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實際可分為借外界熱力發汗法和針刺放血兩類。燠室發汗是借外界熱力發汗法的代表,是將為密閉居室、室內生火或床下置火盆,提高室內溫度幫助發汗的方法。張子和認為:“出血乃發汗之一端”[2],“血實者宜決之”[3],其將放血廣泛運用于頭面五官、皮膚科等疾病。“大抵治喉痹,用針出血,最為上策”[2],“目疾頭風出血最急”[2]。張子和放血多用針,針即鈹針,九針之一,“其長四寸,廣二分半,末如劍峰,以取大膿。”[4]鈹針放血特點為三多:次數多,部位多,出血多。“背疽”案中一女子背疽如盤,張子和以鈹針繞疽暈刺數百針,去血一斗,如此三次,微出膿而斂。這種針法為“刺腫”法,漢馬王堆帛書已有此記載:“用砭啟脈者必如式,癰腫有膿則稱其小大而為之砭。”[5]“刺腫”法是早期針灸治療癰腫的經驗形成的定式刺法,主要是用不同的針具和刺法直接刺腫塊局部。張子和許多針刺放血案、刺瘤排膿案思路類似。除上述發汗法,還存在以怒取汗法,在“不寐”案中,一婦人因思慮過度而不寐,張子和激其大怒汗出,是夜困眠。當“開玄府”尚不能達到預期的治療效果時,則常配吐法、下法,以期取得治療效果。
2.2 吐法張子和認為,凡是上行的方法均為吐法。《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其高者,因而越之”[4],奠定了吐法的運用原則,《儒門事親·汗吐下三法該盡治病詮》言:“風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2]指出上焦病變可用吐法。張子和的吐法突破傳統“凡在上者,皆宜吐之”[2]的治療框架,擴展了吐法的應用范圍,直接病因病位的治療在張子和現存醫案中只占極小比例,大多與上述病因病位無關,如治療“泄瀉”“石淋”“骨蒸”“白帶”“皮膚瘡瘍”等病證,通過涌吐,可以啟玄府、開下焦、調水道、宣瘀滯、通關格、交心腎、暢氣機。吐法目的在于“令其條達”[2]。
張子和認為,吐法使用“宜先小服,不涌,積漸加之”[2],涌吐次數根據病情或患者體質而定,“強者可一吐而安,弱者可作三次吐之。”[2]服藥后不吐可輔以“撩痰”法,“以釵股、雞翎探引,不出,以齏投之,投之不吐,再投之,且投且探,無不出者。”[2]如吐至昏眩,可“飲冰水立解”[2]。張子和對吐法的運用,“過則能止,少則能加[2]”。《儒門事親》“風水”案中,張子和先用酸苦之劑加全蝎一枚,后逐漸加至三錢(3 g)。“隔食中滿”案中,李官人妻病中滿食不入,張子和認為,此病為陽盛隔食,分兩次涌吐,先用通經散越其一半,后以瓜蒂散再越之。“撩痰”法可單獨使用,也可用于服藥之后。涌吐之后宜飲涼水。“熱厥頭痛”案張叟服涌吐藥后昏仆,張子和令服涼水后蘇醒。吐法是引起機體劇烈反應、耗傷正氣陰液的治療方法,心理狀況較差或持不同觀點的患者不宜使用。如“性行剛暴、好怒喜淫之人,不可吐;患者頗讀醫書,實非深解者,不可吐。”[2]病勢危急,老弱氣衰,自吐不止,亡陽失血者,皆不可吐。
《儒門事親·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言:“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順而下之尚猶不樂,況逆而上之,不說者多矣。”[2]張子和吐法可分為藥物催吐、類涌吐法、撩痰、旋轉取吐法。常用涌吐藥有:獨圣散、三圣散、瓜蒂散、茶調散,滄鹽、熱面羹亦可催吐。類涌吐法有引涎、漉涎、嚏氣等,醫案中使用不多。吐法還有發汗、開玄府的功能,“吐中有汗”[2],“風水”案中張子和使用酸苦之劑,患者出痰數升,汗隨涌出。“因其一涌,腠理開發,汗出周身。”[2]達到了開玄府,祛邪外出的效果。
2.3 下法張子和認為,只要是下行的方法均為下法。《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因其重而減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于內”[4]。《儒門事親·汗吐下三法該盡治病詮》言:“寒濕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2]指明一般下法的使用范圍為下焦病變。張子和運用下法,不限于上述條文,涉及病種廣泛,有“風水”“水腫”等水濕病;有“胃脘痛”“呃逆不食”等脾胃實(濕)熱病;有“風搐”“痿”“痹”等神經運動系統疾病;有泌尿系統疾病、皮膚瘡瘍外傷類疾病、婦科疾病、外感六淫類疾病、虛損病。除了汗、吐二法之外的一切攻邪方法,幾乎都包含在下法之內,下法目的在于“推陳致新”[2]。
張子和會針對不同的疾病運用不同下法。暴病、卒痛等來勢迅猛的疾病,常用峻下法,“蓋有毒之藥,能上涌下泄,可以奪病之大勢。”[2]案中李繼之忽病牙痛,服舟車丸,大下乃愈。疑難病癥,如濕邪、積聚等不易速去的疾病,張子和常反復攻下,“腰胯痛”案中常仲明身有濕病,一年瀉下十余次,病才慢慢好轉。虛中兼積則應選用緩下法,“如沉積多年羸劣者,不可便服陡攻之藥”[2],應緩緩攻下。如“泄瀉”案中一講僧,病泄瀉數年,張子和以無憂散泄其虛中之積。無憂散以黃芪、白術、陳皮、木香為主,僅配一味牽牛子泄下,是攻補兼施的緩下劑。使用下法后則應時時察病勢,驗指征,如瘀血暴阻卒痛者,以疼痛“痛隨利減”[2]為驗;以大便“換過大便黃色,以為效驗”[2]。掌握這些指征,攻下方能恰到好處。張子和在使用下法的整個過程特別注重胃氣的養護。“馬刀”案中馬國卿病馬刀癰,張子和在瀉下之前令其先吃湯餅,安撫胃氣。若是準備多次攻下,在兩次攻下的間隙,固護胃氣,以利再攻。如《儒門事親·卷五·婦人無子》可用無憂散瀉十余行,吃蔥醋白粥三五日,“胃氣既通,腸中得實”[2]后再行下一次攻瀉。“濕痹”案則在瀉下后令服白粥養胃。張子和反對濫用攻逐,他認為,純虛無邪者不宜下,如“洞泄寒中者不可下”[2];表證不可首先用下,如“傷寒脈浮者不可下”[2];老、幼、孕、弱皆應慎用下法。
下法是一種峻猛的治療手段。“下之攻病,人亦所惡聞也。”[2]張子和在“腰胯痛”案中用大承氣湯時也不敢向患者說明是瀉劑。即便如此,下法是其用得最多,最熟練的方法。《儒門事親·十形三療》中收錄下法醫案93例,單純用下法30例。醫案中瀉下次數最多可達300余行,“痿”案中宋子玉病痿,張子和用舟車丸,浚川散大下三百余行。瀉下量最多為六缶(1缶約160升)。“腹脹水氣”案中張承應病水氣,張子和以舟車丸為引,下六缶。醫案中下法只用藥物泄下,方劑數量多,方以丸、散為主,常用舟車丸、浚川散、神祐丸、通經散。選方原則采用“急則用湯,緩則用丸,或以湯送丸[2]”。因丸劑、散劑作用緩慢,張子和在臨床上通過增大劑量(常用量的三倍以上)來實現緩藥急用的效果。瀉下手段雖單一,勝在方劑數量多,可相互配合使用。“沉積疑胎”案中一婦人病癥瘕,張子和以舟車丸為主,配合調胃承氣湯、桃仁承氣湯、豬腎散、通經散,分四次攻下,對應氣分、血分、水分、血分不同層次的治療,以適應疾病需要。下法除了攻下瀉邪,還有補益作用,“陳莝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榮衛昌”[2]。上文提及的“膏淋”案正是典型案例。從現代醫學角度看,下法有增強腸道功能、改善微循環、提高呼吸功能,促進機體反應性的作用[6]。“不補之中,有真補者存焉”[2]。
綜上,張子和將攻邪三法歸納為汗法開玄府而逐邪氣,吐法令其條達,下法推陳致新,擴展其使用范圍。臨床運用時既遵守原則,又能根據病情靈活權衡,同時不忘“禁忌”,對藥物或非藥物治療手段均能嫻熟掌握,隨證運用。
3 綜合應用
疾病發生發展是一個動態完整的過程,治病也是如此。除上文所述的禁忌證,張子和在治病前還會考慮氣候、年齡、懷妊等因素。“癩”案中張子和認為,初春尚寒,不可用藥,將治療時間改為五六月。“中暑”案中因患者年事已高,不敢使用涌吐藥。“孕作病治”案中認為:“凡治病婦,當先問娠,不可倉卒矣。”[2]張子和治病前細致入微,治病時胸有成竹,“風水”案中曹典吏妻病風水,先撩其痰,火烤助發汗,以舟車丸、浚川散瀉下,后四五日用苦劑涌吐,用舟車丸、通經散瀉下,過六日又用舟車丸、浚川散瀉下。此醫案運用多種攻法,多種方劑配合,層層遞進,攻之有度。治病達到如此境界除熟悉各種治法方藥,還需對病情有準確判斷。上文“下法”中所述的察病勢,驗指征,患者癥狀明顯,可較輕易觀察,有些醫案并非如此。“胃脘痛”案與“傷寒熱急”案,一則下后病不減,一則三下不通,均是服藥后病情無改變,后續治療卻一則加量攻下,一則改用吐法,治療方案完全不同。“嘔血”案李民范病嗽血,張子和攻下后嘔血一碗,再次瀉下后病愈,病情判斷全憑其經驗。張子和除用攻法,必要時兼用眾法,“予亦未嘗以此三法,遂棄眾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眾所當才一二也。”[2]“泄瀉”案中張子和使用下法后以白術調中湯、五苓散、益元散調理數日,具體使用順序與劑量并無記載,可見眾法在治病過程中占比不多,但其又不可或缺。疾病治愈后,張子和會提醒患者養護,告知病后宜忌。“沙石淋”案中張子和恐暑天小兒有失所養,留張氏小兒五日而歸。病后宜忌在《儒門事親·卷九》中有詳細記載。
綜上,張子和治療前對禁忌證、年齡、氣候等因素進行周密考量;治療時對病情發展判斷準確,治療方法的選擇與使用經驗豐富,除攻法外能依據病情兼用眾法;治療后提醒患者注意事項。
4 結語
張子和雖為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大師,但后人對其褒貶不一。俞東扶言:“較之子和不辨寒熱虛實,總與吐下者,誰圣誰狂?”[7]王孟英說:“亙古以來,善治病者,莫如戴人,不僅以汗、吐、下三法見長也。”[8]張子和抨擊了金代部分醫家盲目投補給患者帶來的嚴重危害,其思想主張不僅對朱丹溪、呂復、吳又可等國內醫家有所啟發,對日本漢方醫學的后世派和古方派亦產生一定影響[9]。攻邪三法近年來已廣泛運用于各科疾病,并已得到現代科學的驗證[10]。雖張子和之后,沒有《儒門事親》這種以攻法為主的醫學著作,但后人以“張子和及其學術思想”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數能與張仲景、孫思邈、李時珍、王清任等相提并論[11],遠超其他醫家。隨著對張子和學術理論的深入研究,必將繼續對現代的中醫藥、中西結合的理論與臨床產生積極作用。